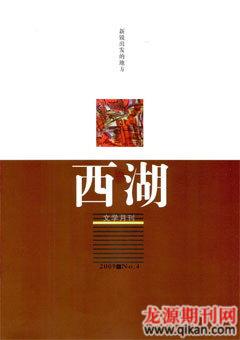阅读着父亲的额纹写字(创作谈)
李 云
父亲种着五亩田地,辛辛苦苦地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父亲因此还拿过政府颁发的“成就开荒人”的嘉奖和殊荣。九岁那年,我第一次站在地头,面对着父亲手中不停起落、被泥土洗礼得干净而明亮的锄头,问父亲道:“爹爹,你费力挖它干啥呀,我们三年前的陈谷都还有呢!”因为父亲的勤劳耕耘,我们家的粮仓总是满满的。父亲听了我的话,温暖慈祥地笑了笑,说:“孩子啊,我们来到世上其实就是一个开荒者,开荒的目的是为了播种,播种的不仅仅是种子哟,还是一份快乐呢!”开荒成了父亲最大的快乐。对我而言,父亲的话更像诗,聆听起来特别舒展,也很迷茫:“我将来会是怎样的一个‘开荒者呢?”……多年后,我回忆起那段刻骨铭心的成长经历,忽然发觉,印象中握在父亲手中的锄头其实就是一支笔么,怎么看怎么像。
父亲是一位农民,也是一位诗人。用大地写字的诗人。他在山东当兵时,给母亲写了很多的信。写信谈情说爱,在那个年代,在封闭的小镇上,它是多么文化,多么富有诗意啊。母亲一度成了当地很多姑娘羡慕的对象。人们羡慕的自然是信、父亲在信里一笔一画写出的文字诗歌。虽然父亲在信里没有说一句爱,就连最含蓄的中国式的“喜欢”的表达也找不到。可是,信依旧是神圣的,让人无限欢喜,只感叹文字真是优美。我在充满好奇的年龄里曾偷偷爬到阁楼,就着屋面碗口大的天窗亮光看完了信。一大箱子的信夹在毛主席语录里,放在楼上角落里,散发着陈年的墨香,一时将我迷惑住了。在很少的、几乎是阅读匮乏的环境里,我读着父亲写给母亲的诗歌,每读完一段,我就会合上信纸,望着天窗想父亲在地头开荒的样子。父亲的诗篇广袤而浩瀚,如新翻的土地散发着新鲜的泥土芳香,字迹也如地夯齐整而深刻!
可我真正握笔写字,却是得益于五音不全。我的母亲有一副好嗓子,而我没有。当屋后表姐的歌声从撒满了阳光的斑竹园里过滤而来,当母亲用她清丽的歌喉在为我们做早饭时叫我们起床时,我都很不安。我一把将被子盖在头顶,默默地跟着哼。我渴望歌声点亮一点什么,我也希望我的歌声能传出小窗……后来我参加了学校的合唱团,庆祝我人生中的第一个六一儿童节。可是,我知道我是在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感觉很难受,我至今还记得那份痛不欲生的感觉。声音不是我的,嘴巴不是我的,我整个人早已飘走了,我站在人群里不知道该如何办——我丢失了,并且还不知道丢失在哪儿了——嘴巴虽然依旧在人群里一张一合,可它不是我的!
我终于放弃了对歌声的向往。读中学时,我到镇上信用社卖日常用品专柜的角落里,买了我生平看的第一本亦舒的小说。那个过程很是值得纪念,我开始幻想着自己要是也能写小说该有多好啊。整个过程中,只觉脑子里有很多的精灵在舞蹈,在飞翔,盘旋在眼里、脑际,一心渴望寻找纸张安身。可我写什么呢,我意识模糊地感觉到小说是能将一部分人的生活展露出来,搬到艺术的台面上去看,去说话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如何来表达。很久后,我写了朦胧的爱情,也许那都是我自己冠名的爱情,它最多是比友情亲密一点的感觉,然后穿插进光怪陆离的身世之谜,再将那些爱情渲染得“死去活来”,挣扎,纠缠,疼痛,哭哭啼啼,爱恨交织。好比一首歌里唱的:爱了,恨了,痛了……
我对写字的热爱从此再也无法抑制。记得第一次写的样子是非常可笑的。我怕同学和父母知道我在写小说(我一直都很怕写小说的秘密穿帮),我节省下缴伙食费的钱买了许多白纸回家,裁剪到语文课本大小的样子,开始锁在房间里闭门造车。在《山魂》里,我写了一个下乡驻队的年轻干部与一个美丽山姑的爱情故事,其中还那么高调地积极地健康向上地穿插了许多他们如何齐心协力建造和改造一座大山的美好情怀,以及科学种植等等。我写得忘乎所以,不知天高地厚。它后来受到了同学之间私下的热传……
现在,我要说的是,我喜欢黄土地,怀念大山憨实的姿态。如同我喜欢土气的、像一个年长的、身为农民、一直如蚯蚓一样游走在泥土芬芳中,且寄居在父亲的额纹里老农妇的千年一叹!我的很多文字都是送给父亲的——不管我走了多远,坐在如何宽敞的办公室里,我的另一只脚依旧是踩在黄土地上那些由父亲犁铧翻开的泥土沟壑里的;我的眼睛,久久地深情地抬着,阅读着父亲越来越深刻的额纹,寻思着于生活于文字的深刻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