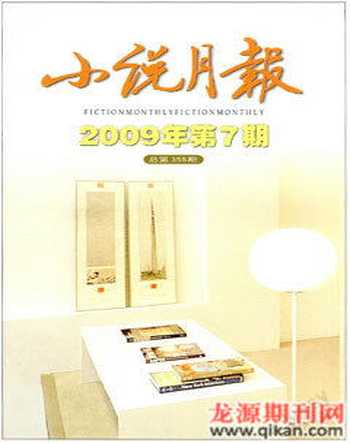船坞上的铁
徐 岩
当人们意识到春天来了的时候,野花正开满北江的南岸。远处看不到冰雪的痕迹了,更看不到群居的江鸥的走向,一些事物随着季节的变迁,也迅速地脱离了一切。
老黄站在船坞上等送菜的师傅来,他每天早上都是这个样子,腰上系着灰色的围裙,手上戴着白线手套。夜里加班的疲惫照常写在脸上。老黄的脸上有太多的褶皱,也就是皱纹,一条一道地布满他的脸颊,像他一生匆匆走过时留下来的记号,很是完美,那种沧海横流般的完美。
船是一艘大船,两层高的举架,白色的船身,庞大的身体侧卧在江岸的青草上。在老黄看来,这船曾经辉煌过,在滔滔的江水中劈波破浪,就像他老黄年轻那段时光,在八岔的青石滩地当鱼把头,不也是驰骋甲板、吆五喝六吗?
岁月催人老,如水迅急流去一般。老黄转眼之间竟成了守船的人。去年年根上,堂弟黄怀志问他愿不愿意帮他看船时,他想都没好好想一下就答应了。他知道堂弟黄怀志的船是一条花十几万元钱从外地买回来的废船,已经不能下水航行,但他还是答应下来。毕竟是生活在船上,咋也比生活在泥屋里要强,感受是不同的。
老黄站在船坞上,等送菜的师傅刘菜园子给他送两天的新鲜蔬菜。无外乎有茄子、辣椒和土蒜、大葱、鸡蛋之类的家常菜,多半是大棚里扣出来的。打老黄扛行李卷给堂弟黄怀志看船时起,黄怀志便跟手下人交代了,工钱是讲妥当的,在吃喝上别亏了我堂兄,鱼把头出身,当年百里江堤上也是个人物。
黄怀志的手下人就找了乐业村的大棚户刘菜园子,嘱咐他每天往船坞上送菜,再给船上送了两桶烧酒,附加一些肉块子,算是给老黄弄好了生活。
船是黄怀志买回来夏天里派用场的,重新修缮之后,拖到江边上开饭馆。经营江水炖江鱼,生意自然紅火。可冬天冰雪封江之后,饭馆的生意也跟着停下来,船就由老黄来看。在后舱的一间屋里生个小火炉子,搭个地火龙,床板就是热乎的了。沿江岸并排泊着大小十几条船呢,都抛了锚歇冬。
老黄的生活算是充实的,他一边替堂弟看船,一边自己动手编渔网。多少年过去了,他还是放不下手中的这份活计,并不是他想挣那一份钱,而是江岸上十里八乡的很多个网滩鱼亮子打鱼的兄弟们都认他编的网,付钱买了网后就四个字:结实好用。其实,这话说起来一点儿也不假,老黄在江边上打了十七年鱼,光鱼把头就当了整整十年,修船补网那是他的拿手好戏。
老黄编渔网是有技巧的,他选的鱼线绳跟别人的不同,细而不滑,一色的用麻油浸过,结起来不脱扣也禁得起江水的腐蚀。从鱼亮子退出来之后,他原本是不想再编网了,可各网滩那些弟兄们不饶他,往往是隔三差五就借着给老把头送鱼吃的名义,买好网线给他送过来,说今年水大,网就费,该添新网了。抹不过面子,只好把活计揽下来,反正也是闲着,编了网交付的时候,人家还给些钱,就应下吧。
老黄打了那么多年的鱼,原本是有些积蓄的,可偏偏贪上个败家的儿子,讨债鬼般从他身上挖走了那些血汗钱。老黄的儿子在县城里开了家小型游戏厅,因经营不好没到半年就赔了本。别人又串通他开饭馆,说就开那种鱼村,凭你老爹当过鱼把头的关系,去鱼亮子收购鱼不成问题,城里吃馆子的那些人吃过一段时间便啥都会吃腻的,杀生鱼却是热门,一准儿挣钱。老黄的儿子信了,又四处张罗钱开饭馆。
普天下的老子没有一个不心疼自己孩子的,就算他千般不孝顺,万般不争气,那也是自己的骨肉,喊过骂过之后还得管。
老黄就把自己守船编渔网赚得的那些辛苦钱悉数给了儿子黄兆东,并嘱咐他开饭馆就开饭馆,但一定得吃苦,静下心来做事情,不得苦中苦,哪有甜中甜呢。
老黄住的船很大,两层高的船体,大大小小有十几个房间,从船头的驾驶舱往后数过去,依次是休息室和客厅及厨房,四五间的休息室被改成了餐厅,连客厅也摆上了几张饭桌,俨然成了一条真正的餐饮船。
老黄住在一层船尾部的一间小房子里,二层的三间房也成了餐饮用的单间,里面摆了酒柜、饭桌和餐具。老黄住的房子虽小却很舒服,他不知道原来是做什么用的,猜想是轮机手休息时住的房间。房子有地火龙,生了火就暖暖的。屋内有一扇窗,圆孔,贴在船舷上,看似小一些,可将脸贴在上面望出去,天地就大了,大江满月,波浪滔天。
老黄编渔网编累的时候,会躺在那张单人铁床上,吸叶子烟。抽烟喝酒,没有什么能再比这两样东西更令他感到舒坦。
其实也不能这么把话说绝,老黄跟叶小芹做那件事时也是舒坦的,这个比他小十岁的女人跟了他六个年头,开始让他牵挂了。有时候老黄就一个人躺在床上想,刚跟叶小芹好上时也没怎么牵肠挂肚呀,怎么老了老了倒放不下了呢。
叶小芹在镇上一家洗衣铺里做帮工,整天缝缝补补赚辛苦钱,两人就有一阵子不在一起了。老黄来江边守船之后,两人才又接上了捻子,因为叶小芹打工的饭馆离江岸只有二里多地,撒开脚片子走上几十分钟便到了。
六年前老黄骑摩托车去镇上卖鱼时跟女人叶小芹邂逅,当时叶小芹正在镇上的一家饭馆里洗菜做后厨。老黄往后灶送鱼篓子时撞见了撅臀择菜的这个女人后,心就活泛了,老黄后来回忆说,他想到了一见钟情那个词,从电视上不是经常听到吗,原来现实生活中真的就有,真就让他给碰上了。老黄在江边上打鱼是经过风浪的,啥人他都接触过,跟陌生女人搭讪不成问题。他借着帮女人往大木盆里捡鱼的时候,搞清了女人叫叶小芹,竟跟他住相邻的村子。几次送鱼之后,两人坐到了镇子东头另外一家饭馆里。那天晚上下大雨,饭馆里客人稀少,老黄请女人吃了酒,也熟识了。后来两人睡到一张床上时,是女人所在的那家饭馆黄摊子了,老黄便把失了业的女人带到鱼亮子里给大家伙儿做饭,两人也就水到渠成了。
老黄将跟女人的战场从镇里的小旅馆转移到了鱼亮子,最终又持续到了他现在看守的船上。这么多年来他没有亏待过这个与他肌肤相亲的女人,女人吃的穿的,都是他一网又一网凭力气捕鱼换得的。叶小芹的身体很让老黄迷恋,他在床上抱住她的时候,就像在使船时网住了一条大鲤鱼,那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兴奋和喜悦,令他总是有使不完的劲儿,割除不了的亢奋。老黄的婆娘死得早,女人叶小芹又跟丈夫离了婚,两人组成一个家庭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但那只是老黄一个人的想法,女人叶小芹却不同意,她要把孩子将就出去。直到一年前,老黄使钱托人把叶小芹的女儿送到城里谋了份工作,她才答应考虑跟他搬一起过日子。
下过又一场冬雪之后,江堤上更是一片肃穆,雪把江面覆盖住,并跟江岸连在一起,雪浪起伏着,如披了棉絮一样。
老黄注意到了旁边的一条船上是蒙着绿帆布的,里面像堆积着什么货物,帆布被厚厚的积雪掩盖住。他知道这条船是外埠一家货商的,船开到港区时机器出现了故障而临时抛了锚。
堂弟黄怀志把他领来看船那天,就跟他特意交代过,也顺带着把一块儿停靠着的十几条船都看了,特别是旁边那条装着货物的船,人家是付了费用的。
老黄坐在船屋里编渔网时,透过那个小圆窗子便能看到周遭的几条船,船身上均覆了积雪,偶尔有风吹过,才能看到几处裸露的船的钢筋骨架,以灰蓝的铁色迎取阳光的照耀。
一个人的生活跟两个人的生活一样,都是单调的。老黄这一段时间来,开始跟儿子赌气,他觉得这个孩子是不孝顺的,总是从他的身上刮油,有种不榨干他这把老骨头就不罢休的架势。
儿子黄兆东已经三次来船上找他要钱,说他的饭馆正在起步阶段,稳一稳就能赚钱了。儿子最后一次走的时候跟他说,半个月之内,再给我准备一万,饭馆里要添一些餐桌餐椅和不锈钢的餐具,都得从城里进呢。老黄说没钱还摆那些谱干啥,就进一些便宜的用呗,一样吃饭喝酒。儿子说,你老了,知道个啥,现在来饭馆吃饭的客人都是有档次的多,挑剔着呢。老黄跟儿子说他没有,砸碎骨头也弄不到那些款子。儿子说去找我堂叔借呗,另外你不是还有个相好的吗?她吃你喝你这么多年,咋还不出点儿血。儿子的话当时差点儿没把老黄气个倒仰。
儿子走后,老黄喝了一晌午的闷酒,他把堂弟让人给他送来的猪肉块子卸了挺大一块下来,全部切成大片加白菜粉条炖到了锅里。他坐在船舱里大碗地喝酒大口地吃肉,心想自己凭啥省吃俭用着,省下的钱要给这个不孝子糟践。
喝了酒后的老黄去找了叶小芹,他舍不下脸来去找堂弟黄怀志,就一个堂弟而已,没什么大的情分在里面,人家又给你了份领钱的工作,吃喝拉撒都管着,能再不知好歹地去一味得寸进尺吗?老黄仗着烧酒壮了的胆气跟叶小芹说借点儿钱,紧急地贴补一下他儿子的饭馆,这次要是真不管怕是要打烊关门了。老黄说过借钱的理由之后,又画蛇添足地加了一句说,毕竟是儿子嘛,没有不管之理。
叶小芹说给你取上一万,不知你嫌少不,我手头也没多少,还得留点儿过河钱。
老黄说不少了,不少了,还是自己的婆娘跟自己亲。
老黄随叶小芹回家取存折,这还是老黄第一次来叶小芹家。进屋之后老黄的心里被震了一下,两间砖泥混合结构的房子里,没有什么像样的电器,地桌上唯一的一台电视机还是黑白的,并且是那么小的尺寸。老黄顿觉沮丧,这个跟自己睡了有几个年头的女人竟是过这样的苦日子。
在叶小芹弯着腰身开柜上的锁取存折时,老黄掉了几颗眼泪下来,是老眼昏花的浊泪。他被酒精熏红的脸涨起一道道青筋来,奔过去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女人。
老黄一直把叶小芹抱到了铺了地板革的炕上,两人紧紧搂到一起的时候老黄说,我开春就娶你,我要让你过安稳的日子。
老黄在第二天把一万块钱交给儿子时说,这是你爹舍着老脸讨借来的,你要是不珍惜这些钱,家败的时候看我不打折你龟孙子的腿。
一天吃晚饭的時候,老黄迎来了乔德军。乔德军是老黄原先在鱼亮子尤家张网当鱼把头时手下的渔民,浪里白条一个。这话说白了就是此人无儿无女无老婆,但天生的水性好。乔德军拎来两瓶贴商标的酒,还买了三斤猪头肉,两人把酒肉铺开来,再加上老黄刚弄得的一个炖菜,就喝起来。
乔德军也快四十的人了,身边还没个女人呢,穿了件破皮夹克,一副落魄样。乔德军跟老黄说,他是特意进城看老把头的,想当年要不是老黄收留他在鱼亮子做舵手,说不定他早就饿死了。乔德军说的话在理,没去鱼亮子捕鱼时,他在镇郊一家砖瓦厂里烧砖,干的是纯体力活,整天累得要死要活不说,包工头还克扣他们的工钱。后来乔德军去镇上酒馆里喝酒时便碰上了给酒馆送鱼的老黄,两人同村,拉上话后再几杯酒下肚,老黄收留了他做舵手。在江边上撒网捕鱼一干就是十几年,本也能攒上些钱娶房媳妇的,可乔德军生性好酒,又染上了赌纸牌的毛病,钱便如黑龙江中的水,到手后便是随波逐流。
老黄从鱼把头的任上卸下来之后,乔德军曾继续留在尤家张网,继续做他的舵手,每天划船捕鱼,喝酒抽烟,近乎于神仙过的日子。可好景不长,在一次随二柜去镇上卖鱼时逛了家洗浴中心,竟依赖上了那里的坐台小姐。在尝到女人的甜头之后,钱也就如流水般去了,手头的积蓄没多久便空空如也。乔德军也随之被冠以不务正业之名被撵出了鱼亮子。
这也是此次乔德军来找老黄的主要原因。乔德军想通过老黄找现任的鱼把头富贵说说情,等初春江开了的时候,能让他再回去做舵手。实在是使惯了船桨,拿锄头铲地却吃不了那份辛苦了。
老黄喝口酒沉思一下说,替你说情倒可以,但你必须得争气,从今往后再不能喝大酒耍纸牌,如果再陷进去那就彻底毁了。
乔德军听了老黄的话很高兴,端起杯自喝了一个底朝天,尔后拍着胸脯跟老黄打保证说,他一定做好活计,不给老爷子丢脸。
两个人喝得昏天黑地,一边唠当年打鱼时的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一边抽旱烟叶,乔德军那个晚上就被老黄留下,睡在了大船上。
临近腊月时,雪就下个没完没了,靠近大江的小镇子因为没了遮蔽而更加狂风肆虐。白色的原野银色的大江,经风雪的洗礼后,充分显示出了无以名状的肃穆和凝重。
泊在风雪中的那十几条船,大大小小都跟裹了棉絮样,错落有致又富庶至极。
老黄早早就等在了船甲板上,边抽着旱烟边朝通向镇子的那条小路上望。他是在等刘菜园子给他送完菜后,好去镇上办点儿事。其实,办点儿事是假,看叶小芹是真。自打上次从叶小芹那儿拿了钱之后,他心里边还真放不下这个女人了,温存善良,懂得体贴人,懂得人情事故,以前花在她身上的钱也值了。
老黄最近有了点儿钱,但不是什么大钱,是他原来手下那个捕鱼伙计乔德军给他送的礼。那天乔德军来大船上找他,求他跟现任鱼把头富贵说说情,留他继续在鱼亮子做舵手,谋个生计,两人喝了酒之后,乔德军没到一礼拜便又来了一次,给他提了两瓶贴商标的酒,还扔给他一个牛皮纸信封,并丢下一句话,事说妥了还会有钱或者物孝敬他。乔德军走后老黄把那个信封打开,里面竟是一千块钱。他心想这小子不是说自己快混到讨饭吃的地步了吗,咋又有钱来孝敬他呢?后来一琢磨,兴许是为了办事从哪里讨借来的也说不定,他想这钱就先收着,是能派上用场的。哪天抽空回村里跑一趟,跟富贵交代一下乔德军的事,能办成的。因为富贵是他老黄的徒弟,曾经跟他在一条木板船上跟头把式地混了几个年头呢。再说了也不是啥大事情,不就是个差事吗,用与不用,鱼把头富贵一句话的事儿,哪能收师傅的钱。
临去镇上前老黄把那一千块钱揣在了怀里,他是想先还给叶小芹,虽说只有一千块钱,离那一万块钱还差九成呢,但还一点儿是一点儿。这样做也是为了给自己增加一点儿信心,好使自己没有退路,逼着自己去找富贵给乔德军说事儿。
天刚刚还晴着,突然一阵风之后就阴了脸,竟飘起雪花来。老黄等了有一袋烟的工夫,才把刘菜园子等来,接了菜筐送进去之后,他便跟刘菜园子结伴去镇上。路上雪越下越大,把整个江岸都下白了。老黄跟刘菜园子开玩笑说,你们两口子种的菜不好吃。刘菜园子说怎么个不好吃法?老黄说菜里有股子尿臊味儿。
老黄的话把刘菜园子弄急了眼,他说凭良心可以发誓的,我们的每座大棚里种的菜都是施的优质化肥,哪会有尿臊味儿?老哥你纯粹是在埋汰你兄弟。
老黄说反正是有尿臊味儿,做出来的菜就酒吃完之后,有点儿反胃。
刘菜园子不吭声了,闷着头顶着风雪走,看架势刘菜园子有些不乐意了。
老黄便紧赶几步追上刘菜园子说,跟你开玩笑,还当真了不成?我说你送的菜里有尿臊味儿那是句反话,有尿臊味儿的菜有嚼头,那是绿色食品。你说说都有多久没吃过大粪浇种出来的菜了,那化肥不是什么好东西,说不定伤身体呢。
刘菜园子听老黄这么一说,才回过头来咧开嘴笑了,说老哥你真能逗弄人。
老黄也咧开嘴笑着说,种菜的小农民不禁闹,说你的菜里有尿臊味儿咋了,也真就说不定,没准你婆娘整天到菜垄沟里拉撒便溺呢。老黄说完就极开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笑声竟将雪末子吞掉。
这回刘菜园子也不生气了,他笑着回击老黄说,真是那样也不为过,不是有句话说吗,肥水不流外人田,俺婆娘做得对。难道你婆娘也在大船上拉撒便溺不成?
老黄顿了顿说,咱的婆娘还没娶到家呢,等有一天娶到了大船上,咱就可着劲儿地晃荡,这江水可是张不错的婚床啊。
雪小点儿时,两个人走到了镇上,半个钟头的路两人的脸都被冻得通红。刘菜园子跟老黄说晌午你在镇上办完事,老弟请你喝酒吧,镇西头刚开了家小牛馆,有筋头巴脑火锅,相当好吃了。
老黄说行,咱要是事办得利落,就去找你,你的大棚不是在镇北头的五金厂附近吗,好找。
老黄顶着风雪找到叶小芹干活的那家洗衣铺,把钱掏出来塞到她手里说,一千块,还差你九千,有了就早点儿还你。
叶小芹说我也不急着用,你手头紧的话就留着花吧。
老黄见洗衣铺里只有叶小芹一个人,便拉住她的手,摩挲了两下。这是老黄的习惯性动作,每到这时候,叶小芹就知道老黄是想做那件事了。叶小芹抽回手,抬眼看了看墙上的挂钟,方把手头几件烫好的衣服折好,说回家里吃饭吧。
两人回到叶小芹的那两间平房后,老黄便迫不及待地将叶小芹拉到了卧房。两人一番动作后,老黄再次跟她提起了结婚的事。叶小芹说这样不挺好的吗,干吗要走那种形式呢。然后叶小芹又问老黄他儿子的饭馆怎么样,赚不赚钱。老黄说估计够呛,啥好买卖也禁不住那龟孙子折腾。老黄拉着叶小芹的手说,他手上还有几万块钱,被他以二分的利借了出去,两人要是结婚的话,他就去把钱要回来,买几样家具和电器,最起码得把房子收拾一下。
叶小芹说找机会跟孩子说一下,就是结婚那也不是急的事。
两人穿好衣服后,叶小芹给老黄煮了两盘冻饺子,又给他温了一壶酒。饺子是她抽空事先包好了的,酒是上回老黄来家里吃饭时买了喝剩下的。老黄边吃边喝,还拿眼睛盯着坐在他身边也吃饺子的叶小芹说,还是有婆娘好啊,饭菜都香。
叶小芹说香你就多吃点儿,我再去给你炒盘下酒的菜来。
老黄将一壶酒喝完后叶小芹又给他倒了一壶来,老黄说不想喝了。叶小芹说外面天冷,再少喝点儿好驱寒,回江边得好几里路呢。
老黄便又给自己倒上酒,就着叶小芹刚给他炒好的一盘葱花鸡蛋喝酒吃饺子。
叶小芹还在两人往出走时给老黄装了一塑料袋冻饺子,说是老黄最爱吃的酸菜馅饺子,一次煮上二十个左右就能喝顿酒的。
老黄出镇子奔江边走时,天上的雪下得大了些。雪片子竟有鹅毛般大小,刮得他有些睁不开眼睛。老黄就在心里骂,×,这鬼天气,说翻脸还真就快着呢。
雪下了小半宿,老黄也睡了小半宿,中午在叶小芹家喝多了酒,也没觉得饿,加之跟叶小芹做了那件事,就疲倦得很。半夜时分,老黄渴醒了,爬起身端茶缸子喝水。
喝过水之后老黄便又有些尿急,他推开船舱门出去站在甲板上放尿水,发现雪已经停了。老黄激灵灵打了个冷战之后,拴裤带的时候,他瞧见了旁边船上好像有两个黑影,一闪就从船上跳到江岸去了。
老黄也没太理会,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看走了神儿呢,就回船舱里继续睡觉去了。直到日上三竿,老黄才从暖和和的被窝里爬起来。穿好衣服洗把脸,把火炉子上的水烧上之后,吸根烟卷到甲板上透空气。
数十里的江堤银装素裹,错落有致。远处的山体和近处的船坞,都成了白色,让老黄的眼睛由远至近地凝视,他在江边打鱼那会儿,还真没发现覆了积雪的江岸竟是这么干净,这么有气势。老黄深吸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的肺管都通透了。
老黄吐掉嘴里的烟头,朝远处挥了挥胳膊,正想回去做早饭的时候,他竟愣在了那里。
老黄发现旁边那条船的尾部有了让他惊讶的异常。那条船的尾部竟然有乒乓球案子那么大一块地方没有积雪,也就是说露出了绿色的苫布。
老黄心里一惊,这不正是昨晚半夜时分自己出来撒尿时感觉到有人影晃动的地方吗,当时还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呢。
老黄三步并作两步,扶栏杆下了船,再扒着积雪上了旁边那条船,来到露苫布的地方。
他发现捆绑苫布的油绳被剪断了,苫布也被掏开一个大窟窿,而大窟窿下边竟是些大麻包,麻包有明显被人搬动的痕迹。
老黄的心咯噔一下子,翻了个个。
下午的时候老黄喝了一壶酒,本想再喝一壶却忍住了,他想晚上得做事情呢,喝多了兴许误事情的。喝了酒后的老黄就躺倒在床板上睡大觉。老黄一直睡到阳婆落了山才爬起来。夕阳把覆了积雪的江岸涂成了金红色,老黄煮了碗面条,放些辣椒咸蒜狼吞虎咽吃进去后,就爬上船体的二层楼上守候。
上午江堤上没人的时候,老黄去查看了旁边的那条装货的大船,发现里面的麻包里全是废铁块儿。麻包是一层层码上去的,十袋子一摞,而苫布的开口处却少了整整七袋子。这说明这些铁块儿被人搬走了,而搬这些废铁块儿的人就是盗贼。
老黄在心里琢磨了一阵子,堂弟让他看船的时候曾给他交代过,捎带着把旁边那些船也给看了,特别是那条外埠抛锚在这里的铁船,上面存着货物,是交了费用的,而这些货物就是这成麻包的铁块儿。铁块儿咋就被人偷了呢?事情反过来看,自己这个更夫不就是失职吗?
叶小芹从县上的孩子处回来,收拾了一下头发和衣着就奔老黄住的江岸上来了,她要把跟孩子商量再成个家的结果尽快地告诉给老黄。孩子同意她再给自己找个父亲,也就是说她到老了能有個伴儿。叶小芹想孩子毕竟大了,走上了工作岗位,看问题的标准就不一样了,也能够做到善解人意了。
叶小芹在心里是愿意接纳老黄这个人的,虽说年岁上两人差了些,但感情的沟通上是不差什么的。这个比自己年岁大一些的男人质朴厚道,知道疼她呵护她就是最大的优点。何况在两人相处的六七个年头里,在生活上没少帮助她们娘儿俩。
叶小芹在去江岸的路上碰见了老黄,老黄说他正赶着回家取猎枪。叶小芹说忙三火四地取猎枪做啥?老黄说看船用呗。叶小芹便站在路上把孩子同意两人结合的事说了,喜得老黄一伸手把叶小芹抱了起来,原地转了一圈儿后,又在她脸上亲了两下。老黄说正好离我看管的船上近,先回我那儿待会儿,他们刚还咱些钱,交给你买些结婚用品吧。
两人拉着手回船上,老黄就翻找出一万多块钱来塞给叶小芹说,扯衣服买被面,咋喜庆你就咋整,钱不够先垫上,缓两天我去拢拢账,咋也得把喜事办得红火一些。
两人借着欢喜宽衣解带像模像样地做了一回,直到酣畅了舒坦了才起身穿衣服。
就是从那天下午起,老黄手里握上了他从家里取回来的猎枪,还有那仅剩的一颗子弹,守候着来盗废铁的人。
老黄的守候可不是一般的守候,他是要抓上他一家伙的,老黄提了猎枪坐在船舱的驾驶舵楼里朝外面望,左掌心里面是一颗黄澄澄的子弹,正好和他右手握着的那杆猎枪吻合。
枪跟了他十几年,总是悬在鱼亮子地窨窝棚的土墙上,当初备用是为了赶狼,而今天却要派用场抓盗船贼的。
到年底雪竟下得勤了起来,有时候天一亮就飘雪花,天擦黑了更是落大雪片子。雪把黑龙江以北的整片荒原都遮盖住,像棉田一般。
一连几天都没有动静,那两个盗铁的贼消失了。
老黄偶尔在白天去镇上帮叶小芹收拾新房,两人用旧报纸糊了墙也糊了棚,还贴了几张不知从哪儿寻来的杨柳青年画。在打眼的窗玻璃处还贴了两幅剪纸,红底白框,剪得生动活脱,不过不是双喜字而是鸳鸯戏水和柳河鸭趣。老黄知道这些剪纸出自叶小芹之手,女人的手是极其灵巧的,洗衣缝补,针线活剪纸样样做得来。
老黄每每看到自己那两间泥屋子里的四壁,甚至是犄角旮旯都被叶小芹的一双巧手布置得焕然一新时,他的心就会热一下。对于这,老黄是有感慨的,没有女人的家是不完整的家,没有女人的日子过得苦哇。
老黄跟叶小芹一块儿去了前屯的李庄,请住在那儿远近闻名的算卦先生给选了日子,剩余的事情那就好办多了,单等到时候置办酒席宴请邻里吃喜糖了。
老黄也顺便去了趟儿子开的酒馆,看能不能置办几桌酒席,可却吃了闭门羹。打听周围的人说是刚刚被工商税务给封了门。
老黄心想开得好好的咋就封了门呢?怕是又干不务正业的勾当了。老黄生着闷气回到船上,心情真是喜忧参半。喜的是要有个婆娘来照顾他了,忧的是儿子还是那么不争气,究竟要为他担忧到何时呢?
这天晚上老黄又喝了酒,原因很简单,他原来鱼亮子的捕鱼伙计乔德军再一次来看他,不光是提了两瓶好酒,还带了下酒菜和香烟。老黄觉得心里边是欠着人家乔德军情分的,收了人家的钱没替人办事,你说能过意得去吗?其实,老黄也想跟乔德军说,不是不替他去说情,只是最近手头上攒了一些事,没还来得及。
外面又下起了鹅毛大雪,两人喝酒的船舱里却很暖和,酒过三巡菜过盘底,老黄就说自己喝多了,嘴上叨咕着说这两天要办喜事,跑东跑西的累得够呛,真是不胜酒力了。他留乔德军住下,可乔德军不肯,说咋也得连夜返回去抱刚结识的相好的。
老黄说那你就回吧,反正咱得歇了,雪大夜温和,喝点儿酒好睡觉。
待乔德军走后,老黄将事先准备的一大茶缸子醋水喝掉,再去船尾舱的厕所里抠喉咙把酒挖出去,洗把脸清醒下头脑,方提了猎枪上船顶。
风不大雪却一直落着,月光把方圆百里都照得通明透彻。老黄便在清凛的月光里看见了邻近那条货船上蠕动着的两条黑影。
老黄心里恶恶地骂了一句龟孙子,便提枪下船,奔那两条黑影而去。
风雪中,那两个正肩扛手抬麻包的人被老黄的猎枪指了个正着。
雪光里呆住的人竟是刚刚跟老黄喝过酒的乔德军和另外一个陌生男人。
乔德军禁不住问老黄说,老把头你不是喝多了吗?
老黄说就那么一点儿猫尿想把老子整倒,笑话。我早就猜出你小子就是窃贼,这回人赃俱在,还有何话说?
乔德军被老黄手中的猎枪着实吓住了,他干笑了两声后说,兄弟一场,你就高抬一下贵手,咱就再倒腾这一回,卖了钱还分你一些花,何乐而不为呢?
老黄说你小子顺嘴喷的哪门子狗粪,咋就说分些给我花?
乔德军再次干笑两声说,上次给你那一千块钱就是卖铁所得啊,难道你没收吗?
老黄傻眼了,他没想到自己竟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别人设下的圈套,他真是后悔莫及。
乔德军见他的话起了作用,忙使眼色给另外那个人,两人抬起麻包继续往岸上走。没走两步,就又被从后面赶上来的老黄拿枪给指上了。老黄说那一千块钱我会还给你的,怪只能怪我不知情,但我也决不能容忍你们再犯法了。老黄说着拉动了枪栓,把子弹上了膛。
乔德军借着酒劲儿没理老黄的茬儿,接着奔岸上走。岸边上的风雪中停着一辆手推车,上面已经码了两包废铁块儿。
乔德军跟那个人在前面走,老黄端着猎枪随在后面。乔德军不时地回头劝老黄,岁数大了又喝了不少的酒,回船上歇着得了,还管啥子闲事。老黄也不吭气,继续随着走。等到了手推车边乔德军跟那个人把一麻包铁块儿装上去,反身回船上继续抬时,老黄拿枪对准了手推车的一个车轮搂了火。砰的一声那只轮胎就被打爆了。
乔德军跟那个人都愣住了,他们回过头看见那只被打爆的轮胎,两张脸都现出了哭相。乔德军说老把头你咋能这么绝情,现在弟兄们混口饭吃多不容易,你这是断了咱的财路啊。
老黄啥都不说,提着猎枪往船上走,他心里想,让他妈的你偷,没了车你就用肩扛吧,弄到镇上不累你个瘪犊子样。
老黄没走出幾步,他就觉得自己的后背被扎了一下,疼得他一下子就跌坐在了雪地上。
老黄回头时看到跟乔德军一起抬麻包的那个男人正站在他身后,手里握着把锋利的尖刀,有血凝固在刀刃上。
老黄的两眼开始冒金星了,他试图把那杆猎枪再一次抬起来,胳膊却使不上劲儿,浑身也变得绵软无力,只觉得漫天舞着的雪片子越来越大,他想好好地睡一觉。
老黄醒来的时候是第二天上午了,他躺在镇卫生院的病床上输着盐水瓶,旁边坐着的叶小芹在给他削苹果。那只苹果是暗红色的,没被削掉的部分依然光泽耀眼。
见老黄醒过来,叶小芹就招手把坐在门口一把长木椅上的两个穿制服的男人叫过来,跟老黄说是镇派出所的同志。
那两个人小声地跟老黄说了破案的经过,他们告诉老黄,盗窃犯一共抓住了三个人,两个人是现行,另一个人是主谋。让老黄感到震惊的是,那个主谋竟是他儿子黄兆东。
对事情加以了解之后,那两个公安走了,说还得赶去县上的看守所,继续提审那两个盗窃犯。临走时跟老黄说,你儿子虽然没有参与偷盗,但参与了策划,估计得拘留和罚款,想救他就赶紧准备罚金吧。
老黄躺在病床上大声骂道,这个孽障,这是老子哪辈子欠他的呀。
叶小芹把削好的苹果放到床头的茶桌上,一边端水给老黄喝一边劝他说,好歹是你儿子,你身上掉下来的肉,不能不管的。
老黄拉住叶小芹的手,想说啥却没说出来,眼泪却先掉了下来。
原刊责编安殿荣
【作者简介】徐岩,男,1966年生,吉林九台人,1988年毕业于武警哈尔滨指挥学校,1986年开始发表作品,出版有诗集《肩上的灯盏》,中短篇小说集《临界的雪》、《说点抗联的事》、《染指桃花》、《从北窗看雪》、《胡布图河》等。短篇小说《河套》、《白粮票》获本刊第十二、十三届百花奖。现在黑龙江公安边防总队政治部任职,黑龙江文学院合同制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