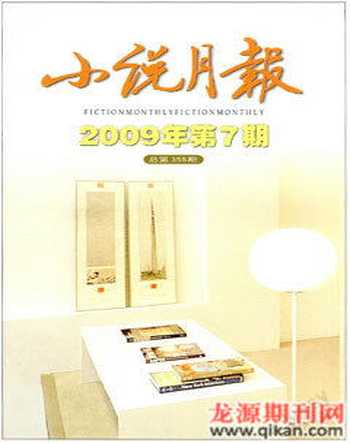家长会
很安静的秋天,看起来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校园里落满了红的黄的叶片,再过几天,再刮几场黄乎乎的大风,就是白雪茫茫的冬季了。教学楼前站立的多是那种钻天杨,直直的,一个劲儿地顶向高远的天。在这个小城,这树种如今已很少见到,也鲜有栽植的了。当初规划时,汤河没听设计师的劝告,一意孤行地让它们在校园里落了户。树种高大,叶片也巴掌似的大,一片又一片地落下来,把整个校园都排满了。每到这个季节,汤河要做的事似乎就是和校工们一起哗哗地扫树叶,今天扫过了,扫得一片都不剩,明天又是厚厚黄黄的一层。
这会儿,汤河又哗哗地扫开了,门房老赵也在一边哗哗地扫,两个人都很卖劲,叶片在扫帚上蝴蝶似的飞舞。楼群静静的,学生们在上课,有几个窗口传出朗朗的读书声。期中考试刚结束,汤河知道各个教室都在讲试卷,下午学生们就要放学,而他们的父母则会坐在各自子女的座位上,来开这学期的第一次家长会。对学校来说,这不能算个小事,学生的成绩怎样,下一步怎么办,各科老师将在会上跟家长们讲清楚。汤河相信教师们能把会开好,都是他从各地重金聘来或挖来的,应该说是一个赛一个,他相信他们能做好。也不是没有担忧,但担忧的不是他的属下,而是一部分学生家长。这个小城的有钱人太多了,都是些开煤矿铁矿或经营饭店商场的主儿,住豪华别墅,驾高级轿车,穿名牌服装,走到哪里说话都冲冲的,牛气得很。也许是认为汤河的学校办得好,他们中的一个把孩子送来了,别人也都赶庙会似的跟着把孩子送来或从公办学校转过来了,送来就以为万事大吉了,不闻不问,没个当家长的样子。
上学期的家长会,这些有钱的主儿,竟然只来了八九个,多数人就没想到该来学校打问一下子女的学习情况。来了的也不守规矩,让他把手机关了,根本就不搭你的茬,依然大模大样地把那东西摆在课桌上,就像他们的儿子摊开一本语文或者物理书,隔不了一会儿就抓起接听,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压根就没想到该回避一下。最过分的是余黑子,也不知接了个什么电话,竟然一拍桌子怒不可遏站起身破口大骂起来,全忘了这是在开家长会。因了这突如其来的发作,众人的目光就都被吸引了过去,可余黑子却浑然不觉,对着手机,情绪像火山爆发了一样,那话一句比一句粗野,硬邦邦的,牛蹄子都踩不烂,妈的,你这孙子给我闭嘴!说完这句,很响地把电话甩在桌子上,人也一屁股跌在了椅子上。他儿子的班主任陪着小心说,余老板,您气也生了,人也骂了,该发个言了吧?余黑子摇摇头,发啥言,你让我发啥言?啊?都让那孙子气饱了,不行,我还得训这孙子几句!说着又抓起了电话,班主任哭笑不得,您就不能歇一会儿吗?您坐下没几分钟就不停地接电话,这会还怎么开?要不让大家一起听您接电话吧?我们也不开会了,听您说单口相声吧。余黑子一瞪眼,你嘲笑我?你当我是谁?卖艺的,还是那些骚哄哄的三流演员?老师给噎得老半天泛不上话来,没一点儿办法了,不得不宣布散会。汤河听说后就很生气,这可是在学校,不是在你们矿场,怎么能这么不守规矩呢?
下次开会,给这些人另请一桌!汤河当时对分管教学的校长说。
这,这合适吗?
怎么不合适?我就是要治治他们!倒要看看他们怎么在我面前表演。我要亲自给这些有钱的主儿上一堂课,告诉他们怎样才能当个好家长。说话时,汤河把他的大班桌拍得啪啪响。
可是,可是他们会听话吗?
听也这样,不听也这样,我就不信这个邪!
在昨天的班主任会上,汤河也表了同样的态。班主任們看到他们的校长表情冷峻,声色严厉,手势坚定,像指挥一场关乎生死存亡的战役。汤河喜欢说话时伴着手势,在他那张大班桌前来回走动,腰杆挺得笔直,就像校园里那些钻天杨。这让老师们又想起他平时常说的那句话,都给我活得精神点儿,让人一看就知道你是博人学校的教师!或许是出于对汤河的尊敬,学校里的年轻教师跟他说话都相当客气,甚至有些毕恭毕敬。汤河觉得这就不容易了,如今的年轻人不比他们当年,说话做事都很牛气,根本就不怕你炒,你炒他,他也敢炒你。应该说,这些年轻人有才华,也很敬业,知道博人虽是个民营学校,却也是个让人干事的地方。但也有让他忧心的事,忧心的人,比如说那个叶娜。
叶娜最近还出去吗?汤河忽然记起了什么。
门房老赵愣了半天才明白校长在问他,支吾着说,您说的是那个小叶老师?
说话痛快点嘛,干吗吞吞吐吐的?
老赵摸摸后脑勺,昨,昨晚她回来时我都躺下了。
汤河脸一下子拉得老长,又是大半夜?我不是吩咐过了吗?过了十二点,一个都不准放进来?
这,校长,小叶老师一个劲儿地敲门,我怕吵了别人,就把她放进来了。
这个叶娜,简直太不像话了。
汤河说完,扔了扫帚,丢下目瞪口呆的老赵朝办公楼走去,一边走一边打电话,吩咐教务处通知叶娜到他办公室来。
约摸十分钟后,叶娜进来了。
汤河没抬头也嗅得是她,是的,是嗅,他的鼻子轻微地不由自主地抽了抽。这个动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呢?汤河曾经很认真地想过这个问题,是叶娜做了余黑子的家庭教师之后,还是他发现余黑子的车常常把叶娜接走时?不管怎么说,肯定是和余黑子有关了。在这个小城,人们可以不知道市长是谁,却很少有人不知道余黑子的,这人本名叫余大白,因为长得像炭块一样黑,又是开矿的,人们背后就都叫他余黑子了。他靠开煤窑发家,初中没念完就跟着他爹出去闯荡,先在井下刨煤,后来父子俩逮机会包了一座煤窑,折腾了几年竟然就站稳了脚跟。再后来他爹死了,他又从别人手里买了几个煤窑,这家业越发闹腾大了。像余黑子这样的人,发家时不太在意自己的形象,功成名就之后就事事注意修饰了,然而不管他怎么往美容院扔钱,那皮肤却不争气,依然黑不溜秋的,好像随意一刮,就能刮出一小平车煤粉来。后来他不再像娘儿们那样刻意去美白,觉得这样也蛮好,至少给他的矿打了个免费广告。也知道人们背后叫他余黑子,但似乎并不在意,有人当着他的面叫他余黑子,他也显得乐呵呵的。
再怎么想,汤河也记不起这个动作的准确形成时间,但他却从中悟出一个道理:人的有些动作是下意识的,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他明明知道这个动作不雅,和他的形象不符,却总也纠正不了,摆脱不了。更让他费解的是,他总能从叶娜的气息里分辨出哪是她身上特有的,哪是附加的,属于另一个人的。
记得有一次余黑子请他吃饭,他没答应,说下午还要开个会,抽不开身子。其实他是不想去,找个借口搪塞罢了,没想到余黑子坐在他办公室不走,说,你总得给我个面子吧?汤河的倔劲也上来了,我为什么要给你面子?在我办公室,哪个学生家长都得守规矩,不管他是多大的老板,就是在天宫里跟王母娘娘做生意也得守规矩,难道你余老板不是我们的学生家长?余黑子笑了笑,当然是,因为是学生家长,你才更得给我个面子。汤河一怔,想探知下文,就让他说个一二三。余黑子又一笑,你是校长这没错,我只想问你一句,校长不需要学生家长的支持?汤河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啥药,点点头,当然需要啊。余黑子说,那就给我个面子,一块儿出去吃顿饭,顺便谈谈我儿子的学习。汤河摇摇头,在这里谈不好吗,为什么非得坐到饭桌上去?余黑子说,现在谈事不都在饭桌上吗?喝上点儿酒,晕晕乎乎的,都放开了说话,学校和家长的距离就拉近了,打成了一片,事情就好办多了。汤河说,但是我们博人有规矩,不准接受家长的宴请,何况我确实有事。余黑子不高兴了,你真不想得到我的支持?汤河说,你能给我什么支持?余黑子说,你们学校有锅炉吧?到了冬季烧啥?总不能烧粉笔面吧?汤河也不示弱,余老板,你总不会包了我们学校一冬的锅炉用煤吧?这两年煤价一个劲儿地往高拔,这笔钱数目不小啊。他本以为这会吓住对方,没料到余黑子说,小事一桩嘛,吃过饭我就给你送煤。那一刻,汤河觉得余黑子咄咄逼人,他禁不住又嗅到了黑色的煤炭气息,看到了那种霸道的物质。他不客气地说,不用了,今冬的煤我们已经买下了,吃饭的事过几天再说。但到了中午,教育局长却打来电话,让他到本城最豪华的天瑞大酒店吃饭,汤河心里有些纳闷,但还是赶去赴宴,毕竟在小城办校是不能得罪这个人的。一进房间,就看到了笑眯眯的余黑子,他脸腾地红了,却也不好再走,硬着头皮坐下了。席间,余黑子一脸得意地说,汤校长,做人啊不能太清高,甭老搞得自己身上一股酸臭味。汤河回击道,余老板,做人也不能太霸道,煤金味道太冲了顶鼻子。
校长,您找我?叶娜好像并不知道他找她究竟什么事。
汤河觉得自己的鼻子又不自觉地抽了抽,本来他想做得大度点,让叶娜在他对面的沙发上坐下,但这个动作却使他心生恼火,不愿再给她这个权利了。
也没什么,一点儿小事。他说。
在汤河看来,叶娜身上的气息原本很清纯,不像这小城的姑娘,今天这个味,明天那个味,换来换去都是化妆品的味道。但现在,叶娜再不是刚进校门的那个清纯的姑娘了,她身上的气息变得复杂了,这一点汤河不仅感受得到,甚至能看到那气息的颜色。是一种什么颜色呢?就是余黑子身上那种黑色的煤金味儿,粗俗,野蛮,还带着一点儿腥。那次请客后,不知为什么,余黑子有事没事常给他打个电话,说是有困难你可以吱一声嘛,毕竟你是我儿子的校长,学校的事我还是乐意帮个忙的。汤河显得很冷淡,说有事当然会找你的。余黑子的儿子叫余小鱼,身上倒没那种纨绔子弟的习气,只是脾性有点黏糊,学习也不肯用功,成绩自然就上不去。有次余黑子打电话,想请他再出去坐坐,汤河一口回绝了,说饭就不要吃了,你还是重视一下余小鱼的学习,不要光顾着挖煤,孩子的学习也要管一管。余黑子根本不当回事,咋管?他不开那一窍,你就是把他一棒子打死在教室,也见不了效。我的意思是,你这里管得严,出不了大问题,就让他好好养着吧,出不了成绩,把身体养好也行,你说呢汤校长?将来啊,他就是啥也考不上,有我那个煤矿也够他吃一辈了吧。汤河本想告诉他富不过三代,你要想留住财富,就得好好培养后代,后代培养好了才能留住财富,但看到余黑子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就不愿多说了。
但后来,不知怎么回事,余黑子突然对余小鱼的学习上了心,一趟一趟往学校跑,说是小鱼语文太差,要给他请个好老师补补课,选来选去就选中了叶娜。一开始是一周补一次,后来,发展到一周补二次、三次,那辆豪华的足足值一百万的进口德国越野车常常堂而皇之地停在校门口。汤河一开始也没太在意,以为余黑子终于醒悟过来了,醒悟过来就好,但慢慢才发现事情并没这么简单,有一次他看叶娜回来时都快大半夜了,身上还沾染着酒气。他把叶娜叫到办公室,郑重地说,你不能再给余小鱼补课了。叶娜扑闪着一对好看的大眼睛问,为什么?汤河欲言又止,这个你就不要多问了,知道我这样做是为你好就行。叶娜说,那我要是还补下去呢?汤河不客气地说,要是这样,那你就不要在博人教书了。叶娜疑惑地看着他,最终还是答应不再补课了。
现在,叶娜站在他面前,汤河又从她眼睛里看到了那种霸道的物质。他不知道叶娜和余黑子的关系发展到了什么地步,但他觉得这样的事最终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能有什么好结果呢?叶娜跟着黑子,最多混个二奶的身份,黑子根本不会娶她的,就算娶了,又会有什么好结果?余黑子的老婆原是他们那个乡书记的千金,这些年他的事业能越做越大,也多亏了老丈人暗中帮衬,摆平了各种关系。余黑子再昏了头,也不会丢了西瓜去捡芝麻的。他只是不明白叶娜怎么会对一个四十岁的老男人感兴趣,当然,也有这种可能,叶娜根本就看不上余黑子,她去给余小鱼补课,也仅仅就是补课,给贫寒的家庭挣点儿钱,根本没有发生他担忧的事和补课以外的情节。
听说昨天你又回来得很晚?汤河盯着她说。
叶娜一怔,但很快便反应过来,是,出去办了点儿事。
哦?办事?该不会又是去余黑子家补课了吧?
没有,我没有!
叶娜使劲地摇了摇头,脸一下子涨得通红。
汤河不信,他认为叶娜这是在撒谎,在欺骗他。这个叶娜啊,真是陷得越来越深了。应该说,这是个不错的苗子,有一阵子,他还让她办过校报,中文系毕业的高才生,报办得还真不错。在市里的同類学校,博人的校报也是一张响当当的牌,新颖,扎实,丰富,看过的人一律叫好,当然这也是个宣传学校的窗口,阵地。校报办好了,做大了,叶娜跟着声名远扬,正像人们可以不知道市长但没人不晓得余黑子一样,在这个小城,人们可以不知道他汤河却不能不知道叶娜,谁都晓得博人有个漂亮的女教师,语文教得顶呱呱,几乎可以说是博人的形象代言人了。最初,汤河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他知道要想把博人办成名校,就得有一批名师撑着,名师就是品牌,他要让博人多出一些这样的名师,越多越好。但他没想到的是,这个他下大功夫培养起来的女教师却被开矿的老板拉下了水。
那你干什么去了?去喝酒,或者到舞场了?汤河鼻子又抽了抽。
汤校长怎么能这么说?谁告诉您我去喝酒了?叶娜眉毛轻挑,一张姣好的脸因为愤怒好像有些扭曲了。
那,那你到底干什么去了?怎么回来得那么晚?汤河也觉得自己说得有些不妥,但话已出口,收是收不回来了。让他不满的是叶娜的口气,他似乎又嗅到了那种黑色的气息。
这是我的个人隐私,汤校长,您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叶娜说完,狠狠地把头扭到了一边。
汤河没想到叶娜会这么说。
隐私,个人隐私,好像正在吃饭,不提防碗里扔进了一把沙子。汤河心里不由腾起一团火来,解聘她,马上就解聘她,让她卷铺盖走人。你不是很牛气吗,成大神神了吗,我这小庙容不下你了吧?那好,那就请你走人吧,从哪儿来,再回到哪儿去,博人不需要你这样不守规矩的教师。是的,马上就召开校委会,宣布这一决定,解聘她!汤河胸中波涛汹涌,面前的叶娜却好像毫无觉察,全没意识到自己面临着失业的威胁,依然倔倔地立在那里,像一块煤炭,挑衅似的站在那里。
我奉劝你,还是守点儿规矩为好,这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汤河老半天才泛上话来。
校长,我怎么不守规矩了,是我没给学生上好课,还是体罚了他们?就不允许我有一点儿教学之外的自由?
叶娜声音里拖了哭腔,肩膀像经了风的树叶,一抖一抖的。
汤河就怔在那里。
桌子上的电话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汤河看了一看,是余黑子打过来的。他看了叶娜一眼,迟疑了一下接起了电话,这家伙会有什么事呢?余黑子在电话那头呵呵一笑,汤校长啊,咋接个电话也这么费劲?汤河有点儿冷淡,余老板有事?余黑子说,我知道你忙,就直说了吧,刚给你们学校装了些煤,一百吨,也不算太多,我的一点儿心意罢了,一会儿车队就从矿上出发了。汤河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你给我送煤?余老板你搞错了吧?余黑子又一笑,错不了的,就是给你的博人送煤,一百吨。
不,这煤我不能要!汤河使劲地摇摇头,声音却很软弱。
为啥不要?是我的煤不能烧,还是啥原因?电话那头的声音拔高了。
这个,过冬的煤我早安排好了,余老板,多谢你了。汤河自己都觉得这理由何等软弱,眼下,只有他自己才知道博人太需要煤了,今年的煤价几乎比往年翻了一番,前几天,总务处把冬季采暖计划送过来时,他发现需要支出的那笔钱数目大得令人吃惊!这么一笔钱,博人怎么承受得了呢?这些年学校虽是扩展了,生源稳定了,资金也不像当年吃紧了,可是银行的贷款还有不少没还啊。说实话,他们这些民营学校,眼下真的很需要有人支持。这学期,博人学校又新增了初中部,摊子更大了,到处都需要钱,这一百吨煤对学校来说简直是雪中送炭啊。可是这煤他又实在不能要,他不是向来看不惯余大黑的为人吗?不是要整治一下余大黑,告诉他怎样尊重老师吗?不是要在很快就要开的家长会上告诉他怎么当个好家长吗?既然这样,他怎么能收人家的东西呢?
汤校长啊,你这不是瞧不起兄弟嘛,听说下午的家长会你打算给我们这些人另请一桌,有这个事吧?
汤河说,有,为了方便管理。
为啥要给我们另请一桌?啊,为啥要另请一桌?恐怕不是因为我们长得好看吧,我们这些人嘛,用社会上的话说就是,都得了富贵病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形象肯定好不到哪里去。但社会又需要我们,离不开我们,这又是为啥?可能你比我们更清楚,说得好听点,我们是企业家,说得不好听点,就是我们衣袋里有几个臭钱。钱这东西,我也不认为它是香的,但说它是臭的我还有点儿不乐意呢,要不然我们拼死拼活地挣钱为了个啥,就为挣个臭东西?香东西又能咋样呢?你比如说花,它是香的,可这玩意儿也就是让人看看吧,能当饭吃还是当煤烧?我看啥都不顶,对吧?我说了一大堆,就是希望你清醒一下,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希望汤校长也能从我口袋里掏几个臭钱。这年头,人见了钱,就跟苍蝇见了屎一样,不少人都想着咋从我衣袋里掏几个钱,可是,我的钱挣得也难啊,今天这个查,明天那个查,不容易呀。所以,好多想从我这里闹几个钱的人都给我顶了回去,不高兴就不高兴呗,毕竟,钱在我的肋条上拴着,谁都抢不走。可对于你,对于学校这种积德的地方,我就不这么想了,我是真想帮个忙。说得再小气一点,我儿子不就在你博人上学嘛。我知道你眼下的光景不好过,需要这一百吨煤,太需要了是不是?就算你一冬的煤安排好了,可这玩意儿多了还能扎手嘛,留着明年用不好?啊?
电话里的余黑子滔滔不绝,语重心长,像博人学校里那些循循善诱的老师。
汤河还真觉得自己给说得心动了,但他努力抗拒着,谢谢你了余老板,煤我真的安排好了,博人现在光景确实不好过,但我能办起这个学校,就能让它撑下去。
敢情我说了半天,都白说了?不行,这煤你要也得要,不要也得要。三个小时后,你务必打开学校大门,出来迎接我!余黑子说罢挂了电话。
这倒是汤河没想到的,余黑子好像失态了,看起来他很生气,很失望。妈的,送就送吧,就当是财富流通一回吧。有了钱你就该做善事,捐资助教,美国不是有个比尔•盖茨吗,他不是把钱都捐给社会了吗?汤河努力说服着自己,只有说服了自己,他才能坦然地收下余黑子送来的煤。
汤校长,余黑子要给我们学校送煤吗?叶娜突然出了声。
汤河这才想起叶娜还在他办公室,他盯着她看了半天,忽然说,你说这煤我要还是不要?
您问我?
是,你帮我决策一回吧。汤河盯着叶娜,这情景有点儿像一只猫戏弄着老鼠。
叶娜摇了摇头,不要,要我说这煤您不能要。
哦,为什么?
很简单,因为您反感他,您一直把他当作您的对立面。您不让我去他家补课,您说他为富不仁,让我离他远点儿,再远点儿。就在刚才,您不也在怀疑昨晚我是去他家补课,和他在一起了吗?您怎么这样健忘?
没错,我是反感他,可是学校确实需要煤啊。
这您自己定夺吧,校长,如果没别的事,我可以走了吧?
汤河无力地挥了挥手,你去吧。
叶娜看了他一眼,拉开门走了,高跟鞋噔噔噔敲击着过道,渐渐远去了。过了一会儿,汤河好像忽然记起了什么,站起身,把自己移向高大的落地玻璃窗前,叶娜刚好出现在了楼下,好像还回过头看了一眼他的窗口,不,也许这只是他的幻觉,她看都懒得看他一眼便轻盈地移向那栋楼。汤河心里又不是滋味了,看来,叶娜和余黑子之间什么事都没有,他的判断失误了。否则,她也不会这样说,不会对余大白表现出强烈的反感。但也许这都是她故意装出来的,她在制造一种假象。她急匆匆地离开,或许是急着给余黑子打电话诉说委屈去了,或者是准备着中午的约会?怎么就让她走了呢?她违反了校规,夜不归宿,就这样不了了之了吗?这不是在纵容她害她吗?想到这里,他又想把叶娜叫回来了,告诉她以后若是再跟那个余黑子来往,就趁早卷铺盖走人吧。但还没等他抓起那银灰色的话筒,电话忽又响了起来。
汤河接起电话,没想到又是余黑子。
汤校长,刚才我有点儿失态,那事,就是送煤的事,你就依了我吧。余黑子显然平静下来了,说话有点儿低声下气。
好吧,余老板。汤河觉得自己这回真的给感动了,但心里同时也疼了一下。
这就好,就好,你总算给了我个面子。
不,我得谢谢你。
谢啥谢,自家兄弟嘛,你的为人我一向敬重,是不是?还有,我,我还有个事,你得帮我一下。余黑子言语有些结巴了。
什么事?
把叶娜给我吧,我这里缺个能写会道的人当秘书。
你可以问她呀,她不是一直给你当家教吗?汤河心里冷冷一笑,绕来绕去原来是为了个这!
早不当了,也不知听了谁的话,怎么说都没用啊,你得帮我劝劝她,我知道她家里比较贫寒,需要钱。
对不起余老板,这个忙我帮不了。还有,你的煤也不要送了。
汤校长啊你可别误会,我送煤是真心的,你不要误会,不要误会嘛。余黑子听起来是真急了。
汤河说,不是误会,是我刚刚想明白。
送煤的车队已经上路了,你不要,他们也会把煤卸在你的校门口。
汤河叹了口气,说,随你的便吧。说罢挂了电话。
到了中午,汤河去食堂吃饭。食堂后边就是锅炉房,汤河停住看了一会儿,见总务处的老郭正好从那边转出来了,满脸满手的黑污,他忍不住笑了,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了?老郭也笑了,那笑从黑污的脸上喷薄而出,不是说余黑子要给我们学校送煤吗?我把后院先收拾了一下,也好卸煤,对了校长,听说电视台记者也要来?汤河脸不由一沉,这事你听谁说的?老郭就有些惊讶了,校长都不知道这事?整个学校都传遍了,一百吨煤啊,上哪去找这样的好事?这样的好人是该采访一下,省台市台也该来嘛。汤河本来想说句什么,看到老郭一脸的喜悦,摇了摇头,什么也没说就进了食堂。里面也是喜气洋洋的,教师们好像也在议论这件事。他一进门,一双双目光就都探向他的脸,好像他的脸就是个矿井,能挖出一百吨煤来。
汤河心里有些不快,匆匆扒了几口饭,便出来了。出门时,他不自觉地扫了那边靠窗的一张桌子一眼,没人,以往那个位置总坐着叶娜。但只是短促的一瞥,他就把目光移开了,心里却好像被什么牵扯着,她怎么没来吃饭呢?
回了办公室,汤河一挨枕头竟然就睡着了。
好像是睡了没多久,开会的时间就到了,那帮财大气粗的老板还真的都来了,一个都没缺。按照他的安排,他们给集中在了一间教室,差不多也有几十号人。汤河亲自坐镇,这会就由他给他们开了,他就是要好好训导训导他们,让他们知道来了学校得有个规矩。你们不都在自己的公司立下不少规矩吗?没了规矩,一切还不得乱了套?这样下去,还怎么给你们的子女树立榜样,成绩能好了吗?汤河脸上没一点儿笑,腰杆挺得笔直,在过道里走着,就好像一棵移动的钻天杨,而这伙人都是他枝杈上的叶片,他说长就长,说落才能落。有个胖乎乎的家伙忍不住了想接个电话,给他狠狠瞪了一眼,居然小学生似的一吐舌头,讪笑着把手机关了。汤河满意地点了点头,在过道里继续走着,他忽然发现这些人中没有余黑子,这家伙怎么能不来呢?不是说要给学校送煤吗?莫非只是一时兴起开了个玩笑,压根就没这个意思?你不来就不来吧,你不来最好!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真正期盼的,他根本就不想要余黑子的煤。
汤河就要登台讲话时,突然给一阵急迫的电话铃吵醒了,他这才知道刚刚是做了个梦,还不到开会的时间呢。他抓起电话一听,是一个陌生的声音,自称是余家湾煤矿的。汤河问他什么事。那人很客气地说,汤校长,我是给余总请假的,他本来想去博人开家长会,但现在去不成了。汤河冷冷地说,我就知道会这样,你们老板向来是说一套做一套。那个人赶紧解释,不不,汤校长,是刚刚我们煤矿出了事故,情况有点儿不太好,要不然余總肯定会去的,这事他都念叨了几天了。汤河眼睛睁得多大,什么?你们煤矿出事故了?电话那头说,是是,余总得马上处理这事,他还让我告诉您,煤车可能快到你们学校了,让您打发人接应一下。汤河放下电话,老半天想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些什么。
两个月后,又到了学期末的家长会,汤河明明知道余黑子不会来了,可心里还是惦记着,盼着他能出现在学校,出现在教室。但等了半天,也没看到余黑子的身影,汤河就想,这个人真的来不了啦。余家湾煤矿一出事,余黑子就给抓起来了,有人说他没什么事,很快就会放出来的,也有人说,余黑子这回事大了,至少也得判个七八年。
汤河在各个教室门口转了转就出来了,下了楼,鬼使神差般的又到了锅炉房前,院子里是成堆的煤,积得小山似的。这个冬天,他常常在煤堆前走来走去的,脑子里乱糟糟的,也不知想些什么。在余家湾的那次事故中,他的一个亲戚也给困在了井下,救上来时人早死了,给煤块砸得面目全非。他总听得煤堆里有人在喊,在焦急地喊,至于喊什么他就听不清了,是那个亲戚的声音,还是余黑子的声音,他更是分不清了。当然,有时,他还能在煤堆前看到一个清秀女子的背影,那是叶娜,是博人的校花。这些煤送来的第二天,叶娜就辞了工作走了,听说是到了外地。
想到这些,汤河心里不由得又一次沉重起来……
原刊责编陈克海
【作者简介】王保忠,男,1966年生,1994年开始发表小说,著有长篇小说《银狐塬》、《男人四十一枝花》、《我的浪漫逃亡之旅》,中短篇小说集《张树的最后生活》,散文集《家住火山下》,长篇纪实文学《当农民的日子》、《直臣李殿林》等。曾获《黄河》首届优秀小说奖,《山西文学》优秀作家奖,赵树理文学奖等。现在山西省大同市文联供职,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