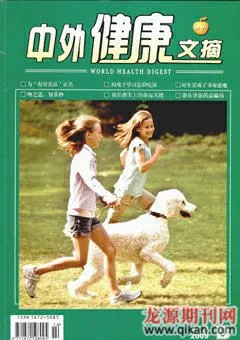滥用抗生素的恶果
瘦 驼
葡萄球菌是很常见的一类细菌,仅有少数能危害人类健康。最臭名昭著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绝大部分的金葡菌感染不过是皮肤软组织感染,或者导致上吐下泻。1944年,青霉素的商业化生产让人在与金葡菌的斗争中占得先机。可很快,人们便发现青霉素渐渐不那么有效了。1959年,甲氧西林,一种青霉素的类似物被投入医疗应用。两年后,英国的一家医院里分离出来了一株不怕甲氧西林的金葡菌——MRSA。随着更新的抗生素的应用,MRSA销声匿迹了。直到1981年,MRSA突然在美国现身,这时医生们惊讶地发现,MRSA不仅不怕甲氧西林,当时市面上除了万古霉素之外大部分的抗生素都奈何不了它。
早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科学家就发现这些抗性是原本存在于细菌中的。大约在每1亿次分裂中,细菌的基因就会出现一个突变,由于细菌数量庞大而且繁殖速度超快,所以它们的基因多样性也无比丰富,那些花样百出的耐药手段,都不过误打误撞出来的。一个能耐受抗生素的细菌在“自然”条件下没有任何优势,反而会增加能量消耗。但当人们大量使用抗生素时,情况就不一样了。面临抗生素的“选择压力”,不耐药的细菌被慢慢淘汰掉。不正确的抗生素使用方式,加速了耐药性细菌的产生。对于经常把抗生素——也就是“消炎药”当万用灵药来用的我国医生和病人来说,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哪里有抗生素,哪里就有耐药细菌,所以医院成了耐药性细菌的集散地。更不幸的是细菌还能互相“交流经验”,细菌的遗传基因经常在个体间,甚至不同种类的个体间交换,好像是一大群坏分子开会互相学习破坏技巧,这大大加速了超级坏蛋产生的速度。
与兴风作浪的金葡菌相比,结核分枝杆菌(TB)带给人类的,可能是一场海啸,它是给人类造成痛苦最大的一种细菌,甚至超过鼠疫和霍乱。在过去,结核病是造成人类失去劳动力和死亡的第一元凶。时至今日,每年全球死于结核的人仍多达近200万。近20年来,结核病在世界范围内大有反攻倒算的势头,这源于一种叫多重耐药结核(MDR-TB)的结核菌。结核的治疗一般持续半年到一年,很多感觉病情好转的病人中断治疗,这给耐药菌的产生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虽然,耐药性是抗生素使用的必然,但是规范严格的治疗能够极大地减少耐药菌的产生。以丹麦为例,由于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严格规范感染性疾病的诊疗,目前丹麦医院感染MRSA的发生率不足0.5%。长远来看,这不仅仅是个科学问题,同样是社会问题,这也是我们对新医改充满期待的原因。
(摘自《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