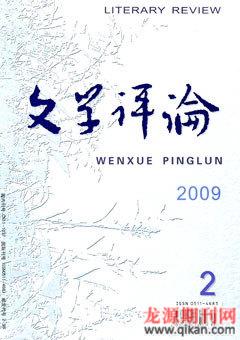评董乃斌《文学史学原理研究》
王志清
董乃斌教授主编的《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是一部筚路蓝缕的开创性著作,具有较高的理论品级和实用价值。董乃斌先生长期从事文学史写作和研究,有着多种文学“史”著主编和独撰的经历,具有良好的理论修养和扎实的书写准备,实践与理论互补而生发,形成了研究的强势站位,形成了辩证性书写的叙述机智,也形成了原理构建的特殊话语权。
巴赫金在讨论“‘文艺学中的现实主义方法”问题的时候说:“根据新康德主义者的观点,不是方法适应实际存在的对象,而是对象本身从方法那里获得其本身存在的全部独特性;对象只有在那些用来规定其认识方法的范畴中,才成为某种现实。在对象本身之中,没有任何规定性不是对认识本身的规定。”从此意义上说,著述的方法不仅使对象成为现实,而且生成存在的独特性。我们在阅读了《原理》,巡视了作者以百年中国文学史为对象实体所做出的全景式观照而形成的原理性的概述和演绎之后,发现最难能可贵的是此著的研究方法,是主编在文学史原理研究中融入哲学思辨的研究特色。这是一种研究尝试,也是一种学术的自觉,进而成为一种叙述与建构上的优势。同时,也形成了此著鲜明的人文品格,成为此著重大开拓的重要的标志,作为研究对象的文学史学原理也“从方法那里获得了其本身存在的全部独特性”。故而,笔者在以此为侧重和视角展开评论之前需要作特别的强调。
一从容而平和的叙述风度
董乃斌比较推崇钱理群的文学史写作观,这也反映了他自己的感同身受的体悟。《原理》里这样引述说:“钱理群在谈到他《1948:天地玄黄》一书的写作时,特别阐述了文学史‘结构与叙述对于文学史写作的意义所在。”此论中所强调的“结构与叙述”,文学史写作如斯,文学史学史、文学史学原理的写作何尝不如斯?以笔者观,结构与叙述,叙述更是首当其冲的。
叙述方式方法的选择,是作者方法论的体现,是其思想原则、思维方式作用于研究对象的物态化形式,我们在对于《原理》的阅读中感到,著述者对“叙述”重视的程度,并确信这是著述者的一种学理坚持,一种学术理性。而这种理性的叙述理念和体现这种理性的叙述形态,集中表现在鲜明的辩证思维上。此著所有论述,均考虑在哲学的层面之上。作者从哲学的高度来观照和解读文学史现象,把研究提升到哲学的高度,诚如《原理》中所指出的:“若想使文学史著作成为具有鲜明史学品格的科学著作,就全靠有正确的哲学思想给文学史的观念和行为以有力指引。”(第396页)同理,要使文学史学原理著作成为具有品级很高的科学著作,哲学思想则显得更为重要。关于这一点,以《原理》观,其认识是十分自觉的,且其表现也是非常积极和具体的。我们以“风度”来评价,是因为这样的《原理》的“叙述”个性特别鲜明,而且特别的富有成效。
1988年《上海文论》特设“重写文学史”的栏目,一时间不少报刊卷入了这场讨论。当下又引发了上海教授“文学史垃圾化”的说法。百年文学史书写,据不完全统计,也在2000部以上,而真正令人满意的文学史论著还实在是凤毛麟角。文学史写作真需要有一次“清理门户”的净场,真需要有一个得失成败的概括,需要有一个孰优孰劣的评判,也真需要有一个何去何从的引领和指示。于是,《原理》出现了。我们以为,《原理》出现的初衷和旨归,虽不能说有其拯救时弊的雄心,但是,这种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则肯定是非常强烈的。以《原理》中解释就是:“唯物主义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且有检验认识与真理关系的尺度。只是加德纳谈的是关于历史的因果解释,他认为历史可以得到解释,并且对历史的解释‘应持一种多元的立场,在阐述自己的真知灼见的同时,并不一定要否认其他解释的有理。”(第402页)
由于现代阐释学和接受美学的影响,十分重视文学文本的阐释,重视文本阐释者的作用,重视接受者的意志,重视阐释现象的消费功能和消费过程,从而使文学史的性质成为一种不断生成中演化发展的活性机体,而非一成不变的被动载体。现代哲学解释学和解释学美学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伽达默尔在他的《真理与方法》一书里指出:“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与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系,在这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就是说,任何事物的存在,必存在于一种特定的效果历史中,因此对任何事物的理解,都必须具有效果历史意识。伽达默尔所说的效果历史意识,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意识。效果历史意识具有开放性的逻辑结构,开放性意味着问题性。我们只有取得某种问题视域,才能理解文本的意义,而问题视域本身就包含了对问题的可能的回答。董乃斌的《原理》“无限论”的提出,是否可以视为建筑在这种哲学背景上呢?文学史史料的无限性,文学史研究者能动性的无限性,文学史样式的无限性,以及文学史范式的无限性,使董乃斌们确信文学史研究具有无限性的广阔前途,也使文学史具有无限多样的书写可能。《原理》著述者不无兴奋地说:“文学史无限论,是本书下面所有论述的理论基础,也为全书的视野和论述打开了辽阔的天地”(第431页)。这种“辽阔”,是一种境界,是一种高度,是对中国文学史鸟瞰式的宏观考察后,对文学史发展规律的检视和揭示的一种决策。因此,《原理》的“叙述”,服从于其总体性思维方式和叙述风格,而这种思维和风度体现在三个坚持的叙述原则上,即坚持人本性,坚持宽容性,坚持开放性。这种对文学史书写史的批判与反思,通过一种总体的考察比较之后再得出结论,上升到原理的层面,这本身就是以整体性思维和宏大叙事方式为前提的。而这种“叙述”所呈现出来的既是风度也是风格,让我们感受最深的是著述者的宽容。著述者不是怨天尤人,而是承认历史,接受现状,通篇不出大言,是耐心的解析,婉转的评论,善意的劝导,积极的引领。故而,这种让我们很受感染的亲切平和的叙述风度,这种以学术宽容为风度特征的书写,表现出哲学上的辩证和交流上的人性化,更加方便阅读也更易于读者作者的沟通。
董乃斌不无遗憾地说:“文学史家,特别是撰写中国文学史的大部分本国学者,真正怀有哲学兴趣的不多,这严重地限制了中国文学史书写的深度。”(第402页)果不其然,《原理》著述者对哲学兴趣和自觉,以“叙述”之“平”而显示其思辨之“深”,形成了表述上练达畅顺、婉转平和的风度,也形成了一种更接近艺术的叙述风格和话语系统。
二坚稳而缜密的建构形态
我们感受到《原理》充满了辩证法,不仅仅反映在其具体的书写中,而且也反映在其著作的逻辑建构上。董乃斌深有体会地说:“史料和建构是文学史定义中两个重要关键词”。他认为:“建构的含义远比编纂丰富,建构更重要的是树立思想和严密逻辑”(第434页)。
那么,什么是“建构”呢?《原理》解释说:“有自身的逻辑结构,有思想,是一个知识体系,而
统帅这一切的一个关键词,则是建构。”(第396页)可见,建构是一种独立自足的系统,是一种有思想而又要有体系的缜密形式。《原理》最后一章里讨论“文学史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侧重阐述了文学史与哲学的关系,其实,即是自述其《原理》著作的建构形态以及何以如此建构的理由。
譬如以《原理》章节排列的次序观,作者认为“哲学关心的首要问题是本体问题。”于是,第二章即安排了关于文学史学原理的本体论问题研究(因为第一章乃“导论”),此乃构架之基,由此而“派生”、“建树”出:“文本、人本、思本、事本”诸种。而此“四本”中围绕“人本”说话,强调“文学史的人本观”的作者也同样把“人本观”作为文学史学原理的基本思想和核心内容,“在文学史研究中,由于对文本的重视,必然会引起对人本的重视”。因此,“文本和人本是构成文学史本体的两个重要侧面”(第73页)。也因此,文学史研究中的人本观则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董乃斌牵此一发,举此一纲,而编织出符合原理“自身逻辑结构”的“知识体系”。
进而,《原理》中涉及到“真实性”问题。作者认为:“对于文学史真实的叙述,也离不开哲学层面的思考。”(第397页)董乃斌花了比较多的篇幅来讨论“真实性”的问题,这是著述者对于文学史学研究中具体处理文学史现象之本体所要体现的原则和方法。文学史学原理研究所关注的对象,不仅仅是文学史本身,还有就是文学史家的素质及其工作。也就是说,这种研究,包括了对文学史成品和文学史研究工作的反思和检验,对文学史研究以学理性的考察和概括。因为辩证思维贯穿始终,全著结构整饬,严谨规范,既有对全貌的宏观把握,又有对细部深切分析。我们可以确信,此著的章节设置,乃至于建构,都是以哲学原理为依据的,甚至是以哲学内容为本体的,连排序的先后都是这么考虑的。董乃斌认为:“史家让事实说话的办法,就在于选择、排列和次序”(第375页)。因此,我们研究《原理》章节的排序,这种意识是很突出的:本体论、方法论、主体论、范式论、史料学、编纂学、形态学等,每一门都是一独立的“学”,而也是一种建构的层次,是连成系统的一个个的“点”。具体到每一章,其推演性的开展也并不完全相同,比如几个“论”多宏观多理念多思辨性的论述;比如史料学与编纂学部分则具体而微,多针对性和实际操作性。作者认为,这样考虑是“建筑在以辩证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对文学史实践的产物进行分析的基础之上”(第397页)。
《原理》的建构体系,是以“人本”为中心而编织的一张网,而这种构成,既是线型的流程,又是复式的构架,每一章只是原理叙事的一个元素而已,是整个一部作品结构屯的一部分有其独立性,但是章与章之间,更有其运动性,更有其照应关系,形成了结构上的先后因果和上下连贯。董乃斌认为:“文学史因为其严密的逻辑结构而形成一张网,每个作家,每篇作品,每一种文学思潮都可在这张网上找到位置。这张网由掌握丰富文学史料的研究者负责编织,编织得越细密,知识系统就越完整越让人感到可靠,这样的文学史就会被人视为信史。”(第137页)同理,对文学史著述有此要求的文学史学研究者,在《原理》的建构上,也自然分外自觉和特别存心,自然也有很好的收效。
三严谨而深入的学理推演
《原理》也属于治史一类,但是,又不完全等同于“史”的书写,“文学史原理就是从文学史学史中抽象、提炼出来的,也必须回到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史中去检验和修正。”(第18-19页)《原理》得益于哲学,哲学的辩证和深度,成全了其著述的理论品级。
董乃斌在评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时指出:“能够在史著的编撰中重视理论,并能将某种理论经自己的消化而妥当地用于史著,这是学术研究达到较高层次的表现,但还不是学术的最高境界,更进一步,应该是通过史著的编撰创造出某种理论,这理论如能自成体系,不但适用于这部史著本身,还能用于更广阔的范围,那就更好。”我们似乎并不能说其《原理》已经达到那个水准,然而,著述者重视理论、重视哲学思辨且能够自觉总结规律、理性抽象而取得了理论上某些突破,则是显见的事实。而且,著述者在《原理》中明言一种挑战传统学术弱点的意识:“在历史研究,包括文学史研究中有意识地作哲学思辨,作理论探索,而不仅仅满足于史料的考证(当然绝非否定必要的考证),这是对中国学术传统弱点的一种挑战,也是对不善于作系统和严密抽象思辨的民族根性的一种克服。”(第403页)因为董乃斌长期工作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处身于代不乏人的资料研究与宏论思辨同兼的大学者之中,又在文学史学研究上长期投入,特别是因为前期的《文学史学史》成果,《原理》占有丰富而牢靠的资料,且又具有熟练而准确运用史料的技能,杜绝了空洞的议论和主观的臆测,而尽可能地以史料说话,从翔实的史料中自然引出自己的结论,因而使原理具有了雄辩的逻辑信度。
譬如,在论及“规律”时,著述者为了强调文学史和文学史研究的人文性特点,而比较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各自特点。自然科学所发现的规律最具刚性,可以重复性的实验和试验,而历史和现实社会中所发生的一切往往是一次性的、无法重复的。这是根据文学史研究的特殊性而提出的得珠之论,这除了说明了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鲜明区别以外,还说明,人文研究与单纯的史料整理在本质上的不同。著述者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并且大量引述了文学史的客观生成的“史”料,得出了文学史发生的“随机性”的结论,而且这种“规律”的无序性和偶发性,确证着文学史不一定是由某一规律支配着的合目的性而理性演进之事实,充分体现了著述者文学史学原理的“相关的规律所具有的多元性、可检验性、可修订性”的宽松和弹性。《原理》的第四章第三节,对文学史“规律”的认识概括出四大特征:即“一、规律或规律性认识的层次性”;“二、逻辑性与随机性的辩证统一”;“三、规律和规律性认识的无限性、多元性和相对性”;“四、规律和规律性认识向常识转化的特性”。这些推演和理论,更加显示出著述者不仅仅具备了对文学史现象以深透考察的视野和敏锐,而且具备了哲学思辨、逻辑推演的机智和素养。其原理不只是以哲学为背景,而且是以哲学为内容,为讨论的具体对象。譬如在关于“真实性”问题的讨论中,著述者列举哲学史上关于真实性论证的流派,概述了论争的过程和历史,也表明自己对历史哲学家柯林伍德“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理论的推崇。正是这种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指导,著述者强调文学史书写和研究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检验认识和真理关系。于是,把文学史的发展、演变史提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提取了带有“规律性”的原理,其学术判别,符合文学史现状之本来面目的客观性,而又具有研究上的独立见解,通过逻辑框架来体现著述者对文学史规律性的认识,持论平允,叙述周密,具有令人信服的逻辑力量。
诚然,“试图对文学史作理论探索,特别是提取规律性认识的,往往要冒概括不周、遭遇例外和受到质疑的风险,(连闻一多也不可能逃避这样的命运)”。(第159页)《原理》似乎也可以找出一些值得质疑的地方,而明显不足的地方如,表述上的重复,举证上的交叉。特别是其中举证,多是百年前的林传甲、谢无量、胡适和他们的文学史,而他们的偏激、甚至幼稚是十分显见的,但是对近期范本的研究不够,或者说未便将之放上解剖台。《原理》中把“批判意识”视为文学史家主体所有素质中的最基本素质,可是,在《原理》中,这种可贵的意识却表现得不够强烈和尖锐,让读者“是非莫准”,或多或少地削弱了《原理》的学术分量。还有,或许是因为太讲辩证,而限制了著述者的学术自信。
然而,《原理》毕竟以其独特的学术风貌而实现了填补空白的意义,确实具有开创、开陌之功。由文学史而文学史学史,都是偏于对现象的阐释和描述,文学史学原理则偏于抽象和演绎,而从理论的层面凝炼和提升,是研究的研究。董乃斌说:“在文学史研究中有意识地作哲学思辨和理论探索,为此而将文学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相结合,虽然艰苦,虽然不能保证成功,但却是极有意义的,值得有志者悉心投入。”此论我们可以视为夫子自道,是作者研究甘苦的深切感受。故而,我们宁可把《原理》视为一部文学史学哲学,不管这是不是董乃斌的书写初衷。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