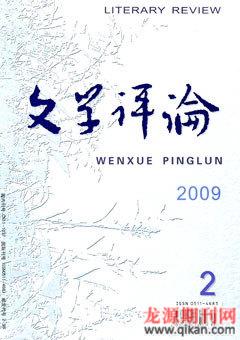潜隐与超越
王攸欣 龙永干
内容提要冯至《十四行集》不仅受西方生存哲学特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影响,也潜隐着中国传统生命哲学的某些因素,冯至在对中西传统的体悟和抉择中,形成自己独特的生存意识,这种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超越了纯粹的西方传统或中国传统,创造出现代中国知识者的生存新范型。《十四行集》所受存在主义的影响是显在的,已被学界充分阐述,而其中潜隐的传统根脉,如个体本位基础上的群体价值取向,体用不二的生命智慧等特征,则甚少为人所注意,更没有被充分阐发,本文力图予以阐述。
冯至自己说,《十四行集》是在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直接影响下写成的。确实,《十四行集》不仅格律上采用了十四行变体,在精神内涵上,也深受里尔克生存哲学的影响,里尔克诗的一些母题,诸如生与死,决断,自由等生存哲学的根本观念,也是冯至《十四行集》吟咏的基本要义,因此,冯至与里尔克的关系,一直为学界所关注,更进一层,他与存在主义哲学家如丹麦的克尔凯戈尔、他曾亲炙的德国教授雅斯贝斯的思想关联,也被充分探讨,这方面的研究,解志熙《生的执著》一书中关于冯至的一章——《冯至:生命的沉思与存在的决断》,理解甚为透彻,作者可谓领会了包括《十四行集》在内的冯至创作所表现出来的生存哲学之特点和精髓,并作了令人信服的论述,在学界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响。毫无疑问,《十四行集》所表现的生存哲学,确实深受西方文化精神尤其存在主义观念的影响,这种影响相对于中国传统而言,占有主导地位。
不过,尽管经过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中国传统对于冯至这样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其根深蒂固,不可摆脱。而且,正如冯至很欣赏,在《传统与“颓毁的宫殿”》一文中予以引述的里尔克名言:“我解释革命是克服许多恶习而有利于最深的传统”,经过社会与文化的革命,传统的深层更显出生命力,更凸显其特征,也更令冯至珍惜。冯至对中国社会现实和国民性持批评态度,颇多针砭,但对中国文化传统,却较少否定,他希望不要因为“颓毁的宫殿”而影响了对真实的传统精神的继承,譬如他对“认真”的生活态度的理解,就并不认为这是西方文化和西方人的专利,他以曾子易箦和王羲之写字的故事来诠释“认真”的精神,而对自由决断,导致生命升华的一跃,他也以王羲之、陶渊明解职归去为最美的典范。在《十四行集》的写作中,冯至并没有着意弘扬传统,但中国传统的根脉,自然滋养着他的生命哲学,与西方传统相互印证,相互扬弃,也相互融合,构成其生命哲学的底蕴。但这方面,因为其潜隐性的特征——或许某些成分,连冯至本人也未必完全自觉——学界关注并予以阐发者很少,即使谈及,也多较笼统地说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未及展开,略微具体的,或则只是谈十四行诗体方面起承转合的特征与律诗的相近,或则谈冯至关注现实民生的态度与杜甫的关联,真正从作为《十四行集》内核的生存哲学的层面来研究者,似未曾见。因此,我们试图予以探索。
一
1930年,冯至到德国海德堡大学留学,在这里潜心阅读克尔凯郭尔、尼采等存在主义先驱的著作——不过,在冯至眼里,尼采并不是存在主义者一倾听存在主义哲学家雅斯贝斯教授的哲学课,尤其再次沉潜于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布里格随笔》、晚年诗作《杜伊诺哀歌》及《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为里尔克的认真、决断、不为世俗名利所动的人生态度所感动,产生精神境界的升华,不仅深受其诗作的影响,而且学会了里尔克观看宇宙间万物的方式。这在他的文章《里尔克》、《一个对于时代的批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译序》、《认真》、《“这中间”》、《决断》诸篇中,多有表白,显示出他受上述诸人影响而形成的相近的生命体验、生存哲学、审美倾向和创作观念,这种影响也显然表现在他1941年创作的《十四行集》中。《十四行集》里,诗人对个体存在的肯定、对生与死的沉思、对生命意义的探索等等都与存在主义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点不容置疑。不过,冯至把他所理解的西方文化资源,熔铸于他的审美心理与生命体验,与他既成的文化心理、社会生活和生命体验等先在视界的各种因素有着密切关系。我们可以说,冯至先在视界中沉淀的一些传统文化的因素,对冯至本人接受存在主义观念,有着相当大的影响,有些他有所自觉,在文章和诗中有所陈述,而另一些则可能连他自己也没有意识到——因为这些因素已经成为了中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解释学和接受美学,都就这个问题谈得很透彻,外来文化理念要么与主体的性情体验相吻合、要么经过了接受主体的改造与“误读”,才可能真正深入到作家的生命体验之中。因此,一个接受主体面对异质文化,所持的态度应该是充分理解与领会,而不是轻率的表态与评判。冯至在“五四”时期与留学德国时,对传统文化与西方现代哲学所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态度。在《十四行集》中他礼赞歌德时,也崇敬杜甫,在讴歌梵高的热情时,也感动于鲁迅的“一觉”。我们仔细吟味与体验《十四行集》文本,所能感受到的是他的“心”在理解与领会中西文化的基础上不断超越所获得的一个“大的宇宙”。
存在主义与以儒家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有着很大的异质性。不管存在主义在其发展流程中呈现出怎样复杂的景观,其一以贯之的观点是他们“把孤独的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克尔凯郭尔认为“群众——在它的基本概念之中就是虚妄,因为它使得个人成为完全不知悔改和不负责任的东西,或至少由于把责任分散而削弱了个人的责任感”。冯至当时没有关注的萨特更是发出了“他人即地狱”的惊世骇俗之论。《十四行集》中的确强调个体生存的意义与价值,强调个体应当有所承担,但以传统儒家群体本位为集体无意识的冯至,对这种极端的个体取向以及蔑视群众的观念显然无法接受。于是,冯至积极地加以扬弃,把独立的个体引导至社会与群体的值阈中。《十四行集》中内蕴的是一种建立在独立个体基础上的自我与他人的融洽,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它强调个体并不是走向极端的个体,不是表现自我与他人、个体与群体的冲突和矛盾以确立自我的存在为旨归,而是表现出个体是以大我为本位,以群体为依托的。而这种群体本位思想既与20世纪40年代中华民族的历史处境和生存危机有着直接的关联,也与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传统伦理观念中强调群体本位和民族大义有着内在的一致。因此存在主义的个体意识虽影响到了冯至,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先在性的文化传统所整合。但这不是两者的简单调和与一般意义上的融合,而是一种成熟主体的创造,是新的生命意识的诞生。
《十四行集》中这种崭新的生命意识,首先正是体现在个体既拥有根本的主体意识,担负起自我生命的意义和价值,但又并没有将其完全局限与自闭于个体自我的值阈之内,而是在主体生成的基础上将生命的价值导向群体、民族。在第一首《我们准备着》中,诗人探索了死亡对于生命的价值。在存在主义哲学中,真正的主体是在“先行到死”的体验中作出生存的抉择,是在一种“澄明”中直面一切
苦难与危险,于是诗人的态度就是“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在漫长的岁月里忽然有/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但在这样一种生命态度中同时可以见到,“小昆虫”在“结束它们美妙的一生”时,是“经过了一次交媾”,是在自我牺牲时用自己的死亡换取了种族的繁衍;“或是抵御了一次危险”,以自我的毁灭保障了他人与群体的生存。可以说,正是在这样一种生命意识中,生与死的界限才得以超越;而在群体与种族的延续与生存中,死亡与牺牲才得以辉煌与灿烂。个体的价值不是封闭的自足,他人与群体也是价值获得确证的领域。于是,生与死的症结才得以解开,群体作为价值母体也再次获得了体现。而这样一种价值观,在中国文化中,由儒家坚守和护持,或许正像英国汉学家葛瑞汉所言,正是中国文化、中国社会能够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因为儒学将它的所有一般观念根植于对已存的习俗、学问和历史先例的缜密研究之中,它独自许诺将个体完全一体化为他的文化、社会和宇宙之中,这一定是中国社会得以延续的秘密之一”。所以《我们准备着》一诗,不止表达了冯至对于个人面临死亡时的生存决断的思考,也不止表达了选择死亡的方式是生存的自觉,是生命的辉煌的观念,同时也表达了他的生存意识中,面临死亡作出决断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与儒家观念是密切相关的。
在《威尼斯》中我们见到的是一座一座“寂寞”的岛屿在“拉一拉手”、“笑一笑”中“结成朋友”、成为“千百个寂寞的集体”。有人把这里的“寂寞”坐实为“孤独”,可能离开了文本的原意,此中“寂寞”是一种冷静与沉着的理性,是经历了苦难和风雨、历尽了艰辛与挫折后的成熟。而“岛屿”则是一个个生命个体的象征,他们之所以是“寂寞”的,那是他们并没有为群体所湮灭。在存在主义看来,对于“孤独”与“寂寞”的强调是他们对于生命思考的一个基本立足点。但冯至没有让个人的“寂寞”陷入封闭与伤感,更没有成为生命的泥淖,而是让人理解到每个人都是承担着作为生命主体的责任与意志,于是在祛除浮躁与叫嚣的混沌中,一个个独立的个体才能成为强大的“集体”,成为更为坚定的“朋友”。此处固然有着对个体意义的强调,但是个体的价值与意义归属仍然没有远离群体本位的值阈。
正因为有着这样一种成熟的群体本位,让个体在人类文化发展的途程中,总是自觉地承续着先驱者的成就和业绩。于是,在《给一个战士》、《蔡元培》、《鲁迅》、《杜甫》、《歌德》、《梵诃》中,诗人对他们的奋斗与努力在生命“同情”的理解上给予了高度的讴歌和赞美。诗人也在他们的导引和启迪下自觉地承担起生命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一种文化守成的态度,也是人类真正实现自我进化和发展的必然路径。在其心理情感上是延续了中国儒家文化“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持存与守成的文化心理,它与存在主义破坏偶像、强调绝对的自我本体是截然不同的。但是在这些文化先驱与艺术大师面前,诗人并没有一味地膜拜,而是在理解中致敬,在“同情”中产生生命的感发,并没有因为“偶像”的存在而“取消自我”,让自我“沉沦”,这种情形是存在主义生命个体意识的一种表现。对于文化大师、人类英雄是如此,对于默默的个体和平凡的生命诗人同样是抱着虔敬的忠诚和无限的爱意。在《有加利树》中诗人见到了有加利树“筑超一座严肃的殿堂”的崇高和神圣,但在《鼠曲草》中,诗人在渺小的鼠曲草身上发现了她的“高贵和洁白”,她的“伟大的骄傲”。作为现代意识中的主体,不仅是对文化传统与既定成就进行自觉的承载和延续,更要有着一种真正的人道精神和生命意识。尊重生命自身的意义、价值,才是真正的生命个体得以成熟和成立的前提。
冯至《十四行集》一个恐怕令所有读者都会感觉到的特点是,他非常频繁地采用集合人称——“我们”,从第一首《我们准备着》,到最后一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总共27首中,15首采用了“我们”作为主语,“我们”这个人称异乎寻常地频繁成为主语,这在里尔克的诗中,以及西方所有诗歌中,都甚为少见,甚至在中国新诗人笔下也并不多见,这些诗除第2l首《我们听着狂风里的暴雨》外,将“我们”替换成“我”也大致并不影响整个诗歌内容的传达。但诗人之所以要将“我们”作为经验的主体,决不是随意而为,恰恰显示了诗人在主体意识中对于私语空间和个体话语的一种自觉超越。这里要注意的是,冯至在诗歌中所指向的并不是个体和群体的简单相加或累积,而是在现代理性的烛照下,强调个体生命的意义和责任,在共同担负着民族和历史命运的基础上结合成一个理性的、自觉的强大群体。冯至的沉思,既没有走向传统的泥沼,也没有走上西方的险途,而是在追求生命主体性的基础上将生命的价值引向了群体与大我,这种价值取向恐怕既是对西方个体本位观和儒家群体本位观的继承,又是对两种传统的创造性超越。
我们还注意到,在对传统价值观的传承上,冯至更倾向于儒家而不是道家,道家的委运任化,自然无为,逍遥自由的观念明显为冯至所不取,冯至《十四行集·序》谈到,十四行诗的诗兴是由庄子逍遥游的梦想引发的:“在一个冬天的下午,望着几架银色的飞机在蓝天像结晶体一般的天空里飞翔,想到古人的鹏鸟梦,我就随着脚步的节奏,信口说出一首有韵的诗,回家写在纸上,正巧是一首变体的十四行。这是诗集里的第八首,是最早也是最生涩的一首,因为我是那样久不曾写诗了”。不过,这首最早产生的十四行诗,却并不是对庄子自由观的阐扬和礼赞,而是对逍遥游梦想的否定:
是一个旧日的梦想,/眼前的人世太纷杂,/想依附着鹏鸟飞翔/去和宁静的星辰谈话。//千年的梦像个老人/期待着最好的儿孙——/如今有人飞向星辰,/却忘不了人世的纷纭。//他们常常为了学习/怎样运行,
怎样陨落,/好把星秩序排在人间,//便光一般投身空际。/如今那旧梦却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
这首诗写冯至看到了我们自己的飞行队在天空飞翔,想起似乎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实现了庄子的鲲鹏展翅逍遥游的梦想,但我们的飞行员们并不是像庄子那样,想脱离和逃避纷杂的人间世,却是要以自己的努力重新安排人世间的秩序,他所欣赏的正是飞行员们积极人世的态度,而不是庄子消极避世的梦想,所以诗歌最后说庄子的旧梦,已经“化作/远水荒山的陨石一片”,也就是成为已然失去活力的旧梦。在《十四行集》的其它诗中,冯至表现出的自由观,是一种敢于承担责任,敢于面临死亡进行决断的自由观,与庄子那种追求任性适意,无所作为的自由观也完全不同。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冯至最钟爱杜甫,跟杜甫仁民爱物,穷年忧黎元的儒家关怀,接受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是直接相关的。同时,冯至也相当自觉地学习杜甫那阔大开朗的胸襟,使《十四行集》有着他此前诗歌不明显的气度阔大的审美特点。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冯至对传统的继承,也是有所选择的,而这种选择,同样也建立在他所接受的西方存在论的观念上,所以,西方思想也不断构
成着他的先在视界。
二
里尔克对冯至的生命体验和诗歌创作都产生了极大影响,这一点我们不须怀疑。但是我们一进入里尔克的《致奥尔弗斯的十四行》,就能深切感受到,诗歌中弥漫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和神秘色彩。诗人旨在探索如何让人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寻求到灵魂回归的途径,渴望在对孤独、死亡、痛苦的歌咏中探寻生命的最终归依。这部十四行组诗所抒写的内容是人们在传说中奥尔弗斯这个神奇的音乐家的引导下,在艺术启迪中获得神灵的启示,让生命探寻到走出沉沦的可能,也即“以我们的本性,以我们的动向/我们仍从属于持久不变/为神所用的力量”。通观整个诗集,其审美张力是建立在灵魂和肉体、物质和精神、此岸和彼岸的对立和分裂之上。这与我们读《十四行集》的审美感受完全不同。我们读《十四行集》,可以发现,两者在诗歌思维上的文化意蕴迥然有别。冯至既避开了基督教中上帝观念启示的外在超越,也避开了个体身心解脱的神秘体验,而是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在平凡生命的种种处境中去体验着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诗歌艺术张力的营构上也并不依赖于一个彼岸世界作为现在的召唤,也没有将神作为内在心灵的最终归宿,更不存在灵与欲的分裂,精神与物质的紧张及天堂与地狱的对立,一切呈现出来的是和谐与安详、宁静与优美。也就是说,冯至在寻求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时,在感性生命和日常生活中找到了意义与价值本身,在种种平凡的处境和现实的生存中寻求着一种内在生命与灵魂的归依和寄寓,这与以里尔克、艾略特等人为代表的西方现代派诗人相去甚远。
人作为一种主体性的存在,如何让生命获取意义与价值,无疑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永恒的主题。生命是有限的存在,如何在这种有限的存在中获取意义,也就成为生命主体首先所要面临的问题。在《我们准备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诗人以昆虫为喻,将个体有限的生命在群体伦理的值域中获得提升的启示,自己的行为就让自己找寻并确证了自己的价值所在。在《什么能从我们身上脱落》中,诗人以秋日的树木作譬,在对自然万物的蜕变轮回的理解体验中走向生命的沉静和成熟。自然与生命相互参证,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的真谛都在具体的经验生活与感性的日常事物中获得再现与把握。在《看这一队队驮马》中,诗人将生命作为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来认同与接受。驮马驮来远方的货物,水从“不知名的远处”“冲来一些泥沙”,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是这种不断的追求和努力中“随时占有”与“随时又放弃”的统一。获得与失去、追求和放弃并无绝对的界限,二者辩证统一,彼此消长起伏,一切悄然而来,悄然而逝,自由自在,了然无碍。如鸟儿“管领太空”而又“随时感到一无所有”。没有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分裂,没有歌德式的无限追求,也不是里尔克的彼岸神灵启示,而就在日常的平凡生活中,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就获得了一种圆满的实现。可以说在整个《十四行集》中,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与获得的历程并不艰辛,二者间的距离也并不遥远,就在这样的一种日常的体验中,在这样的一种有限的存在中,无限与永恒,超越与本体都获得了。简单地说,就是在日常的生存体验中,获得对生命价值的追求。这在其内在致思路径上无疑是中国传统的“不合弃,不离开伦常日用的人际有生和经验生活去追求超越、先验、无限和本体”,也就是所谓的“体用不二”,“平常心即道”。
与这种“体用不二”的哲学本体论相应的是,人们在寻求道体过程中的认识方式,往往是虚静去欲的静虑和体悟。老子的“涤除玄鉴”,“虚静而一”,庄子的“心斋”“坐忘”都有此种倾向,禅宗融合道、佛,更是如此,无论是南宗“顿悟”还是北派“渐修”,都强调以空灵心境来对待外物,用一种涤荡情怀、空诸一切的意趣来感悟宇宙人生。《十四行集》中,诗歌主体在面对自然万物,永恒时间、亘古宇宙时,如佛家面对所谓无量无边的三千大世界,胸虚灵廓,心无挂碍。也就在一种心不动念、万事具如的境界中把人引入到一种“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的境界之中。诗人也曾在称述里尔克的“诗歌需要的是经验”的观念时说,诗歌的经验,就“像是佛家弟子,化身万物,尝遍众生的苦恼一般”,于是在这样一种近似于禅的感悟中,“一生有几回春几回冬/我们只感受时序的轮替/感受不到人间的年龄”(《我们招一招手》)。“我们在朦胧的原野上认出来/一棵树,一闪湖光;它一望无际/藏着忘却的过去,隐约的将来”(《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刹那即永恒,瞬间就是终古。在一种与自然和谐一体的境界中,自我得以空如,化为世间万物,如《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中所写的:“我们站立在高高的山巅/化身为一望无边的远景,/化成面前的广漠的平原,化成平原上交错的蹊径”。体验到“有多少面容,有多少语声/在我们梦里是这般真切/不管是亲密的还是陌生:是我自己的生命的分裂”(《有多少面容》)。小狗在往昔“领受的光和暖”会“融入将来的吠声”“在深夜吠出光明”(《几只初生的小狗》),生命的幼稚与成熟、既往与将来,平淡与灿烂之间的相辅相成、丝丝关联,这一切都有着传统审美智慧的种种内在联系,特别是一种“妙悟”的诗性精神。同时,在诗歌中主体对于万事万物的“领会”并非是主客分化之后、对立之后而形成的片面的知识范畴与理性认识,而是主客的同一状态,它超越时空与主客界限,是一种澄明朗照之境。这样,也就让我们在直觉到传统诗学的“妙悟”的同时,能会心到海德格尔“此在”的那种内在精神的相通之处。
《十四行集》中那些自然隽永的诗行,葆有着生命的内在律动,有着一种现世的充实,也有着一种平和的超越,更能给人一种“读之身世两忘,万念俱寂”之感。对于生命和时间的种种领悟不是逻辑的推演而是直接感受的,不是神秘的启示而是感性经验的。我与人、人与物合为一体、不弃不离,个体达到无限,瞬间感受永恒,一切又都是从具体的空间与时间出发,一切皆不脱离现实的感性世界,“不落因果”而又“不味因果”。超越不离感性,对象世界虽然依然存在,但是不被当作实在也不被当作虚空,于是就获得了一种脱去物欲执着,少却因明逻辑的自由和快乐。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诗意化的愉悦与自由,与抽象思辨带来的认知愉悦颇不相同,更不是在概念与逻辑推演中的理性自娱,也不仅仅是一种东方式的感情抒发与情愫倾诉,而是一种源自主体感悟中的审美体验和生命情怀,是一种诗性的智慧。这在《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有着突出的表现。面对如何把握无限、抽象、永恒的矛盾与困境,诗人并未生发焦虑与分裂,而是通过椭圆的水瓶、草木的荣谢、风中的旗帜等等具体的事物来获得审美的超越与自由,所体现的是独特的审美神韵,“对时间、人生、生命、存在有很大的执着与肯定,不在来世或天堂去追求不朽,不朽(永恒)即在此变易不居的人世中”。同时,他的这种追求又在不停的“蜕变”与“追求”中,“奔向无穷”。可以说在冯至那“狭窄的心”中,有一个文化与生命的“大的宇
宙”,中国传统的审美体验方式让他摆脱了存在主义哲学思辨的玄奥与抽象,而存在主义的冷静与哲思让他脱离了浅层的情感缠绕而走向了生命的深度。
从《十四行集》的诗性思维和体验方式上来看,他一方面超越了中国传统诗歌的抒写情感的表现方式,有着“智慧的诗”的风度与探求精微哲理的理性;另一方面又依然有着东方神韵的底子,有着“体用不二”的哲学根底和禅悟的思维方式。这两者不是简单的调和,也不是一般所谓的取长补短,而是在诗歌主体充分理解与领会两者基础上的一种创造与超越,也只有在这样一种基础上才可以创造出这样一种“诗性的智慧”。
三
中国现代作家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上,都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一点众所周知,不过,在意识的不同层面上,受西方影响的程度是不同的。在思想观念的层面上,现代作家们在文本中往往有意识地反省甚至否定传统,而在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实则也为价值领域之一方面)的层面上,虽也有着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却更深地潜隐着传统的根脉,除了胡风、路翎、穆旦等少数人,确实相当程度地西化以外,几乎都深深地熏习着中国的传统,即使早年立意反叛,最后也总是某种程度地回归。他们在融合中西传统的审美创造中,往往呈现着与西方作家明显不同的风骨和神韵,这或许部分地根源于汉语本身所固有的特征,部分地根源于现代作家们所受的中国传统文学作品的熏染,从鲁迅、周作人,到沈从文、卞之琳,再到钱钟书、张爱玲,虽或有程度之异,却无不有着真正属于中国文化的独特审美趣味和风韵。冯至虽然属于在审美倾向上,也较大地受西方诗人影响的作家,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十四行集》与传统审美风韵相似或相通的地方,尤其和冯至当时所致力研究的杜诗风格有明显的关联。
在《十四行集》的艺术表现上,我们能体会到它的宁静和谐之美所表现出的传统情趣。中国文化与诗学向来以“和”为美,新文学虽然以反对平和中庸为务,张扬个性解放与强力意志,但是和谐之美依然是现代作家为之心仪的审美情趣。周作人的冲淡平和,徐志摩的温和明丽,废名的宁静淡远,沈从文的自然清新,卞之琳的圆润精致等,都可以看作中国传统追求和谐审美倾向在现代文化语境中的体现。冯至虽然以歌德、里尔克为典范,但其诗歌的内在意蕴既不是歌德式的在不断蜕变中寻求无限的探索意志,也不是里尔克那样在一种无法言说的神秘与晦涩中向着上帝与天国乞灵,他的诗,有沉思,有追问,也有疑惑,但更多的是经过理性沉淀过的澄明、清朗,如《原野的小路》,诗人的诗思由原野的小路,引向心灵的小路,再引起对一切与自己有过关涉的人事的怀念,深情以平淡出之,没有张扬,没有神秘,甚至也没有伤感,显现出澹定自如的风度。
在《十四行集》中,诗歌内部有着对生与死、形与神、瞬间与永恒、空虚与实在、有限与无限等等因素对立与冲突的表现,但创作主体并未将诗歌张力简单地建立在两者的冲突与矛盾之上,而是将两两对立的诸多因素融化在生命的“气象”中;不是以一种拒斥、敌对、征服的方式去面对,而是以一种生命的宽容与博大去承接与拥抱。情因事生、理由事发,智慧因此也就油然而生,却没有任何生硬之处。在《看这一队队驮马》中,诗人探究的是“虚无”与“实在”的矛盾,但作者却在一种通达中领悟到生命是在“随时占有”与“随时又放弃”的统一中拥有自己的意义和价值,没有消极和绝望,也没有焦灼与困惑,澄明与旷达的生命感悟让整首诗歌有着一种雍容的朗照。也正因如此,他的《十四行集》不奇肆、不怪诞、不抑郁沉重、不幽茫伤感,在中正淳朴中有一种通达宁静,明了朗悟的智慧。也正是这样的一种情调让他在芜杂浮躁的现代语境中造就了一种极为难得的“平淡和谐”之美。.
诗歌主情,但中国现代新诗尤其是早期白话诗,往往在表现情感时陷入两极而不能自律。要么情绪奔进而缺乏应有的含蓄与蕴藉,要么是简单直白而缺乏形象与情感的丰富。要追求诗歌的含蓄蕴藉,自然不能将心理情绪等同于审美情绪,更不能将诗歌简化为说教。冯至性情平和、气质内敛,早期创作的《我是一条小河》、《蛇》、《在郊原》等都呈现出含蓄幽婉的风格。《十四行集》中虽多了智性的沉思,但是整个诗集在情感的把握上依然是含而不露、隐而不显,情理相融,相辅相成。在第一首诗中,面临“彗星的出现,狂风乍起”,“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迹”,诗歌仅用“我们准备着深深地领受”,不峻急亦不森严,坚强的生命态度与沉着的生命意志在沉静平和中得到了形象的再现。面对文化先驱、历代伟人,诗人心怀崇敬与爱戴,但诗人并未让这种情感漫流与放纵,而是将这种情感建立在一种内在相通的生命体验的基础上,在“不卑不亢”中将自己的情感有节制地予以传达,形成了一种平和冲淡而又意味隽永之美。在《我们常常度过一个亲密的夜》中,虽是写诗人与自己的爱人“在一间生疏的房里”所拥有的一个“亲密的夜”,但是作者却是将这样的一种境遇具像化为原野、黄昏、道路所拥有的“同在”与“关联”,让激隋以浸润的方式予以弥漫式的扩散,但情感并未因此而稀薄,而是在一种体验式的传达中获得悠长的表现。这种情形在其它作品中也有着同样的表现,其情感把握的法度则显然是深合中国文学传统的蕴藉之致。显然,在这里诗人并不是一般的“以理节情”、或“情理相融”,而是把其情感对象化以后,再在冷处理的情形下将其纳入到先前的存在状态与诗歌主体的生命历程中进行审视与圆融。可以说,整个诗歌是在感性基础上生发,但在其凝定过程中又是理性向感性的靠拢与融合,这其中或许也有着里尔克、艾略特等人所谓“诗是经验”的观念的影响,但又与中国传统哲思的那种注重整体体认和直观把握的趋向有着内在关联,它为冯至接受上述诗歌理念提供了广阔的生发土壤,是一种“外启内发”、“兴来如答”的双向生成过程。
从具体的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艺术传承来看,《十四行集》与杜诗关系是相当明显而深厚的。在写《十四行集》的前一两年,冯至正致力于杜甫诗和陆游诗研究,深有心得,他后来总结杜甫的诗歌经验也即艺术上的三个特点,都适合于描述《十四行集》,这也足以证明《十四行集》对杜诗的继承。冯至总结杜诗的经验,第一是“稳”,杜甫所谓“赋诗新句稳”;第二是要求生动活泼,出语惊人。杜甫所谓“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第三是讲究诗律,所谓“晚节渐于诗律细”。
冯至的十四行诗,都有稳重的特点,没有险句和奇特的意象,但又能够自出新意,于平常事物中见出作者的新感悟,新哲思。《十四行集》中,诗人所用的语言都是平实自然的。这里没有输入的外来时髦语词,也没有源自传统诗歌中的典雅华美语汇,一切都是从日常生活中来,自然朴实,明了单纯,但在诗人允持厥中,澹定自如的审美风度下,生发出一种“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苏轼评陶诗语)的美,在最后一首《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中,诗人旨在表现自己的艺术原则与美学追求,是在思考如何借助有
限的诗歌,去把握和表现世界的无限和思想的丰富,是在探讨抽象的意义与具体实在的矛盾等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诗人并没有用抽象的词语,也不造生涩的句子,而是平平道来,“我们空空听过一夜风声,/空看了一天的草黄叶红,//向何处安排我们的思,想?/但愿这些诗象一面风旗/把住一些把不住的事体”。用语都从日常生活中得来,自然平淡,有如与人拉家常,但其内在的诗意却是隽永悠长,令人回味无穷,所蕴含的哲思又非中国传统所有。这种在平淡处见神奇、在单纯中见深邃的风格,深得杜诗神韵。
冯至在选择诗歌体裁时,由于时代的原因,虽然并没有直接选择中国古代诗体,却也没有采用“文学革命”以来成为主流的自由诗体,而是在西方的十四行诗这种与中国近体律诗最相近的诗体上找到了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冯至在《我和十四行诗的因缘》中说:“我渐渐感觉到十四行与一般的抒情诗不同,它自成一格,具有其他诗体不能代替的特点,它的结构大都是有起有落,有张有弛,有期待有回答,有前提有后果,有穿梭般的韵脚,有一定数目的音步,它便于作者把主观的生活体验升华为客观的理性,而理性里蕴蓄着深厚的感情。”可以说十四行这种诗体形式上的起承转合和融化经验的思维方式,颇像杜甫最为擅长的七律的结构规则和理性态度,冯至在对十四行起承转合的运用中,也恰恰学习了杜甫七律的经验。当然,这种选择不仅仅是所谓诗体的问题,同时也是诗人的审美经验和心理的问题。可以说,正是特定的审美经验和心理让他在表现情感时有一种貌似平和含蓄实则阔远闳深的生命气象。也正因此种气象,让诗人在表现形式上突破了闻一多、孙大雨在写作十四行诗时刻意追求整齐的诗形之似,也摆脱了新诗在诗体大解放后的毫无节制的做法,而是“尽量不让十四行传统的格律约束我的思想,而让我的思想能在十四行的结构里运转自如”,并且进行了调适。面对十四行诗内在结构上“起承转合”的要求与诗行排列上的固定程式,《十四行集》都进行了自我的创化。第2首,第3首、第5首、第9首、第19首、第27首等诗歌中都对其进行了调整与改造,如第5首《威尼斯》中,第1行到第4行是“起”,第5行至第11行为“承”,而“转”与“合”则融化在第12行至14行中了。诗人并没有“削足适履”,而是将其给予了灵活的转化。在冯至创化的十四行诗中,可以见到诗人在“起承转合”的内在安排上又特别喜欢将“转”与“合”紧黏,这与杜甫七律如《登高》、《登楼》、《秋兴八首》等名作在“转”时的强调顺势突变、另起境界,在“合”时蓄势敛合、余味悠长等方面都有着诸多相似陛。如在第23首中,写小狗将“领受光和暖”时写道:“……你们没有/记忆,但这一幕经验/会融入将来的吠声/你们在深夜吠出光明”,由“承”而“转”,紧接着“合”,但“合”中又自然圆融全诗,回味悠长,其安排更多的是一种内合传统律诗的结构法度。
纵观《十四行集》的27首诗,我们可以说因诗人的诗歌思维中智性与感性的融合,哲思与情感的互渗,形成了既澄明清朗而又沉着深婉的整体风格,这种风格确实得益于歌德、里尔克等人,但又似乎是盛唐气象和宋诗风骨的融会,是杜甫诗歌精神的现代创化——这种描述或许最符合于唐宋诗歌风格尤其于杜诗有所领悟的读者对冯至十四行诗的感受——因此,从纯粹审美风韵的角度来看,《十四行集》与传统也血脉相通。
责任编辑邢少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