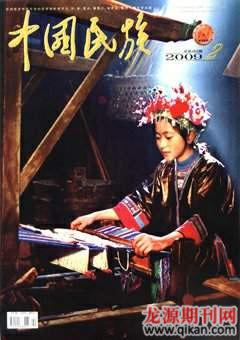壮乡边地
张邦兴
三月赶花街
算起来,以前我是没有真正赶过花街的。但是,由于生在壮乡长在壮乡的缘故,花街已然深深融入我的生命,多年来关于它的记忆日久弥深,挥之不去。去年春天有幸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县委、县人民政府之邀,回壮乡广南参加了2008年度的昆明国际旅游节广南分会场暨花街节开幕式,算是真正地赶了一趟花街,领略了一次花街风情,自觉这才不枉为一名壮族子弟,也了却了一桩多年未曾实现的心愿。

小时候,我的整个童年都是在壮乡度过的,那时虽然不谙世事,对花街风情浑然不觉。但每到花街,都要随大人一齐去凑热闹,图的是可以穿上一身平时舍不得穿的新衣去人多的地方显摆,在街上能够见到平时见不到的稀奇和古怪,更主要的是能够吃到一顿爽口的凉粉或滑溜的卷粉。
广南的花街从县城而那伦、由那伦而者兔、从者兔而珠琳,持续一个多星期,每个街场都不下万人。而富宁剥隘、皈朝一带的花街,则从古至今盛况连年,长盛不衰。当代人则干脆给壮乡花街,起了一个贴切、鲜亮而又浪漫、消魂的名字——“东方情人节”。
在壮乡,年年都有无数的青年男女,在花街场上将人生弥足珍贵的友情守望,年年都有无数的年轻人在这里收获了令人陶醉的爱情。待到“谷子黄侬人狂”的秋冬季节,就会有一双双一对对早春时节在花街场上结识的有情男女,在一片木叭喇声和鞭炮声中,牵手步入婚姻的殿堂。这样的交友、择偶方式,既保证了男女青年的自由恋爱,避免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带来的种种弊端,又有效地扩大了年轻人的交友圈和婚姻圈,保证了婚姻的质量、人脉的优化和族群的延续。壮族先民很早就懂得尊重婚姻自由,并结合壮族善歌的文化现象,以赶花街的方式,用歌传情,以歌为媒,世代传承,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促进族群的繁衍。遗憾的是,我这个壮家子弟,却因为还没有完全长成,就外出求学和谋职,竟然硬生生地与壮族花街擦肩而过,在自己的人生履历上,留下遗憾。
去年,广南花街节开街的那一天,自然又是一番热闹非凡的景象。一大早起来,整个县城就被装点一新,熙来攘往的人们都身着色彩艳丽的民族服装,脸上荡漾着节日的喜气,整个城市都笼罩在浓浓的节日气氛之中。从太平寨到马蹄井的街道上锣鼓喧天,人们弄(壮语:舞)着娅歪(壮语:母牛。这里指饰以牛形的舞蹈)、舞着彩扇、跳着手巾舞,一路踏歌而行,载歌载舞,抬着供品和花轿去接皇姑,沿途观者如堵。而在人群集中的莲湖边、马蹄井、皇姑庙等处,已有性急的男女青年搭起歌台,歌声此起彼伏。县政府门前宽阔的铜鼓广场上,来自全县各地的壮剧班都使出浑身解数,纷纷拿出看家绝活。县文化交流中心里,正在展出广南出土和民间传承的34面铜鼓。句町古乐团则在演奏有着古董身价的句町古乐……整个广南县城变成了歌舞的海洋。那天下午,我们看完铜鼓展和新近出土的东汉木椁墓,乘车从县文化交流中心出来,刚到莲湖公园门口,忽然一阵悦耳的歌声击中了我的耳鼓,定睛一看,灼人骄阳下,竟有好几群男女在众人的簇拥下,在那儿忘情对歌,此情此景是那么熟悉,那么亲切,一下子就唤醒了我封存已久的童年记忆,我急忙叫司机停车,在那驻足聆听。听着听着,不觉已经到了吃饭的时间,司机催了几次,我竟然都没有听见,看来,不仅唱的人醉了,听的人也醉了。
吃过晚饭,我们又去参加县里安排的一些活动,归来时夜已经深了,但湖边依然有歌声传来。不用说,今夜的广南,又是一个通宵达旦的歌场,那些歌手不眠不休,壮乡自然也不会入睡。推开宾馆的窗户,聆听湖边传来的悠扬歌声,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人类有情感真好,世界有歌声真好;生活有激情真好,日子有情歌真好!
广南春风暖芳魂
1652年(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南明小朝廷土崩瓦解。虽然适逢乱世,年景艰难,但在清军远还没有到达的极边之城广南,老百姓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年还是要好好过一过的。正月十六,浓浓的年味还没有完全散尽,一支衣着华丽但略显狼狈的队伍,在张献忠大西军部将的护送下,急急奔广南城而来,人数不下300人,虽在逃难途中仍排场不小,甚至还带着自己的戏班。他们便是由广西逃难到云南的南明永历帝朱由榔及其文武官员和仆从。在永历帝逃亡的队伍中,有一个貌美如花,然而却面带病容、弱不禁风的二八少女,她便是永历帝的胞妹安化郡主。

在长期受汉文化主体论影响的中原人心目中,那时的广南尚是“徼外荒服”之地,这里的人不是茹毛饮血,就是冥顽不化,他们讲鸟语、着兽皮,不通礼仪。哪料这里的土著却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创造了另一种文明,他们植水稻、纺棉纱、铸青铜、通贸易,早在秦、汉年间就建立了句町古国,以自己独到的生存智慧创造了一方富庶。因此,永历帝一行逃难至此以后,受到了优厚的礼待,他的胞妹安化郡主被安置在广南西郊的火烧寨。在这里,安化郡主得到了壮医的精心治疗,并时常与当地的壮族妇女纺纱织布、挑花绣朵、学唱山歌。
可是,就在安化郡主心情逐渐平复,病体有所好转的时候,永历帝经不住大西军将领李定国的劝说,再加上清兵大军压境被逼无奈,决定逃往贵州安龙避难。行前,由于安化郡主的病情尚未痊愈,永历帝决定把她留在广南,交由火烧寨的乡亲继续照顾和医治。且料,永历帝走了以后,难舍骨肉之情的安化郡主日夜思念皇兄,以至于食不甘味、夜难安寝,竟天天到位于城郊那浮村内的马蹄井旁,朝着其兄远去的方向,伫足北望,直至心力交瘁,病体难支,香消玉殒,于当年四月初死在马蹄井旁。可怜一缕芳魂,竟断在了与京都有万水千山之隔的极边之地。
火烧寨的壮族民众念及与皇姑相处的旧情,便来收殓皇姑遗体,移至寨后安葬。说来也神了,火烧寨之所以得名火烧寨,主要是因为年年被火烧,但自从安葬了皇姑后,便从此再无火灾了,因此,改名为太平寨。村民们感念皇姑的庇佑,便在皇姑坟前建庙祭祀,而且兴起了接皇姑的习俗。到现在整整356年来,每年的农历四月第一个寅日(皇姑安葬日),广南城郊的壮族群众便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抬着供品和花轿,到马蹄井迎请皇姑芳魂,送至太平寨的皇姑庙祭祀。当日,颂经祈福、对歌唱和、演出沙戏、交易物品,通宵达旦,举城同欢,热闹非凡。皇姑坟并皇姑庙竟发展成了历史文化名城广南的一个文化亮点和旅游景点,接皇姑活动也被打造成广南的一张文化名片。
去年5月13日,我受邀前去广南参加接皇姑活动,有机会一睹“接皇姑”的盛况,感触颇深,感慨良多。那天清早,我们一干人还在下榻的宾馆吃早餐,街上就已经人来人往地变得热闹起来,我们匆忙扒完碗中的卷粉,相约着往街上奔。到了街上,确实已经是一派熙来攘往的景象,人们大多身着节日盛装,结伴去往马蹄井或是太平寨的方向。接皇姑的仪式是从太平寨开始的,启程仪式不仅隆重,而且是整个活动不可或缺的部分和环节,同伴们跟着我这个并不称职的向导,竟然稀里糊涂地看漏了,也算是一个遗憾吧。
到得马蹄井,只见空地内、凉亭里、水井边、大道旁、石坎头、围墙外、房顶上到处都挤满了人。广南这个云南省第四人口大县的人气之旺,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站在路口,翘首等待迎接皇姑的队伍。突然,一阵锣鼓声传来,人们抬着花轿、抱着公鸡、挑着麻鸭、端着花糯饭和糯米粑,由两面令旗开路,接皇姑的队伍绵延了两三里长。缓缓行进的队伍里,有弄(壮语:跳、耍)娅歪(壮语:水母牛:这里指饰以牛形的舞蹈)的、有跳手巾舞的、有舞彩扇的、有耍棒棒灯的、有跳芦笙的、有纵弦子的……从服装上看,除了大多数着壮族侬、沙、土各大支系服装的以外,还有着苗族服装、彝族服装和当地汉族传统服装的,一派异彩纷呈。偌大一支队伍一路走来,一路载歌载舞,街道两旁,万人空巷,到处被围得水泄不通,众多摄像的、拍照的更是跑前跑后,忙得个不亦乐乎。接皇姑的队伍到了马蹄井,先落了花轿、摆了供品,然后布摩(壮语:神职人员)上香,口中念念有词。念罢,各村寨的代表也一一跪拜。
到了这一步,本以为仪式该结束了,但是旁边的当地人却说,一定要等到有蛐蛐、蚂蚱或是不拘之类的小动物跳入轿内,才表示皇姑的魂接到了,并且用来祭祀的公鸡要打鸣,才说明吉时已到,那时才能起轿回程。这就奇怪了,这里那么多人,闹哄哄的,真会有胆大的蛐蛐、蚂蚱敢穿过密实的人墙跳入轿内,而且公鸡也恰好会打鸣吗?我们都不相信。便决定等着看个究竟。约莫过了半个来小时,果真有一只蛐蛐跳入花轿内,虽然我没看见,但离得近的很多人都证实说看到了,恰好这时,原先一直沉默的公鸡也接二连三地打起鸣来。接皇姑的队伍又敲锣打鼓,载歌载舞,簇拥着花轿原路返回。
望着渐渐远去的接皇姑的庞大团队,我不禁在心里揣摸:这是一群多么善良的人啊!他们竟然为一个不相干的人,几百年不间断地祈福祷告,一直以不变的真情,温暖她那无所归依的一缕芳魂;这是一块多么文明多情的土地啊!这里的春风曾经温暖了漫长历史,并且依然温暖着今天。
原来,天下无处不春风,人心与人心原本是没有距离的,即便是在“徼外荒服”的极边之地也不例外。而真情酿就的春风,是一剂疗心的良药,有她,就没有一颗心会恒久地疼痛,有她,人们就能相扶相携着走向真正意义的和谐明天。
春天, 到剥隘去看水
还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十大标志性工程之一——百色水利枢纽工程竣工蓄水之前,我就想通过广播把工程的建设情况和工程效益,以及蓄水量达60多亿立方米的这片高原平湖告诉世人,为即将被淹没于水底的千年古镇——剥隘,留下点什么。但是,终因种种原因,没能实现。
去年春深似海的时候,终于有机会又一次来到我魂牵梦萦的剥隘,走近了那片令人神往的剥隘水。但是到了那儿给我的第一印像,是一种物去人非的感觉。好在作为剥隘灵魂的那片水还在,而且较之以前变得更开阔、更壮观、更深邃了。原来的一线江流,已经完全被淹没在一片湛蓝的湖泊之中。但是,一个地方不管如何变迁,只要它的灵魂还在,它就永远也不会丢失。
沿着新剥隘码头长长的水泥台阶拾级而下,那片已然是高原平湖,汪洋恣肆的水便扑面而来。这片水,曾经是这样熟悉,又是那样地陌生。熟悉,是因为它依然由驮娘江、谷拉河、那马河汇集而成,它们各自从自己的故乡奔腾而来,在老剥隘交汇成蔚为大观的右江。由此顺江而下,便有了右江沿岸的沃野千里,而千年剥隘就位居在这千里沃野的最顶端。守着这个状如牛弯担的口子,成了千百年来云南通往广东、广西和两广及其他沿海省区进入大西南的要津,拥有了“滇粤津关”的美誉。守着这个口子,剥隘如一个沉静的女子,坐在自己家门前的石阶上,把挽了裤腿的双脚伸进江流,一边晃荡着脚丫,一边以一双传情的美目,看千帆竞渡、看百舸争流、看江流远逝、看岁月老去,直看得青苔爬满了自己的皱纹。说它陌生,是因为在百色水利枢纽工程建成蓄水以后,它的水面已经宽阔了不止十倍,水的最深处竟有180多米,原来浅而窄的江流已经被一片汪洋所取代。由剥隘到广西百色市郊的右江河段,也已经变得像一个大湖泊,不仅湖面宽阔,而且更有气势了,过去只能行些小木船的江面,现在已经具备了进出五百吨级大船的吞吐能力。如果单纯从这个角度看,因为淹没而搬到更高处的剥隘,拥有的是一个男子的伟岸,换了一个更高的角度,自信地看着脚下的江流、看着远方的世界,露出一种伟丈夫的博大胸襟。
说话间,负责运送我们的“富州一号”就要出发了,大家都迫切地想要融入这蓝天碧水间,做一次物我两忘的神游。船在水中行,人从景里过。游船一离岸,我们就被水中和两岸的景色给彻底迷住了,稍不留神,我们和游船竟在不知不觉间成了湖区里的一处截然分不开的风景。为了更清楚地看两岸的景色,感受迎面扑来的风,看清幽深发蓝的水体和被船犁得翻滚的波浪,我爽性离开船舱里舒适的座位,站到了船尾的舷杆旁。举目望去,前面是看不到尽头的、越来越宽阔的水面,后面是不断被犁起的、晶莹洁白的浪花;我们的侧边不时有船驶过,多是一些只能载二、三十人的铁皮船,每遇我们所乘的庞然大物,它们都绕得远远的,巧妙而小心地让过我们这艘船掀起的波浪。
千百年来,古老的剥隘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见证了太多的风和雨,见证了太多的兴衰与沉浮。而今,它不仅把自己作为一段悬念,沉到了深深的江底,让现实和未来用尽想象去解读;而且像一只巨大的乳房,悬在右江的上游,给下游的田地以丰沛的浇灌、给下游的工厂以充足的电能、给下游的生灵以生命的滋润、给下游的年景以丰收的保障;还像一个巨大的平台,通过航运的水道,让高峻的大山和浩瀚的大海在这里会晤,实现它们企盼已久的历史性对话,它们呼喊着彼此的乳名,把手伸给对方,牵手走向未来。
剥隘是个典型的壮乡,以稻作文明饮誉于天下的壮族人引水造田、以田植稻、以稻裹腹,并把自己的这一伟大发现和发明传播到全世界,现今地球有128个国家种植水稻,使得现今的人类有近30亿人赖稻米为食。因此,在很多地方都有“壮族占水头”、“水做的壮乡”之说,而90%以上的壮族人口都生活在剥隘。感谢历史,曾经给了剥隘那么一片水!感谢现实,又给了剥隘更大的一片水!这水,不仅是剥隘的景,更是剥隘的魂!
好在,有春天,有水,希望就会成长,生命就会葳蕤。在回程的路上,我看到好多人已经在引水灌田。剥隘,你已经怀揣种子,和春天一道并肩站在希望的田头了吧?抑或是你的第一把种子,已经和春风一道播进了你春梦一般绚丽的憧憬里了?
阅读坡芽
大前年春天,偶然听说,富宁县剥隘镇的坡芽村的壮族妇女用一套特殊的符号记录民歌并世代传唱。之后,关于这种奇特民族文化的报道接连不断,也相继有多个专家组和研究人员前来实地考察。经研究得出:“这套符号形固定、音固定、意固定,基本具备了文字性质。是云南省民族文化遗产中可以与东巴文化交相辉映的宝贵资源,是我国活着的图画文字之一。它的发现,填补了壮族没有古老文字的空白。”并正式将这套符号命名为“中国富宁坡芽歌书”。
好奇是人心使然,对于未知领域的探索是人永远的兴趣。于是我便找了一个机会,奔坡芽而去。途中,由于对心中圣地的朝圣和对未知文化的好奇让我完全忘记了山的险峻和路的崎岖,心中充满了肃穆和敬意,甚至还有几分诚惶诚恐。
汽车在林间下了几道坡又上了几道坡,把我们送上了一处绿树掩映、竹林婆娑的半山腰。蓦然,一座设计独特的寨门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这是一道类似汉字的“人”字在上,“开”字在下,两个字又组合成一个整体的寨门。进了寨门,映入眼帘的便是神往已久的坡芽。一个黄墙碧瓦、有着明显壮家干栏式木楼风格的村寨呈现在眼前一个绿树掩映的山凹处。进得寨来,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位于寨前一片空旷平地上的老人亭。我们到的时候,只有几个村人闲散地坐在亭内乘凉,显得随意而休闲。但是,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老人亭里,我们却有了惊奇的发现,那就是成串地挂在亭里的数以百计的野猪下颌骨。细细问了那几个村人,才得知这是坡芽人从古时候起,猎食野猪后特意留下来占卜用的,它是村里人卜问天气、年景、出猎和其他大小事情吉凶的专用工具。而这样的卜问方法,在其他的壮族村寨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早在汉代,壮族的祖先就以鸡卜闻名天下。经村中布摩(壮语:宗教职业者)的演示和指点,竟觉得这种卜问方式,与看鸡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至此,我才恍然悟到,这个古老的村寨承传的卜问方式是狩猎文化的遗存,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种比看鸡卦还古老得多的文化现象。但是坡芽人靠什么继承了如此遥远的智慧,并且让它作为一种活态文化,至今仍为人们所用,这确实有着经得住事实不断检验的玄机!
这样的发现,让我对坡芽更加着迷了!神秘的坡芽,你让我用什么方式来解读你?带着疑问我们顺着一条以石块镶嵌的洁净村道,爬上了位于老人亭上方的《坡芽歌书》传习馆。这是一座依山而建的新近刚刚落成的建筑,同样是典型的干栏式结构,分上下两层,走进房里,但见正堂悬挂着壮族女始祖乜六甲的巨幅画像,靠前厅的两侧,置有(卜少)的闺房和织布房,而房里的其他各处,则有序地摆放着鱼网、篾箩、纺车、掼斗、牛角号等生产生活用具。最让我感到新奇的是,在房里竟然发现了一块用竹篾与笋壳扎成的类似于蓑衣的遮雨工具。不用说,这又是聪明绝顶的坡芽人,在劳动中就地取材的发明创造。看来,从古至今,坡芽人历来是一个善于发现和创造的群体,他们从自己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从大自然的恩赐中,取来各种各样的材料,运用自己的智慧,发明和创造了各种有益于群体生存发展的工具,从而使得自己的族群能够在这深山之中顽强地繁衍生息。
正当我们沉迷于传习馆的种种物件时,屋外已经聚集了许多闻讯而来的乡亲,其中就有作为《坡芽歌书》传承人,在外界大名鼎鼎的农凤妹和农丽英。于是,我们便提出要她们当场演示《坡芽歌书》。一开始她们还有些扭捏,但在我们的一再要求下,便在门前的篾桌旁坐了下来,掏出带在身上的一块折叠得十分整齐的土布,展铺在篾桌上。但见那布片上画着许多紫红色的符号,有的是一弯月牙、有的是一堆石子、有的是几棵竹笋、有的是几片枫叶、有的是一件衣裳、有的是一把斧头……都是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东西。据资料显示,《坡芽歌书》壮语记音为《布瓦吩》,意为“把花纹图案画在土布上的山歌”,它一共用81个图形符号记录了81首壮族情歌,以叙事和抒情的手法,描写了一对青年男女由偶遇到相识,从相互倾慕到相恋、相知,最后相约白头、誓同生死的全过程。可是,当我有缘直接面对歌书的时候,却什么也看不懂。于是,只好信手点去,让农凤妹和农丽英先唱以一弯月牙来记录的第一首歌。但却迟迟不见她俩开口唱,经催促,她俩才说第一、二首是该男人唱的。就在我为自己的冒失和无知而脸红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两个男人已经唱道:
“今晚月皎洁∕皎洁如明镜∕照彻四方天∕白得像油浸∕趁着月色好∕约月亮出行∕月亮若有意∕听我诉心情∕若得遇知音∕像水恋坝塘∕像牛恋草坪∕月亮若无意∕忧愁又伤心∕月光虽然好∕对我不公平∕照亮他人面∕不照我的心∕天高月亮冷∕欺我不如人。”
多亏了两位及时解围的男歌手,让我避免了一场尴尬和窘迫,所以,他们才一唱罢,我又指了以一幅半身人像记录的第三首,才一指定,农凤妹和农丽英的歌已经脱口而出:
“哪个站那边∕是竹还是树∕美如荔枝花∕亮似太阳出∕若是愣头青∕我用歌拦路∕若是成年人∕尽管把情抒∕卯时哥出门∕辰时妹上路∕相约在天涯∕同栽麻栎树∕以歌对生辰∕共把真情诉。”
歌声惹得人心醉。之后,我们又接连点了几首,男女歌手均如流唱答。那甜美的歌声让人如饮琼浆、如嚼甘饴,使人的心旌禁不住随歌意的延伸起起伏伏,难以平复。我们进寨时所见的用来做寨门造型的那个符号,在歌书里也有记载。
唱到最后,歌声已是如泣如诉,唱得山也动容水也悲情;唱得我们一群人都忘了挪动脚步。歌里所表达的那种誓同生死的真情,强烈地震撼着我们在场的每个人的心。直至天色向晚,我们才十分不舍地告别出村。走一路,那歌声就随一路,仿佛我们人已经出来了,而双耳和一颗心却留在了坡芽,仍痴迷地聆听着那里永远的歌声,依旧忘情解读着那里神秘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