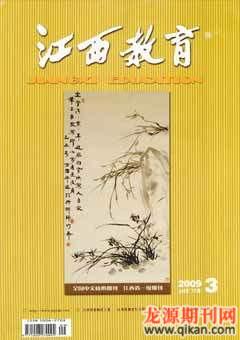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儒家音乐心理思想研究
杨 婷 张义瑶 何永峰
人类的任何实践活动包括音乐活动,都是在人的心理的调节下完成的。科学理解音乐与各种心理现象的关系及发生规律,有助于人们改进音乐的学习方法;有助于利用音乐发展积极的个性品质,克服消极的个性品质;有助于用音乐调节自己的不良情绪,保证身心健康;而且音乐还能影响人们的社会行为,祥和愉快的音乐有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一、音乐与个体心理
1.“乐”与需要
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需要的产生是有机体内部生理上或心理上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一旦这一状态消除了,需要也就得到了满足。这时,有机体内部又会产生新的某种缺乏或不平衡状态,产生新的需要。音乐首先是满足入耳的需要。《荀子·礼论》曰:“钟、鼓、管、磬、琴、瑟、竽、笙,所以养耳也。”;《吕氏春秋·孝行览》曰:“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人类在满足了简单的生理需要后,进而产生了更高级的需要,如《易传·象上》曰:“先王以作乐崇德”用音乐来歌颂王者的功德,以满足王者虚荣心的需要。还有董仲舒(公元前179—104,汉代新儒学思想家)在《贤良对策》中也说“王者未作乐时,乃用先王之乐宜于世者,而以深入教化于民。……故王者功成作乐,乐其德也。”意思是王者根据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需要,选择“宜于世者”的“先王之乐”“教化于民”,而当“王者功成”时,又用音乐来“乐其德也”。先哲们不仅认识到需要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而且还已认识到高级需要对低级需要的调节控制作用。如《吕氏春秋·侈乐》中说:“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其含义是耳朵的本能是要求听声音,心情不快乐时,各种音乐就在身边也不想听。
2.“乐”与情感
古代儒学思想家认为,人皆有七情,即“喜、怒、哀、惧、爱、恶、欲”,而音乐就是这些情绪变化的表现形式。《荀子·乐论》曰:“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意思也是“乐”所表现的是人的感情。
儒家学者有诸多文字论及情感对音乐的影响。《乐记·乐本》曰:“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这段话说明由于主体哀、乐、喜、怒、敬、爱等不同情感,而使得表现出来的音乐也不同,或慷慨悲歌,或低吟慢奏。2000年前,古代思想家们提出的情绪影响音乐的理论,到了现代不论是音乐家还是心理学家都是认同的。儒家学者不仅论述了情感对音乐的影响,还精辟地论述了音乐对情感的影响。例如,《荀子·乐论》中说:“故齐衰之服、哭泣之声使人之心悲;带甲婴胄、歌于行伍使人心伤;姚冶之容、郑卫之音使人之心淫;绅端章甫、舞《韶》歌《武》使人之心庄。”意思是指丧礼的装束、哭泣的声音使人们的心情悲痛;军人的装束、嘹亮的军歌使人心情振奋;妖娆艳丽的打扮、郑国和卫国的音乐使人心情放荡;庄重的仪表、舞起《韶》和《武》,使人心情庄严。
3.“乐”与意志
从事心理学研究的人都知道,情感与意志这两种心理过程是不能分割的。古代圣贤们也从音乐与情感的关系,进而谈到了音乐与意志的关系,用现代心理学的观点来分析这是合理的。儒学思想家认为,音乐是影响意志的,高雅的音乐强化人的意志,而低级的音乐往往腐蚀人的意志,前者如雅颂之声,后者如郑卫之音。荀子认为“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荀子·乐论》),在此基础上,《吕氏春秋》和《乐记》的作者进一步指出“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太小则志嫌……太清则志危……太浊则志下”(《吕氏春秋·侈乐》);“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乐记·魏文侯》)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思想家们已经认识到音乐能影响人的意志,这是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的重要发现。音乐家在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过程中都会有这样的体会,音乐能激励意志也能使意志消沉。
4.“乐”与性格
在国外的心理学文献中,“性格(Character)”一词源于希腊语,意为雕刻或戳记的痕迹。这个概念强调个人的典型行为表现和外部条件决定的行为。我国心理学界倾向于把性格定义为个人对现实的稳定的态度和习惯化了的行为方式。如果是一个音乐家,他的性格便会表现在他的乐曲创作和音乐表演上。孔子认为君子好“雅乐”,小人好“淫声”,因为君子性格坦荡正直,故好“雅颂之声”;而小人性格自私扭曲,故乐“郑卫之音”。《乐记》把这一思想更加具体化、理论化。在《乐记·师乙》篇中说:“子贡见师乙而问焉,曰:‘赐闻声歌各有所宜也。如赐者,宜何歌也?师乙曰:‘乙贱工也,何足以问所宜。请诵其所闻,而吾子自执焉。宽而静、柔而正者宜歌《颂》;广大而静、疏达而信者宜歌《大雅》;恭俭而好礼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静、廉而谦者宜歌《风》;肆直而慈爱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断者宜歌《齐》。”从子贡与师乙谈话的内容就可知道他们谈的是性格与音乐的关系。先哲能在当时提出性格和音乐艺术的关系这一心理学观点,就已经很有研究价值了。音乐能培养人的性格这一可贵的音乐心理学思想,对于当前音乐教育有重大实践意义。
二、音乐与社会心理
1.音乐反映现实社会
古代儒家学者不仅论述了音乐与个体心理的关系,还论到了音乐与社会心理的关系。《吕氏春秋·侈乐》中说:“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乐记·乐本》篇中也有记载:“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两段话的文字很相似,意思是说:通过音乐可以了解国民心态,透过国民心态则可以了解国家政治是廉洁还是腐败,是昌盛还是衰退。这正与社会心理表现在社会行为中的现代社会心理学观点相近,也体现了古代儒家学者的真知卓见。
2.音乐影响社会行为
《荀子·乐论》篇曰:“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荀子认为音乐这类事物,是圣人所喜欢的。它可以改善人们的精神面貌,用它感化人十分深入,用它改变社会的风俗习惯也很容易。《吕氏春秋·侈乐》中也有记载:“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意思是大凡音乐都相通于政治,优化风俗,民风稳定是音乐对它起的作用。
3.音乐与个体心理、社会心理的关系
它们紧密联系,互有影响。人是社会的产物,音乐文化使人类的心理和行为具有共通性,通过和谐的音乐可以消除不同阶级、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人群之间的差异。《乐记·乐化》就曰:“是故,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用来说明这一观点。同时,音乐行为又主要表现为群体行为。音乐家花费大量的时间闭门作曲和练习,其最终目的是与他人共同分享他们的创作成果。《孟子·梁惠王》中记载:“孟子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封建社会儒家学者就能提出“与民同乐”这种思想真是难能可贵。这对现代社会多元化文化,对现代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影响的研究是很有借鉴价值的。
三、音乐与心理健康
现代心理学认为,情绪(情感)的压抑,往往形成“情结”,“情结”得不到解决,就会造成心理异常。早在几千年前荀子就提出“夫民有好恶之情而无喜怒之应,则乱” ,认为人有“喜、怒、哀、惧、爱、恶、欲”七情,如果这七情得不到正常的渲导,人就会心理异常,导致混乱。在此之前的《国语·周语下》中记载:“夫乐不过以听耳……若听乐而震……患莫甚焉。夫耳目,心之枢机也,故必听和而视正。……若视听不和而有震眩,则味入不精,不精则气佚,气佚则不和。于是乎有狂悖之言,有眩惑之明,有转易之名,有过慝之度。”这论述了音乐平和与否必然影响人的元气,进而影响人的精神状态,以至胡言乱语,思想混乱、恶念丛生。《吕氏春秋·本生》云:“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此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其观点就是“五者”(衣、食、住、行、乐)只要能使心情愉快就可以了,凡事不可太骄奢浪费,要多注意节制,这是“圣王”的养生之道。这些观点都为现代音乐治疗学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祥和平静的音乐能使人心智澄明,柔和抒情的音乐能舒解人们内心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总之,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由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从《论语》到《乐记》,有着丰富的音乐心理思想,为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提供了宝贵的理论依据。本文发现古代儒家学者早已认识到通过音乐教育,利用音乐的感染力培养学生的美感和道德情感,进而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坚强的意志、良好的性格和文明习惯,这些都是具有实践意义的美育心理学观点,丰富了现代音乐教育心理学知识,有利于提高当前音乐教育的效果。瞻望未来,我国古代音乐心理学思想的研究工作,必将出现一个更加广泛深入、系统全面的局面。◆(作者单位:华东交通大学艺术学院)
□责任编辑:方 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