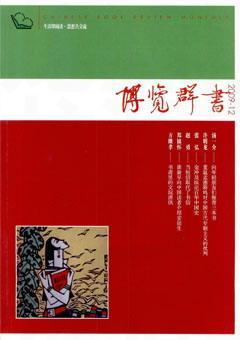文艺学的反思需回到原初起点
杜晓杰
进入一个新的纪元,学术研究该走向何处?在人类发展的长河中,又该如何为上一百年的学术研究定位?目前整个学界都弥漫着反思和重评的氛围。而文艺学学科经过近百年的坎坷浮沉,确实也累积了大量需要整理的问题。因此近几年出版了大量再年文艺学反思的学术著作。这既是学人回望历史的冲动与激情,也是新世纪文学理论研究的起点。
暨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傅莹撰写的《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史》(以下简称《发生史》),聚焦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现代文艺学理论的发生、发展和演化,重新梳理了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并反思和剖析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以探求其未来发展的方向。
文化诗学:广阔的学术视野
随着西方文化理论引入中国,文艺学内部出现了两种研究路径:一种是力图打破传统的文艺学研究界限,将纷繁复杂的文化现象纳入文艺学的研究体系,用文化研究取代文艺学研究;另一种则是文化诗学的研究路径,把文化研究的方法引入文艺学,在广阔的文化、社会背景中,重新定位和思考文艺现象。《发生史》正是后一种方法在学术史撰写方面的尝试。
它首先着力于还原历史文化语境,回到学科发生的原点,重新梳理学科发生的历史。《发生史》别出心裁,摆脱名家史、观念史或思潮史的写作方式,将其置于教育学制、编辑出版、外来文论影响的宏阔背景中,以较为开阔的视野来把握相关观念、范畴、话语与理论的嬗变,从而丰富了学术史的书写与言说方式。
中国近代的改良主义思潮不仅为政治体制的革故鼎新提供了思想依据,也为文学更生提供了新的模式;白话文运动为现代文论的发生准备了语体和思想资源,同时也向文论话语的重构发出了呼吁;近、现代教育制度的变革与发展,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权力场所与制度依托;翻译事业的兴盛,使得大批西方前沿文学理论著作进入中国学人的阅读视野,为中国本土现代文学理论的创立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源;新文化运动更是以摧枯拉朽的伟力,实现了文化范式的转变,加速了传统文论向现代文论的转化——正是这种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共同运作所产生的合力,最终将中国文论推上了现代化的进程。独特文化背景的勾勒,既深化了著作的历史维度,也真实呈现了现代文艺学发生发展的原初状态,使读者能一睹现代文学理论的初始面目,明了其发生背后复杂的文化纠结。
其次,《发生史》从跨学科的角度,详述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生成的多重语境。
由于体悟型的古典文论话语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所以传统文学的现代转换,尤其是语体和思想内容的变革,客观上要求生成一种全新的文学评价体系。作者通过史料的钩沉,勾画了现代文艺学学科化、体制化的进程:壬寅一癸卯学制的初具学科意识,壬子一癸丑学制的学科范式的确立,壬戌学制文学理论现代话语转换的最终完成,这样现代文学理论学科的发展进程便明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由于现代文学理论是伴随着教育体制的发展而来的,因此其话语与理论的衍生、变迁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规约,文学理论既与现实脱节,也未能在形而上的层面生长,创新能力逐渐丧失。可以说,高等教育制度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影响具有双重特性:教育制度推动了文学理论学科和学术话语的独立进程;却也使之在新八股式的体制中逐步失去了活力,沦为意识形态的附庸。
文学及其理论的翻译,打开了借鉴西方的窗户,为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提供了思想资源与学科范型。《发生史》梳理了当时翻译界关于日本、欧美、苏俄几种文学理论范式的译介情形,追溯了这些理论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建构的影响,抽绎出“长袍马褂模式”、“西装革履模式”、“普罗列塔利亚模式”三种本土文论的发生形态,剖析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对于外来资源的扬弃。正如作者所言:“旧中国的教育,从借鉴日本开始,到全面译介美国、欧洲的模式,及至再模仿前苏联,无论学制、内容和方法,都深受外来因素影响。即便是具有本土特色的文学基本理论著作,其思维模式、学术体例、言说方式,都已经深深打上了外来文论的烙印。翻译介绍和照葫芦画瓢的模仿,一刻也未停止过,即便建国之后也如此。”对于传统文论的放弃和对西方范式的紧随,逐渐演绎成当今文艺学学科的失语,所以我们必须回到历史的源头去找寻它产生的原因。
新文化的传播必须有稳定的传播媒介才能产生社会性的影响,而出版事业的繁荣为文学理论教材和普及读本的编撰提供了传播途径,这就使得现代文学理论学科有了媒介的支持,从而可以更广泛地改变人们的文学观念。作者指出,20世纪20年代中国出版业出现了出版文学理论著作的热潮,从翻译介绍到本土编撰文学理论教材和知识读本,使得新的文学理论话语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这是通过从上述文学、教育、翻译、出版等多个学科历史材料的交集中,作者条分缕析出文学理论发生的原初状态,阐明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发生的真实样貌。从作者书后附录的大量参考文献中,我们也可见作者做学术之勤勉。
新意迭出:扎实的学术涵养
《发生史》以其独特的视角丰富了文艺学学术史的书写和言说方式,显示了作者扎实的学术涵养。
第一,回到原点的历史理性主义。文艺学学科危机在“文学消亡论”、“文论失语症”、“文艺学边界游移”等问题的公开探讨中时常突显,因此要实现当下文艺学研究的突围,就必须从根本上剖析文艺学危机的根源所在。诚如《发生史》作者所言:“让我们从零点开始,寻找我们的理论之源与精神之根。而且,那些历史的神秘与学科的偏谬也会浮现出来。”《发生史》认为文艺学当今的危机决非“一日之寒”,它在发生之初就已埋下了隐患。作者认为,文艺学学科的发生与社会变革时的政治思潮和运作紧密相联,这就使得文艺学先天具有意识形态气质。所以文学理论不仅仅是在传播新的文学批评观念,而且同时在布道新文化、新思想。它所具有的功能性与西方对文学进行科学研究的主旨一开始就发生了背离。更致命的是,现代文学理论的学科建构从一开始就以与中国传统诗文评论断裂的姿态出现,或取法日本,或照搬欧美,或臣服于俄苏文学理论,完全套用它们的话语理论进行学科建设,因而必然会遭遇“失语”困境。
第二,对厚重的历史资料进行梳理。当方法的翻新出奇,使研究对象的阐释变得不具有恒定性的时候,脚踏实地的搜罗原始资料便更加难能可贵。《发生史》如著者所述:“原始资料的查证数量之大,难度之高,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其中艰辛,冷暖自知。”作者大量阅读了上世纪20年以来出版的文学理论书籍,详细分析的文论文本达8种,引证教材近20种,书后所附录的“文学理论教材目录”、“译介到中国的代表性文学理论著作”书目总计有百余种,正是在较全面地掌握了现代文论建设过程中的
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才使得他对学术历史的阐述有着坚实的材料支撑。其中许多材料系首次系统研究和阐述,这样一方面还原了文艺学发生的历史原貌,另一方面也为文艺学的深入研究开启了新视域。
为了揭示文艺学在现代教育体制内部的生存状况,作者详细查阅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暨南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高校的史料档案,对于文学理论的课程设置、教师队伍、教学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转录,并由课时设置、教学内容和师资队伍的变迁等资料中,侧证了文艺学观念和社会文化心态的转变,由此勾勒出从传统诗文评论到现代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过程。这种方式的学术研究以往很少有人进行,所以《发生史》不仅还原了历史面貌,更从中发掘出攸关文艺学自身发展的新意义,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阐发了富有创见性的学术观点。
第三,以文学概论教材作为学术研究的切入点。在文艺学的反思著作中,大多数是文艺学学术史、文艺学史、文艺思想史。这些著作虽然也论述周密、见地深刻并勾画了文艺学的百年历程,但总体上来说,一方面游离了文艺学的核心阵地——教材建设,另一方面也缺乏对于文艺学学科的全方位把握。《发生史》由于选择了巧妙的切入点,就避免了上述这两种缺失。
现代文艺学的发生发展,离不开教育体制的制度保障。与新文学不同,现代文艺学思想的传布一直依赖于教育系统,教育的使命促使现代文学理论形成了以教材为中心的辐射圈和话语建构体系。正如作者所言:“中国现代学术建制过程中,学制的颁布更多为原则性指导,而课程设置、教材编纂和新知识范型的确立,则具有实质的推进意义。”教材的编纂不仅仅是知识体系的建立,还牵涉到整个文艺学学科的建构,包括知识范型、学科归属、教学设置等等,这些因素围绕着文学概论教材形成学科的力量场域,构成学科的严密体系。所以,单从思想史的方面切入百年文艺学的反思,不管怎样编织理论话语,都显得偏颇和狭隘,而从文学概论教材切入则可以达到窥一斑而知全豹的效果。以文学概论教材为中心,其实就是一种学科史的研究,既包含文论思想的演变,又有学科发展的清晰脉络;既有学术的迁移,又有体制话语的转型;既涵盖了文艺学的方方面面,又旁及教育学,可以在突显文艺学学科演变过程的同时,一览教育现代化的进程,达到在总体上把握文艺学百年积淀的效果。
历史与言说的缺憾
任何学术著作都不可能是完美的,瑕疵是不可避免的。《发生史》在对材料的驾驭上也仍有遗珠之憾。首先,《发生史》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生成、发展轨迹做了详细的描画,关节点也给予了充分的重视。但定型之后的学科及学术体系究竟是什么样的?这本书则缺乏总结性的概述。其次,该著作一大亮点是原始资料的挖掘整理,但在学术意义与价值的分析上则欠细致。再次,外来文化固然提供了中国现代文学理论转型的直接资源,但本土自身的接受和消融土壤也不容忽视,而这本书对如晚明以降文学新变的因素便未能涉及。
回顾历史,并非要沉醉于历史的昏黄意蕴;回到起点,也不是要高扬历史循环论或者文化复古主义的旗帜。历史是走向未来的参照,是学科规划与发展的镜鉴。回到历史的原点,就是要开拓出新的学术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