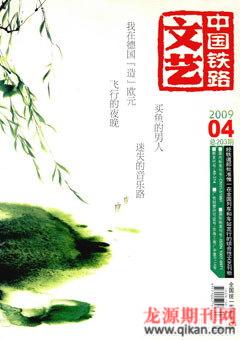渔鼓声声里
肖景儿
当夜幕降下所有的黑,男人们就着暮色中幽蓝的光线收拾粗细家伙,拖着疲惫的身子纷纷回到家中,这时,女人则将已预备好了的晚饭端上饭桌。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王家村大多数农家餐桌的内容基本一致:一大盘红薯,两三碟咸榨菜,每人手里一碗荞麦或玉米粥。家境宽裕的男人隔三差五需要一小杯米酒来填补心思,一盅下肚,迷迷瞪瞪,待到女人收拾完余下的家务活,便搂抱了女人,捻灯睡去。
在远处的狗吠声渐渐平息后,乡村便都归寂于静,耳旁除了男人的鼾声,便是墙角、阴沟、树权间、田野里隐隐约约的虫鸣。只是王家村有个例外,每个月圆的晚上,倘若你睡眠浅些,心思再细腻一点,便可听见从村西口的那间木板房内,传来凄婉的渔鼓声。那种凄婉,哀怨悠长,划过夜空,直抵达人的心坎。倘若你任凭心思跟了那调子婉转而去,定会勾出你许多泪水。
油菜花,金灿灿,
今日个夜(ya)里把妹念
未开言,泪涟涟。
思绪千千万。
柔肠寸寸断
……
王家村的人都知道,唱歌的是曾家二叔,一个拒绝所有媒婆上门提亲的单身汉。我离开故乡已经整整二十八年了,曾家二叔的模样在我的记忆中已经非常模糊了。然而,他那凄婉的渔鼓声,一直萦绕在心头,惹得我生命沿途的忧伤马不停蹄,反反复复。
我与妹妹难成对呀,我冒得钱财,你爷(ya)娘何该会(怎么会)将你配
我与妹妹难成双呀,我冒得房子,你爷(ya)娘只把我往屋外面赶
我与妹妹难成婚呀,你爷(ya)娘狠心拆散鸳鸯两地分
……
记忆中的许多月圆之夜,总是那样伴一腔哀怨的渔鼓,在奶奶沉重的叹息中度过。曾家二叔口中的妹妹叫胡七妹。按辈分。我应该叫她姑姑,虽然不是本家,但同是一村人,多少有点沾亲带故,所以,平日里,我们唤她为“七姑”。七姑的母亲,我叫她“二奶奶”。听村里的奶奶们说过,“二奶奶”好吃懒做,出了名的嫌贫爱富。
七姑是个瘦小且沉默寡言的姑娘。农家女孩长得黑,偏又贫穷,七姑那瘦小的身子终日被套在宽大的青衣粗布里,经常辛劳于田间活计,尘土满面。听小姑姑说过,七姑仅仅那么一件没补丁的衣服,还是她们一起上山挖山药挣下来的钱买的。不过,七姑有双丹凤眼,长长的睫毛又浓又密。我的记忆里,七姑的笑容灿烂得跟阳光一样明媚。
曾家两兄弟无父无母,曾二叔跟着哥哥相依为命,两兄弟都生得浓眉阔口,白白净净。那时候的我,不过是五、六岁的小姑娘,不会评价也不会欣赏男孩的英俊与丑陋,只知道曾家两位叔叔的模样逗人喜爱,又加上平日里最喜欢听曾二叔吊上一段渔鼓调,因此更觉曾二叔比别人亲切些。然而,令我惑解的是,曾二叔那双幽幽的眸子中总藏着无限的忧愁,那痴痴的神情里,总流露着无尽的惆怅。渔鼓的唱腔本来就是张口便有,词的编排没有严格的章法,也许是因为曾二叔的歌声中揉进了那些哀怨缠绵的情调,才格外动人心弦。
记得那是个星期天的下午,乘着大人们各自忙碌,我们一群孩子玩捉迷藏。玩伴冬梅悄悄地告诉我,公家牛棚的顶上堆了许多新收的稻草,是个躲藏的好地方,我便跟在冬梅的后面悄悄地爬上了牛棚里新搭建的草架。为了藏得隐秘一些,我俩一块儿缩在一个狭小的角落里,我瘦些,蹲在里面,无法看见外面发生的事,只得用耳朵去捉摸各种声音。不一会儿,就听见有脚步声进了牛棚,窸窸窣窣。起先,我认为是找我们的伙伴,于是赶紧平心静气,片刻之后,感觉不对劲,因为除了有奇怪的急促喘息声,还伴着很轻很轻的呼唤声,极度压抑,听不很真切。同时,紧挨着我的冬梅全身跟筛糠一样颤抖,她的右手开始使劲抓住我胳膊,直到抓得我生痛。最后,我在无法忍耐的情况下,奋力一挣,硬生生地把冬梅从牛棚的架空顶上挤了下去。也就是那一刻,我清晰地看见两个全裸的大人相拥在一起。一个是曾二叔,一个是七姑!那当儿,曾二叔迅速地将一件蓝色外衣裹住七姑的身子抱在怀里,蹲进草堆,尔后惊恐地看着我们这两个小姑娘。
后面怎么收场的,除了七姑那美丽的胴体、丰满的双乳印在我的脑海里之外,剩下的那些记忆现在已经非常模糊了。只记得后来几天,每次碰到七姑,我总情不自禁地多看几眼,因为我简直无法相信那件宽大的粗布蓝衣里会装着个那么美丽的躯体。这件事过去不到三个月,一天,挨近吃中饭的时候。胡家来了三个陌生人,把三张贴满钱的报纸很自豪地铺在胡家饭堂里的那张八仙桌上。我从来没见过那么多钱,赶紧跑近去看。摆在最上面的,贴的全是拾元,第二张全是伍元。最下面一张贴的是壹元和贰元的。我惊讶的目光全部在那些钱上。拾元的钞票那么多呀!我见都很少见,那还是春节父亲回家过年。在他的手里见过那么几回。我很是羡慕七姑的娘,她布满笑容的脸上焕发出淡淡的红晕,七姑的爷(ya)一个人闷闷地坐在灶膛前抽着旱烟,一脸的阴沉。
我弄不明白这三个陌生人为什么要送给胡家这么多钱?转头听他们谈话,还是没明白缘由,他们讲的都是平时很少用的客套话。直到奶奶喊我回家吃饭,我才恋恋不舍地离开胡家。吃饭时,我不停地跟奶奶说胡家那些钱的事。奶奶一个劲地摇头叹息:“咯杂老耄亲(这个老太婆),真要这样活生生拆散儿女!哎!这样做,害人也害己呀!”
见奶奶那样叹息,我更是疑惑,忍不住反复追问奶奶为什么胡家有人给送钱?可奶奶很不高兴地呵斥我:“小姑娘家不可以总关心这种事,赶快吃饭吧,别磨磨蹭蹭。”
几天后,来了一队敲锣打鼓的迎亲队伍,他们抬走了被五花大绑在一张竹椅上的七姑,后面跟随着贴满红喜字的箩筐和小板车。
自此,每个月圆之夜,都能听到村西头曾二叔在自己破旧的木屋里哼着悲伤的渔鼓。
记得那日妹要嫁,堂前聘礼堆成山
记得那日妹远嫁,一溜嫁妆光鲜鲜
妹妹呀,你哀怨成冢泪流干
声声来把哥来唤
……
——旧诗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