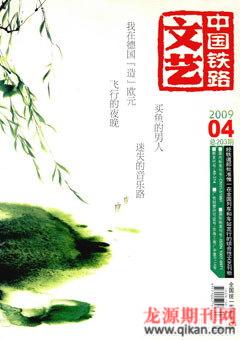飞行的夜晚
洪 荒
陈木鱼和冰坐在那家经常去的百合料理饭店临街靠窗的位置上,窗外夜幕刚刚降临。寒气袭人的街上各种汽车尾灯划着流长的弧线匆匆闪过,猩红的荧光诡秘得像夜的眼睛。散着热风的窗玻璃里是一张陈木鱼麻木的脸。冰在那边像在调色板调色颜料一样在点生菜橱窗盘子里的菜。背景音乐悄悄在背后响着《回家》。低婉缠绵的旋律在若明若暗中徘徊……街面上一口结着冰马葫芦盖子上,在昏黄的街灯下地冒着白汽。寒冷让街上偶尔走过的行人都匆匆竖起了大衣领子。这样一个寒冷的冬日夜晚,让他想起邻居家刚刚出生的一窝小狗崽,他和弟弟背着母亲把一只沾得满身是雪的狗崽抱回家来,捂在被子下面,狗崽发出唔唔细小的叫声。
陈木鱼是在林区的一个小镇子上长大的。
狗肉热煲。冰坐下来,一脸的坏笑。
对不起,我不吃狗肉。他冷淡地说。
我记得以前你是吃狗肉的……冰莫名其妙地看着他。
以前是以前……他的脸上堆上了一丝不快和潮红。
外面不知什么时候飘起雪花来,窗里的热气不断把扑到窗玻璃外面的雪花融化了,就像蝴蝶纷纷无声地投进了河水里一样。寒冷还是叫窗外慢慢结上了窗花。春天山坡上开满了野百合花,小镇被后来建起的一座水泥厂污染了,他回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那是他八岁以前待过的小镇。
从外面走进来一个脸蛋冻得红扑扑的小女孩,她身上头上的围巾上落了一层雪,胳膊上挎着一个塑料布包着方篮,她抖落掉雪。
“先生,买支花吧。”两支塑纸包着的红玫瑰伸到了他们面前。
陈木鱼和冰微微一愣?冰很快就笑了起来:“我差点忘了,今天是情人节吧?”
小姑娘点点头。
“老六不会来了。”他们本来说好晚上一起过来喝酒的。
“好吧,我们要了。看看我们有多可怜,只有我们两个大男人像傻瓜一样坐在这里喝酒。”冰掏出钱来付给了小女孩。
果然他俩看到别的座位上都坐的是一对对情侣,有年轻人,也有像他们这个年龄的。
“等着,今晚会有人要我们的玫瑰的。”冰暖昧的眨眨眼睛,啤酒让他的眼睛泛着一种多余的红色。
陈木鱼知道他今晚又要到那里去了。冰自从和他第二个妻子离婚后,就一直独居。冰说他对婚姻已经冷到了冰点,冰打算一直独身下去,这样他很快乐。
窗外,大片大片的雪片落在地上,像棉花糖一样变得软绵绵的,行人踩上去留下很深的脚印……
“霞要的她那幅油画你给她画了没有……”
“还没有。”陈木鱼摇摇脑袋。
他们的话题转到霞身上,冰的目光有些散淡。霞是老六的前妻,不过他们现在还在一起同居,霞是青少年宫的一名音乐教师。当初老六和霞是在本城的一次青年歌手大奖赛上认识的,老六是通俗唱法的第一名,霞是美声唱法的第二名。霞对老六天生有一种崇拜。老六那时还是工厂里的一名油漆工,大奖赛后老六就调到文化馆里来了。老六一米八零的个头,长长的头发,穿着一件被油漆涂抹得花花绿绿的黄上衣。陈木鱼见到他第一天就觉得这个家伙早晚要从文化馆飞走的。他们的婚礼也很标新立异,两人在婚礼那天坐上了一只租来的热气球,从这个城市最高的楼顶层上飘过。当时霞穿着长长的白婚纱裙吓得哇哇大叫。如火如荼的爱情让她已有了三个月的身孕,从热气球上下来她就蹲在地上呕吐不止。他们的爱情宝贝就这样流产了。他们下来时,陈木鱼对霞说,她和老六不会长久的。霞的目光就久久盯着陈木鱼,那一刻她恨不得杀了陈木鱼。那天的阳光很好,霞白白面孔皮肤上的汗毛都瞅得清清楚楚。
“她不该把音乐教师的工作辞掉。”冰说。
自从老六开了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家迪吧夜总会以后,霞也辞掉到了工作跟他一起干了。霞负责夜总会的酒水、茶点、水果的采购,打理着夜总会的每日收入。
“今晚他们那里一定很热闹。”冰兴奋的眼里已有些急不可待了。
买了单,走出来,在门口的房檐下他们又看见了那个卖花的小女孩。她抄着碎蓝花棉袄袖站在那里,身上又披上了一层新雪。
“……买花么?”
“你还有多少?”
“十、十几支吧。”
“我都要了。”他掏出一张百元钞票给了她,“不用找啦。”
“谢谢你,叔叔,你会交好运的。”小女孩冰冻的脸上绽出了笑。
冰拦下一辆出租车,他们钻进去。“去老六那里么?”在车里冰又一次问他。他以前常和冰晚上去那里,可是今晚他不想去。
在卡尔加里路的中段,有一个巨幅广告牌竖在路口上:让我们到西部去,一架大肚子飞机腾空而起,箭头指向飞行夜总会往西500米,城市森林公园西侧。只有老六才会这样标新立异。他俩在这块牌子下分的手,他从出租车里钻出来,一束玫瑰伸出来:“把这个给你老婆带回去,她今晚会高兴的。”有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的手,他缩了一下手。出租车欢快地溜走了。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早回去,过去了两辆出租车他都没有拦,怔怔站在这块被五颜六色的灯光照射的牌子下面。上面还新拉上一块红布:2月14日情人节狂欢夜大奉送,每人免费赠送一杯鸡尾酒,一枝玫瑰。刚才丢在地上的那束玫瑰无聊地在地上滚动着,很快被雪遮盖住了。
一辆出租车无声地停在了他面前,他拉开车门坐了进去。
“就你一个人?”司机有些奇怪地问。
“嗯。”
他从反光镜里看到,车轮滑动时那束遗弃在雪地里玫瑰被碾压得粉碎,像一摊血淌在雪地里。
城市五光十色的灯光在车窗外的夜幕里缓缓流动,最早知道情人节这个日子还是在七、八年吧?在省城的索菲亚大教堂广场前,他和妻子刚刚从百货公司满头大汗采购大包小裹出来,坐在教堂前面的石凳上歇息一下。准备中转晚上那趟进山里的火车回父母家过年。他腰间的汉字传呼机响了,他摘下来,看到显示屏上跳过一行小蝌蚪:祝节日快乐!落款一位朋友。节日?什么节日?
谁的传呼?妻子随意地问了一句,她的目光在瞧着教堂的门口那边。
一位朋友。他如实地说。
圆形的褚色教堂尖顶上,午后的阳光暖嗳地落在上面,让人丝毫感觉不到冬日的寒冷。几只鸽子很温情地在屋顶上飞来飞去。
一对新人款款地从教堂里走出来,新娘披着洁白的婚纱,纱裙一直长长地拖在台阶上,夹道的人群向新人头上抛散着玫瑰花瓣。花瓣在雪地里很刺目。
妻子看傻了眼,喉结像喝了一大口什么饮料,蠕动了一下。
妻子一直抱怨她结婚时没穿过婚纱,连租借的婚纱照也没留下。他们的婚礼很寒酸,也是冬季,就在妻子单位分的那问平房里举行的,参加的朋友也不多。妻子就穿着一件订做的藏青色西服外装。他当时的理由是冬天太冷,没办法穿婚纱。
当教堂的钟声响彻广场的时候,一群白色的鸽子从教堂上空盘旋着飞起,划着哨音儿……他从纷纷离去的人嘴
里知道,这一天的确是一个节日,2月14日,西方的情人节。后来他才知道那天给他打传呼的是给他做过模特的一个师范学校的学生。
“到哪?”
他不知是该回家还是该回画室,也许该把那幅画完成了。
情人节的第二天,冰的弟弟来到陈木鱼家中,陈木鱼才知道飞行夜总会昨天夜里出事了。冰的弟弟是一名刑警。冰的弟弟和冰一样细瘦,不过眼睛却要比冰犀利得多。他一进来目光就很职业地在陈木鱼家各个房间打量着。
“……昨晚发生了什么事?”陈木鱼木木地问。
“飞行夜总会老板开枪伤了人,现在下落不明。”
“你是说老六开的枪?”
陈木鱼这才知道老六那杆猎枪派上了用场。
冰的弟弟问陈木鱼昨天晚十时以前在哪里啦,和谁在一起?十时以后又在哪里啦。另一个警察坐在一边的沙发里打开一个小本记着。
陈木鱼说十时以前他和冰在百合料理喝酒。冰的弟弟打断他,他们是不是约了田川(老六的本名)也要一起在那里喝酒?陈木鱼点点头说是的,可是后来他没有来。冰的弟弟又一次打断他,他为什么没有去?陈木鱼说他不知道,十时以后他就回来了……有谁可以证明?冰的弟弟问;陈木鱼说没有谁可以证明,他昨晚一个人在画室里作画。
你妻子呢?
她昨晚值夜班,还没有回来。陈木鱼说,陈木鱼的妻子是一名外科手术医生,他家房间里到处都飘荡着一股来苏儿味儿。
冰的弟弟问可不可以带他们到他的画室去看看。
陈木鱼就带冰的弟弟和另一个警察过去了。
十分钟后,他们来陈木鱼的画室里。这间画室的窗户都被遮挡得严严实实,屋里一张墨绿布罩着的画台上,摆着两幅没完成的油画。一幅是一条河流环绕山区小镇,小镇四周是光秃秃的白桦林,中间生长出一个巨大红烟囱,而河水流淌的是黑黑的颜色。另一幅画面上只画了一个女人的乳房和臀部,面部还没画出来。冰的弟弟站在这幅画前打量了一会。
走的时候冰的弟弟第一次悄悄在他耳边说:陈哥,如果老六来找你,你叫他去自首,争取主动,或许可以算正当防卫。陈木鱼听了一愣。
从这天起老六就从这个城市失踪了。
陈木鱼回到家里来时,他妻子刚下夜班回来了。他妻子困倦地打了个哈欠说,昨天夜里她们医院里接治了一个受到枪伤的病人,她们一早才下手术台。妻子的面部皮肤有些松弛,她最近很注意美容保养,常出入美容店。听到“枪伤”两字,陈木鱼问:那人伤得怎么样?妻子说,即使是好了那人也得在轮椅上坐一辈子了,子弹击中了他的腰椎穿过了他的肾脏,他的下身瘫痪了。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叫王大胜。
陈木鱼以前从冰嘴里听说过这个人的名字,说他是荒城地界上连警察都惧怕三分的人物。
是谁这么狠呢?妻子随意地说了一句,找出睡衣要去卧室里睡觉了。
从早上到现在听说的事情让陈木鱼有些迷乱了。他不能告诉妻子这人是老六开枪打的,妻子对老六也有一种崇拜。
你昨晚去哪里啦?
我去画室了。
他尾随着妻子走进了卧室去。“……我累了。”她从他眼神里读懂了什么。每次妻子夜班从手术台上下来,陈木鱼都会莫名其妙地有这样的冲动。可每次妻子都会这么说,两个人顿时都会索然无味起来。
下午陈木鱼在画室里作画,冰来了。冰一屁股坐在画室里一张破沙发上,嘴里倒着气说:“惊险,太他妈的惊险了,简直像美国枪战大片一样……”陈木鱼说警察已来他这里找过他了,他们怀疑老六昨天晚上出事后来找过他。“他真的没来找过你吗?”冰神神秘秘问他,陈木鱼摇摇头。“你昨晚去哪儿了?”“我就在这里作画。”停了一下,冰说他也没有想到老六会开枪,王大胜和他的手下腰里都掖着枪和片刀。为一个小姐这么做真是不值得。冰摇着头,从冰的嘴里听到那个小姐叫李怡时,陈木鱼的画笔抖了一下。冰说王大胜昨晚到夜总会来就是指名要找李怡出台的,李怡拒绝了他。她也不看看王大胜是谁,她以为在那种地方还能装什么清高呢……冰的嘴里喋喋不休地在说。
飞行夜总会像一只疲倦的大鸟安卧在夜幕里,屋子的外形是迷彩色美式空军一号飞机造形。也许是因为昨天夜里发生枪战的缘故吧,迪吧里面显得冷冷清清,吧台里面被击碎的香槟酒和XO酒瓶的痕迹还在残留着,墙壁上还吊着两只仿制的卡宾枪,是老六从解散的文工团收集到的。吧台的斜对面有一幅陈木鱼临摹的梵高包着耳朵的自画像,现在那只耳朵又穿过了一颗子弹弹孔。老六说他喜欢梵高那种生命的激情。
冰说是梵高的耳朵替他挨了一颗子弹。
看见他俩走进来,霞走了过来。她脸色苍白,看来从昨夜到现在她还没有合过眼。
霞问他昨天夜里到哪里去了。
陈木鱼说他在画室。
老六没去找过你么?霞也这么问他。
没有,老六还没有什么消息么?
霞摇摇头,说警察还在找他,我担心……
担心什么?他俩同时问。霞没有说出口。
你别担心,老六会没事的。他俩在安慰霞。
她怎么样?他是指李怡。平时她是站在吧台里面的,有时也到音乐池子里给客人献歌,她的通俗歌曲唱得很好。
霞的面孔堆上了一丝怒气,口气一下子冷了下来:发生了这种事情,她还有什么理由留在这里。霞说她上午就离开了迪吧,尔后她又叹息了一口气,说老六为了她真不值得这么做。
一个服务生过来冲霞耳边说,门口又来了两个警察,霞就迎了出去。过了一会儿,冰的弟弟和陈木鱼早上见过的那个警察就走了进来。看见他们也站在这里。冰的弟弟就走过来,“六哥还没消息么?”
他俩摇摇头。
冰的弟弟说,他们来是找几个昨天夜里在现场的服务生再了解一下当时情况的。霞就说那你请便吧。冰的弟弟就和那个警察走到里边去了。
你们要喝点什么吗?霞说。
不要。陈木鱼摇摇头说,你忙你的去吧。霞就走到后屋去招呼客人去了。
老六当时是怎么拿出来的枪,你当时在哪里?陈木鱼问冰。
我、我当时在包房里……冰嘻嘻一笑。尔后说:听见枪响我跑出来,王大脑袋当时已捂着肚子倒在地上了,大厅乱做一团……我也没有想到老六会开枪。昨天夜里来的客人特别多,包房都占满了。
那杆鹰牌猎枪就藏在放香槟酒的后屋库房里,老六给陈木鱼看过,老六还说等过一段时间要带他到山里去打猎。
其实我昨天一来是想让她陪我的,我把玫瑰都给了她,她要是跟我去包房也不会发生这种事,她说吧台忙走不开拒绝了我……活该她倒霉。冰悻悻地说。
墙壁上除了猎枪子弹弹痕还有沙管枪钢珠子弹痕,冰说王大胜腰里的五四式手枪还没来得及拔出来,老六要不是趁乱趁着大厅里灯灭了逃出去,肯定会被他们打死的,警察赶到时把王大胜四五个手下都带走了。
冰的弟弟和另一个刑警走后,又来了两个治安警察,他们向霞宣布:鉴于昨夜这里发生的斗殴事件,飞行夜总会要查封暂时不得营业。
霞就和服务生在迪吧里收拾东西了,收拾得挺晚才离开,霞也给服务生放了假。他俩一直陪霞收拾完。问霞回哪里去?他俩以为发生这种事,霞会回她的父母家去住。可是霞说她回自己的家,她说说不定老六夜里会回到家里来。他俩就送霞回去。
以前他俩到飞行来玩,也是待到12时以后和老六回到他和霞的住处去住的,他们的家就在中林街上,是一处三居室,陈木鱼和冰睡在客厅的地毯上,他们往往先看一会儿碟片,老六这里有不少从朋友那里弄来的大片。
和以前每回夜里回到他们的住处一样。霞给他们端来了水果茶点和一瓶红酒,把家庭影院也打开了,问他们想看什么自己去碟架上去找。霞困倦地打了个呵欠说我累了,先去睡了。霞从昨夜到现在一直没合眼。刚才看霞去卫生间冲澡,陈木鱼本来想说,我们回去吧。冰瞪了他一眼说,这种时候我们怎么能走!陈木鱼就不吱声了,陈木鱼就和冰歪在沙发上看碟片。冰找了一个《钢琴师和他的情人》,这个碟他们以前和老六在一起看过。
你说老六夜里会不会回来?冰问了一句。
从卫生间传来哗哗的冲澡声。以前不管忙活到多晚,霞回来总要冲个热水澡的,霞的皮肤很白,冲过澡后面部蒸发着一种红晕,长长的头发上被一条毛巾挽起,穿着一条睡衣长裙走出来。有时陪他们一起看一会影碟,有时去隔壁琴房弹一会琴儿,自从不在少年宫当音乐教师以后,霞惟一的留恋就是弹一会儿琴了。那台黑色钢琴还是刚结婚时老六给她买的。
陈木鱼的睡眠很差,每次到老六家来住,他都很难入睡。有一天夜里,他去卫生间起夜,从琴房里传来一种很奇怪的响动,从敞着的门缝里他看到老六和霞就在琴房地毯上做爱。霞的身下是黑色的罩钢琴的绒布,霞性感的身子自得炫人眼目。后来老六告诉他,他和霞第一次做爱就是在文化馆那间黑暗的琴房里做的。霞当时穿了一条黑色长裙子。老六说他喜欢黑色。
霞现在越来越很少弹琴了,每天回来更多的是喋喋不休的是告诉老六一些夜总会账目收入的事。她的那双手也变得越来越粗糙。对于霞当初辞掉音乐教师工作跟他一起干,老六是反对的。
她是不放心老六。冰有一次跟陈木鱼说。陈木鱼就觉得霞很愚蠢。果然没过多久他们就办了离婚手续。不过他们还住在一起,不知是为了双方的老人,还是为了他们八岁的女儿,他们的女儿在上一家私立学校,每周接回来一次。他们没有把离婚的事告诉女儿。
夜里霞突然发出一声惊叫,霞从卧室里穿着睡衣走出来,脸色煞白,双手捂着胸前站在门口对他俩说:我刚才做了一个噩梦,梦见老六被人追杀,满脸是血……他俩还没睡,冰还在看着碟,他俩从电视的光线中站起来,陈木鱼叫她别害怕,老六不会有事的。冰的目光落在霞高高撑起的睡衣乳房上,冰说有我们在你去睡吧。霞就扭转身走回卧室去,霞的臀部也很大。
第二天早上起来,霞还是一脸的倦容。霞向他俩说老六会到哪里去呢?看得出她很为老六担心。陈木鱼就劝她别担心,老六会没事的。
他俩离开老六家走出来,听冰说,霞本来情人节那天晚上是打算单独和老六在一起过的。店里的事情她已经打点好了。
他们为什么还同居在一起?陈木鱼问了一个他以前问过的问题。
霞离不开老六了,你不懂女人。老六是天生让女人喜欢的男人。冰有些嫉妒地说。陈木鱼知道他指的是什么。
陈木鱼回到家里,老婆并没有问他干什么去了,他们已经习惯这样了。老婆只是说他们医院里前夜里抢救的那个受枪伤叫王大胜的病人醒过来了。陈木鱼说你知道他是谁开枪打的吗?老婆摇摇头。陈木鱼就告诉他是老六。老婆听了倒吸了一口气?问是怎么回事?陈木鱼就把前天夜里飞行夜总会发生的事情简单向她复述了一遍。老婆还是不能相信,口里怔怔地反问道:就为了一个小姐……
李怡是半年前来到飞行夜总会的。那天晚上陈木鱼一走进飞行夜总会,冰就过来跟他说:老六这里来了个冷美人。陈木鱼每回到这里来坐坐就是喝两杯啤酒,对小姐他是一向是没兴趣的。而冰如果在这里找小姐也是要自己买单的,这是规矩。陈木鱼回过头去,果然看见吧台里站着一位新来的小姐,她正把调制好的红酒,一杯杯放进服务生的托盘里。她身材修长,穿着一件白色长裙子,挽着披肩长发,姣好的面容含着淡淡的忧郁。就是这丝忧郁让陈木鱼觉得有些似曾面熟。
李怡的歌唱得也很好,一支《月亮代表我的心》博得满堂喝彩。等大厅里的人渐渐少了时,老六把她引过来,给陈木鱼介绍:
这是我最好的朋友,画家陈木鱼。
一双纤纤玉手伸过来,与陈木鱼轻轻握了一下。等老六走开,他们在卡座坐下时,忽听她说道:陈老师,我们是见过面的。
陈木鱼一愣?
她抬起头来黑盈盈的眸子看着他说:在你的画室……
陈木鱼瞪大了眼睛?……他渐渐想起来了,那还是六、七年的事,他当时还没有离开过文化馆,陈木鱼要创作一幅《白桦与少女》的油画参加全国一个画展。陈木鱼需要一个少女模特,有人给他介绍了李怡,那时她还叫李青青,是本市一名师范二年级学生。陈木鱼一见到她的身材就相中了,更主要的她的气质。是那种在山里长大的女孩子才有的气质。果然李青青说她是在小兴岭山里长大的,她喜欢白桦林。这么说来他们还算得上老乡,当时山里的孩子观念还是比较封闭的,李青青说她之所以答应做他的模特,是她需要一笔钱,她家里惟一的一个弟弟患了肾病,需要这笔钱住院。这是陈木鱼后来才知道的。
李青青像一株青青白桦在他面前把衣服一件一件脱掉了,露出曲线分明白皙的胴体来,圆圆的像青苹果一样的乳房。她卧在沙发一件墨绿色绒布上,就像卧在家乡白桦林丛草地上一样自然。
后来,他的这幅油画在参加全国这个画展中获了奖,他把这个消息写信告诉了李青青。李青青也给他回了一封信,李青青说他是第一个看过自己身体的男人,她不想让别人特别是学校老师和同学知道她当模特这件事。以后他们就再没有联系。
他也决然没有想到在这里会碰到李青青?
李青青说她师范毕业后,分到一个偏僻县城去教书,可是弟弟的肾病还没有好,为了弟弟的病她只好辞掉了那份工资很低的教师工作,前年又回到这个城市里来……
离开的时候,他给李怡留下了二百块钱小费,李怡说什么也不要,她说没想到陈木鱼和田老板是好朋友。陈木鱼从她眸子看出了什么,他说他不会把他们认识的事跟老六说的。他也不知道李怡为什么不让把她家里的情况跟别人说。
以后陈木鱼再到飞行去,都要李怡陪一陪。走的时候照例给她留下小费,这一点连冰和霞都看出来了。
陈木鱼是两年前离开了文化馆,开办了陈木鱼个人画室。这两年城里有钱的人多了
起来,也学得高雅了,画肖像油画的多了起来,陈木鱼的生意一直不错。可是有些富婆身上的那一身赘肉常常让陈木鱼直皱眉头,城市的垃圾真是越来越多了。他常常这样感叹。一到夏天他就回到山里去写生。
重新见到李怡让他眼前一亮,他想让李怡再给他当回模特。他要给她画幅肖像画,可是李怡说她身子已经脏了。李怡说这话时脸上又现出淡淡忧郁的表情来。
没人在的时候,陈木鱼问她弟弟的病怎么样啦?
李怡说他得换肾。陈木鱼知道这得需要一大笔钱。
李怡陪的客人很多,可是她很少陪客人到包房里去,她就静静地站在吧台里,像一幅画。每晚李怡都在大厅里为客人们献上一首歌,这之前是由霞来唱的,许多来飞行的客人都是冲着李怡来的,所以那天晚上王大胜来直接找李怡一点也不奇怪了。
无论是冰的弟弟和霞后来都再次问过他,老六那天夜里真的没有找过他?陈木鱼说没有。霞说老六身上可没带多少钱。他也很奇怪老六那天夜里出事后为啥没来找他,在这个城市里他和老六是最好的朋友。老六逃离这个城市至少会和他打一声招呼的。
陈木鱼的老婆从医院带回来的消息说,王大胜的伤势在不断好转。他手下的人中有人传出话来。王大胜是不会放过老六的。陈木鱼的老婆就说老六还是不要回来得好。看得出她现在也在为老六担着心。她又说她以前就说过老六不该开飞行夜总会。可是老六想做的事情谁也拦不住。
一个星期后还没有老六的任何消息,陈木鱼和冰都相信老六不会回来了。陈木鱼想起有一次老六跟他说过这样一句话。他早晚要离开这个城市。那是崔健刚到这个城市来演出不久,这个城市的年轻人跟着崔健一起疯狂了。大街小巷里都在吼着《一无所有》,老六说他要做个流浪歌手。老六说这话时,霞正在做着第三次流产手术,是在陈木鱼的老婆医院里做的,是陈木鱼的老婆找的妇产科的崔大夫给做的。老婆回来说了一句:老六可真能干。
霞现在既希望老六回来,又不希望老六回来。虽然那天夜里的事情警方调查清楚了,王大胜是带人持凶器聚众闹事。王大胜一伙人已被警方刑事拘留了,可是谁知王大胜在外边的手下会不会报复。飞行夜总会又重新开业了,霞又忙碌了起来,只是她的面孔有些憔悴。
女人就像花一样,缺少男人的滋润会老得很快的。冰说。
冰又常泡在飞行夜总会里了。当然用他的话说他想帮帮霞。每次夜里店里忙活完霞回去住时,他都送霞回去。如果陈木鱼在,他又会和陈木鱼住在霞的家里。
日子在一天天过去,有一天夜里陈木鱼突然接到了霞打来的电话,霞在电话里说冰出事了,冰在送她回家开门时被人刺倒了,现在正在送医院抢救。陈木鱼一听穿上衣服就赶到医院去,冰被送到这家医院正是陈木鱼老婆工作的这家医院。他赶到二楼抢救室门口,外面除了霞还站着几个警察。警察拦住了陈木鱼,警察正在向霞了解情况。
陈木鱼的老婆这天夜里值夜班,他想通过他老婆来打听一下冰的伤情,就朝一楼的外科手术值班室走去。他很少到医院里来找他的妻子,所以无论是与妻子同科室的人还是不同科室的人都不认识他。值班室的一个小护士目光有些闪烁地告诉他你到妇产科值班室里找找看。他不明白他老婆为什么去了妇产科值班室里。等他敲开妇产科值班室的门,一个衣着不整的男大夫不耐烦地推开了门,他显然是刚刚从床上爬起来,“你要干什么?”
“我……”他从虚掩的门缝里看见里面的一张手术床上裸露着一个女人的两条白腿肚子,床下的一双红色高跟鞋他是熟悉的。
男大夫指了指门口上的一个指示灯,男士止步。他就张大嘴,止住在哪里了?
可是里边发出了一声惊叫——
他忘记自己是来干什么来了。此刻他觉得今夜受伤的不是冰而是他自己。
第二天早上回到家里时,他呆呆地坐在沙发里坐了好久,后来他问他的老婆:“你和崔大夫有多久了?”他想这个人应该是他常听从老婆嘴里提起的崔大夫。
“就是去年的情人节。”老婆的脸上竟然没有一抹羞涩。这叫他很愤怒。
“我们离婚吧。”
不用说那天夜里刺伤冰的人是王大胜的手下人干的,他们显然把冰当成了老六。也难怪,听霞抽泣着说,每次冰夜里一个人送她回来,上楼时都是他走在她的前面,开门后又让她先进去再关好门。那天夜里她刚走上楼去,冰就被躲在门口楼道里的一个人刺倒了,冰瘦瘦的身子像面条一样弯软了下去。
冰从医院里醒来后第一句话就说他爱霞。以前因为她是老六的妻子他没有这份非分之想,自从他们离婚后他就暗暗喜欢上了霞。他愿意为他做任何事,包括为她去死。陈木鱼觉得这会儿冰很像一个男人。
陈木鱼走在春天的大街上,突然觉得自己老气横秋起来。瓦白瓦白的太阳晃在头顶上,把他的影子拖得老长老长……
“你会娶我么?”
他手中的画笔一抖,他没有想到李青青会这么说。就是在那次她给他做完模特后。
“你是第一个看过我身子的男人……我愿意嫁给你。”
他知道山里的女孩把童贞看得很重。虽然他和他老婆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可是当时他还没有把它打碎的勇气。
“你知道你的画里缺少什么?”以前老六常常这样对他说。
“缺少什么?”
“缺少一种像梵高一样的激情。”
他不得不承认老六说得对。
半年以后,冰的弟弟从外地追捕王大胜的手下回来,说他在北京看到过田川了,他成了京漂流浪歌手的一员,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李怡。他把家里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他,叫他回来取个证言。可是他说他现在走不开,他要给李怡的弟弟做换肾手术,李怡的弟弟现在正住在北京的一家医院里,是他姐姐和田川给接来的,他要把他的一个肾换给李怡的弟弟,否则他就死了。他们只好在京郊的一间破屋子里取了证言笔录。
听到老六这个消息后,他们都很平静。他们不再关心老六什么时候回来了,老六似乎成了跟他们三个人生活无关的人。只有陈木鱼的心里会偶尔想起那年冬天情人节的午后省城索菲亚大教堂前飞起的一群白色的鸽子,和那个像鸽子哨音一样从他心里划过一下的传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