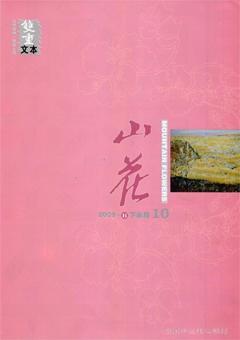文学史视野中的言文之争
郭 勇
在晚清和“五四”的文学变革中,语言其实始终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不约而同地对“言文一致”这个命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重视,而对于“言文一致”的追求事实上折射出他们对于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共同渴求。学界对“言文一致”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已经达到一定的深度,但其中还是存在不少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对“言文一致”历史语境的还原做得还不够,对于“言”、“文”在不同语境中的复杂意蕴缺少细致的分析,从自身的理解出发加以阐释;与之相关的是,探讨这一命题时,很少意识到言文一致的追求其实包含了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汉语的全新反思,涉及汉语,也牵涉到汉字,形成了日后的汉字改革、国语运动与文学革新的汇流;此外,对于这一命题,或是分析晚清知识分子的观念,或是研讨“五四”知识分子的观念,而忽视了这一命题其实是两代知识分子共同关心的问题,而且两代知识分子对待同一命题,其观念与态度也存在深刻的差异。
一、文学启蒙——“言文一致”的历史动因
“言文一致”从根本上说其实是语文变革的要求,这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
但是,晚清和“五四”时代中国知识分子提出的“言文一致”要求,则与此前的语文变革有了根本性的区别:此时的变革要求并非是从言文问题自身出发,而是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启蒙民众,在总体上是中国思想文化现代转型的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的“言文一致”命题,已经带有鲜明的“现代”印记。
学界一般将晚清时代“言文一致”的首倡之功归于黄遵宪,依据便是他的诗句:“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但是,黄遵宪后来提出的观点更值得关注。他认为“语言文字离,则通文者少;语言文字合,则通文者多”,由此要创造“明白晓畅,务达其意”、“适用于今,通行于俗”的文体,“令天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
与此相应,晚清的维新派也注意到开启民智的重要性,对于言文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把“言文一致”纳入到改良革新的总体计划之中。梁启超最初是以其变法主张而备受关注,他注意到语言文字问题也是源于变法需要。最早的相关论述见于1896年所作之《变法通议》。梁启超宣扬变法,坚持以育人才、开发民智为要义。但是当时中国的教育却存在极大的弊端,其中一项即是“未尝识字,而即授之以经;未尝辨训,未尝造句,而即强之为文”。有感于此,梁启超把当时的语言文字与古代文字作了比较,发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缕言之矣。今人出话,皆用今语。而下笔必效古言,故妇孺农氓,靡不以读书为难事”。
然而,言文分离已是既成事实,汉语处于这样一种尴尬境况,如何能够担当启蒙国民的重任?为此,梁启超找到了国语与国民性的一个结合点——文学。
“五四”时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识分子探讨的一个热门话题。但是“五四”知识分子强调的是个性自由的观念而非一般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胡适提倡白话文运动,正是要以白话文传递现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价值的国语文学,养成一种信仰新文学的国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文章应该传达出个体的独立意识并以此达到启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识分子在探讨“言文一致”时的基本出发点,体现出更为彻底的现代意识。
启蒙国民、开启民智是中国知识分子在探求救国救民之路时意识到的问题。在他们看来,要做到这一点,既要引进西方的思想文化,又要向民众进行传播。这就涉及了语言问题,既然语言被视为传达思想的工具,要变革思想,语言就是一个关键环节。另外一个方面,文学与文章都是依靠语言而写成的,文学作品对民众的影响力不言而喻,因而选择文学作为突破口,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语言运动和文学变革发生了密切关联,以文学实现启蒙为目的,自然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首选。
二、反思汉语——“言文一致”的现实起点
晚清和“五四”时代对汉语的反思,是在同日本与西方语言文字的对比中进行的,这就使得中国知识分子有可能跳出本土文化视野,对汉语和汉语文化重新进行思考。
由于晚清知识分子一开始就不是从语文自身的特性出发来探讨言文问题,而是出于启蒙的需要,汉语与西方语言的对比自然被纳入到二元对立之中,不是二者各有优胜,而是有了明显的高下优劣之分。因此,梁启超的这种思路实际上代表了晚清与“五四”两代知识分子探讨“言文一致”问题的两条思路:语言变革(落实为白话文运动)与汉字改革(主要是拼音化运动)。
语言变革和汉字改革运动其实是并行不悖的。在晚清时代,就前者而言,众多白话报的出现就是实际的证明。就后者而言,众多的汉字改革方案纷纷出台,耐人寻味的是,语言变革是要以白话取代文言,树立其作为国语的地位。汉字改革却是借鉴国外,以外语作为改革的参照。“五四”时代的白话文运动要求言文一致,但与晚清时代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虽然胡适所说的白话依然是“俗语俗字”,采纳方言土语,但是“五四”知识分子所树立起来的“国语”——白话——实际上是“一种口语、欧化句法和古代典故的混合物”。正是因为这种白话文不是单单采纳方言土语,也不是口语言说的直接记载,而是承载现代思想的重要媒介,因而现代白话不仅没有拉近民众与书面语的距离,反而拉开了这种距离。而在言文一致的大背景下,真正提倡书写和言说的一致是拼音化运动。鲁迅和钱玄同等人对汉字拼音化十分看重,其中包含的思路是实现书写和言说一致,使汉字变成表音文字。
但从实际结果来看,恰恰是白话文运动取得了胜利,而拼音化主张步履维艰,直至今天也没有实现。从文言到现代白话的转换意味着古代汉语体系退出前台,现代汉语体系得以建立。但无论是古代汉语还是现代汉语,二者共同的书写基础都是汉字。
三、“文学”观念的革新——“言文一致”的实际成果
在晚清知识分子看来,言文分离是实际存在的事实,因而需要通过语文改革来改变现状。
晚清知识分子对“言文一致”的追求促成了文学观念的现代转型,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学格局。但是“五四”时代的变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层面触动了古代汉语的根基,由现代汉语建立起现代思想文化。胡适等人发起了文学革命,推行白话文学,但是在进行的程序上,新文化阵营内部是有分歧的:陈独秀在1917年《新青年》3卷2号“通信”的编者附记中提出:“白话文学之推行,有三要件:首当有比较的统一之国语;其次则须创造国语文典:再其次国之闻人多以国语著书立说。兹事匪易,本未可一蹴而就者。”对此,胡适反驳说:“国语不是单靠几位言语学的专门学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单靠几本国语教科书和几部国语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国语,先须造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自然有国语。”
从实际情况看,胡适的主张立足于进化论。后来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也把新文学追溯到明代公安派那里,也不无这种意味。但胡适对语言的文化意义显然有所忽视,周作人却意识到“这荒谬的思想与晦涩的古文,几乎己融合为一,不能分离”。因而“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朱希祖的话可以做很好的注脚:“新文学有新文学的思想系统,旧文学有旧文学的思想系统”,“文学的新旧,不能在文字上讲,要在思想主义上讲。”由此来看,“五四”知识分子所提倡的“言文一致”,真正促成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发生。
综上所述,晚清与“五四”时代“言文一致”的命题,表面上是语文改革,实际上是以启蒙立场为基本前提,是以外语为参照对汉语进行全面反思,现代意义上的“文学”与“文学”观念也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得以建立的。
作者简介:
郭勇(1978-),男,湖北麻城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三峡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论、中西比较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