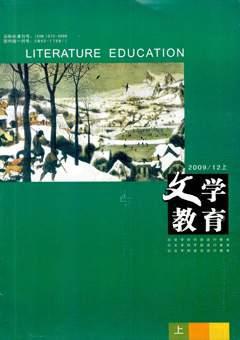文学证象的证明
文学是语言艺术,是人类的特殊语言活动。语言作为人们交流、沟通的主要工具,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描述外在事物(叙事);二是表达感情(抒情);三是阐明观点(议论)。作家艺术地运用语言,也体现在对语言的不同功能的强调上。其中议论功能的文学审美表达往往被理论研究所忽视,下面就文学审美表达所形成的议论方面的功能形象形态简要作出概括。
文学排斥直接的议论、说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不能够表达作家对生活、人生的深入思考,恰恰相反,作家只有感悟到人生真谛,揭示出生活本质,才能写出意义深刻的文学作品。正如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1]意思就是说文学的议论和说理是必要的,只不过要做到“不涉理路,不落言筌”。我们这里所说的文学证象,就是作家创造的为精神生命表达提供佐证的艺术形象。就是说在文学创造中存在这样一种倾向,他们只注重社会、人生本质的揭示,而游离了文学传统的规定性,这种艺术形象只是作为议论说理的工具,丧失了文学特有的情感内涵和情感意义,因而,艺术形象就成为了单纯的表意符号。其附带的情感也就成为了外在的、次要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学证象是文学被“说教”化的产物,只是这种“说教”已不是简单的说理,而是被“不涉理路,不落言筌”的艺术呈现所取代。如:寓言《揠苗助长》,(见《孟子·公孙丑》)无论你从中对那个宋国人持什么样的主观情感态度,“傻的可爱”也好,“蠢得可笑”也好,都毫无意义。它只不过是在用形象证明做事不能违反客观规律,否则尽管是好心好意,结果只能是“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这种形象的创造在上个世纪的西方超出了寓言的体裁范围,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出现了大批有影响的作家和大量的文学作品。
文学证象从创造目的上看,它的作用有三:
1.议论说理的证据
文学证象作为议论说理的证据,或称之为议论的论据,明显的体现在寓言中。寓言就是通过创造形象来阐明某种观点或哲理,其中的形象就是用来论证道理的。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大多散见于思想著作之中就是明证。现代主义的文学形象或类同于寓言中的形象,袁可嘉在《外国现代派作品选·前言》中说:“你想了解垄断资本是怎样把一切(包括才智)据为己有的吗?《中锋在黎明前死去》这个荒诞剧就为你提供了一个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所讲的更生动、形象的说明;你想了解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人化现象及其后果吗?弗郎兹·卡夫卡的《变形记》会使你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2]这段话就很好地说明了文学形象在活动中成为了理解社会政治经济现象和特征的工具。就作家创作方面而言,他也正是想通过艺术的手段、形象的工具来表达他对生活的认识。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说:“科学时代的戏剧能使辩证法成为享受”,“戏剧成了哲学家的事情了”。[3]总之,文学证象就是作家用艺术形象在作议论文章。他在阐明一个“生活是什么”或“生活是什么样的”观点,为了这一目的,其它的都是可以随意摆弄的手段和工具,超越生活事实和逻辑,编造各种契合这一观点的“证明材料”,人变成甲虫(卡夫卡《变形记》)、鬼魂随时出现(斯特林堡《鬼魂奏鸣曲》)等子虚乌有的的形象都被拿来“说事”。
2.人生感悟的证明
文学证象的创造强调对社会现实和人生的内心独特精神体验、感受和感悟。个人化、个性化的心灵世界成为他们唯一感兴趣的东西和文学创作的主要内容,心理化、幻觉化、非理性成为创作上的重要特征。文学证象正是作家对生活现实和人生进行独特精神把握的证明。诗人马拉美说过,诗歌的整个目的就是要“解脱‘近亲即具体回声的束缚”去创造“纯粹的观念”。[4]莫雷亚斯说:“在这种艺术中,自然景色,人类的行为,所有具体的表象都不表现它们自身,这些富于感受力的表象是要体现它们与初发的思想之间的秘密的亲缘关系。”[5]艾略特更是提出“思想知觉化”的创作观点。从这些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文学证象迥别于传统文学形象的特征是,只注重思想认识的表达。诚然传统文学形象也注重表达思想,但它的表达是透过情感的流露和具体形象的蕴含来自然表现的,是在了无痕迹的“操纵”自然形象的基础上完成的。而文学证象却忽视形象的具体描述和人物的个性特征,思想的表达成为它的唯一的目的,为了这一点,可以肆意阉割形象,失去了文学典型的“这一个”内涵,形象被抽象化为思想的证明材料。如:卡夫卡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被抽象为一个共性符号。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人物似影子般的模糊,对白莫名其妙、寡淡无味。
3.生存状态的证实
文学证象创造要求突破生活存在的表象而表现生活存在的实质,要求突破人的现实行为描写而揭示其内在的灵魂,要求突破偶发的社会现象而展示社会的本质。作家的这种企图又被人为地把个人存在和社会生活本身对立起来,他们正是以这种对立的方式来证实自我的存在状态和意义,因而,文学证象强调写作家独特的内心活动、直觉、梦幻,采用内心独白、呓语、幻境、假面具、潜台词等来表现自我的心理存在状态。英国批评家马丁·艾思林把荒诞派概括为“寻找自我”的文学,正是说文学证象追求自我存在的感觉和证实。奥登在《K的寻求》中说:“如果要举出一个作家,他与我们时代的关系最最近似但丁、莎士比亚、歌德与他们时代的关系,那么,卡夫卡是首先会想到的名字。——卡夫卡之所以对我们重要,是因为他的困惑,亦即现代人的困惑。”[6]奥登之所以把卡夫卡与文学大师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相提并论,就因为卡夫卡用形象证明了他的、现代人的生存状态,即:“他的困惑”及“现代人的困惑”。如他的作品《地洞》就写了一个动物为保存食物千方百计地营造地洞后患得患失、惶惶不可终日的生存状态,深刻地揭示出他的也是现代人的生存处境。现代主义创作中不乏这一类的文学证象。再如:奥尼尔的《毛猿》写的也是杨克在丧失了宗教信仰和与大自然的和谐以后,精神上处于悬空状态。作家在给《纽约时报》的信中认为这个现代工人无所归属的问题实际上象征着人类始终面临的命运问题,因此具有普遍的、永恒的意义。
正因为受创作目地的制约和影响,文学证象具有了它和传统文学形象迥然不同的审美表达特征。
首先,创作趋向上的内向性。文学证象的创造在西方现代主义那里一开始就打破、颠覆了传统的文学艺术与生活现实、艺术真实的关系,强调自我意识和无意识的表达。无论早先提出的“心理现实主义”,还是后来提出的“独立发言”、“人物私有的幻想”、“思想知觉化”、“联想自由化”等口号,无一例外的倡导创作走进作家独特的主观内心世界,表现作家独特的主观内心世界。因此,主观内向性是文学证象的标志性特征。
其次,形象形态上的荒诞性。在现代艺术中,“荒诞”成为一个极常见的术语,不合事理、不合情理的荒诞形象形态是文学证象的又一重要特征。清代袁于令说:“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7]“极幻”在现代主义这里进一步流于“荒诞”,他们为了证实自以为的“极真之理”,往往牺牲事理逻辑、情感逻辑,对形象为所欲为地、大胆地夸张、变形、扭曲,创造出荒诞的形象、荒诞的情理。
最后,思想蕴含上的模糊性和深刻性。文学证象要揭示的是社会人生的“至理”,把证明思想和观念作为文学创造的目的和最高理想。艾略特说:“诗人最后的地位必须由他诗中所表现的哲学以及表现的程度如何来评定。”[8]瓦莱里也讲过:“每一个真正的诗人,其正确辨理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强得多。”[9]由此可见,“证至理”是他们文学创造的核心工作,这也决定了文学证象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但这种深刻的思想毕竟不能直白地、赤裸裸地表达,文学的规定性要求必须通过形象来呈现,传统形象在这方面显然有点“不堪重负”,因此,他们别无选择地通过“极幻之象”来实现。但是,“极幻之象”为人们的接受制造了重重障碍,人们必须经过对文学证象的思考、揣摩、猜度,然后才可能上升到哲理观念的领悟。马拉美说:“诗永远应当是一个谜”,“诗写出来原是叫人一点一点地去猜想。”[10]由于文学证象接受依赖于人们的猜想,就使得它的蕴含具有了多义性和模糊性。
文学证象的独特特征使得它明显地区别于传统的文学形象,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表现功能,成为了文学艺术百花园中一支艳丽的奇葩。
注释:
[1]严羽《沧浪诗话》见《中国历代诗话词话选粹》上,光明日报出版社1999年版 第43页。
[2]袁可嘉《前言》见《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版,第25页。
[3]参见叶廷芳《现代艺术的探险者》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248页。
[4]参见查尔斯·查德威克《象征主义》昆仑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5]莫雷亚斯《象征主义宣言》见《象征主义·意象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5页。
[6]转引自《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1册 第752页。
[7]袁于令(幔亭过客)《西游记题词》见《中国历代文论选》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91页。
[8]引自傅孝先《西洋文学散论》,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15页。
[9]见《现代西方文论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37页。
[10]马拉美《关于文学的发展》见《西方文论选》下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6、262页。
张汝逍,河北邢台学院初等教育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