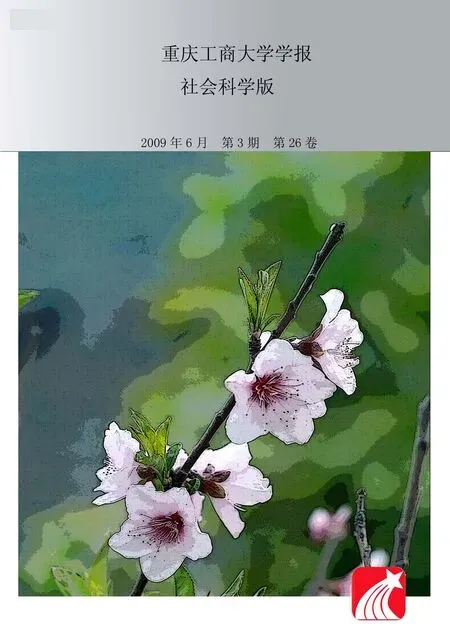论魏晋之际“三不朽”的价值困境*
吴增辉
(复旦大学 中文系,上海 200433)
所谓“三不朽”最初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针对范宣子“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的疑问,回答说,“豹闻之,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1](P1979)刘畅先生通过对先秦语境的分析,认为原始“‘三不朽’说强调的更多的是‘群体精神’、‘公天下意识’以及‘立言为公’的思想。依附性、群体性、崇公抑私性是它的本质规定”。[2](P17)与后世“三不朽”说强调对个体永恒价值的追求具有不同的文化内涵。随着汉末局势的动荡及士人独立人格的觉醒,一度衰落的儒学以入世面目重新得以高扬,“三不朽”也被充之以自我实现的价值内涵而由群体性转向了个体性,但魏晋玄风的勃然而起又使“三不朽”面临解构的困局,也使得此期士人陷入一种价值困境。
本文主要选取羊祜这一标志性的人物作为研究对象,围绕汉晋之际的政治文化变局对羊祜及其价值观进行描述和剖析,试图通过羊祜个案窥察魏晋士人的矛盾心态,进而揭示“堕泪碑”的历史文化意蕴。
一、经学的衰落与“三不朽”价值观的凸显
“三不朽”在《左传》中被正式提出后,在先秦至两汉的长时间里,并未受到士人的充分注意。盖因汉代儒学在经学化过程中,其社会伦常秩序、君臣等级观念迅速积淀于士人心中,对皇权的崇拜与服从成为普遍心态。在通经而可入仕的背景下,两汉士人兀兀穷年,皓首穷经,繁琐的章句之学遮蔽了士人的自我意识及对自我价值的追求,至东汉中后期,“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竟论浮丽。忘謇謇之志,习諓諓之词”。[3](P1126)士人志节日微,曲学阿世,具有鲜明的独立人格及自我价值指向的“三不朽”因而湮没不彰。搜检《汉书》,明确提及“三立”者仅有两处,其一出自《汉书·王莽传》,“太保舜等奏言,‘《春秋》列功德之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唯至德大贤然后能之。’”[4](P4066)这里乃是太保舜等谗媚王莽的说辞,不仅谈不上个体追求,恰恰反映出自我人格的沦落。正如顾炎武所指出,“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5](P752)其二出自《汉书·叙传第七十上》,“宾戏主人曰,‘盖闻圣人有一定之论,烈士有不易之分,亦云名而已矣。故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4](p4225)此处是有人讥刺班固以著述为业而不能立功于当世,故以古人“三立”之说激发他立功扬名,初步体现出追求个体不朽价值的趋向。《后汉书》并无明确提及“三立”者,且涉及功名的言论在东汉中叶以后开始增加,更多集中于汉末,如《后汉书·袁绍刘表列传》,陈琳在为袁绍草拟的讨伐曹操的檄文中说,“乃忠臣肝脑涂地之秋,烈士立功之会也”。[3](P2399)又《后汉书·刘焉袁术吕布列传》,“吕布与韩暹、杨奉书曰:‘二将军亲拔大驾,而布手杀董卓,俱立功名,当垂竹帛”。[3](P2449)汉末政局的混乱及经学的衰落则为“三不朽”价值观的凸显提供了历史机遇,有关三国时期的历史著作提及“三立”者所在多有,如:
1.《三国志·魏书·文帝纪第二》裴注引袁宏《汉纪》,“斯乃播扬洪烈,立功垂名之秋也。”[6](P58)
2.《三国志·魏书·三少帝纪》裴注引《魏氏春秋》,“(高贵乡公)曰:‘且太上立德,其次立功,汉祖功高,未若少康盛德之茂也。’”[6](P135)
3.《三国志·魏书·荀彧贾诩传》裴注引《荀彧别传》,“彧尝言于太祖曰:‘……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诚仲尼述作之意。显制度于当时,扬名于后世,岂不盛哉!’”[6](P317)
4.《三国志·蜀书·先主传》,“下邳陈登谓先主曰:‘今汉室陵迟,海内倾覆,立功立事,在于今日。’”[6](P873)
5.《三国志·蜀书·许麋孙简伊秦传》,“事立功成,则系音于管弦,勒勋于金石,愿君勉之!”[6](P966)
可见汉末士人的价值观已发生巨大转向,由埋首经学转向立功扬名,“三不朽”开始上升为士人的主流价值。
这种转变首先源自儒学自身道德至上的价值观及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两汉士人虽然整体上屈从王权,沉溺经学,但亦有不少士人恪守士志于道的圣人遗训,严于律己,崇尚名节,不畏强权,舍生取义,这在东汉中后期士人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陈仲举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7](P1)“李元礼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7](P4)面对东汉后期外戚、宦官专权横暴的黑暗局面,李固、杜乔、李膺、陈蕃、杜密、范滂等正直之士振臂而起,誓死抗争,显示出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力量。在汉末战乱背景下,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入世精神自然会得到极大发扬,而汉末士人个体人格的觉醒又将这种入世精神引向了对个体价值的追求,两汉经学发达,士人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所谓“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其最为消极的后果便是思想的封闭及自我的迷失,正如班固所说,儒生“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4](P1723)因此,经学的衰落也使士人获得了精神的解脱与个体自觉,余英时认为,“士大夫自觉为汉晋之最突出之现象”,[8](P265)此已成学界公论。在这一背景下,对经学的研习不再被视为神圣高贵的学问。《三国志·魏志·王肃传》裴注引《魏略》曰:“(董遇)字季直,性质讷而好学。兴平中,关中扰乱,与兄季中依将军段煨。采稆负贩,而常挟持经书,投闲习读。其兄笑之而遇不改。”[6](P420)“其兄笑之”别有深意,它表明在王纲解纽、礼崩乐坏的形势下,经学在一般士人心目中已经丧失了其文化的神圣性及谋求仕进的现实功利性,失去权力支持的经学在一定意义上还原为文化性的儒学,董遇之“投闲习读”暗示出士人对儒文化价值的接受不再是一种政治性的绝对服从,而带有了个体思想信仰的意味。研习经典已由两汉强烈的政治导向转到了个体价值指向,并因儒学的入世精神,而与战乱时代建功立业的追求相结合,形成带有自我实现色彩的价值观。儒家“三不朽”恰于此时呼应了士人的心理渴求,从经学的废墟中凸显出来,成为带有时代精神的人生理想,这在曹氏父子的政治及文学活动中得到最突出的体现。曹操以其“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9](P545)这样气韵沉雄的诗句,表现出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更以盖世功业建立了赫赫功名。曹植说“太上立德,其次立功,盖功德者所以垂名也。名者不灭,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论,孟轲有弃生之义”。[6](P569)并表示要“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10](P1307)曹丕亦表达了立德立言以致不朽的观念,“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6](P88)由上可见三曹追求声名永存、生命不朽的强烈愿望,体现出刚健有为的时代精神。
随着三国鼎立局面的形成,曹魏政权内部政治斗争的加剧及玄风的兴起,建安精神迅速落潮,“三不朽”的价值理想随之衰颓。晋代羊祜之堕泪碑及杜预之沉潭碑虽然以醒目的方式加以标榜,毕竟只是空谷传响,而不再是建安时代的黄钟大吕。然而它却以碑石的方式将“三不朽”固化成一种难以动摇的主体价值而绵延后世,对后世文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玄学背景下,“三不朽”也不仅囿于狭隘的儒文化范畴,而且呈现出形上的终极意义。羊祜在登览岘山时感叹说:“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岁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山也。”[11](P1020)羊祜立德立功,名高位重,对自己百年之后的结局仍然充满惶惑与感伤,表明他并非是从儒家“三不朽”的原始意义生发感慨的。邹湛回答说,“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仍然从儒文化角度回应,并不完全符合羊祜的本意。羊祜并非不懂得德行功业与不朽声名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贤达胜士”自然都是一些有德有功甚或有言的人,却都“湮没无闻”,显然,羊祜并不认为儒家的“三立”能实现“不朽”,因此,儒家“三不朽”并不能作为终极价值抵消羊祜对生命消逝的忧惧,他的情感实已突破“三不朽”的原初意义而延伸到更为幽远的生命底线,以追寻更具终极意义的心灵归宿。在这个意义上,羊祜的感伤便具有类似玄学思辨的终极意味。
儒家“三不朽”实则希望通过功业道德的永恒传递泯灭生死界限,消除个体对生命消亡的悲伤情绪。然而生命必然消亡,死后难以预知,无论孔子“未知生焉知死”的回避态度还是建功立业的辉煌人生,事实上都无法安顿心灵的落点。“中国因为人文精神发达,很早便消解了原始宗教,慢慢以人文精神代替宗教。但是,在现实中,人生有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如生死、最后归宿等问题。因此,对宗教的要求,在一般人中间还是存在着”。[12](P214)儒家“三立”的功利性行为只能调解矛盾而不能解决矛盾,并不能以宗教的方式为个体在彼岸世界建立安顿心灵的乐园。因而,当个体觉察到生命有限并产生出延续生命而致永恒的追求时,这种心灵无所归依的痛苦便会强烈地迸发出来,并可能产生类似羊祜这种感伤情绪。所以,所谓“三不朽”只是中国儒学设立的一种理想化的生命图式,是一种虚幻的心理安慰,它并不能消解士人终极追求所带来的焦虑,至多只能成为激发士人建功立业以名垂后世的动力。
在某种意义上说,玄学正是要以其更为深入的理论思辨解决儒学无法解答的本体问题。何晏、王弼都以老释儒,在平易的文句中挖掘比传统儒学更为玄妙的“微言大义”。如《论语》中“子曰:志于道,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王弼注曰:“道者,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本,不可为象。是道不可体,故但志慕而已。”[13](P624)孔子之道乃是儒家具体的可以依循和遵从的包括礼乐在内的伦理道德及典章制度,并不具有形上的本体意义。而王弼却将“道”定性为抽象的“无”,“寂然无体,不可为象”,这就将儒家的伦理规范纳入道家及玄学的理论框架,儒家的“道”也便具有玄学的终极意味。王弼说,“万物虽贵,以无为用,不能舍无以为体也”。[13](P93)王弼实则要“以无为本”,“举本统末”,以玄学的“无”沟通儒道,证明“名教出于自然,自然合于名教”,从而将儒学的终极价值引向“自然”。“正是在这一思路的转向中,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被放置在其合理性需要被追问的位置上,于是,那种‘不可以物象’、‘不可以言说’的终极问题被凸显出来”。[14](P322)在玄风的激发下,羊祜已开始突破“三不朽”的价值阈限而追问生命更终极的本体意义,然而他并没有走得更远而皈依玄学的自然观,因而仍然对生命的消逝表示感伤。这种感伤正是对终极问题追问而不得的结果,它一定意义上也折射出玄学对儒、道调和的失败。
玄学以“自然”调和儒、道只是一种理论的调和,这种调和能否落到实处取决于个体是否按照“自然”原则立身行事。事实上,归依自然只有如陶潜一样归隐田园才有可能,置身于波诡云谲的政治漩涡不可能完全遵循所谓“自然”之道,因此,羊祜一方面汲汲于功业,另一方面却要小心翼翼地防范政敌的暗算。即便如阮籍、嵇康之类放达之士也依违于儒、道之间徘徊困惑。嵇康在狱中作《家诫》,告诫儿子恭礼守法,谨言慎行;狂放任诞如阮籍却口不臧否人物,并且不许自己的儿子违礼悖教。魏晋士人这种违礼与崇礼、狂放与谨慎的冲突,昭示出此期士人价值取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可见,玄学只是一种哲学理论,并非安抚心灵的宗教,它之所谓“自然”只是一种哲学原则,而非彼岸世界,所以也就不可能成为士人精神焦虑的解决方案。于是在玄学的阴影之下,类似羊祜这样以儒立身的士人便只能在名教与玄学之间徘徊挣扎,羊祜之岘山感伤正是这种价值矛盾的形象写照,在一定意义上又折射出“三不朽”的时代困境。
二、羊祜价值观的内在矛盾
据《晋书》本传,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也。世吏二千石,至祜九世,并以清德闻。祖续,仕汉阳太守,父衟,上党太守。祜,蔡邕外孙,景献皇后同产弟”。[11](P1013)其祖父羊续即为著名的“悬鱼太守”,外祖蔡邕乃东汉著名学者,曾正定《六经》文字。先辈的清德令望及学术渊源无疑会影响到羊祜的价值取向。羊祜在《诫子书》中说,“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典文。年九岁,便诲以诗书”,可见羊氏重视诗书德教的家风。羊祜谆谆告诫子孙“恭为德首,慎为行基。愿汝等言则忠信,行则笃敬,无口许人以财,无传不经之之谈,无听毁誉之语。闻人之过,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后动”[15](P922)。《文选》李善注引山涛《启事》曰“羊祜秉德义,克己复礼”。[10](P1797)这种道德观无疑与其家庭背景有关。
羊祜“立身清俭”,“贞悫无私”,“道嗣前哲”,[11](P1015)谨言慎行,其立身行事处处体现出仁德至上的价值观,这在他与吴国的对峙中体现得极为充分。据《晋书》本传,羊祜“每与吴人交兵,克日方战,不为掩袭之计。将帅有欲进谲诈之策者,辄饮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吴二儿为俘者,祜遣送还其家”。诸如此类的行为使“吴人翕然慑服,称为羊公,不之名也”。羊祜的上述举措虽是收买人心的政治策略,却也是儒家“德化远人”的实际运用,以致对手陆抗“每告其戍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11](P1016-1017)
坚守儒德是羊祜的基本价值立场,而对名利的态度则又表现出冲虚自守的道家风范。羊祜劳苦功高,多蒙奖拔,却屡屡上表辞让,至今尚留有《让开府表》、《让封南城侯表》(残句)。据《晋书》本传,“祜每被登进,常守冲退,至心素著”。[11](P1019)在与从弟羊琇的信中说:“既定边事,当有角巾东路,归故里,为容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满受责乎!疏广是吾师也。”[11](P1020)羊祜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老子》曰,“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16](P5)又曰“功遂身退,天之道”。[16](P19)可见羊祜深深懂得《老子》谦退自保之道,因而将“功成身退”的疏广作为效法的范本。《汉书·隽疏于薛平彭传》载,疏广、疏受“父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广谓受曰:“吾闻‘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如此不去,惧有后悔,岂如父子相随出关,归老故乡,以寿命终,不亦善乎?”[4](P3039-3040)于是二人同归乡里,皆以寿终。羊祜对疏氏二人的推许正是对《老子》盈虚思想的认同。
《晋书》本传载羊祜“所著文章及为《老子传》并行于世”。[11](P1022)《老子传》现已亡佚,但羊祜受到《老子》思想的深刻影响是不言而喻的。由《晋书》本传来看,羊祜对《老子》哲学的笃信首先出于全身远祸的需要。魏晋之际政治斗争残酷,曹魏与司马氏两大集团之间的斗争使许多著名文士卷入其中,死于非命,这种险恶的局势不能不影响到羊祜的处世态度。羊祜很早即处事谨慎,《晋书》本传载,羊祜“与王沈俱被曹爽辟”。王沈劝他一起应征,羊祜以“委质事人,复何容易”[11](P1013)婉言谢绝,后来曹爽果然被诛。并非羊祜有什么先见之明,应是羊祜始终在观察双方斗争形势,他的辞不应命应是基于对当时形势的判断。本传又载,羊祜入仕之初,“时高贵乡公(曹髦)好属文,在位者多献诗赋,汝南和逌以忤意见斥,祜在其间,不得而亲疏,有识尚焉”。[11](P1014)在司马氏一手遮天的形势下,高贵乡公不过是一个傀儡,随时可能被废黜。作为司马氏“外戚”的羊祜自然要与曹魏集团保持一定的距离,因此,这里的所谓“识尚”显然带有强烈的政治因素,则羊祜所为与其说是一种谨慎,不如说是一种清醒。
行事谨慎成为羊祜一生恪守的原则,以至“其嘉谋谠议,皆焚其草,故世莫闻。凡所进达,人皆不知所由”。[11](P1019)羊祜之“缜密”固然可能有涉及军国大事需加防范的用意,但更是一种全身自保之道,因为这种“缜密”显然有些不合常情,杜预即曾不满地说“羊祜与朝臣多不同,不先搏画而与陛下密施此计”。[11](P1029)在《诫子书》中,羊祜告诫子女“慎为行基”,“思而后动”,这也正是他一以贯之的原则。《老子》的道家思想正为其全身远祸的现实需求提供了理论依据。
从魏晋的学术背景来看,羊祜对《老子》的推重并不仅是个人偏好。魏晋何晏、王弼等人注《易》《老》而煽扬玄风,影响到一代学术风气,羊祜为《老子》作传显然也受到时风的感染。尽管现在无法看到羊祜《老子传》的具体内容,但由其平生事迹仍可断定羊祜对《老子》的接受与阐发不可能建立在排斥名教的基础上,而应与何晏、王弼“以名教为训,形上学为体”[17](P142)的基本立场相一致。羊祜晋室重臣地位决定了他不可能完全超越名教注释《老子》,而他对王衍“辞甚俊辩”的不以为然间接地证明了他对崇尚虚务、一味谈玄持否定态度。《晋书》羊祜本传载,“从甥王衍尝诣祜陈事,辞甚俊辩,祜不然之,衍拂衣而起。祜顾谓宾客曰:‘王夷甫方以盛名处大位,然败俗伤化,必此人也。’”[11](P1017)据《晋书》王衍本传,王衍虽处重位,但“口不论世事,唯雅咏玄虚而已”。[11](P1236)其后晋室败亡,王衍终为石勒所害,似乎证明了羊祜的预见。羊祜所忧虑者正在于王衍终日清谈、不问事务的作风,这与儒家的踏实务实扞格不入,自然引起了羊祜的反感与警惕。羊祜告诫子女“无传不经之谈”,亦可看做是对清谈的否定,由此也不难推测羊祜《老子传》的基本立场。
由此可见,羊祜的思想包括儒、道两个方面,儒家思想无疑占据主导地位。从其人生实践来看,羊祜并没有调和名教与自然,而是儒、道分立,各有所用,儒以用世,道以全身,表现出羊祜的政治家本色。但在羊祜这里,儒、道的分立并不是绝对的,儒家思想固然主导着羊祜价值观的基本方面,但老子的自然哲学也并非仅仅作为全身远祸的理论武器,而是逐渐向主体价值渗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羊祜的精神趣味。具体而言即羊祜思想中老子的自然观呈现出一定的玄学化趋势,并外化为山水审美意识。据《晋书》本传,“羊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11](P1020)蔡英俊在《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中说,“缘于道家哲学传统的点明,魏晋人从追求玄远的风气中,找到了一个解决自我生命之安顿的方案:因于‘自然’。而此一形而上意义的‘自然’,又具体化为山水的世界,而成为抒情的自我寄托情的世界”。[18](P11)羊祜初步的山水审美意识显露出羊祜的价值观向“自然”方向的转化趋势,但这种转化远未完成,羊祜并未把“自然”作为安顿生命的方案,因此也就没有陶潜那种“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19](P50)的从容潇洒。然而在玄学大畅的背景下,羊祜的文化视野及价值取向不可能完全囿于儒家范围而不与玄学相通,在践行儒道、追求事功的同时,亦不排除羊祜对生命本体意义的感悟与思索,并可能超越“三不朽”的价值层面而达到更为形上的哲学高度。
《庄子》外篇《知北游》有云:“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未毕也,哀又继之。”[20](P845)余英时认为,“(魏晋)士大夫之怡情山水,哀乐无端,亦深有会于老庄思想也”。[8](P293)无穷的宇宙与渺小的生命之对比极易诱发强烈的生命悲感,诚如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所谓“天高无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21](P305)羊祜在深广的宇宙背景上所产生的情感体验与儒家“三不朽”并不处于同一精神层面,因此邹湛之宽慰不免有风马牛之嫌。它表明儒家“三不朽”因其等而下之的功利性,不可能全然消解老庄哲学所带来的生命悲感。
于是“三不朽”与自然观之间便形成了一种文化张力,这种张力事实上造成了羊祜这类以儒立身的士人的价值焦虑,他既固守“三不朽”的原始价值,又企图超越它而上升到更高的本体境界,而其对儒家原则的固守及对“虚妄浮诞”的玄风的排斥又使这种超越成为不可能。这种固守而不甘、超越而不能的心理矛盾恐怕正是羊祜岘山感怀的深层文化原因。这也可以看做是“三不朽”的价值观在魏晋玄学背景下的一种尴尬处境。而恰恰是这种价值矛盾,赋予了“堕泪碑”以其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后人“来到这座碑前流泪”,并非仅为怀念羊祜的“盛德”,而是因为“回忆起了他对无名先人的回忆”。[22](P29)后人正是在对羊祜创造的历史情境的不断复原与重温中体验生命的悲剧意味,追寻生命的终极价值。堕泪碑因而就超越了“三不朽”的价值层面而具有更其深邃的文化意蕴。
[参考文献]
[1]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80.
[2] 刘畅.三不朽:回到先秦语境的思想梳理[J].文学遗产,2004(5).
[3] 范晔.后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大16开精藏本).
[4] 班固.汉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大16开精藏本).
[5] 日知录集释[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6] 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7] 徐震堮.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
[9] 郭茂倩.乐府诗集[C].北京:中华书局,1979.
[10] 萧统.文选(李善注)[C].长沙:岳麓书社,2002.
[11] 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95.
[12] 徐复观.心的文化[A].中国思想史论集[C].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
[13] 楼宇烈.王弼集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0.
[14]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15] 董志安.唐代四大类书·艺文类聚[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
[16] 冯达甫.老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17]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1.
[18] 蔡英俊.比兴物色与情景交融[M].转引自龚鹏程《汉代思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19] 孟二冬.陶渊明集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
[20] 王叔岷.庄子校诠[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1] 王勃.滕王阁序[A] .古文观止[C]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2](美)宇文所安.追忆[M].郑学勤.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