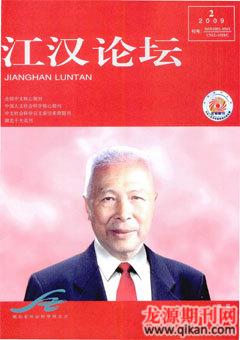杜诗三笺与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
丁功谊
摘要:明末清初,钱谦益三笺杜诗:《读杜小笺》以史证诗,《读杜二笺》以诗正史,《钱注杜诗》以诗补史。三次笺注贯穿的诗史互证精神,对其晚年创作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钱谦益;杜诗三笺;诗史观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09)02-0100-03
钱谦益,明清之际著名的文学家、学者,其诗文创作与文学主张对明朱清初的文坛产生了较大影响。他先后三次笺注杜诗,时间跨度近30年。从三笺杜诗的学术活动中,我们可以考察出钱谦益诗史观的深化过程。
一、《读杜小笺》:以史证诗
崇祯六年(1633年),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诗史”观。他在《郑典设自施州归》笺注中说:“施州,裴冕也。冕性侈靡,好尚车服及营珍馔。每会宾友,滋味品数,坐客有哨声于名者。二诗记汧公、施州事,皆诗史也。”“二诗”是指此诗及《赠李十五丈别》,钱谦益认为它们真实地反映了裴冕等人的事迹,故可称之为“诗史”。
关于钱谦益的“诗史”观,我们还可在其序跋中找到有关论述。崇祯四年(1631年),他在《跋汪水云诗》中说:“《湖州歌》九十八首,《越州歌》二十首,《醉歌》十首,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他认为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堪称诗史。
钱谦益认为杜诗有诗史意义,这确实把握了杜诗的真精神。杜甫“三吏”、“三别”、《北征》等诗为史诗中之名篇。五代以来,杜诗即诗史成为许多士人的共识。五代孟棨在《本事诗·高逸第三》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宋代欧阳修等人编撰的《新唐书·杜甫传》云:“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白宋以来,杜诗即“诗史”之论为人们所理解,并促使了“诗即史”观念的产生。宋人严粲《诗缉》卷二十二“鼓钟刺幽王”条云:“然古事亦有不见于史,而因经以见者,《诗》即史也。”明人何楷《诗经世本古义》卷首,明人朱朝瑛《读诗略记》卷四“鼓钟”条均引用严粲此句。宋代以来,严粲诸儒以《诗经》补史,体现了古老的诗、史合一的传统。元人刘养吾则明确提出“诗即史”,其《送钱方立游荆二首》(其一)诗云:“阿年耆旧谁家传,一代衣冠又古丘。乱后题诗诗即史,未应轻付水东流。”
正是在诗史观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背景下,钱谦益在《读杜小笺》中提出了他的诗史观,即以史汪诗,并在笺注中多次运用。如《投赠哥舒开府》诗注,引用天宝十一年哥舒翰与安禄山同到朝中事迹,笺释“受命边沙远,归来御席同”句;《上韦左相》诗注,引天宝十三年杨国忠精求端士事,笺释“霖雨思贤佐”句;《塞芦子》诗注,引安史之乱时,史思明兵进太原而致崤、丽空虚渚事。笺释“崤、函盖虚尔”句。这样的笺注,在《读杜小笺》中俯拾皆是,反映出钱谦益“诗可传史,史可证诗”的诗史观。
二、《读杜二笺》:以诗正史
崇祯七年(1634年),钱谦益作《读杜二笺》。在《渎杜二笺》中,钱谦益在以史证诗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笺注方法,即以诗正史。这主要体现在他对杜甫《洗兵马》主旨的阐释。
在《读杜小笺·洗兵马》笺注中,钱谦益认为肃宗诚心思父,迎玄宗于巴、蜀,后因李辅国谗间,遂有移仗之事:
郭湜《高力士传》云:辅国趋驰未品,小了纤人,一承攀附之恩,致位云霄之上,欲令猜阻,更树勋庸。移仗之端,莫不由此。与公诗意正相脗合。关中即留萧丞相,谓房琯也。瑁自蜀奉册,留相肃宗,故曰即留也。张子房谓张镐也。时镐方代琯为相,故曰复用。琯与镐皆玄宗旧臣,遣赴行在,肃宗用之而不终者也。钱谦益引用郭浞《高力士传》,把房琯罢相之因归咎于李辅国谗间,这用的是以史证诗的方法。后来钱谦益修改此论,在《读杜二笺·洗兵马》笺注中,撕开了肃宗温情的面纱,认为肃宗尽孝迎父为假,猜忌囚父是真,玄宗移仗之根本原因不在于李辅国谗问,而在于肃宗为了皇权而不尽孝道。他把批判的矛头直接对准肃宗:
呜呼!伤哉!公以上疏救房琯,自拾遗移官,流落剑外,终身不振。此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唐史有隐于肃宗,归其狱于辅国。而后世读史者无异辞。司马公《通鉴》乃特书曰:令万安、成宜二公主视服膳,四方所献珍异,先荐上皇。呜呼!斯岂李辅国所谓匹夫之孝乎?何儒者之易愚也?余读杜诗,感鸡鸣问寝之语,考信唐史房琯被谮之故,故牵连书之如此。并探究出《洗兵马》之主旨: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钱谦益此论可谓意味深长:第一,读诗首先要学会知人论世,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挖掘人物的性格与内心,才能得出正确的主旨。杜甫因上疏救房瑁导致四处飘零、终身不振。当朝廷清洗旧臣之际,杜甫上疏论救,非不察也;言微人轻,卷入党争,非不智也,是儒家“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的信念支撑着杜甫,而上疏之举成为杜甫日后命运多舛的一个转折点。第二。读史而不能尽信史,房瑁并非浮薄之臣,肃宗并非孝顺之君,《通鉴》并非完全真实,以史证诗可能误解诗人的心曲。
钱谦益两次笺注,使《洗兵马》诗旨发生巨大变化。《读杜小笺》把房琯被贬归咎于佞臣谗间,语气委婉,对肃宗有所回护;《读杜二笺》则直接刺君,显露肃宗之逆状,语气峭刻。在这种诗旨变动中,钱谦益赋予了诗史观更加丰富的内涵。那就是史可证诗之旨,诗也可正史之误。
三、《钱注杜诗》:以诗补史
《钱注杜诗》是钱谦益晚年重要的学术著作,也是其《读杜小笺》和《读杜二笺》学术思想的延伸和发展。与前两次笺杜不同的是,钱谦益晚年注杜时,已经做了清朝的子民。山河易代之悲,黍离麦秀之感,沉潜于胸,形诸于笔,使《钱注杜诗》出现了、充满了浓重的家国之思,具体表现为以诗补史观念的深化。
钱谦益在崇祯年间笺注杜诗,已经注意到诗歌记载的事情有时会遗落在史家的视野之外,即诗能正史。那么,他晚年的注杜则明确体现了诗能补史、正史的功用。如对《寄岳州贾司马六丈巴州严八使君两阁老五十韵》的笺注,《读杜二笺》云:“严武之贬,已见于贬房琯之制,而贾至以中书舍人出守汝州,《旧书》不载,他皆无可考。”《钱注杜诗》云:“至出守汝州,在乾元元年。《旧书》不载,皆无可考。……当据此诗,以补唐史之阙。”二笺相较,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明确提出杜诗可补唐史之阙,其以诗补史的意识更加强烈。
在《钱注杜诗》中,这样的以诗补史的事例不少,如《览柏中允兼子侄数人除官制词因述父子兄弟,四美载歌丝纶》笺注:“此诗云:‘方当节钺用。必茂琳,非贞节也,史既不详,而《通鉴》尤为阙误,故详辨之于此。”又如《九日奉寄严大夫》笺注:“宝应元年四
月,代宗即位,召武入朝。是年徐知道反,武阻兵,九月尚未出巴。《通鉴》载六月以武为四川节度使,徐知道守要害拒武,武不得进,误也,当以此诗正之。”钱谦益以此两首诗补《通鉴》之阙,又正《通鉴》之误。可以说,钱谦益《钱注杜诗》中的以诗补史的诗史观,是其《读杜二笺》以诗正史的诗学观的发展和深化。
我们还注意到,相较于《读杜小笺》,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有意识地将诗史观与杜诗写作技巧有机地结合起来。在《钱注杜诗·秋兴八首》笺注中,钱谦益加强了对杜诗组诗篇章结构的分析,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充分表现了杜甫的写作技巧:第一,错综互举,重重钩摄。题下笺日:“此诗一事叠为八章,章虽有八,重重钩摄,有无量楼阁门在。今人都理会不到,但少分理会,便恐随逐穿穴。如鼷鼠人牛角中耳。余义则更于分章下详之。”其八笺曰:“公诗如骇鸡之犀,四面皆见,故错综互举,以告知者。”钱谦益有些自诩,认为自己独得杜甫的作诗之秘,在钱谦益看来,《秋兴八首》中每首诗既可独立成篇,又章章蝉联;既章章蝉联,又遥相呼应。每首诗都指向一个主题:“每依南斗望京华”,八首诗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第二,事讫重申,章重事别。后四首体现了叠章的写法:都是写长安,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回首可怜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这个主题,而这个主题又服务于“每依南斗望京华”这个总主题。后四首既是八首之结尾,又是一个有机的、独立的小单元。第三,工于起兴,善于承接。“玉露凋伤枫树林,巫山巫峡气萧森”是第一首诗之起兴,第一首诗又是《秋兴》全篇之起兴。“末二句,结上生下,故即以‘夔府孤城次之”,“今谓‘昆明一章,紧承上章‘秦中自古帝王州一句而申言之。……于上章末句,克指其来脉,则此中叙致,褶叠环琐,了然分明”。钱谦益非常注重诗与诗之间的过渡衔接。
钱谦益对杜诗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是与其诗史观紧密相联的,即诗人要担当起“诗史”的称号,必须具备极强的叙事能力。在动荡的年代里,诗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会让诗歌承载起以诗叙史的任务,而在一个诗缘情的国度里,诗歌的叙事功能并不发达,诗人们对叙事技巧并不讲究,如何让诗歌更好地发挥叙事功能,成为摆在诗人面前的一个课题。所以,我们就能理解钱谦益为何以“铺叙排比”为杜诗的一个鲜明特点,为何对杜诗写作技巧极其重视。他对《秋兴八首》篇章结构的独特分析,实际上也回答了明人胡应麟提出的一个问题,胡氏说:
四言之赡,极于韦盂。五言之赡,极于《焦仲卿》。杂言之赡,极于《木兰》c歌行之赡,极于《畴昔》、《帝京》。排律之赡,极于《岳州》、《夔府》诸篇。虽境有神妙,体有古今,然皆叙事工绝。诗中之史,后人但知老杜,何哉?胡氏也是从叙事技巧而论,他提出一个疑问,千载而下,叙事绝妙者不乏其人,为什么只有杜甫能担当起“诗中之史”的称号呢?而牧斋对《秋兴八首》写作技巧的分析,实际上回答了胡氏提出的这个问题,那就是《岳州》、《夔府》等排律表现了杜甫卓绝的叙事能力,《秋兴八首》等抒情性质的七律也表现出杜甫谋篇布局的高超才能;杜诗之难,不仅难在排律上,还难在七律上;七律之难,不仅难在声凋字句,还难在能够涵括巨大的历史内容。杜甫正是以七律诗,完美表现了诗歌叙史和诗歌补史的艺术功能。
四、诗史情结与诗歌创作
从《读杜小笺》到《钱注杜诗》,钱谦益诗史互证的精神一直贯穿于其中。这种精神来源于“诗可以观”传统的儒家诗教。《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公子季札到鲁同观周乐的事迹,季札从反映政治盛衰的角度来批评《诗经》诸作,这种批评方法开启了后世以“诗史”论杜甫的法门。钱谦益也是从“诗可以观”的视角来论杜诗,他在《学古堂诗序》中说:“余往与泾华数子言诗,以为自汉以来,善言秦风,莫如班孟坚,而善为秦声者,莫如杜子美。”从杜诗中可以观出秦声、秦风,他在《王元昌北游诗序》中对杜诗中的秦声作了解释:“秦之诗,莫先于《秦风》,而莫盛于少陵,此所谓秦声也。自班孟坚叙秦诗,取‘王于兴师及《车辚》、《驷铁》、《小戎》之篇,世遂以上气力,习战斗,激昂噍杀者为秦声。至于近代之学杜者,以其杜诗为杜诗,因以其杜诗为秦声,而秦声遂为天下诟病。甚矣世之不知秦声也!”他认为杜诗中的秦声并不是那种充满兵象之音的秦声,而类似于《诗经·秦风》中的篇什。杜诗温柔敦厚,婉而多风。杜诗多风,从杜诗可看出开元、天宝至大历年间的政治之兴衰,唐帝国如何从盛世一步步走向衰微。而当钱谦益也不由自主地卷入历史的漩涡中,身经天翻地覆的朝代更迭,激烈动荡的社会动乱时,他会更深刻地感受到诗歌与时代政治的密切关系。而正是这种感受,极大激发了钱谦益以诗观风、以诗存史的诗学思想。
钱谦益晚年在《有学集》中,也多次流露出他的诗史情结。顺治八年,他在《浩气吟序》中说:“鼎钟铭勒,岂徒托诸诗史,终有考于斯文。”钱谦益作此序文以悼念他的门徒瞿式耜;作于顺治十三年的《金陵杂题绝句二十五首继乙未春留题之作》(其十四)诗,云“闽山桂海饱炎霜,诗史酸辛钱幼光。束笋一编光怪甚,夜来山鬼守奚囊。”钱谦益此诗写给抗清义士钱秉镫;作于顺治十八年的《王奉常烟客七十寿序》云:“余定陵老史官也,佩文肃琬琰之遗训,故记斯宴也,亦用史法从事。诸子有志于古学者也,作为歌诗以祝寿,岂亦将取征诗史,耻为巫祝之词,则余之志其不孤也矣!”钱谦益作此序以纪念他的老师王图,钱谦益晚年还念念不忘自己老史官的身份。我们注意到,这种诗史情结与崇祯朝时的诗史意识有一脉相通的地方,即都是遗民心态的折射。《有学集·跋汪水云诗》称宋末汪元量诗写尽国破家亡之痛,“可谓诗史”。而当钱谦益也像汪氏一样身处朝代变革时,他过去的涛史意识就会转化为浓厚的诗史情结,这种浓厚的诗史情结也影响着钱谦益的诗歌创作。钱谦益晚年的《投笔集》,不仅体现了《钱注杜诗·秋兴八酋‘》中的创作技巧,更体现了其强烈的诗史观念。这里,我们以《投笔集·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为例,来观照杜诗三笺中的诗史观对其创作的影响。
《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写于顺治十六年,是时郑成功率主力北上,破瓜州,降镇江,前锋部队已抵达南京城下,复明运动出现转机。在这种形势下,钱谦益心情兴奋,写下这八首组诗。第一首,钱谦益以起兴开端,“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为此诗之起兴,此诗点明当时的抗清形势:郑成功水师势如破竹,直抵金陵。“长干如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两句,喑指战争平息。钱谦益希望复明运动能取得最后胜利,万户不再有离愁。此诗为全篇之起兴,奠定了全篇的基调。第二首,“十年老眼重磨洗”写出钱谦益十年的艰辛等待,钱谦益自顺治六年就开始受永历朝之命联络东南,至此正好十年。第三首基调高昂,“大火西流汉再晖”,喻指明朝宗室再兴。第四首,诗人从想象回到现实,情绪也转入低沉,开始描写内心之悲痛:“九州一失算残棋,幅裂区分信可悲”,山河沦陷,国家分裂。“局内正当侵劫后,人间都道烂柯时”,局势如棋局争劫,仍然难以预料,而人们的等待已经太久。“推枰何用更寻思”,战争还在继续,而复明之心义无返顾。后面四首诗的前六句都写抗清斗争,后两旬诗意都是诗人对自己的描述。其五写抗清将来之前景。其六写抗清目前之局势,其七写抗清战争之场景。其八写抗清意志之坚定,都是写抗清,但角度不同;虽然角度不同,但都结穴于“依然南斗是中华”这个主题。这种写法既体现了钱谦益笺注《秋兴》时所总结的“事讫而重申,章重而事别”即叠章的特点。又描写了当时真实的抗清时局。
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复明运动》中指出:“《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绝大著作也。”也道出《投笔集》诸诗在思想内容、篇章结构及以诗叙史等各方面都深得杜诗之精神。从顺治r六年到康熙二年,钱谦益在五年内创作出十三叠《秋兴》组诗,既充分表现了谋篇布局、铺张排比的高超才能,又传达出抗清的复杂局势及其内心深处的渴望和悲哀,实为明清之诗史。
钱谦益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弘扬了他在杜诗笺注中阐释的诗史观,他的注杜与学杜互为映证,紧密结合。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杜甫身后并不寂寞,八百多年后。钱谦益可谓少陵的真正知音。
(责任编辑刘保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