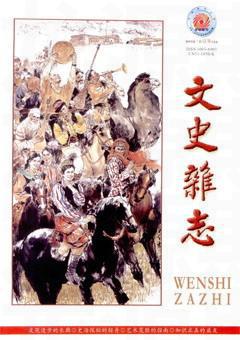张献忠屠蜀人数疑案
冯广宏

有关张献忠的不同评价
作为老一辈四川人,对张献忠无可回避;因“湖广填四川”事民间一直口口相传,追到源头总与张献忠脱不了干系。20世纪50年代以前,史界对此人多持否定态度,或斥之为“流贼”,鞑伐其“屠蜀”罪行;仅有少数史家持不同见解,如四川史界前辈任乃强1946年即曾著《张献忠屠蜀辨》,认为“史家通病”是“苟不慊于其人,天下之恶皆归之”;献忠屠蜀即是一例。“参验诸家。逊绎当时蜀人绝灭之原因,盖死于饥馑者什七八。杀于献忠者什一二而已。”不能说张献忠杀尽了四川人。文中还分析了张献忠的才能和性格,总结为6条:粗识文字,知人善任,颇有志略,轻率易怒,好用谲术,个性强毅。
20世纪50年代以后,史学界的评论渐趋一律:首先肯定张献忠是农民起义首领;但因他后来有与李白成分裂、摩擦乃至厮杀的情节,故而对他有所贬抑;更因张献忠曾接受明廷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还有人说张献忠是叛徒,是革命队伍中的败类。不过,在20世纪50-80年代中,“阶级斗争”理论始终指导着史学研究的大方向;涉及农民起义,大家总是措辞谨慎,“屠蜀”一事众所讳言,甚至曲为辩护。笔者所敬佩的一些师友,亦未能例外,盖因时势所使然。
对于张献忠其人,1981年版《辞海》中如此记述:
张献忠(1608~1646)明末农民起义首领。字秉吾。号敬轩,延安柳树涧(今陕西定边东)人。出身贫苦。初从军,因被人陷害革役。崇祯三年(1630)在米脂参加起义军。自号八大王,因身长面黄。人称黄虎。初属王自用,后自成一军。崇祯八年(1635)荥阳大会后,与高迎祥大举东征。攻破凤阳,焚明皇陵,转战豫、陕、鄂、皖各地。崇祯十一年(1638)。接受明兵部尚书熊文灿的“招抚”,驻兵谷城(今属湖北)。但拒绝裁减军队,不受调度。次年再起。崇祯十三年(1640)率部突围,进兵四川。用“以走制敌”的战术,拖垮敌人。次年,在川东开县黄城击破明军,继又出川,破襄阳,粉碎了敌人围攻。十六年(1643),取武昌,称大西王,旋克长沙,宣布钱粮三年免征,湘赣农民群起响应。次年,再取四川,他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即帝位。年号大顺,严厉镇压地主阶级的反抗。大顺三年(1646)清兵南下,他引兵拒战,在西充凤凰山中箭牺牲。
从辞条里,看不出张献忠屠蜀的一点迹象。他受明廷的招安,辞书上还打上引号,而且赶快表明他不属于投降派之列;也看不出他与李自成有什么摩擦。
1980年3月,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专门召开过“张献忠在四川”学术讨论会。会上一致指出,过去把张献忠说成“杀人狂”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诬蔑;至今无论城市农村,举凡四十岁以上的四川人,大多程度不同地受到过所谓“八大王剿四川”的传说影响;为此要拨乱反正,还张献忠以本来的历史面目。会议结论是:明末清初四川人口锐减,主要责任不能归之于张献忠;对于农民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问题,不能扬李抑张,也不能扬张抑李。
平心而论,积年以来史学界养成了一种倾左习惯,基本上不敢对张献忠稍有微词,即使是批评也尽量柔和;特别是面对四川人大多相信“八大王剿四川”的实况,不愿予以注意和剖析。从这一点,就使人怀疑史界到底有无违心之论?民间传说影响力究竟怎样形成的?“封建统治阶级”有没有那么大的能量可以加以操控?
不过在史学圈外,舆论便很有不同。
早在1935年,文化巨子鲁迅便在《病后杂谈之余》里说过:“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记载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着这‘流贼的凶残。”鲁迅认为张献忠“凶残”,显系受到封建人物记述的影响而未觉。
西蜀本土作家李劫人在《二千余年成都大城史的衍变》曾说:“成都经张献忠这一干,所有建筑,无论宫苑、林园、寺观、祠宇、池馆、民居,的确是焚完毁尽。但是也有剩余的:一、蜀王宫墙和端礼门的三个门洞,以及门洞外面上半截砌的龙纹凤篆的琉璃砖;二、横跨在金河上的三道石栏桥……总而言之,自有成都市以来。虽曾几经兴亡,几经兵火,即如元兵之残毒,也未能像张献忠这样破坏得一干二净!”李劫人认为张献忠是个彻底“破坏”者,显系从客观事实得来;但他并未像某些史学家那样怀疑过:会不会有人栽赃陷害?
著名作家成都人流沙河2004年所写《大屠杀之真相》,引四川人爱说的“言子”——“张献忠剿四川,鸡犬不留”;评价为“口碑记恶,代代承传,到我童年,故老犹说如此。”并且义愤填膺地指出:“1644年张献忠入川,四天沦陷成都,随即在成都平原拉开了一幕残酷的大屠杀。”“今天,翻开《蜀碧》、《蜀警录》、《蜀难叙略》等书,满篇血腥扑鼻而来。”流沙河认为张献忠是个大屠夫,显系听信了那些野史作者的话;但他却未像某些研究家那样,对他们做点阶级分析。
话说回来,如果张献忠真的屠了蜀,而且相当残酷;那么,他纵有千好万好,也不能抹杀掉这桩罪孽;更不能用各种赞歌来淡化他的过错——我想,这应该是史学家、文学家和其他学家,以及关心这类问题的人们所能接受的观点吧?
明史屠蜀人数荒谬引发争议
学者孙次舟据查继佐《罪惟录·张献忠传》指出:“张献忠入蜀以后,只有三次杀人较多。”“此外并没有别的记叙。这虽然也说张献忠杀人,但不只在人数上和《明史》所说大为悬殊,而且所杀的对象也和《明史》所记有根本的不同。”
看来张献忠在四川杀过人,已没有什么争论了;但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却有很大疑问——争论的焦点,在于杀人数量问题。《明史·流贼传》提供的数字是“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显然十分荒谬。
早在任乃强《张献忠屠蜀辨》中业已指出:《明史》说献忠屠杀蜀人六万万有奇,但又记万历六年四川十三府六州人口仅310万余,难道六十几年人口就增生200倍供他去杀?何况献忠所据之地,不足全蜀的三分之一,“虽合鸡犬计之。亦不能达此数”:驳斥得相当有力。
不过,在1980年以来的学术讨论中,某些权威研究家却抓住《明史》这一夸大得离谱的数字大做文章,借此推论清初所修史书之栽赃、诬枉;然后追踪到史料来源的《后鉴录》,说此书作者毛奇龄是个媚清的文化流氓;另一《绥寇纪略》的作者吴伟业,他的亲戚吴继善投靠农民军,后为张献忠所杀,而且他本人也没到过四川。言外之意,是指他们记述的屠杀情节和相关数字,纯属恶意造谣;而写《明史》那一段的人,也带有种种个人目的。这类分析明显已过了头,非客观史家之所当言,实难服众。
关于张献忠所屠的蜀人,权威研究者极力评断所杀者仅是“地主阶级的贵族和官僚”,以及各县“图谋暴乱的地主、绅士”;至于杀戮士子,则因他们进行间谍活动之故。总之,正义始终归于张献忠一边。讲到四川人口锐减的原因,权威研究者则着重
归结于明朝官军的“残害”,摇黄土暴子的“屠杀”,吴三桂和清朝军队的“血腥罪行”;谈到“八大王剿四川”的民间传说,便委之于统治阶级的编制谎言,进行文化垄断,实行愚民政策。这类论断,基本扎根于史料取材的倾向性上:凡是不利于张献忠的材料,或加以淡化,或设法贬斥;凡是有利于张献忠的记载,尽管十分零星,也充分肯定,反复引用,辅以推理。
采取两个“凡是”的研究成果,给了知识青年不少误导。有些人一开始对张献忠相当崇拜,对清廷极端仇视;等到学会了古汉语,看到大量明末野史原文,发现他们心目中的张献忠根本不是那回事,感到疑惑不解;再进一步查证,进而对张献忠产生反感,觉得过去未免有点幼稚。
中国人自古便有历史责任感的基因。比如住在江河边的人,遭遇空前巨大的洪灾,常将崖上水痕镌刻下来,并刻记洪灾年月,有时还加上一点灾情记述。这类民间洪水题刻,全国成千上万。刻记者基本是普通民众,当然也不乏地主官僚;但大家刻记洪痕,一不为名,二不利。推而广之,凡有大灾大难幸存者如果略知文墨,总想把全过程记载下来留给子孙,作为鉴戒;多数人觉得这是一种历史责任,别无他求。明清时期没有互联网,无法制造舆论,亦无公开报刊可以宣传观点;除了科举,做文章绝少成名得利的机会,刻印成书也相当困难。如果记录者抱有造谣诬蔑、欺骗后人的想法,那真是非常的不现实。因为他写的东西能否流传下来,并无多大希望;让子孙们知道先人曾经遭过劫难,也就够了。娄东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原叙》说明编写那部野史的意图,较有代表性:
寒夜鼠啮架上,发烛照之,则明季三王时邸报,臣畜之以为史料者也。年来幽忧多病,旧闻日落,十年三徒,聚书复阙,后死之责,将谁任乎?臣因是博搜见闻,讲求实录,刊讹谬,芟芜秽,补缺遗,类分为四十一篇。或曰:子之所言,皆信而无疑乎?曰:作《春秋》者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所见三世、所闻四世、所传闻者五世;世远,而闻见因以不齐,三传所以多庞也。兹虽采纪说,咨之耳闻,犹从及见之年。臣敢以自欺者欺人哉?执简之臣,不以忌讳于当时之士,谓狂言可矣。
当然,野史所记内容不一定全属亲历,也杂有大量传闻,必然存在失实之处,而且也不排除顺势夸大和想当然的笔墨;但却不大可能有故意编造、无中生有、栽赃陷害的东西。
章学诚说过:大丈夫纵然不能安邦定国,也该编史修志——这是不少知识分子的共同信念。野史中的第二手材料,多由这些想法衍生出来。除了少数人为了升官发财给统治阶级涂脂抹粉以外,多数作者大都按照传统的“史笔”、“史德”办事。国史体系对于维护“正统”非常重视,所以称胜利者为王,失败者为寇,不值得大惊小怪。将大量罪恶归之于失败一方,确是国史的通病;不过那些诬枉的地方是明摆着的,未加掩饰,易于判断。如果既不相信正史,也不相信多数野史,只凭一己之见有选择地挑出若干条史料来说事,显然不是客观研究的基本态度。贻误后生,在所难免。
明史屠蜀人数的来源探索
再寻找一下“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数据来源。研究者多以为见于毛奇龄《后鉴录》以及彭贻孙《平寇志》的“四路杀人说”。孙次舟认为:四路杀人说的编造者是冯甦,即《见闻随笔》的作者。其书载: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平寇志》无下一“八”字),女九千五百万(《平寇志》“九”作“五”)。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
上述1646年四路杀戮数据列表如下:

即按偏小的数字,总计也有65940万人之多,《明史》所记依据即在于此。这么惊人的数目,究竟从何而来?说老实话,讲它纯属凭空乱造,似乎又不太可能;因为即使要编,也要使人可信,不能编得太离谱。何况《明史》原文是“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意思说,那时杀人要评军功,结果报出那个大数,并不是据以记录在案。
关于这一点,有亲历经验的费密《荒书》说:丙戌二月,“尽屠川西、川北州县、以人手为功。凡贼验功之处,聚手如山;焚之,指节之骨,散弃满野。”
彭遵泗《蜀碧》则根据传闻说:贼每屠一方,标记所杀人数。贮竹围中,人头几大堆,人手足几大堆,人耳鼻几大堆,所过处皆有记。
存在这种军事记录,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史事。包括战利品、金银财宝,不记录怎行?何况杀戮数量又与军功挂钩。古往今来,多数军队鼓励杀敌,尽皆如此,何足为怪?
同样有亲历经验的欧阳直《蜀乱》(《蜀警录》)说:
每官兵回营,以所剁手掌验功。掌一双,准 一功。凡有军官衙门所在,手掌如山积;而成都城内人掌,则更几于假山之万叠千峰矣。
尝见一札,付自副将升总兵:其札头空白处,用朱笔细字备注功级:算手掌一千七百有零。呜呼惨哉!即此推之,他更可知也。
欧阳亲眼所见文书,写下那人计杀1700多人,以手掌为凭,从而由副将升成总兵。这条史料十分可贵。欧阳此书研究者经常引用,总不至于说他在凭空编造吧?类似他这样的说法,实不知其凡几。沈苟蔚《蜀难叙略》说过:
每贼日须首级,或二三,或四五,多寡以地方大小繁简论,如式乃已;不,则亦杀之。后利其轻。代以手鼻;其数亦如之。死者数千万,骨肉如山,累累相望。”
孙錤《蜀破镜》也说:贼约:凡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子倍之。以手足为记。兵以上官,较次进级。不者,当以大逆无道论死,妻孥坐戮……其编裨不忍行诛,多自经于野树。
这说明军士杀人,也有点迫不得已!
由此可见,张氏农民军四路,显然把屠戮民众也算做军功了。难怪大家要“上功疏”,以公文形式呈报杀戮数量;因实际上无从核查,其中任意夸大,虚报冒领是必然的情况。近至20世纪50年代大跃进,一亩田的产量本来只有几百斤,后来上报到几万斤,居然夸张百倍,可见这种事情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看来,“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的惊人数字,应该基本上来自农民军的文档。如果说那是有意编造,则野史作家与农民军统领应各负一半责任。作家审查不严,把关失察;统领虚报浮夸,贪功希赏。
大西军究竟杀了多少四川人?研究家所信任的《罪惟录》说一次杀了“数千人”;《蜀碧》说一次杀了“近万人”;《荒书》说一次杀了“一万七千人”;《绥寇纪略》说一次杀了“二万二千三百人”。在明末清初仅有300万人口的四川,若按任乃强教授“什一二”的估计,至少也应该杀人30万;所以《蜀记》所言共杀“三十余万”,应该是个合理的数字。
张献忠的本来面目在前代有了一次扭典,经过现代研究家翻案又翻过了头,再一次被扭曲,真有些不幸。不略作厘清,良心何在?
作者: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成都)馆员
——解码四川人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