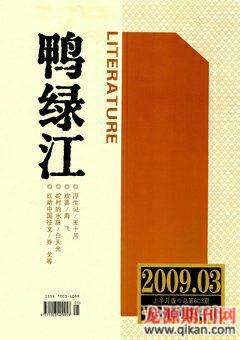水鸟
张羊羊,七十年代末生于江苏武进,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习作散见《散文》《山花》《鸭绿江》《天涯》《作品》《青年文学》等,有诗集《从前》出版。
水老鸦
截青黛色的石板码头伸入水的内部,被水孕育的另一种生命——绵滑的青苔覆裹在它的表层。盛夏。一个皮肤晒得黝黑的孩子小心翼翼地踩在码头裸露的部分,根据水位的深浅,或蹲身,或趴下,或双膝跪着,无论哪一种姿势,他必定是用双手并拢弯成半碗状,捧起清凉河水,美美地喝上一口,以消减酷暑的燥渴与炎热。捧,一半虔诚一半敬畏,仿佛出生时已渗入骨髓里,以恩谢水对于一个碳水化合物而言的珍贵补给。这个孩子曾在码头边发现过太多的乐趣,锁定码头一侧的目标,双手轻轻伸入水中,掌沿沿着一条板石郎(华鳏)悄悄挨近,围拢,小鱼离水后一个劲地蹦蹿,然后随手扔入水中;或者淘箕淘洗米时没入水中二十厘米,弥散的白色米浆吸引越来越多的小鳑鲏,趁它们尽情享用时,猛地提拉出淘箕,有时候米上有十几条
鳑鲏之多。接着再放入水中,任受惊吓的小鱼游去。
水。鱼。苏南水乡的重要组成元素。有水,有鱼,也就有网。苏南用网捕鱼的方法很多:挺丝网,丝网宽度几乎占河面的三分之二,丝网下面间距均匀地缀有铅块,拿根竹竿南面敲几下,北面敲几下,一会儿工夫就有鱼撞上来被卡在网眼里;撒网,左手握住一圈尼龙绳,右手握住鱼网(褐黑色麻线编织)甩几下,抛出一个尽可能大的包围圈,抛网时左手配合速度放线,等铅块拖着网沉到水底,再慢慢收紧尼龙绳,拖上来,有鱼,也可能是烂树枝、破砖破罐头;扳网,一种用木棍或竹杆做支架的方形大鱼网,通过支架,轱辘,糅合了滑轮的原理,但仍需要很大的劲才能把网扳离水面,如果四个罾角刚刚起水你已没有了力气,大一点的鱼还是能逃窜的……
我的叙述至此该奔向主角了。鸬鹚,也叫鱼鹰,家乡叫水老鸦,帮助渔民捕鱼的猎手。鹰,给人一种凶残、暴戾、桀骜不驯的印象,鱼鹰为何温顺地收拢翅膀,甘愿在一条渔舟上听命呢?不得不惊叹人类驯化动物的能力、天赋和智慧,即便极其凶残的动物也能俘虏,从“野生”的那支分离出来乖乖地为人类的利益效命,然后为其取个比原名听来善良多了的名字。早在秦汉时期的《尔雅》、《异物志》等书中就有“鸿鹤入水捕鱼,湖沼近旁居民多养之”的记载,经过一代一代的努力,于是有了“南方渔舟往往縻畜数十,令其捕鱼”的繁荣。
水老鸦黑羽,带紫色金属光泽,肩羽和大覆羽暗棕色,比鸭狭长灵活。嘴粗长,最前端有向下的锐钩,喉下那个能暂存捕捉到的鱼的皮囊,似乎就为了归顺人类而生。水老鸦下水前主人会用细绳圈扎住它的皮囊下端,捉到的小鱼如果能滑入喉管可以自食,大一点的鱼由于颈部圆圈所限使它只能将鱼衔在宽大的口腔里却不能咽入胃中,于是像个乖孩子般交到船上来。主人眼疾手快地一手抓过水老鸦,一手把鱼扔进鱼篓。水老鸦之间的配合也令人惊讶,遇到大一点的鱼,几只水老鸦会齐心协力,叼住大鱼游向船边,主人用网兜把鱼捞进船舱。“船头一声鱼魄散,哑哑齐下波光乱。中有雄者逢大鱼,吞却一半余一半”,这是明末清初布衣诗人吴嘉纪(江苏东台人)在《捉鱼行》中对水老鸦捕鱼的一段生动描写,虽然描写的是白洋淀的水老鸦,其实和苏南的情形大致相似。
记得儿时每逢听到“嘎呀嘎呀”的水老鸦叫唤声从附近河面上传来时,村里的男女老少会争相跑过去看热闹,欢呼不已宛然成了水老鸦捕鱼的拉拉队。一只只水老鸦姿态不一,但都雄赳赳气昂昂地整装待发。待小木船停在河中央,渔人便手握长长的竹篙,不断地拍打水面,他两脚叉开,一轻一重地左右晃动船板,把河面荡得水花飞溅。一声吆喝下,水老鸦一个个扎入水中开始捕鱼,当水老鸦争先恐后地叨着活蹦乱跳的鲫鱼、翘嘴鲦、鳊鱼、白鲢、草鱼……交给主人时,小孩子更是兴奋不已,恨不得跳入水中和水老鸦赛上一场。
《武进县志》曾记载,解放前武进县的渔民有两种:一种是依靠捕捞收益为生的专业渔民,另一种是副业渔民,大部分在滆湖附近,农忙务农,农闲捕鱼捉虾。专业渔民以原籍和生产方式的不同分成若干“行帮”。比如苏州帮用刀鱼网、鲥鱼网捕捞,镇江帮使用春花网,常州帮驱鱼鹰捕捞、摸鱼。在“内河捕捞工具”也记载了“鱼鹰,捕捉大小杂鱼”并归入常年性捕捞工具。然而我年幼时还能常见的这种捕鱼方式在南方水乡几乎绝迹了,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故?在南方,我已很难找到一条洁净的河流,它们灰暗,长着一张生锈的脸,病怏怏地卧在故乡不再肥沃的土地上,等待现代工业催生的城市的最后审判。
今日无意中翻到一张照片,我头戴竹篾编织的斗笠,肩上一根担子,两头各站只水老鸦。那是二零零六年夏天,我从漓江的游船上下来,在去阳朔西街的码头边拍的。那天我二十八岁生日,可能有整整二十年没见过水老鸦了。《禽经·王雎》说“王雎、雎鸠,鱼鹰也”,晋张华注:“毛诗曰:‘王雎,挚而有别,多子。江表人呼以为鱼鹰,雌雄相爱,不同居处。《诗》之国风始《关雎》也”,我常把《诗经》看作一部动植物的小百科全书,没想到掀开《诗经》第一页的居然是水老鸦。
翠鸟
英国摄影家迈克·莫克勒有幅1994年获世界野外摄影大赛奖的作品《囫囵吞虫》,一只翠鸟稳稳地站在一块色彩斑斓的大石头上,正张大嘴巴将一只不知名的昆虫纳入嘴中。这幅画有点令人费解,因为翠鸟没有丝毫的捕捉动作,仿佛那只昆虫有足够的献身勇气。作品配有简单的文字说明:甲虫因为其丰富的蛋白质含量而成为许多动物口中的美食,这只欧洲(蓝胸)佛法僧就正在坦桑尼亚的塞伦盖蒂国家公园里享用一顿甲虫美餐。佛法僧长有艳丽的蓝色翅膀,粗壮的躯体及钩形喙,它们喜好攻击,尤其以擅长在繁殖季节中翻滚旋转的飞行而出名。
如果没有文字说明,我极易把这幅画的背景设置为中国东部水乡的一个普通角落。然而画面上的鸟叫佛法僧,与翠鸟长得极为相像,嘴长,矮小短胖,仔细比较才发现我所见的翠鸟背、翅、尾为亮蓝色,腹部棕栗色,嘴、腿为赤红色;而这只佛法僧的羽色略有挪移,胸为浅蓝色,背部赭棕黄,翅膀深蓝。在鸟纲中我对佛法僧这一目颇为好奇,这名称似乎和宗教扯上些关系。据说“佛法僧”这个名字是由日本传过来的,当时如此命名是因为它们的叫声很像日语“佛、法、僧”的发音,便用了这三个字来命名。后来却发现发出“佛法僧”叫声的是东方角鸮,看见的则是另一种鸟。于是将错就错,佛法僧的名字就继续沿用了下来。而“佛”、“法”、“僧”正是所谓的佛门三宝,因此它又有了“三宝鸟”的别名。日本只有三宝鸟属,而中国还有佛法僧属,这个名字传到中国后,我国就把一个属叫做三宝鸟,另外一个属叫做佛法僧。
翠鸟就属于佛法僧目。在水乡,我没有见过比翠鸟更漂亮的留鸟了。当成群结对的麻雀风般卷过田野或栖息树林时,叽叽喳喳声里窜出一声银铃般的“唧——唧——唧——”抛物线般落向小河边的芦苇丛中。我不复再来的童年总是天空晴朗:在风里赤足奔跑的孩子沿河岸追逐着一只翠蓝色的精灵,他很小就拥有了对美的认识和渴望。他停下喘气,那只小精灵也在一定的距离处停下,站在纤柔的芦苇尖上,上下起伏。他永远记得小精灵清澈的眼睛,那是会说话的眼睛,他到现在还能感觉到它音乐般的心跳。值得一生怀念的童年可能源于类似的对峙片断,如初恋般纯美。
翠鸟机敏伶俐,冷不防地闪入你眼帘,贴水疾飞,多像水乡一个闪亮的动词!然后找一个停歇处耐心注视水面,一有动静,它像箭一般射向水面,离水时尖长的红喙已经牢牢叼住一条挣扎的红眼鳑鲏或板石郎(华鳏)——一名有的放矢的聪颖猎手!如此画面,早在唐人钱起《衔鱼翠鸟》里就有过令人惊叹的生动描述:有意莲叶间,瞥然下高树。擘波得潜鱼,一点翠光去。“一点翠光去”可谓笔追清风心夺造化,钱起算是把翠鸟捕鱼的一瞬写绝了,如雅克贝汉善用的一组细微小镜头,这逼真一幕绝非丹青高手能挥洒到传神至致的。
冯梦龙有《翠鸟移巢》,讲的是翠鸟先把巢筑得高高的以避免祸患,等生了小鸟,特别喜爱它,唯恐它从树上掉下来,就把巢做得稍稍低了一些;等小鸟长出了羽毛,翠鸟更加喜爱它了,又把巢做得更低了一些,于是人们就把它们捉住了。这个寓言式的故事可以多角度地去理解,至于这个习性翠鸟好像没有。倒有一个至今未曾实现的愿望令我耿耿于怀,就是摸一摸翠鸟翠蓝发亮的羽毛。我留意过翠鸟喜欢在岸旁洞穴营巢(也有在土崖壁上凿穴为巢),以致终于发现了一个翠鸟的窝。窝口直径五六厘米的样子,有些杂草遮掩。我扒开草,随手抓过一块瓦片,稍倾斜用其棱口一圈圈地扒大洞口。我细幼的胳膊慢慢伸进去,洞壁冰凉冰凉的,怀揣激动与几丝慌张,却未能够到底。也许那天那只翠鸟未在家中,也许它就蜷缩在离我的欲望半厘米的地方惊恐地看着如它身体般大小的拳头。也许吧,我试过几次后那只翠鸟就搬离了危险的地方,夕阳下一个家门变得无限荒凉。
翠鸟还有个名字叫翡翠,“翡翠形如燕,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我却没见过那只翠鸟有过伴侣,有过孩子。我的印象中就见过那么一只翠鸟,它孤单、冷漠,是苏南留鸟中的异数,从不和邻居打招呼,独来独往,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它却仿佛热衷于享受内心世界的宁静。如我今夜念想翠鸟时,或者说循着记忆里几近模糊的痕迹难以写下详述的文字时,我才觉得过多地掺合于热闹的江湖其实挥霍了太多属于自己的时间。
那只翠鸟早已飞离了我的视野,在江南,我分外想念久未谋面的它,如果某年某月某日于某个地方它能突然出现在我眼前,那感觉定像再次相逢第一个深爱过的姑娘一般。因为她和它的存在,我的记忆里还闪现着色彩鲜艳的柔软部分,那是生命之初的纯净底色,不同于生活的光怪陆离,杂沓,眩晕,早把我抽打成一个身不由己的陀螺。而翠鸟低调的性格让我懂得了一个简朴的道理:与这繁杂世界过于亲近的麻雀往往乐极生悲,“唧——唧——唧——唧——”之声虽单薄,却是属于自己的独特声音,这被世界疏忽的细微之声却在默默地酝酿着否极泰来的无限可能,那么我为何也不平静为一个单数?
野鸭
那确实是一只野鸭,翅膀笨笨的,让人心悬着会不会跌下来,在我的视线里缓慢飞入铁栅栏内的一片草丛,我把这看作城市的一个重要事件。差不多五年的时间,光阴之手轻轻抹淡了这片树林的人造痕迹,栽植者印在每一株植物躯干上的指纹已被风雨洗净了,它们过得越来越像自己。我每天穿梭这里两次:早晨与傍晚。这里只有常见的麻雀、喜鹊和燕子,偶尔几只黑羽红嘴的八哥露露脸;这一年来,许多不知名的鸟儿突然欢聚这里,我一点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甚至时常窘迫于对汉字储备的不够和对其运用的笨拙,我真的无法用精确的汉字来表达一只鸟的声音,哪怕是单音节的。
野鸭是典型的水鸟,家乡是典型的水乡,遗憾的是我未曾在水乡见到成群的这种水鸟。儿时也常能遇见一只野鸡野鸭,或一只野兔什么的慌慌张张隐入稻田,可是,依然有乡间猎人的身影尾随着这些动物单薄的量词。于是想起高晓声的一篇文章,他说他叔叔看见他手里拿的宝贝野鸡蛋时不屑一顾地说,从前每年秋天有大群的野鸭子从这里飞过,天晚了就在芦苇里宿夜,天一亮便飞走。这时候如果有人进芦苇塘去,就交了好运,塘里雪白雪白铺了一层,一个人光捡也得捡大半天,一箩一箩装着,放在船里运回来,白花花的像一船银子……这文字读得挺馋人的,倒不是琢磨野鸭蛋的味道究竟怎样,闭目想想捡拾的过程也实在是一种乐趣。
常州的金坛有个长荡湖,也叫洮湖,没去过,只知道盛产螃蟹。当地有个民谣,每当白露过后,野禽成群而至,有“飞起不见天,落下盖湖面,天寒三日冻,一塘数百连(一连为六只)”之说,我猜这民谣里的景象大概也在高晓声叔叔所描述的时间之前了。听说武进的滆湖上现在各种水鸟也越来越多,可能是这几年倡导生态环境给了已处穷途末路的鸟类一丝喘息的机会。滆湖离得不远,惭愧的是一直没找机会去走走,但那些刚缓过神的水鸟,又被好食之徒盯上了。好几次有人邀请去滆湖的渔船上吃饭,没成行,说是船上做的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鱼、虾、螺蛳之类的水产,还有就是野鸡、野鸭之类野禽,挺诱人的。人家也送过我几只滆湖上打的鸟,纯黑色羽毛,我没敢处理。父亲用平常处理鸡鸭的方法,开水烫一会,再拔毛,却没想到一只小鸟费老大劲也没清理干净。邻居说只要直接撕皮就行,果然三下两下就光溜溜的了。油爆后,夹了块也没吃出多好的味道来,竟有了份暴殄天物的内疚。我想象站在滆湖边看它们飞,比吃它们要心情愉快得多。
差不多两年前的冬天,有友相邀去瓦屋山玩。瓦屋山不是四川的那个森林公园,在常州的金坛、溧阳和镇江的句容三地交界处。我到的那块在句容界内,站在水库大坝看青山碧水着实一下子来了精神,幽静,清朗,湖光山色如小楷般娟秀,分明可以感觉到好客的大自然正送来款款情意。我们去的目的地是被湖面围住的一个半岛,好像叫承仙山庄,有一艘快艇接送。快艇其实开得不快,在湖面上晃了一圈让我们看看四周风景。那天阳光不错,湖面上却弥漫着淡淡的雾气,水面上的几只野鸭和盘旋的白鹭被慢慢逼近的噪音和波浪惊了一下,又飞远了一点。无论我的内心多么想接近它们,总在一定距离的时候被它们毫不客气地拒绝了,蛮好的兴致一下子变得郁闷起来。于是我也成了从餐桌上认识它们的一员:野鸭煲。野鸭是腌制过的储存品,炖是炖得透烂了,放进嘴里没嚼头,配料绿笋倒挺好吃的。喝口汤吧,也不见得比家鸭煲出来的鲜,现代饮食很多时候会被丰富的调味佐料愚弄。
我看见的那只野鸭可能就是从滆湖边飞过来的。当时我也纳闷,喜水的野鸭为何飞到草木丛中来?当时对光的缘故,我只能看到它大致棕褐色的羽毛、胸腹部有黑色条纹。我也想过有可能是只落单的大雁,白露已过几近秋分,该到雁南飞的季节了。我童年时代的秋天,头顶会时常传来雁阵在风中制造的高亢音乐。我会抬头数数,会边看大雁变阵边默念着书本里的“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一直目送它们至南方的南方。
我问妻子,你以前见过大雁吗?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妻子说,见过,那时想大雁真聪明,飞的时候还在写字。我又问妻子,这几年你还能见着它们吗?妻子顿了顿说,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好些年没见到它们了。妻子问我,为什么?
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大雁应该还在飞着,就像《鸟与梦同行》里开头的一句解说词“鸟类迁徙,是个关于承诺的故事,归来的承诺。历经困难重重的数千里的行程,只为一个目的——生存”。生存,候鸟的迁徙是一场攸关命运的搏斗。记录片里的红胸灰雁振翅穿过极度污染的大气层时,我仿佛听见它们的咳嗽声;它们累了想休息一下,落脚的地方,从锈金属管道里排放出来的污水正漫过它们的脚丫。它们迷惑了,祖祖辈辈的迁徙路线常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鸟与梦同行》中雅克贝汉运用着适当的镜头,叙述了工业文明中遭受着无尽苦难的鸟的遭遇。大雁绕道而行也许就是见不到它们的答案,只不过我们听不懂它们心中的抱怨。
多年后的某天,我的孩子坐在宽敞明亮的课堂,用越来越标准的普通话朗读着“一会儿排成一字,一会儿排成人字”,她怎么也想不到,大雁可以从书本里飞出来、从头顶飞过,那是父亲年少时简单的幸福。大雁也好,野鸭也好,它们都是一个个童话。孩子,你知道吗?一个美丽的童话曾是我的启蒙读物也将是我的终老读物,一个美丽的童话故事是我一生享用的语文。
责任编辑 高 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