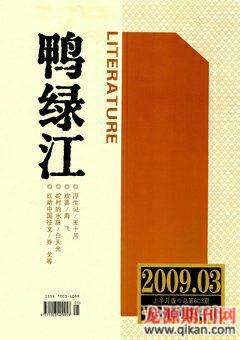老龙口·酒神(连载之八)
邹长顺 李同峰
王新富慷慨激昂的讲话,震撼了台下的干部职工,他们个个摩拳擦掌,一腔烈火在胸中盘旋,眼泪顺着脸颊落了下来,滋润着脚下的大地。
从来不掉眼泪的王大卫今天也掉泪了,而且掉得很多,这位南北征战多年,不知打了多少场仗的硬汉子,为什么竟然会泪流满面呢?因为王新富的发言震撼了他,他仿佛又回到了那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仿佛又看到了几年前那战场上的一幕一幕。
他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了,噌地站了起来,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泪水,说:“职工同志们,我这个人心很硬,从来都不相信眼泪,从来也不掉一滴泪,就是连我爷爷、奶奶去世我都没掉一滴泪,可是……”
王大卫再也说不下去了,堂堂的七尺汉子,竟然哭得说不出话来。但是,职工们还是在抽泣中期待着王大卫讲下去。
王大卫稍微停了一会后,擦干了脸上的泪水,继续说道:“我作为一名军代表,被组织上分到了其他单位,可是,我却向组织提出了不同意见,我说,我哪也不去,我必须来老龙口制酒厂。”
台下职工不明白王大卫一定要来老龙口酒厂的用意何在,人人都在心里猜测着,一双双眼睛在期待着。
王大卫接着说:“我为什么要抛家舍业来老龙口酒厂,是我爱喝酒吗?不是,是我要多挣钱吗?也不是,是一颗心,一颗让我无法平静的心,让我下定决心来沈阳老龙口制酒厂和我们的干部职工朝夕相处。”
台下的职工还没有听明白王大卫到底为什么非要来老龙口制酒厂不可,心中仍然悬着一个问号,都在竖着耳朵静静地听着,整个会场静极了,静得连王大卫的眼泪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真真切切。
王大卫激动万分、铿锵有力地说了一句话:“我是为了一壶酒呀,只有一壶酒。”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这就是王大卫的心声,他知道战场的残酷,他知道他是战争洗礼中最幸运的人,他被“古来征战几人回”的名句打动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战场上撕心裂肺的喊声……
硝烟弥漫人似鬼,呼啸弹雨能认谁?福大命大活下来,命短是谁也不会回。
王大卫平静一下心情,讲述了他终生难忘的一幕——
淮海战役是国共两党在军事上进行战略大决战的三大战役之一,国民党称之为徐蚌会战。这次战役范围广大,既有大战场,也有小战场,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洲,西抵商丘,北自临城,南达淮河,跨越江苏、安徽、山东、河南四省,贯穿于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始自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结束于一九四九年一月,历时六十天。国民党先后投入的兵力有七个兵团,两个绥靖区,三十四个军近八十万人。共产党参加兵力有华东野战军十六个纵队三十六万人,中原野战军七个纵队十五万人,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结束后,部分人南下至山东,配合华野、中野部队作战。
在山东境内,王大卫所在团接到一个命令,要连夜急行军,拂晓前赶到莲花山,攻克国民党以莲花山为屏障设下的军事封锁线。队部准时到达后,便发起了进攻,但是,由于情报的不准确,在我军进攻时,国民党凭借有利地形,突然暴露出了许多新的火力点。瞬时间,大批的解放军战士成片地倒了下去。时间紧任务重,师、团首长向王大卫连长下达了命令,无论如何要在天亮之前,冲上山去,为后续部队的到达扫清道路。
王大卫敬一个军礼:“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想办法,把山前的火力点给炸掉。”
团首长拍一下王大卫的双肩,点点头,脸上带着一股子信任,说道:“我知道你这个硬骨头连长是有办法的。”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整个战场枪声不断,敌方炮声隆隆,不断地在我军前沿阵地爆炸。跑了一夜的战士似乎忘掉了所有的劳累,眼睛瞪得像牛一样,死死地盯着前方敌人阵地。王大卫派出了几个爆破小组,都是在临近敌人火力点时,前功尽弃,英勇牺牲。
一个敌军碉堡是最大的障碍,必须除掉。李虎林在战壕里,心如火焚,眼看着倒下去的战士,他挥着拳头“嗨”地一声砸在地上,又抓下帽子重重地摔下,顺手从腰间摸出了水壶,还沉甸甸的,他仰头喝了一口。这是他经王大卫同意后,特意从沈阳带回来的一壶老龙口酒,按照王大卫的吩咐等把这一仗打完后,他就将回家一趟,把这壶酒送给多年没见的老父亲。而且,这个地方离他的家只有百十里路。
王大卫浑身冒汗,嘴里大骂道:“他妈的,我就不相信攻不上去——李虎林,跟我上!”
“不。”
“什么?”王大卫眼珠子一瞪,十分惊讶地问:“你敢违背我的命令?”
“不,连长,你不能去,我去,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投降。”
“啊,你……”王大卫听了李虎林的话,头发根都立起来了。
就在这个时候,李虎林把四个手榴弹捆在了一起,脱掉了衣服,背在身后,又用绳子在腰间固定一下,然后又把那壶酒斜挂在肩上,手抓着白衬衫,跳出了战壕,说:“连长,我‘投降去了,等着我的消息吧。”
李虎林像只猛虎,跳出战壕后,光着个大膀子“吱啦”一声把雪白的衬衣撕成两半,抓在手中,挥舞着,另一只手高举着水壶,对敌人阵地大声地喊着:“别打了,弟兄们,我投降……别打了……我投降……”
敌碉堡里的敌人发现了朝他们猛跑过来的李虎林,一敌射击手说:“你看,跑来一个光着膀子的人。”
“打死他。”
“用不着,看来他是真来投降的,除了身上的裤衩子,浑身上下什么都没有。”
“看来,不光我们的人投降解放军,解放军的人也有来投降我们的啊。”
“唉,不管谁投降谁,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我看国民党是打不过共产党了,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哥儿几个也得像他一样。”
“只要能留下一条命,回家和老婆孩子团聚,怎么样都无所谓了。”
在此间,李虎林仍然大喊大叫着,不时地打开酒壶喝上一口,又用力高喊:“我喝的是东北的老龙口酒,香着呢……”
说时迟,那时快,李虎林已经跑到敌人的鼻子下面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十米……连敌人从射击孔里露出的脑袋都看得清清楚楚了。
李虎林攀着陡峭的石壁,终于来到敌碉堡跟前了,他手举着酒壶喝上一口后,便大声说道:“弟兄们,好酒,来喝一口东北老龙口酒吧。”
敌人彻底放松了警惕,李虎林笑着来到碉堡前,把酒壶递给了碉堡里边的敌人。“怎么样,不假吧?”
“好酒,我也是东北人。”
“咱们是老乡。”
“对喽。”李虎林说着故意把脑袋向里探着,挡着碉堡内敌人的视线。只见碉堡内敌人手举着酒壶你一口、我一口地品尝着,不时地称赞说是好酒。这个时候,李虎林手朝后一摸,取下了捆好的四颗手榴弹,猛地拉开了引线,手里顿时“哧哧”地冒出了白烟。为了不把手榴弹过早投进去被手疾眼快的敌人反投回来,李虎林等了两秒钟,等到眼看就要爆炸了,趁敌人没反应过来,他双手突然把四颗冒着白烟的手榴弹塞了进去,同时狠狠地说:“喝完酒后,再吃点点心!”
话音落,李虎林用身子挡住射击孔,一秒、两秒后,“轰隆”一声震天响,碉堡飞向了天空。王大卫用望远镜望见这一切,大喊道:“给我冲啊……”
敌人失去了重要火力点,枪林弹雨不那么密集了,我军在火力掩护下,不大一会儿功夫,部队便冲到了山下,进入一些敌碉堡射击的死角。
李虎林浑身是血,仰卧在一块青石上,胸前的肌肉被炸得像红赤赤的烂柿子。
王大卫第一个冲上来,抱起了李虎林,急急地喊着:“虎林,虎林,你睁开眼睛!我是大卫呀,我们冲上来了!”
在王大卫的呼喊中,李虎林慢慢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脸上带着一丝胜利的微笑,喃喃地说:“连长,大卫哥,我的酒呢?”
王大卫四下望了一下,看到被炸到身旁的酒壶,拽了过来,朝李虎林嘴里倒着。当仅有的一滴酒滴入李虎林嘴里时,李虎林叭叽一下嘴,吃力地说:“连长,我没喝够老龙口酒啊……”
“虎林,等到全国解放后,我们俩向组织上申请,去东北,去老龙口工作,那个时候老龙口酒我们有的是,随便喝。”王大卫一只手托着李虎林血葫芦般的头说道。
“连长,大卫哥,我真的好想家啊,想媳妇,孩子……”李虎林断断续续地说。
“时间不会太长了,等打完这一仗之后,你养好了伤,咱们就可以回家看她们了,我陪你一块儿回去,一块儿……”
李虎林像是十分费劲地晃动一下脑袋,轻声地说:“连长,看来我是不行了,我想,等到我们的孩子都长大了,就让他们俩……我恐怕看不到这一天了,到那个时候,你多弄点老龙口酒,让我……让我老爹天天有老龙口酒喝,行吗?”
王大卫点着头,泪如泉涌:“嗯,我一定让他们俩……一定让你和李大叔天天有老龙口酒喝……”
李虎林脸上再一次露出微笑,身子一挺,脑袋歪在了王大卫的怀里……王大卫使劲地晃动李虎林松软的身体,他喊叫着:“虎林,虎林!我的好兄弟……”
……
整个会场里,职工们被王大卫的故事深深地打动着,个个眼里含满泪花。
“这就是战争。”王大卫擦了一下湿润的双眼说:“如今,美帝国主义对朝鲜发动了侵略战争,妄图以朝鲜作为跳板侵略我国,这是白日做梦!”
“打倒美帝国主义……”愤怒中的黑秀龙高喊出了一声,接下来震天吼的“打倒美帝国主义”,“誓死保卫祖国”,“响应毛主席号召,抗美援朝保家乡”的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
十
“静蕾。”在厂区里,李伟彬叫着正走向办公室的丁静蕾。那一天丁静蕾陪他走了一阵子后,到这天他一直也没有机会见到丁静蕾。
“伟彬,有事?”丁静蕾回过头来问。
李伟彬涨红着脸,点着头,却没有说出事来。想了好一阵子,才手拽着衣襟说:“我和黑秀龙都报名参加志愿军了。”
“我知道。”
李伟彬转移了话题,问道:“这几天,你们家去人没?”
“没有。”丁静蕾摇摇头。
李伟彬听了丁静蕾的话,觉得那个英鸽是骗人的,压根儿没有去。实际上,英鸽早就去过了,只是丁静蕾一百个不答应,也不说什么理由,英鸽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今天,丁静蕾是在和李伟彬说假话,只是李伟彬不知详情罢了。
李伟彬四下环视一下,急忙从兜里掏出了一封信,递给了丁静蕾,说:“自从那天你对我讲了好多话后,我十分地感动,这是我写给你的,你回去后看吧,我走了。”
丁静蕾接过李伟彬的信,心里早已明白了信里说的会是什么事儿了,因为在日常的接触中,丁静蕾早已从李伟彬的眼神里看出了,李伟彬爱恋着她。可是,这是根本不可能的,自从她迈进老龙口酒厂门槛的时候,对黑秀龙便一见钟情,加之书记和军代表慧眼识人心,代表组织给订下了这桩婚事,他们两人便是一对了。只是到如今,两个人都还没有对自己爸妈说呢,何况李伟彬呢?
丁静蕾回到办公室后,打开了李伟彬写的信,看了起来:
静蕾:
当我认识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可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说什么也张不开口对你说个爱字。就是那一天我们俩单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还是没有那个勇气。如今,我要走了,要上前线了,是该告诉你的时候了。除了我喜欢你、爱你外,我爸、我姑也都十分地喜欢你。
静蕾,答应我吧,希望你在我临走之前给我一次机会,让我把心中的话像竹筒倒豆子一样全都倒出来,好吗?
丁静蕾看完李伟彬的信后,无奈地提笔写上了宋代文学家苏轼的诗句:
枝上柳绵吹又少,
天涯何处无芳草。
已是夕阳一对愁,更着路遥和风雨。
夕阳把黑秀龙和丁静蕾的影子拉得老长老长,今个儿,他们俩走道靠得比较近了,仿佛已经是应该如此的时候了。因为再有不长时间,他们俩就要分别了。这一别,对丁静蕾来说,将是一种煎熬。成天在枪林弹雨中穿行,随时随地都有生命危险,她真的不想让黑秀龙去,可是她不能这样做,因为她和黑秀龙都是共产党员。书记和军代表也时常教育她们,抗美援朝是每个青年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倘若丁静蕾自己是个男人的话,也会毅然决然地报名,去朝鲜战场。不管怎么说,自己的事再大也是小事,只有大家有了安宁,自己的小家才能谈上幸福。担心是担心,可她必须无任何条件地支持黑秀龙走出国门,打击侵略者。
丁静蕾想到这,突然想起了李伟彬给他的一封信,掏了出来,递给黑秀龙说:“这是李伟彬给我的信。”
黑秀龙接过信,借着暗淡的光,很费劲地看了一遍后,说:“伟彬和我一样,太傻了。”
“什么意思?”
“就像当初你喜欢我一样,我傻得都看不出来,多亏了书记、王代表做媒。”黑秀龙感慨后又问:“没有把咱俩的事告诉他?”
“我不好意思,开不了口。他私下跟我说了很多中听的话,我没有直说,我以为他能看出来,可是谁知道……”
“我说他傻吗。”
丁静蕾指着信说:“这不,我在信上给他写上了两句诗,我想这一回他该明白了吧。”
“他不但写了这封信,而且还让英鸽去我们家做媒呢。”丁静蕾接着说。
“噢,有这事?”
丁静蕾点点头,说:“要不,明天我们一块告诉他好吗?”
“不用啦,书记对我说了,我要是参加志愿军,走之前要我们把亲事办喽。到时候,他就什么都知道了。”
“为什么这么急呀?”
“书记说了,我要一走,妈在家没人照顾不行。成亲后,我走了,我妈就有你照顾了,好让我安心打美国鬼子。你说行吗?”
丁静蕾思索了好一阵子,抬起了头,望着黑秀龙,点点头,轻轻地答应着:“嗯。”
“咱们今天回去后,我就把我们的事给我妈说,你就给你爸讲,怎么样?”
“行。”丁静蕾很干脆地答应后,又似乎有些担忧,深情地说:“秀龙,说实在话,你这一走,我真的为你担心。”
“担心什么?”
“担心……那是战场,不是老龙口酒厂。”
“用不着,我妈说过,我从小命硬不会有事的。小的时候,我刚会爬我妈就带我去农村串门,她们一不留神,我掉进了井里,结果井里没有水,是口枯井,我只是划破了一点皮,大人们费了好大劲才把我从井底弄上来。
“我还听我妈说,我刚几个月的时候,耳朵里,肛门里都生蛆了,我爸和我妈把我包巴包巴放在大门后边,准备天亮时把我扔喽。可是,等到天亮时我又哇哇地哭了起来。我妈便用清水给我轻轻地洗掉了耳朵眼里、肛门里的蛆,我吃了我妈几口奶水,又活了。
“还有一次……”
“我知道了,你给我说过了,小时候淘气上树摘枣吃,一脑袋顶在蜂窝上,让蜂蜇得满脑袋大包,肿得像个大头娃娃一样。”
责任编辑 乔 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