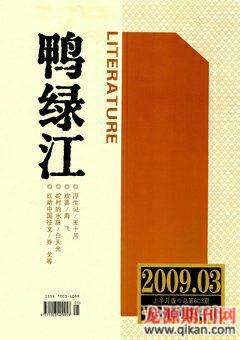山路之上
王朝明,男,1970年代生,文学爱好者,业余作者。近年来有小说、散文及文学评论散见于《光明日报》《读者(乡土人文版)》《人民日报》《中国青年》《鸭绿江》《青岛文学》等报纸杂志,现居青岛。
1
大地上,只要不停止行走和仰望,总会看到山。或者,即便在四顾茫茫的海洋里漂泊,如果运气不是太差,你也会发现它。通常,它是以岛的形式存在并被命名。岛也是山,大海里的山。
每一座山的诞生都是一个传奇,不管出于不可料的偶然还是冥冥中的必然。或者在大陆板块的倾轧挤兑下艰难隆起,或者源于地核深处炽烈岩浆的猝然喷薄,再或者,只是因为发生在身边和脚下的动摇、放弃、退却、坍塌、陷落、沉沦。
山上本没有路的。设若单靠脚步的力量,人的脚,动物的脚,而不是借助石子、柏油、水泥,甚或还有钢铁……走得再多,未必会成为路。成了路,也未必会久远。无论怎样的山,本质上大抵应是排斥路的。一座青山,草、灌木、藤萝会耐心而坚定地把每一颗脚印覆盖和湮灭;一座童岭,风沙和日光从来不喜欢有别的东西在属于它们的领地上留下印记;而一座雪峰,甚至不惜以同归于尽的崩塌,拒绝和排斥任何外来的进入和践踏。
山是大地的驼背。只有路知道,在大地上驼着背躬着脊梁沉默地站立着的山,在水光和时光浩淼之海里昂着头颅的山,是多么的倔强和孤傲。也因此,一条路要走进、贴近、攀爬和附着在山之上,要把自己镌成大山额头一条深刻醒目的皱纹,当然不是那么容易,注定要经过许多曲折。
2
爬行是路的宿命。匍匐是它的基本姿态。一条路,倘若忽然有了站起来的渴望,于是它的视野里便出现了山。一条山路所能抵达的高度,通常取决于它所能接受的弯度。宁折不弯值得崇敬,但并不适用于山路,能屈能伸一向为它的立世圭臬和前进智慧。
一座山,如果没有路,就像一部书没有目录。在惯常姿态和俗世场境下,要读它,该先从哪一页、哪一个章节翻起?但山路却又非山的简单索引,跟山一样,独立性天然是它的基因。路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山从不过问,也从不干涉——尽管山有时会以一树幽花、一涧冷泉、一声鸟啼甚或一蓬熟透了的浆果,不动声色地来诱引路;有时,又会以一刺荆棘、一条游蛇、一道断崖甚或一场突如其来的滑坡,来吓阻路。而山路通常不为所动,它一贯有着自己的立场和主见。它知道哪个方向的阳光能照亮心灵的影子,哪个弯度和坡度是生活的迂回与生存的必须,哪一棵松树下沉睡着憨厚的草菇和圆滑的瓜蒌,哪一个山垭口将迎来前行的踟躇和抉择的痛苦……
几乎所有平原上的公路都是趋同的从众的,每一条山路却各有各的个性。它们厌恶雷同乃至相似,拒绝被格式化和同质化,抵制整齐划一的标志线、护坡及道旁树。它们不知疲倦地把热爱山野的人、兽、昆虫乃至候鸟引向时间的深处和世界的边缘。它们对野兔、蜗牛和樵夫一视同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一个野兔、蜗牛和樵夫对山路有所失望和抱怨。相反,他们留在山路上的每一个脚印,如同岁月之河上静静流淌的一片叶子,都会因为贮满了慷慨的天光和本底的山色,而闪闪发亮,灼灼动人。
3
听到自己的呼吸、心跳和脚步声,这在城市的马路、在大道通衢上该是多么的奢侈,但在随便一条真正意义的山路上,不过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我曾经有四年的时间,一千多个日夜,呆在一座“大海里的山”,也即一个孤岛上。以五百多米的海拔,倘在陆地,这样的山通常会为人们所不屑和忽略。然而,它的脚下是海水而不是大陆;也因此,即使在大比例尺的中国地图上,我也能很快发现它的存在,尽管它总是被浓缩成不过一滴水的模样。山岛之上有一条混凝土浇铸的环岛路,是早先驻军留下的。或许是出于节约的考虑,这条路只硬化了两侧的车辙带,中间仍留了“白”;后来因为裁军,营盘尚在,兵的流水却越来越细,于是原本要修的“环”最终没有完成最后的圆满,就像一弯不规则的锈渍斑驳的蹄铁,被时光的白驹一蹶子尥在了生活的外围。这样的一条路,两边是蓬生的山草,中间也是坚韧的草,却抻长了当初我迷茫蹇涩的青春。有无数个潮声瀚澹的黎明,我走在青草离离或衰草萋萋的路上,到岛东面临海的崖头上等候日出。彼时,灰白的大海漫漫淼淼,悠长寂静的山路上少有人走,一个人的足音,就叩出无边的清寥和旷远的回响。
海上日出,在人们通常的印象中,在一些文章里,似乎多是与壮观、热烈、辉煌、激越这些字眼联系在一起的。而对于已走出海岛有些年头的我,每每于芜杂的生活罅隙里沉静下来,反刍起瀚海孤岛上的那段岁月,慢慢回放彼时彼地守望日出的映像,却发现涌上心头的,仍是当初的那些滋味:清寥,落寞,说不清来由的怅惘,以及一点儿苦涩。
在环岛路上,有时我会碰到赶早潮出海的渔民。大步走来,他们的脚板掷地有声。他们的手中拎着粗劣塑料制作的“葫芦头”,肩头扛着补好的鼓囊囊的网,或者溜着圈沿缀满鱼钩的篓筛。我停下来,侧身站到路边的草棵上,给他们让路,目送他们的机动船突突地开出湾子,径直驶向颜色由灰转白继而恢复素常的蓝色的大海。比起岛上的山径,他们更熟悉海中的路,那些路隐藏在蓝色的水里,随洋流漂游不定,而这一切都蒙不过渔人的眼睛,海路的来龙去脉都把握在他们粗砺老硬的手茧上。
在一个垭口,我经常会与早起上学的孩子们相遇。岛上有十几个小村子,像礁石上的海蛎子一样,随意地巴在远远近近的山坳里。小学却只有一个,因此散落在这些村子里的渔娃子,背着书包的大大小小的渔娃子,天天都要早些起来,与亲切的熟悉的山路展开或长或短的对话。低年级的小一些的渔娃子,须自己一步步走着去学校。他们从各自炊烟袅袅的家里出来,三五个一伙聚了,踢踢踏踏地往岛西面的教室赶——他们的鞋子一定是要踢着一块石子、一截树枝或者一个酒瓶盖什么的,他们的眼睛一定是会被山梁上的一只野鸽子、路边草丛里的一个蚱蜢或者海面上悄然驶过的一艘军舰所吸引,而总会有一些小小的战争,因为一个恶作剧、一点好胜心甚至仅仅是不愿让这段上学路悄无声息,就像海浪花一样自由任性地生发,又简简单单地泯灭。大一些的中学生,则会更晚一些出现在环岛路上,而在两三道山梁之外,就可以听得到他们揿得疾疾乱响的车铃;然后,随着路边树丛里一只睡意惺忪的山鸟惊叫着窜上半空,这帮飚车族早已过了垭脖子那段陡且弯的下坡路。
几乎每一个早晨,他们都会很准时地出现在海岛山路上,就像那一爿时光里的我。只是我很快就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要早地离开了那座海岛,同时也离开了岛上那条朴素的寂寥的山路。
可直到今天,那条“留白”的山路,连同那段留白的岁月,却常常执拗地清晰地进入我的梦。
4
山路的出现,山路的存在和延伸,仿佛使世界与大山的联系变得轻易、必然和紧密。然而这只是表象。就像一些文字,在我们机巧的手上,经过一番排列组合,拉成一些或长或短的句子;而竭尽心力所传递出来的,或许,与生活的本意和世界的真相恰巧擦肩而过,甚或是南辕北辙。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逝者如斯,不舍昼夜”。那台上的、岸上的古人,可否瞥见了湮没在时光深处的那条歧路?抑或山路?
山在哪里,脚步就走向哪里,山路就出现在哪里。真的是这样吗?
听说,有一座为人和神明崇奉的雪山,当地政府已经禁止任何人登攀。真若所闻,那么,至少又有一条山路将永远离山而去了。这也许是山路的悲哀,这何尝不是大山的福幸。
5
裸露的皲裂的岩石,清癯然而苍劲的松树,杂生的灌木和草,落寞的青白的天,这是北方的山路上寻常见到的事物。
在漫长而严寒的冬季,有许多被遮掩在繁荣表象下的东西一点点剥离出来,世界水落石出,生活目光咄咄。山路倏然凸显于大山的额头,素面朝天,醒目惊心,如磊落的疤痕。
一条路,如果诞生在城市,它仅仅是一条路。不管它是什么质地,不管它是多么光滑可鉴、明眸皓齿,不管它的胸前被别上了怎样的标准和衔级。它的厚度,只从路基之上起算;而这当然不包括大地。
一条路,倘若卧于山野中,它将不仅仅是一条路。没有人会用路的标准来衡量和要求它,它可以隐没也可以中断,不必在意有没有坚硬的甲壳和华丽的镶边,当它被人仰望时,它的目光正尾追着天边的大雁。
更重要的,山路的厚度,是山路之下的山的厚度。
6
在山路上走着,想起梭罗的话:“说什么天堂,你羞辱了大地。”
7
跟人一样,山不能选择自己的出生地。路却可以。一条路,选择了山,于是它昂起了头,然而它放弃了平坦,它以命运的曲折来换取呼吸的深度、生命的厚度和精神的张力。
山路是道路中的陶潜,当然这并不妨碍它偶尔在青天之上李白一下,其实它的骨子里很有些老庄。有的恐龙属于白垩纪,绝大多数的山路相悦于东晋。
与山路对话,最无拘和知己的是流水,最执拗和倔强的是草,最不需要言语的是高原上的朝圣者和雪线上的守护者。没有人怀疑,雪域冰川上的每一条路,本质上都是山路,无论衡之以地理的高度,还是仰之以精神的海拔。
山是普遍存在的,即便在城市里,在林立的楼的罅隙,总会有它沉默的坚守。它与它的兄弟们在各自的重围里深情凝望,在地壳的深处互相支撑,没有一座山会屈服和放弃,即使觊觎和蚕食让它们日渐骨骸蚀陨。
不放弃不抛弃的,还有山上的路。
单位的楼后难得留住了一座小山。如果上班来得早,时间赶趟儿,我会到山上走一走。时候正是早春,风还硬,却渗着春的意味。在一条朴素的山路上,人的思想没有理由不变得简单,何况清冽的风、沉默的松树和山草、灰白或青白的天,还有一群扑打着宽大翅翼的貌似安逸的喜鹊,这些,总有一样会让人的嗅觉、视觉或触觉变得敏锐起来。
漫漫走在山路上,忽然想:滚石上山的西西弗斯,天天走的可是同一条山路?或者,他每天都将趟出一条新的路?
而俯视脚下,这个城市早已醒来,一条路在晨曦里闪闪发光,一条路上出现了寻常的拥堵,还有一条路,正顶着累累疤痕决绝地与挖掘机迎头相对。
光阴的碎片,在浩渺的时空里飘洒、翻飞、流动、闪转腾挪,亮色忽隐忽现,波光诡谲叵测,谶言和诱惑一路结伴同行,先知们在远远近近的将来平静回首,表情冷峻,目光炯炯。山路埋头奔走,不问能否一头扎进光明,它们蜿蜒而上又曲折而前,走进一座座山,又将一座座的山捆在身后。
一条路的进入,似乎意味着对一座山的解析从此成为可能;山厚重的秘密在淡薄的雾和新鲜的风中撬开熹微的一角,路俨然成为山的卧底和知情者。然而不动声色的山,却凭藉一些脆而薄的时光的碎片,轻巧地俘获并且把路化为自身秘密的一部分。同时,作为柔韧的光阴的绳索,山路也顺便把一些试图逸出庸常生活的思考者一并缚之以形,直到他们以及他们所看重却又令上帝感到可笑的思考随光阴一起湮没。
山路之上,一个蜗牛拥有的从容令人惊讶和艳羡。有一条蛇,它甚至把一整个中午浪掷在阳光下的崖石上,目的也许只是为了一觉睡到自然醒来。还有一些变化,在山路之上悄悄发生和进行着:一天清晨,路边灰褐的茅根间突然冒出几瓣孱弱的绿;一场雨后,崖上的数丛野杜鹃约好了一般扑剌剌齐把红妆簪满头;某个出神的刹那,云的影子飕飕地从脚下滑过,阳光忽然亮得让人睁不开眼;而一只山猫的突然到来,引发了喜鹊们集体的疑虑和不安——它们在枝头和岩石上不停地起落纷飞,把愤怒的叫声砸向鬼祟又敏捷地穿行的山猫,直到后者在它们警惕的视野里消遁。
在时光之水的某个拐弯处,回忆停顿了一下,河面上起了旋涡,波光潋滟,另一条山路的影像刹那间清晰起来。
104,287,312……这些数字,落实到一幅边框外注有“保密”字样的军用地图上,是一座座山的海拔标高。数字的道白就是如此直接——显然,山不高,甚至可以说太过矮小。以至于随便哪个毛头稚儿或耄耋老人,倘有兴趣把他们中的任一座踩在脚下,也不会是件很困难的事。然而,当这些小小的山手搭手肩并肩站在一起,当对它们的依次攀越被严格限制在以分秒计的时段之内,当群山脊梁上的每一个黎明和黄昏——不管这些黎明和黄昏是雨雪肆虐还是风沙凛冽——都要靠“解放鞋”(或“大头靴”)来叩醒或送走,对于十六年前的我和我的战友们来说,面对这些山,显然不会像如今从嘴里抛出几个音节这样轻松而随意。
那些山,我相信他们中的每一座都有着雄性的基因。一如■过他们胸脊的路,每一条,都是那么粗砺和坚硬,每一条,都磨穿了且还将磨穿无以计数的解放鞋,抑或翻毛的大头靴。在那条联结了104还有287的山路上,兵们的脚步呼啸着在山路上飞奔而过,眼睛从来都盯着下一个标高,他们把原本多彩的四季摔打成一个格式和颜色,以至于路边的山草也都留了一如他们的发型……
8
山路之上,最先在春天醒来的往往不是草,也不是树,而是花。
与矜持的夏花不同,春花的亮相从来不须绿叶来铺垫和渲衬。它们还都是急性子。先是迎春,然后是杜鹃,然后是丁香,说声要开,不过几天的工夫,一簇簇,一穗穗,扎着堆儿,抱成团儿,扑剌剌全开了,一丁点儿后手都不留。还有紧紧贴着大山肌肤的荠菜。一株荠菜的青春期是多么的短暂:萌生,在阳光里展开简约的清癯的叶,抽茎,然后吐出素白的米粒样的荠花,而这一切,也才不过几天的工夫。有个挖野菜的人从坡上踅回山路,提着铲子,篮子是空的,他的脸上挂着沮丧,嘴里嘟哝着,“怎么这么快就老了呢”。然后他走了,“老了”的荠菜匍匐在山路边,迎着微微的风。
这些花,簪在崖头,别在山路上,让登山者的眼睛变得明亮和温柔起来。随后,是一场缄默的雨,花集体谢幕,新生的草登场了。
草长得很快。一些草芽儿竟从山路中间钻出来。这让登山者的脚步有些犹豫和迟疑。新的生是这般柔弱,然而这柔弱中蕴涵着不可小觑的力量。在雨水渐渐勤奋起来的春天里,如果一条山路没有人走,很快,草就会把它埋没。
草在山路上生长,鸟飞过草和山路的头顶。喜鹊,斑鸠,啄木鸟,云雀,山草鸡,野鸽子,鹰,还有刚从南方千山万水仆仆飞回的燕子。
跟草的生长一样,山路之上,一些事情悄悄发生着。譬如,春风终于放弃了对一棵枯树的呼唤,那棵树,它的年轮和记忆截止于上个冬天的风雪;山坳里一个隐蔽的采石场传来碎石机疲惫低沉的叹息,内心早已伤痕累累的它,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停止对坚硬的山以及山上坚韧的路的啃噬;有一座曾经被树阴、藤萝和泠泠泉水声包围的小山,如今包围它的,是一幢幢高傲又孤独的别墅……
山路边的草坡上,零落着几撮鸟的毛羽。两片残缺的翅膀,像皴干的树皮,难以分辨和想象它们曾经被什么样的喙轻轻梳理,曾经把怎样的一只鸟轻盈地送上清明的天空。风从松针间轻易地滤过,暖暖的阳光百无聊赖,蓬生的草正一点点地把一场杀戮遗留的所有痕迹掩盖和湮迷。
海匍匐在城市的边缘,它总是有着天一样的颜色。有一些水汽在更远的洋面上升腾、聚拢,然后奔涌又扩散,直到生成一种被叫作“平流”的雾。那雾,随涨起的潮头轻松地登陆,被丢了方向的风推怂着,漠漠地朝栉比的楼群和夹在楼群里的山走来。很快,楼,山,还有山上的路,一切都陷入到混沌的疑似的仙境里去了。
责任编辑 郝万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