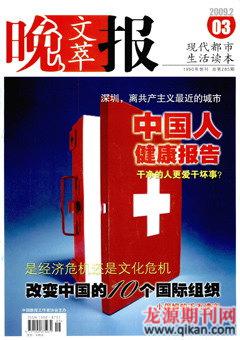通往地狱的死亡行军
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和新加坡大屠杀,是日军在二战期间制造的三大暴行。列斯特·坦尼是当年在巴丹被日军俘虏的一名美国大兵,他花50年时间写成《地狱的梦魇》一书,再现了这次死亡之旅。
1942年4月9日,对我而言,是噩梦的开始。昨天,我们还在为保卫巴丹殊死战斗,今天我们却成为了日军的俘虏,因为我们孤立无援、弹尽粮绝,还有饥饿、疟疾的困扰。日本人来势汹汹,我们每天都要伤亡数千弟兄。继续战斗下去,只能徒增伤亡,巴丹最高指挥官金将军决定投降。伙伴们都相信,等到交换战俘,我们就能回家了。大家七嘴八舌地讨论着回家以后要做的事情,我闭着眼睛,想起了亲爱的劳拉(坦尼新婚的妻子)。带着对劳拉的思念,我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噩梦的开始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刺耳的枪声惊醒。一队日本兵扛着步枪,端着机关枪,闯入了我们的营地,他们凶神恶煞般地嚎叫着。我的两脚开始发抖,浑身冒汗。
数秒后,成群的日本兵冲进我们的营房,拿走他们想要的一切东西。一个日本兵走到我面前,把两个手指并在一起,伸到嘴边,做了个抽烟的姿势。我明白他的意思,却摇了摇头。他笑了笑,猛然挥起枪托照我脸砸过来。血从我的鼻孔和颧骨伤口处流出,他大笑,说了些什么,然后他的同伙也跟着大笑起来。他向我右边的吉尔伯特走去,用同样的手势要烟,吉尔伯特正好有烟就给了他一支,他抬手把整包都拿去了,然后他的同伴们开始用步枪枪托及手杖长的竹棍击打吉尔伯特,直到他站不住。在巴丹半岛投降的人近10.5万,这大大超出了日本人的估计。日军最高指挥官本间雅晴正忙着调集兵力,准备攻陷美军在菲律宾最后的堡垒——克雷吉多要塞。他不打算就地收容我们,而是命令我们从巴丹步行到奥唐奈。参加行军的有6.5万名菲律宾服务人员、2.8万名菲律宾市民、1.2万名美国人。这一段路长达65英里。对我们来说,这太不幸了。在过去的40天里,我们每^每天配给的食物能量只有800卡路里,我们不得不用蛇、猴子或大蜥蜴来充饥。伴随着饥饿的,是脚气、皮肤病、坏血症和疟疾。在巴丹密林中有大量携带疟疾病毒的蚊子,我们孱弱的体能已无法和它抗争,99%的人都得了疟疾。
行军从马里韦莱斯机场东面两英里的167号里程碑开始。道路混乱不堪,20英尺宽的路面上充斥着各种车辆、马匹和大炮。重型卡车、坦克的碾压让石头路面坑坑洼洼。在这种路面上走一小段已经很痛苦,长距离行军的折磨可想而知。
我们四人一列,每组四列开始步行。走完一英里,我们已经不成队列。很多兄弟开始把随身物品丢在路边,牙刷、牙膏、修面油、刮胡刀、毯子、绑腿,丢得到处都是。我的个人物品早就被日本兵洗劫一空了,只剩下劳拉的照片,日本兵疯狂抢劫的时候,我偷偷地把它藏在袜子里。我想我—定要活着去见劳拉。
负责押运的日本兵不时捡起路边的棍子抽打我们,试图让我们走快些。到午饭时间,我们已经连续走了四五个小时。可是日本人没有让我们停下来的迹象,我们饥肠辘辘,却只能拖着虚弱的身体继续前行。
突然,和我同组的汉克滑倒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一个日本兵朝这边跑来,我们冲着汉克大喊:“起来!起来!”太迟了,那个日军用刺刀指着汉克喊了几句日本话,然后用刺刀朝他虚弱的身体连扎了四五刀……
汉克的死证明了一件事:如果你想活命,那就不能停下。有的伙伴得了疟疾,蹲在路边腹泻时被日军刺死。为了求生,我们的大小便只能在裤子里解决。第二天,一辆日本兵车从队伍旁边经过,车上的日本兵肆意鞭打着走不快的人。一个日本兵突然用绳子套住一个战俘的脖子,把他拖倒在地。卡车在加速,日本兵在狂笑。这个兄弟被拖出100多码,他的身体翻滚着,锋利的石块让他鲜血淋漓,遍体鳞伤。他终于挣脱了套索,当他挣扎着站起来时,大喊道:“你们去死吧!我会活着在你们的坟墓上小便!”愤怒给了他新的力量,他站直了回到队伍里继续跋涉。
194坦克连有一位帅气的中尉,大约28岁。他是个大个子,有一头金色的卷发。他看起来很强壮,却背着个大包,走得很慢。我超过他时,看到他那呆滞的眼神,他走不动了,一直在摇晃,像喝醉了似的。我劝他丢掉大包,但他摇了摇头,包里一定有什么值得他用生命去捍卫的东西。在又坚持了数百英尺后,他倒下了。押队的日本兵跑到他身边,毫不犹豫地用刺刀插进了他的胸膛。中尉躺在路中间,奄奄一息。几分钟后,一辆卡车从他身上碾过……
拿命换水喝
挨到傍晚,我们在卡巴拉森停下。我看到一个日军军官刚吃完一盒米饭和一个鱼罐头,罐头底部还剩了两匙鱼。他扭头看到我的眼睛,便把罐头盒扔给了我。我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全身只有饥饿、疲惫、沮丧,我毫不迟疑地拿起罐头盒,从路边捡了根松树枝,挑出一块足够我美美吃上一口的鱼。我看到站在我身边的战友鲍勃盯着我,便把剩下的鱼和“勺子”给了他。从那一刻起,我和鲍勃成了知心朋友。第三天,我们很早就被赶到路上。依旧没有食物,没有水。我该死的胃病又犯了,让我挪不开脚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
其实路边并不是没有水,巴丹半岛上有很多泉水和自流井,但日军就是不让我们喝水。一次,我们路过一个自流井,恰好看押我们的日本兵远远地走在我们前面,我和法兰克迅速跑到井边。几分钟后,井边就聚了10多个人。就在这时,一个日本兵过来了,他狞笑着,冲着刚要喝水的一个兄弟的脖子上就是一刀。那个可怜的兄弟脖子上喷出的血染红了自流井,他双膝跪地、呼吸急促、脸朝下仆倒在地。一口水也没喝上,他就死了。两小时后,我们走到一个水塘旁边。水面泛着绿色的泡沫,成群的绿头苍蝇在水上盘旋。一个兄弟用手语向一个日本兵询问能否喝些水。日军笑了,示意可以。眨眼间许多人跑到池塘边,他们用手把绿泡沫拨开,把带有寄生虫的水喝进肚里。
几分钟后,一个满脸堆笑的日本军官来到了我们的队伍旁边,在我们周围转来转去。突然,他命令日军士兵将衣服上沾过水的兄弟从队伍中拉出,并让他们排成队。令人震惊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日本军官竟命令日军向那些喝过水的兄弟射击……我很庆幸自己没有去喝水,但是不一会儿厄运就降临到我的身上。一个日本军官骑着马从我身边经过,当时我正和坦克连的布隆格、西格走在一起。我不小心走到了队伍的外面,他向我挥起了军刀。尽管我迅速低头。但是刀刃还是滑过了我的左肩,离我的头仅有不到两英寸的距离,肩头的伤口需要缝合,但如果我想活着就要继
续行军。
当那个日本军官走后,布隆格和西格立刻把一个医务兵叫来。那个医务兵用尽身上所有的线来缝合我的伤口。之后的两英里是我的两个朋友架着我走的,才使我没掉队,我们明白,掉队就意味着死亡。西格和布隆格救了我的命。
第四天当我们进入贝德摩加城时,菲律宾市民站在路两旁把各种各样的食物扔向我们,米饭团、肉饭团、小片的炸鸡还有甘蔗。这时甘蔗显得比其他任何食物都重要,它的汁液和糖分可以补充我们所需的能量和营养。突然我听到队伍中间响起了枪声,几秒钟后,路两边的人四处散开。日军向扔给我们食物的菲律宾人开枪,两个菲律宾市民倒在了他们的枪下。
我们继续向城中心行军,夜幕降临时,我们被聚集在一个有75英尺宽、160英尺长的大仓库里。没有在仓库里找到位置的人只有露宿在外面的一块空地上,我在仓库里面。仓库里挤满了人,我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如有人要小便,只能尿在裤子里。要大便也只能拉在仓库的角落里。这一晚,仓库里到处都弥漫着那些患了痢疾的战俘们的屎尿味。
恶臭,临死的人绝望的叫喊,虚弱而不能动弹的人的呻吟,让人无法忍受,我只好将衣服的一角塞进耳朵。日军关上仓库大门,在外面监视我们。
第二天早上仓库门一打开,我就蹒跚着走了出来,感到一阵眩晕。这天早上至少有20具尸体被抬出仓库,扔在后面的田地里。
零人性杀戮
第15天,我见证了一件最残忍的事。有个兄弟患了严重的疟疾。他发着高烧,简直连路都分不清了。一个日本兵将他踢倒在地,冲他的身体开枪,然后又叫两个就近的兄弟挖坑埋掉这个被枪击中但还活着的兄弟。两个人开始挖坑,坑挖到一脚深的时候,那个日本兵命令将那人放人坑中,要活埋他。那两个^一直摇着头,日本兵又开枪打中了其中的高个儿。接着日本兵又从队伍中拉出更多的人,命令他们再挖一个坑来埋高个儿。日本兵就是要让战俘们明白他的命令必须服从。他们挖了第二个坑,将两个人放在坑里,往他们身上扔土。其中的一个人还活着,土扔在他身上时,他凄厉地叫喊着。
从卢保出发四五英里的行军成了另一个噩梦。日本兵突然强迫我们奔跑。“跑”了好一段路,又命令我们停下来。我看到一个美国士兵跪在一个日本军官面前,那个军官从刀鞘里抽出了他的军刀,在空中划着大弧。他让那个兄弟跟着他刀指的方向移动膝盖。日本兵很亢奋,高呼着“万岁”。结束“热身”,那个军官快速地挥下战刀,刀锋过处,我只听到沉闷的“砰”的—声,那个兄弟身首异处。
我们又走了两天多的时间到达了圣费尔南多。我们走到当地的火车站,在铁轨边坐了大概有一个小时。一个由旧车头牵引的闷罐车,“咔咔”地驶进小站。我们就像畜生一样被赶进闷罐车,每节车厢都塞进了80到100人,而通常它只能容纳25到30人。太挤了,很多人无法呼吸,特别是那些在车厢中间的人呼吸不到一点新鲜空气。我很幸运,我坐在门边,脚悬在外面。
享受着新鲜空气,伴着一丝微风,周围没有刺刀,真幸福啊!但这幸福感并没有持续太久,一个日本兵走了过来,挥动着一根藤条,死命地打在我的膝盖上。我疼得喊出声来,日本兵又猛地抓住门把手,用车门使劲地撞我的腿,我疼得差点晕了过去。我的疼痛为大家带来了一点福利,门没有被关上,我们才能够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大约5个小时后,我们到达了卡帕斯,我们的目的地奥唐奈集中营就在这里。我慢慢地跳出车子,腿已不听使唤了,我跌到在路边。一个日本兵用枪托猛打我的背、腿和脖子,我用双手护着头部在地上爬。当他要用刺刀戳我的时候,我赶忙爬起来了。很多车厢中部的战友没有能够走下车厢,车里太挤,他们窒息而亡。
大约10分钟后,日本兵又驱赶着我们前行了。我走了大约两英里,就觉得自己不行了,我发起了高烧,身体好像着了火。不久,我就因精疲力竭跌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我发现西格和布隆格抬着我往前走。运气又撞上了我。
行军的最后一天,我又差点送了命。当时我的脚肿得有原来两倍大了,很难跟上队伍。一个伙伴看到我肿胀的脚,建议我砍掉靴子的两边,我吃力地弯下腰松开了鞋带,好让脚继续膨胀。我仍然发着烧,当时我想自己就快死了。就在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劳拉的照片。我奇迹般地站了起来,继续往前走。我们终于看到了一片模糊的营房。苦难的跋涉总算要结束了。在巴丹被俘的人有一多半死在这次行军途中。
这次灭绝人性的行军完全是有预谋的。后来我才知道本间雅晴发布了如下命令:“和我军在巴丹对抗的每支部队,不管投降与否都应被彻底地消灭掉,任何一个不能走到集中营的美国俘虏都应在离公路200英尺处被处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