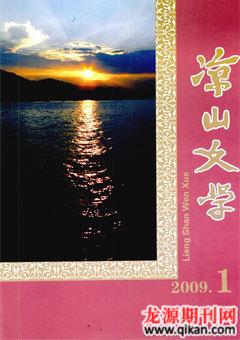阿固脚·几勒吉巴(外三首)
艾 尼
阿固脚·几勒吉巴
我不知道是哪个地方了
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
就是这个地方啊,几勒吉巴,他被打死了
死亡在梦幻与现实间,可你在哪里?!
在白天也像黑夜的日子里
他被打死了,一颗熟悉的子弹穿透他的胸膛
而不是陌生的。在很久以前,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就在你这里
在你这里啊
在黑夜也如白天一样平和的日子里
他被打死了,留下许多的遗憾
滋生许多的可能,像针尖一样使人
难以入眠。他是我的亲亲的爷爷吗?
他是我的亲爷爷啊
我终于知道那个地方了,阿固脚
在你的天空下,在你的大地上
但我却不敢认领了,阿固脚啊
就是这个几勒吉巴,我知道你在哪里!
我在说:记住任何地方都不要记住你
思念任何地方都不要思念你
像针尖一样刺疼的你,在阿固脚
在我的心里,在我的梦里
父亲与我对脚睡觉
我的父亲哟,是我的父亲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父亲跟我对脚睡觉,在阿固脚的一个屋内
父亲喝醉酒了
听着他时高时低的呼噜声
我却怎么也睡不着
我知道他的父亲就葬在这片天空下的山中
他的母亲葬在离这里挺远的
就翻过那匹大山那片名叫小金洛姑的土地上
他喝醉酒了,他的话听起来像是在胡言乱语
他喝醉酒了,他却说得一本正经很一本正经
他在说:是葬在他父亲这里好呢?
他还说:还是葬在他母亲身边好呢?
一个是在山的这边
一个又是在山的那边
他的父亲和母亲。诚如像我们一样
我和父亲一样,虽然住在同一车铺里
但是各自睡在一边,对脚睡觉
我小时候躺在他的怀抱,长大了
我和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并起睡下
这让我伤感,在阿同脚的一个屋内
他势将老去了,我正年青啊
因此,我们是在走一条相反的路线
除了我们都是彝人,除了我是他的儿子
除了他是我的父亲。在阿固脚的一个屋内
啊,俗话说:隔了房子就是家门
与别个家门是完全一样的了
我在做着比别人还多的孝敬父母
我是无能为力的,除此之外
我的父亲哟,是我的父亲
父亲跟我对脚睡觉,在阿固脚的一个屋内
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我想了很多,很多……比如想死亡和生存
比如想来和去,比如说爱与恨……
父亲喝醉酒,睡觉了
他只管放任他时高时低的呼噜声
明天,我要告诉他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觉
诉诺勒拖·火葬地
从阿固脚抬头望一望
就能够见到它的了
它在森林的腹地,它在河谷的坡上
啊,我仿若看见
昨天,还在昨天,一帮彝人
一个个整妆祭奠这个彝人
而这个彝人,却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啊,我仿若看见
今天,就在今天,一帮彝人
开口对我说:那就是你的爷爷的火葬地
不要去到那里,去了什么都没留下
从阿固脚抬头望一望,就能够见到它了
我听话地没有去。我终于也晓得了
爷爷的火葬地
啊,谁叫他生的时候
是那么地受人尊敬,和蔼可亲
像雄鸡像猎狗像骏马
像生在众人的眼睛中
啊,谁叫他死了以后
还是那么地受人尊敬,难以忘怀
像雄鹰像猛虎像巨龙
像活在众人的心目中
啊,我心满意足了,从阿固脚抬头
望一望,就能够见到它了
在森林的腹地,在河谷坡上
梦
梦啊,梦,你是什么样子呢?!
从昨天到今天,又从今天到明天
一个人,要活着就是一口气而也
像太阴与太阳一样相互生存
一个人,要活着就是骨气而也
像出生与死亡一样相互依赖
梦啊,梦,你是什么样子呢?!
我清楚地记得,你是始终半遮半掩
我只知道,很凶的斑斓虎豹也将老去
我还知道,弱不禁风的虫儿也将死去
然而很多事情,事实上就是过眼云烟
足可聊以自慰的是你在人们的记忆中
梦啊,梦,你是什么样子呢?!
你的面纱我好想把它揭开,我能行么?
我只一味地知道,迎接我的有很多个彝人
在阿固脚的街上,给我送行的也有很多个
很像我的父亲,行为和语言都一样
不像我的父亲,阳光和月色不一样
梦啊,梦,那就是你的样子么?!
人生如梦,人生果真如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