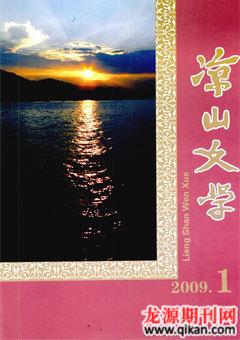本色
阿 蕾
罗果果又叫勒布果果。
以前知道凉山州歌舞团有个男领舞叫勒布果果,因为看凉山州歌舞团演出时,总听报幕说:“……演员勒布果果等。”那时只顾欣赏男子群舞的刚劲奔放或欢快热烈,对于领舞罗果果的印象却不是很深。
直到有一天闲侃中听罗果果的老乡夸起罗果果:“别看罗果果是凉山州歌舞团的台柱子,可他的妻子儿女还在甘洛乡下呢,他对妻子那好啊,每逢节假日都回家帮妻子干活,这种人难得啊。”从此以后,我总是被一幅蓝天丽日下一脸阳光的罗果果高挽裤脚手握春墙棒“咚咚”春墙的画面感动着,被怀揣农民妻子的照片在花团锦簇中自守自持的忠贞感动着,并萌发了一定要写一写罗果果的想法,而且在心里一再地给自己打气:不写泥土一样淳朴、本色的罗果果写谁啊!
罗果果的家乡在甘洛县一座形似马耳朵的半山腰,家里养有牛羊,小时候他给家里放牛时,春夏总是从家中偷偷咬下一小块砖盐,宝贝似地扎在衣兜里,到吃晌午时,扳来嫩笋倒插在地上,将捡来的于树枝覆在上边烧熟后,剥去笋壳蘸上隔着衣服咬成碎末的盐巴下养粑或是洋芋;秋天将嫩包谷撕去皮后,将小木棒戳进包谷芯的根端栽立在地上烧来吃,那香那甜至今回忆起还使人口舌生津;找着一窝鸟蛋或雏鸟时,用马尾编织的套子套亲鸟,还可吃到香喷喷的烧雀肉。可他不满足于这些,他时常眺望着远处终年积雪的贡嘎山和形似一把梳子的勒支哦布山,猜想山的那一边该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色呢。
那时山下河谷养羊的人家到了春末夏初就总是把羊赶上山托付给羊亲家,到秋末冬初才赶回山下过冬。每当山下的羊亲家们把羊赶上山或羊亲家们上山来剪羊毛时,是寂寞的罗果果最高兴的时候。因为这时羊亲家们总是把他们的孩子也带上山来和罗果果玩,还带来糍粑呀,落花生呀等等山下才有的稀奇东西,那时孤陋寡闻的罗果果还以为落花生是结在树上的呢。
剪羊毛前一两天,罗果果和这些山下来的小伙伴一起把羊拦进水塘洗澡,羊不肯下水时,他们就把羊们捉住,一只只“扑通扑通”丢下塘,溅起的一阵阵水花使他们的心花也跟着怒放,可惜那欢乐是短暂的。羊亲家们下山后,怅然若失的罗果果整天面对的仍然是静默无语的蓝天和层峦叠嶂的大山,还有石包一样大大小小埋头啃草的牛。那时的罗果果好想变成一只雄鹰飞出山外。
有一次来了一个和他差不多大的叔伯兄弟,那男孩是山下来的,已上学了的他站着坐着都在唱:
“毛主席呀哟,
我勒波果洛果觉(我们虽然身在大山)哟,
黑马北京觉(心儿向北京)哟……”
罗果果被这美妙的歌声迷住了,央求那男孩教他时,那男孩却把眼睛翻到额头上,说什么都不肯教他。那时的罗果果多么渴望能上学读书啊。他的四爸见罗果果那么聪明伶俐,竭力说服罗果果的父亲把孩子送去学校读书。为了让罗果果进斯补民族小学读书,他家于1959年从山上搬到乡政府附近居住,可惜碰上食堂化就辍学又放牛去了。
1965年9月凉山州在全州范围内选了三十几个舞蹈方面的苗子,送到中央民族学院艺术系学习舞蹈专业。罗果果有幸被选中,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也能到北京读书,那高兴啊,生害怕那是一场梦,所以他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文化大革命停课闹革命时,虽然没有老师上课,但罗果果想起以前自己过的苦日子,想起学习机会之难得,在别人或坐车或徒步进行大串连、斗“封资修”,“破四旧”、“立四新”时,顶着只专不红的指责埋头苦练基本功。
功夫不负有心人,他没有辜负老师的殷切希望,父母的竭力支持,于1969年9月毕业分配到凉山文工团担任舞蹈演员。在同班同学陆陆续续转行的情况下,罗果果凭着自己扎扎实实的基本功和不断学习提高的业务技巧,年过半百了还活跃在舞台上,挑起舞蹈队的大梁,直到去年还在《火·图腾》中担任角色。
爱岗敬业的罗果果不论平时的基本功训练。不论排练,不论正式演出都对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一丝不苟。他曾是很多舞蹈,如《阿哥,追!》、《刀舞》、《喜背新娘》、《金色铃铛》、《鼓声》、《谁最美》、《清清小河边》、《蹄脚舞》等等保留节目和《五彩凉山》、《彝之舞》的领舞。曾在大型彝族舞剧《奴隶颂》中担任一号主角,大型彝族歌舞剧《月亮部落》中任主要角色。还编创了《跳火神》、《尔玛茹萨独》、《解施且》、《抢柴火》、《抢羊》、《连干》、《马布情》等舞蹈节目。
天道酬勤,有关部门对罗果果的业绩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多次给予他省级、国家级奖及各种荣誉。如: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舞蹈研究会会员、四川省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凉山州文联委员、凉山州政协委员、凉山州民革二支部副主委等等。曾选他参加中国民族艺术团,赴希腊、马尔它、英国、土耳其等国家举办的国际艺术节演出,为宣传凉山,为彝族文化的对外交流作出了贡献,受到国家民委和文化部的表彰。
罗果果不仅在事业上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对爱情也坚实忠贞,始终不渝。当年为了事业,他连自己的婚礼都没能参加,父母在家为他操办婚事时。担任剧中一号角色的他正在渡口为建设渡口而奋战的人们演出大型彝族歌舞剧《奴隶颂》。
按理说象罗果果这样的、在当时来说比较稀有的文艺人才,是完全可以娶个吃商品粮的、有工作的女孩儿轻轻松松过日子的,而且也有人给他介绍过这样一些条件优越的女孩儿。
但很有孝心的罗果果考虑到自己是独子。家中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娶个可以在家照顾父母的农民妻子,他才能放心地搞自己的事业。夫妻俩一直两地分居到两个老人都去世后,罗果果才将妻子接到身边过团团圆圆的家庭生活。妻子在农村的将近三十年里,每到节假日罗果果总是匆匆忙忙地赶了火车赶汽车,紧赶慢赶赶回家帮妻子干活。很难想象一个活跃在五彩缤纷、莺歌燕舞的舞台上,在花团锦簇的脂粉堆中生活的人,还能挽起裤脚下地干活,手握春棒站在高高的山墙顶“咚咚”地春墙,可罗果果却习以为常了。
当问到他的农民妻子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拴住了他的心,使他对这桩在别人看来极不般配的婚姻如此忠贞时,他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娶妻娶德不娶色,糟糠之妻不下堂。就如阿鲁斯基夸赞自己的妻子相貌似麻布,心灵赛绸缎一样,我的妻子也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要不是她为我照顾老人,抚育孩子,为我解除后顾之忧,让我放心工作,哪能有我今天的事业呢。如果说我为宣传凉山,为凉山的文艺事业作出了一点贡献的话,我的荣誉有一半属于我的妻子。人家为我作出那么大的牺牲,作出了那么大的贡献,我能昧着良心伤害她吗?人得讲点良心呢。”
罗果果的确是个讲良心的人,他觉得妻子在乡下没机会出去见世面,就把妻子的照片揣在贴身衣兜里,到外边演出时走到哪儿带到哪儿,到了名胜景点就拿出来对着照片说:“你的人没能到这里。你的照片到了这里,就当你也和我来过这里了。”乍听象是俏皮话,显得有些幽默。但细细想想也有些酸楚:要是家庭经济宽
裕一些,罗果果的爱人自费跟着演出团到处游览也未尝不可吧。但罗果果家没那个条件啊。他那点微薄的工资除了自己省吃俭用,就全部拿回家添补家用了。
两个老人去世后,儿女们也相继成家立业了,罗果果觉得妻子在乡下苦了大半辈子,应该让她享享清福了,于是将妻子接到身边,将每月的工资及每场30元的演出补助悉数交到妻子手中,由她掌管。对家庭极负责任的罗果果完成了赡养老人的职责后,为了帮扶儿女,又主动将两个不满周岁的孙儿孙女接到身边照管,该上幼儿园的送到幼儿园。该上学的送到学校,日子虽然过得紧紧巴巴的,但因为家中有爱,日子过得很温馨。
见罗果果半边户的日子过得艰难,曾有人动员罗果果狠下心将沉重包袱一样的农民老婆离了,找一个年轻漂亮又拿工资的女孩儿过潇洒日子。我问罗果果动心了没有,果果说:“虎死留张皮,人死留个名。人活一辈子,要留下好名声、好家风给后代,不能留下坏名声、坏家风给子孙。我这辈子就认定了我这个农民妻子,我不会让其他女人替换她在我心目中的位置的。”
罗果果夸赞他的妻子有颗金子般的心,瞧他说起他的妻子时那副一往情深的神态,我有罗果果自己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象罗果果这样丈夫在单位上工作,妻子怀着金子般的心在乡下照顾老人,抚育孩子,支持丈夫事业的妇女很多。这些在单位上工作的男人也不乏罗果果这样知道感恩的,但也有不少良心缺失的人,在妻子竭力支持下混出个人模狗样后,就忘恩负义,不愿再面对为他耗尽青春年华的妻子的黄脸,而另觅红颜知己,还振振有词地以感情不合为借口,堂而皇之地将妻儿推进痛苦的深渊,昧着良心过他的幸福日子去了,所以罗果果的农民妻子是幸运的——她遇到了有着金子般心肠的罗果果。
彝族自古崇尚的是贤达男子要“集会骑骏马,进屋推磨子。”就是说作为男子汉在外面的世界要活得有尊严,不要猥猥琐琐。要干得起大事;在家里对妻儿老小要体贴、关爱。这和儒家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相一致的。能治国平天下的人属于凤毛麟角,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才出个把;可修身齐家却是只要有心人人都能努力做到的。但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婚姻象鸡蛋壳一般易碎的当今,虽然每场婚礼上都有令人感动的婚誓:“无论贫穷富有,无论疾病健康,不离不弃,相伴一生!”但因为受到社会转型期形形色色的诱惑,能真正履行誓约白头偕老的人恐怕不多,有些人甚至今天结婚明天离婚。所以每次应邀参加亲朋好友的婚礼,我总是病态地怀疑这场婚姻能坚持多久?我对那些为了自己享乐,无视最起码的道德准则。不管不顾家人的痛苦,抛家别子另觅新欢的人持怀疑态度:连自己的家都可以不负责任。连自己的亲人都可抛弃的人,能指望他(她)爱祖国爱人民吗?
罗果果不仅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亲人,也爱祖国爱人民,本着这样的忠贞,他在舞台上四十多年如一日,坚持把最美的精神粮食奉献给观众,出国演出为国争光。如今因为年岁不饶人,不再上舞台演出了,但他有个愿望:发挥余热,继承弘扬优秀文化,编导出本民族原生态的歌舞,将本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原汁原味地再现于舞台。说到这里,罗果果轻轻地哼起了家乡的童谣:
“老祖宗——
回来吧,
穿上你最华美的新衣裳,
披上你蓝靛染的新技毡,
穿上你最新的绣花鞋。
回来和儿孙欢欢喜喜过新年……”
看他那投入,那深情,仿佛过年时节晨曦中袅袅青烟下,孩童们齐声唱和着呼唤祖先归来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眼前,琅琅的童声合唱又在他的耳畔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