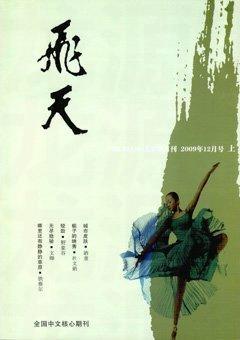《苦恼》中人性的冷漠与人的孤独感
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学医出身,在求学时期接受了自然科学的熏陶。他们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时代,都站在科学理性的角度,看到了社会空前的愚昧与无边的黑暗。契诃夫是俄罗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是闻名世界的短篇小说巨匠,其作品对世界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契诃夫说:“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1]鲁迅说他的小说多采自病态社会,以医学的类比来体现自己的文学主张。中俄两国的社会背景又有相似之处,所以我们看到了契诃夫和鲁迅作品的相似之处:在乍看起来令人可笑的社会现象里发掘出并不可笑的富有深意的内容。这在契诃夫的《苦恼》和鲁迅的《祝福》中都得到了印证。从中我们看到了两位作家崇高的艺术良心,对被压抑的小人物的深挚情感,含蓄的艺术风格和隽永的文学意境。
契诃夫的文学创作是从幽默小品开始的,但是随着在生活中与社会现实不断的碰撞与磨擦,他的作品在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也略显深沉。《苦恼》的问世,在俄国文坛上展现了与以往不同的契诃夫,幽默的契诃夫变成了“忧郁的契诃夫”。在表面冷淡和极度客观的叙事笔法之中隐含了道德的、社会的、民主的激情,从每一行话或每一个字里都感觉得到契诃夫对劳动人民的爱。《苦恼》写作的历史背景是19世纪80年代,地理背景是俄国的首善之区彼得堡的街头。文章开头的一段描写就已让人感觉到无尽的悲凉:隆冬时节,湿雪飘飞,车夫姚纳·波达波夫伛着身子,纹丝不动地坐在车上,瘦骨嶙峋的小母马“像拿一个小钱就可以买到的马形蜜饯糖饼”一动不动地呆立着,被遗忘在“这个充满古怪的亮光、不断的喧哗、熙攘的行人的旋涡里”。
契诃夫低沉的笔触写出了姚纳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的孤独。姚纳的儿子刚死不久,需要向人诉说他的苦恼。但无人真正理会他的痛苦。小说的主要内容便是姚纳四次想将苦恼向人诉说而遭到冷漠的拒绝,最后他的瘦马成了他倾诉对象的全过程。
姚纳的第一个诉说对象是一个军人,也是姚纳的第一个顾客。车夫姚纳试着跟“打趣”的军官说他儿子的死:“老爷,我的……嗯……我的儿子这个星期死了。”“哦!……他害什么病死的?”这似乎是很合人情的谈话方式。车夫姚纳立刻调转了整个身子朝向客人,足见其欲将苦恼倒出的强烈渴望。可他才要开始说军官就不耐烦地吼道“赶车吧……照这样走下去,明天也到不了啦。”姚纳得到的只是一句无关痛痒的敷衍而已。姚纳的第二个诉众是三个青年。他们在车上不住地胡说八道。姚纳试图抓住他们谈话的一个短暂的停顿倾吐他的苦恼。不料其中一个驼背青年却说:“大家都要死的,赶车吧!诸位先生啊……什么时候他才会把我们拉到啊?”三个青年与军人一样,对他的苦恼无动于衷。车夫姚纳看着三个青年的背影直至消失不见,他又回归了孤单,寂寞又向他侵袭而来。“苦恼,刚淡忘了不久,现在又回来了”。“淡忘”?丧子之痛怎么会就这样轻易淡忘?三个青年没有听他的诉说,甚至拿他开玩笑,这也可以让他对苦恼有短暂的忘却!之后,孤独、寂寞、苦恼的姚纳看到了看门人,希望再一次燃起,又一次下定决心跟他攀谈,结果却受到无情的呵斥。姚纳的第四个诉说者是一个爬起来去喝水的年轻车夫。可也只是一句“我的儿子死了”,年轻的车夫已经蒙着头睡着了。姚纳是这样急切的想把这一切苦恼讲给什么人听,这在他的生活中几乎成了必需,但竟没有一个人愿意听。无奈的姚纳,孤独的姚纳,苦恼的姚纳,最后把这一切说给小母马听了。小说以这样一段凄凉而又意味深长的话结尾:“小母马嚼着干草,听着,闻闻主人的手……姚纳讲得有了劲,就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它听了……”从姚纳四次失败的倾诉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对车夫姚纳的痛苦漠然置之的不仅仅是那个军官和三个游手好闲的青年,而且还有同样是劳动阶层的看门人和青年车夫。而正是他的拒绝把姚纳推向了绝望,他把心里的话统统讲给小母马听了。
小说从两个层面来写“苦恼”。从车夫姚纳来讲,儿子去世是苦恼,丧子之痛无人理睬是苦恼,但是更让他无法回避的苦恼是拉了一天马车,“连买燕麦的钱还没挣到呢”,姚纳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这么苦恼的缘故了”。然而作者从一个更高的角度让我们看到了茫茫人海中一个孤独的身影,同时也感受到当无尽的孤独感遭遇无情的漠视时的痛苦。《苦恼》写的是人的孤独与人与人之间的冷漠。人生最大的苦恼与其说是人人皆有的烦恼,不如说是人人对别人的苦恼都漠然视之。
契诃夫的《苦恼》让人很容易联想到鲁迅的《祝福》。如果说《苦恼》是契诃夫对人性的冷漠与人的孤独感力透纸背的刻画,那么在《彷徨》开篇的《祝福》中,鲁迅则将这一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祝福》写于1924年。在鲁迅笔下展现的是社会的丑恶,民众的愚昧和人性的冷漠。祥林嫂就是这种环境下的一个牺牲品。《祝福》的内涵要比《苦恼》丰富,但《祝福》中有一个内容与《苦恼》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对人性的冷漠与人的孤独感的表现。那么祥林嫂的遭遇又是如何的呢?
祥林嫂第二次来到鲁镇是再嫁再寡,又被大伯“收屋”,走投无路之时。“镇上的人也仍叫她祥林嫂,也还和她讲话,但音调和笑容却是冷冷的了。”这些她全不理会,只是直着眼睛,和大家讲她自己日夜不忘的故事。“我真傻,真的,”她说,“我单知道雪天是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我不知道春天也会有。我一大早起来就开了门,拿小篮盛了一篮豆,叫我们阿毛坐在门坎剥豆去……他躺在草窠里,肚子的五脏都给吃空了,可怜他手里还紧紧拎着那只小篮呢……”看到此,似乎是祥林嫂要比姚纳的情况好。她毕竟能把儿子是怎样惨死的经过讲出来,而且还产生了一些效果:“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的走了开去。”“女人们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难道祥林嫂的悲惨遭遇真的能唤得鲁镇人真心的同情和由衷的关心吗?当然不能!反而是出于“礼教”的教义鲁镇的人们都以同样的目光贱视她,嘲笑她。人们来听祥林嫂讲故事,那不过是鲁镇人百无聊赖的生活的一种消遣,只不过是为他们平淡无奇的生活增加些点缀,为他们波澜不惊、麻木不仁的日子平添了一件趣事罢了!祥林嫂的遭遇难道能比姚纳好一点吗?当然不能。事实上,祥林嫂的遭遇比姚纳悲惨得多。《苦恼》中姚纳的悲哀只是没有人理会他的丧子之痛,而《祝福》进一步写到了祥林嫂的悲哀先是被人们谈论继而被人践踏。这种“又尖又冷”的漠然令人避之惟恐不及,而这竟然是充斥着祥林嫂生活的全部。
契诃夫对不冷漠的明天的希望要比鲁迅朦胧,但这种希望毕竟是存在的。他说,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照生活的原样描写生活,但由于字里行间像浸透着汁液一样充满着浓重的个性,所以除了现有的生活之外,你还可以感觉到应有的生活,就是这一点使你入迷”。这“可以感觉到应有的生活”应该就是契诃夫的期望,也是他要给我们的希望。鲁迅在《祝福》后对这一主题也有思索:“古代传来而当今还在的许多差别,使人们各自分离,遂不能再感到别人的痛苦。”[2]这种人性的冷漠与人的孤独感是否也具有某种全人类性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因为各个肤色的人们都有着对交流、理解、关爱的渴望。因此契诃夫和鲁迅的期望不仅表现在他们的笔下,也延伸到了全人类。两位文学巨匠的呐喊也是人性最深处的呼唤。
【参考文献】
[1]朱逸森(译).契诃夫文学书简[M].合肥:安徽
文艺出版社,1988.
[2]鲁迅.坟·灯下漫笔[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作者简介:王春红,吉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