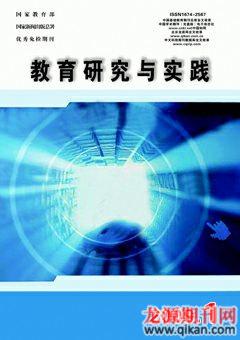话语伦理学与思想政治教育沟通
谷佳媚
[摘要] 话语伦理学以语言为基础,以普遍化原则和对话伦理学原则为核心内容,主张通过主体间的商谈和对话以保证思想道德规范普遍有效。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注重话语伦理,可以促使教育者转变角色、重构受教育者主体性道德人格;营造理想的沟通话语环境以及引导实践理解型沟通,从而促使沟通主体的共同成长,达到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目的。
[关键词] 话语伦理思想政治教育 沟通
Discourse Ethics with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the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Beijing,100872;
KaiFeng University, the Department of Marxism Studies,Henan Kaifeng,475004)
Abstract: Discourse ethics based on the language, its core contents is the generalize principle and the discourse ethics principle. Discourse ethics requests using talks and dialogue to ensure universal effective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standards . Pay attention to discourse ethics during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an make changes in the role of educators, rebuilt the main moral character of the educated, create an attractive environment for speech communication and practice 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And thus obtain thecommunicators common growth, achieve the purpose of communication of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Key words: discourse ethics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communication
沟通法是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中最常用的方法。它是指“教师借助语言劝导学生,根据学生的认识水平,充分地陈述理由,使学生理解并接受某种道德观点,改变或形成某种态度”。[1]P114话语伦理学主张一个有效的道德规范必须平等、自由地为所有参与者赞同。而沟通法是就教师和学生双方所依据的道德价值与规范(正当性要求)进行的商谈对话。教育者要想使受教育者接受所要求的道德规范(即使之产生有效性),就必须运用论据与受教育者平等、自由地说理。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本质上就是一种话语过程。
一、话语伦理学的主要观点
话语伦理,也称商谈伦理、对话伦理。它是德国哲学家、伦理学家哈贝马斯关于交往理论在道德理论领域的运用,其核心思想是:如果不存在外在的强制与内心的心理压抑,即在理想的交往共同体中,人与人的关系就应该通过语言的相互理解和理性的共识来协调。交往关系是人类的基本关系,人们之间必然会发生交往行为,因此人们就必须具有确定性和规范性的准则,这包括共同的语言背景和语言规则,也包括共同的价值准则。哈贝马斯从此引出了话语伦理学的问题,其最终目的是通过理性论证达致的理解和共识来解决现代社会里的道德价值和规范的多元冲突问题。
话语伦理学有两个基本原则。其一是普遍化原则,它是确定道德规范有效性的标准,即一个有效的道德价值和规范必须是值得所有人认可的价值和行为规范,能为大家普遍接受和遵循。哈贝马斯认为:“每个有效的规范都必须满足如下条件,即:那些自身从普遍遵循这种规范对满足每个个别方面的意趋预选可计产生的结果与附带效果,都能够为一切有关的人不经强制地加以接受。”[2]P33普遍性原则是随着人的道德意识和判断能力的发展而逐渐形成的。人们的道德判断只有真正自觉自愿,才会出于理性创立普遍的道德原则,并自觉接受这些原则的指导。只有当主体能够意识到自己是个自主自由的个人,而且能够把他人看成是自由自觉的个体时,才能从人类理性角度去思考问题。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人,同他人平等商谈,以达成共识。为此,哈贝马斯提出了“论证原则”,他认为,“只要一切有关的人能以参加一种实践的商谈,每个有效的规范就将会得到他们的赞成。”[3]P65也就是说,当人们对某一规范产生分歧甚至冲突的时候,应让人们展开充分的讨论和商谈,使所有具有理性的、参与讨论的人都可以根据自由意志提出自己的观点,通过自由讨论,进行认真的论证,确立何者为普遍规范,并进而通过这些规范达到为大家普遍接受和同意的结局。这里就包含着一个认知原则:一个规范当它符合一种普遍的或总体性利益(Generaliable Interest)时,才是正确的,这要求个体的利益都能被所有参与者接受。
其二,是对话伦理原则。此原则说明话语伦理学的必要性,“一切参与者就他们能够作为一种实践话语者而言,只有这些规范是有效的,他们得到或能够得到所有相关者的赞同。”[4]P67这就是说人们予以承认和尊重的规范标准应能代表全体社会成员的意志,能为人们自愿而非强迫地接受和遵循,因而每个主体都拥有话语权,都有权在商谈对话中表达自己的意志利益和要求。建构话语伦理需要一种“理想沟通情境”(Ideal Speech Situation),在这一理想的沟通环境中,每一个进入话语论证的人都必须拥有同等的参与话语论证的权利,同等的解释、主张、建议论证的权利,同等的实施表达式话语行为的权利,同等的实施调节性话语行为的权利。遇到意见分歧时,讨论者不依靠权威或其他控制手段去令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而是用“更佳论据的力量”(the Force of Better Argument)来说服对方,通过反复讨论达致共识。因此,“一个道德价值与规范是否合理有效,就在于能否经得起一个富有反省性的反复讨论过程的检验”。[5]P64 话语伦理学强调话语论证,因而非常重视交往资质(Communication Capacity)。交往资质是指个体在长期交往、学习中所形成的内在素质与能力。交往资质的形成是个体自我的语言认知能力及社会认同能力不断发展的结果。从话语伦理学的角度看,每个个体的交往资质及其社会化,并不是在个体意识里生成与发展的,而是在实践中生成并在话语交往、主体间构成的世界里发展的。正是在人际交往的话语互动中,每个单独的个体才能逐渐理性化、社会化,即被社会的语言规范和伦理原则“一体化和同化”,同时,又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发展出具有独立道德品性和独立道德人格。因此,道德个体的成长体现在主体间的对话与商谈活动中。个体道德意识的发展正是个体不断地运用语言在交互活动中自觉处理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冲突中获得的。个体道德能力的逐渐发展与交往资质的逐渐形成是同一过程。由此可见,话语伦理学与道德发展理论的相关关系使其更可能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提供一些启迪。
二、话语伦理学立足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是一项兼顾目的与手段的特殊的活动,它既希望通过沟通实践使得受教育者接受正确的思想道德内容,同时它又需要注意沟通过程和方法的“道德性”。按照美国学者麦克·莱伦的说法,如果道德教育要让儿童接受承认的道德观点,那么道德教育就有灌输之嫌,就体现出一种非道德性;而如果教育不将成人的道德观点传授给儿童而以一种“道德”的方式给儿童以放任和自由,那么儿童就难以有效地将道德规范领略于心。也就是说,如果以道德的方式来教,那么就教不会道德;而要教会道德,则需要借助不道德的方式。从中不难发现,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客观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相对立的两难现象。同时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又是一个价值传递与生成的过程,它有三种价值传递态势即灌输、引导和澄清,而现实中,这三种价值传递形态都不能很好的解决这种两难现象。
价值“灌输”本身就是不“道德”的。作为一种强制性的施教方式,灌输是为了追求内容上的“道德”而摒弃了方法和过程的“道德性”。灌输不仅仅是一个方法的问题,它有更为丰富的内涵。从目的上讲,灌输主要指教育者的目的、意图或指导思想是要通过诸如说服、规劝、奖惩等方式使受教育者接受所讲授的内容;从内容上讲,灌输是指教育者把某种具体的信念、教条或价值当作真理来教授而排斥其他一切与之相悖的价值,而这些具体的道德规则和特殊的行为准则都无法证明其在道德上的合理性;从方法上来讲,“灌输就是教育者为达到一个固定的目的而采用强制的非理性的甚至是‘权力主义的手段和措施,而不管受教育者是否愿意或是否有能力接受”。[6]对于价值灌输的排斥,理论界尽管已取得了共识,但由于社会道德风尚的日益低下,也有人认为灌输还是不可少的。正如美国学者霍尔指出:“在我们这个多元社会里,尽管这种直接的灌输方法是无效的,然而,任何道德上放任的企图也没有取得更好的结果。”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法就面临“要寻找一条中间路线。它既不强迫年轻人接受一套道德规则,也不给他们这样一种印象,即做出决定完全是一件个人主张或想入非非的事情。”[7]P292可见,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应该选择一条兼顾目的与手段的“中间路线”。
相比较灌输而言,现今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人们更愿意用价值引导和价值引导下学生的自主建构来作为价值传递方式。价值引导更注重过程的“道德”性与民主性:教育者打着“民主”的旗号,采取各种各样“民主”的教育方式,他们对受教育者“悉心照顾”、“关怀备至”,使受教育者在“感动”之中接受既定的价值规范。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的价值的引导是必要的。然而,由于价值引导信奉的仍旧是一套外在的、既定的价值规范体系,“引导”在实践中很容易就变成合法灌输的借口。教育者在所谓的“引导”中,充当的是道德真理的“代言人”和“善”的代表,所施行的乃是一种“温柔”的“暴力”,久而久之,受教育者就会失去批判反思能力;或者是受教育者在其时其地会“感动”,会暂时信奉既定的价值规范,而当他们面对社会现实时,这种假大空的规范体系会变得不堪一击。因此,价值引导采纳的依旧是单一的、不容受教育者商榷的价值体系,依旧是教育者的一种单向性“独语”而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双向性“商谈对话”,受教育者并不能真正地进行思想道德的自主建构。
价值澄清则是将思想道德教育沟通过程完全视为受教育者道德判断、道德评价能力的自我培养过程,将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形式”的注重发挥到了极致,相对于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灌输来说,它毫无疑问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然而,价值澄清本身就是一种无道德的价值传递模式,它只注重教育沟通的“过程”、“形式”而忽略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的价值观内容。价值澄清模式忽视价值观形成的社会性,强调价值观源于个体的经验,并随着个体经验的变化而变化,把个体的活动和经验作为确定其价值观的标准。由于单个个体的经验相异性,这样必然排斥思想道德教育中所存在的人类共享的价值,其最终结果必然走向道德相对主义;同时,这种模式更看重“如何获得价值观念”而不是“获得怎样的价值观念”,认为只需要“关注个体用以获得哪些价值的过程而不是特定的价值结果”,[8]P25这种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完全视为一种能力、技巧的培养,只重过程而轻视内容的做法,事实上消解了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功用,使得思想政治教育沟通成为一种“无道德”的教育沟通。
由此可以看出,这三种价值传递形态在面对目的与手段的“两难”问题时都是执其一端而无法兼顾的,而话语伦理以商谈和对话的形式较好地处理了目的与手段的两难,从而使话语伦理学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立足显得十分必要。
三、话语伦理学对思想政治教育沟通的积极意义
1.促使教育者转变角色
在传统的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教育者往往被认为是社会思想道德权威的代表,在沟通中充当着价值法官的角色,将毋庸置疑的价值观灌输给受教育者。在这种沟通模式下,沟通过程其实是控制式权力运作,教育者只是“制造螺丝钉”的“技术人员”,他们没有创造性和主体意识,不敢僭越雷池一步,自我的角色期待化为乌有,失去了生命的活性和丰富的色彩。而在现代的价值澄清道德教育沟通中,价值完全成了“个体经验的产物。它们并非孰真孰假的问题。”[9]P34在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教育者完全充当着价值旁观者中立的身份,这就完全抛弃了社会对其的角色期望,因此被人们指责为引起道德相对主义的肇事者。因此,这两种教育者的角色都是不可取的。在话语伦理学视野下,教育者的角色要从 “价值法官”的角色转变到“对话者”。既然是商谈对话,就意味着沟通双方在价值面前的平等性,就不存在谁领导谁、谁服从谁的问题,双方只服从于共同的价值真理。教育者角色从“法官”向“商谈者”的转变,就意味着双方以商谈、对话为目的的和谐关系的建立,意味着二者人格上的平等和相互尊重,意味着双方在商谈过程中“学生教师”与“教师学生”身份的不断转变。教育者要积极地参与商谈对话,共同地探讨价值真理。作为教育沟通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教育者要领导受教育者确立程序,选择沟通方式;作为精神领袖和激活者的角色,教育者又是沟通对话中的民主先锋,必须做到身体力行,并引发学生全身心投入的热情。
2.重构受教育者主体性道德人格
话语伦理学强调个体充分的话语权,鼓励共享与合作。传统的灌输型思想政治教育沟通中,教育者施行的是“一言堂”式的沟通方式,受教育者很少对价值观点进行质疑,或者是即使心中有疑问,在教育者的绝对权威之下仅有的一点灵性也化为乌有,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很难得到培养。话语伦理学视野下的思想政治教育沟通过程中,作为主导者和组织者,教育者要避免对话语的完全支配,避免整个沟通过程成为自己的“一言堂”,更应避免对受教育者话语权的“假性赋予”。让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拥有完整的而非部分的话语权,还他们以“言说”的自由,尊重受教育者的独特生命体验,使每个受教育者都能在体验中寻找自我价值,汲取生命的营养。因此,保证受教育者充分的话语权意味着鼓励受教育者,使受教育者愿意沟通;而作为受教育者,不能保持缄默,只听不说,要认识到自己在法律上、在人格上与思想政治教育者是平等的,有参与、说话和表达意思的权利。只有这样才能激活受教育者的主体意识,保持主体地位,自觉地根据社会要求调整已有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规范,主动地进行思想政治品德的建构,也只有这样,沟通所传递的信息才能成为对其有价值的信息。通过这样的 “沟通”,就能够培养受教育者正确的价值观念、良好的价值创新能力和自主价值建构能力。同时,话语伦理学下的沟通还是沟通主体之间经验共享和共同合作的过程,在共享、合作中沟通主体从封闭、僵化的“单子主体”成为开放、灵活的“交往主体”。这种模式的沟通能够增进沟通主体间相互了解与信任,让受教育者掌握处理人际关系的技能、技巧与策略,学会更合适地、更有效地表达自我。因为只有在与别人的合作与交流中,个体才能学会理解、尊重别人、考虑别人的需要和意图,在此基础上做出自己的决定并对这种决定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