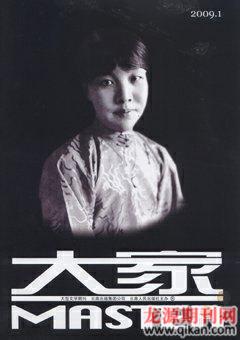维西河谷的时间碎片
李贵明
维西小镇
春天四月,雨滴温暖了,维西小镇四周山峦上白雪在消融。水从冰的舌尖一滴一滴淌下来,汇聚成溪流,山脉深处遍布透明的血管。大地的血液,穿过森林,从东西两面的磅礴群山轻流而下,最终汇聚成清澈的永春河。河水由南向北,经过不太宽广的谷地,穿过田野上无数村庄,朝着北方隐秘的出口轻轻流动。维西小镇在群山环抱的河谷,被春天的田野和闪光的河流轻轻拥抱。
这个季节,白色的蚕豆花在河流两岸的微风中轻轻摇动,麦苗碧绿,正在雨水和阳光中拔节生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芳香。我穿过田野的迷人香味,推开了维西小镇安详的门扉。
小镇倾斜的土地上有两座浑圆的山冈,像两座绿色的岛屿浮在半空。南边的山冈上古木苍劲,几棵高大的云南松在山冈上以各自的姿态屹立着,其间还有苍翠的香柏树。高原风吹拂下,树木们枝干扭曲却未曾停止生长,最终长得苍劲庄严。这山叫做白鹤山,维西小镇上的人们却叫它文昌宫。白鹤山上那些历经百年的清华古木得以存留至今,就是因为这座山冈上有一座“文昌庙”。清朝以前,众多远征军队和流边垦土的汉族官员,不远万里来到云南的雪域高原,在温暖的维西河谷定居下来。道光六年的春天,他们在白鹤山破土修建了一座川人会馆,里面供奉了“文昌帝君”。柏树们也被文昌帝君的信徒移植至此,云南松却是维西小镇上土生土长的,它们和香柏树一道逐渐成为遮盖文昌神庙的葱茏树木。
文昌帝君的居所在“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中轰然倒塌,但生活在小镇上的人们在时间的更替中,谁也没有妄想砍伐这些树木。他们的内心仍然存留着“文运昌盛”的虔诚心愿,也自然对古木心存敬畏。这些外形虬曲的树木也因此成为维西小镇上年代久远的植物。
白鹤山北边不远处的山冈,是维西人的“关圣殿”,树木葱郁的山冈,是武圣关公的领地。
站在关圣殿的山冈上,大地阶梯上的维西小镇尽收眼底。几百年,小镇上的人们生活在缥缈的炊烟深处。他们在历史中,感受着和平与战火,感受着生命的隐秘脉动。关圣殿门前一片开阔的空地,曾经是维西小镇的封建统治者处决犯人的地方。当年,气势恢弘的庙宇里,那个长胡子的战神,手提月牙长刀、怒目圆睁、一动不动地注视着维西大地,放眼茫茫雪山。那些身穿红色囚衣的犯人被狱卒五花大绑,踩过小镇十字街巷子的青色石板,一步一步走向高处的刑场。他们之中一定有饥饿的贫民、一定有鸡鸣狗盗之徒、也一定有豪气冲天的志士。无一例外,都在关圣殿前划破空气的鬼头大刀中人头落地。
我曾经见过这个庙宇的一段残破墙壁。那个时候,庙宇里泥土塑就的关公已经分崩离析,身体往低处塌陷,重新成为土地的一部分。
前殿的平台仍然存在,那里一度是维西小镇的人们上演大词戏的地方,那些穿着绸缎衣服的演员面容光鲜,在维西群山的波涛中敲响金锣铜鼓,上演着一台又一台来自中原的汉语戏曲。戏台前面有两棵桂树,一左一右,一棵金桂,一棵银桂。花开时节,满树繁花像两件暗香浮动的大词戏装,神秘的香气在透明的空气中化为无形的翅膀,笼罩着关圣殿的残垣断壁。今天,桂树仍然散发着它的香气,而关圣殿的位置已成为保和镇小学宽敞的教室。朗朗书声穿过蔚蓝天空,落在对面“文昌帝君”的白鹤山。这些坐在关圣殿的废墟上朗诵唐诗的学子,仍然延续着祖先“文运昌盛”梦想。
两座山冈仿佛维西小镇的时间之门,文神武圣分列左右,像贴在木门上的桃符。沿着它们折射的隐约秘光,可以看见小镇的人们崇文尚武的古风。进山冈之门西行半里,就是小镇的核心——十字老街。
这里有通往东南西北的街道,也曾经有过黄土筑成的城墙和四个破旧的城门,作为冷兵器时代军事防守的标志性建筑,如今它们因为失去价值而荡然无存了。芳香的田野上通往四个城门的道路,成为居住在高山峡谷中的山民出入小镇的途径。我常常在小镇的街道上看见那些居住在流霞山谷中的傈僳人,牵着他们的山地马,驮着栗木烧制的木炭,在小镇的巷子中游荡、出售。清脆的马蹄踏在早晨清冷的石板上,回声落在巷子中。住在巷子中的汉族女人会打开他们暗色的门扉,对马背上的木炭估价。
傈僳人不会过高讨价,但往往会坚持内心底线上物品的价值。与傈僳人相处了上百年的小镇居民知道。因此,我们很难在傈僳人的交易中看到不休的讨价还价,这个小镇俨然与它正在经历的商品时代相距遥远。
那些出售山货的傈僳汉子,强壮的腰间常常佩带着木柄长刀,显现出神秘部落远古武士的苍凉身姿。他们的女人穿着鲜艳的衣服,像温顺可人的绵羊跟随他们。几乎每个出入小镇的傈僳人,都挎着一个做工精致的布包。布包上绣着鲜艳的花朵和飞翔的图案,图案下面是飘动的丝须,走起路来,腰间便跳动着绯红的彩霞。沉默的傈僳人,其实都是富有激情的浪漫饮者。他们在维西小镇上偶有相聚,便会在街角饭店或者山间路旁开怀畅饮,倾其所有,毫不在乎。偶有情人相见,也会饮酒高歌。
兴尽,翻身上马,绝尘而去,回归他们众神栖息的苍茫大地。
十字老街热闹的街道上,还残留着清代建筑的陆离光斑。几栋有着乌黑筒瓦和暗色门扉以及陈旧雕饰的阁楼。它们的颜色在时间的光中脱落下来,还原为陈旧的铜色。二楼都是雕花的木格窗子,一二楼的的结合部是黑色筒瓦的屋檐,看起来更像是“阁”而不是“楼”。不难看出,这些房屋与江南水乡的建筑风格如出一辙,它们也曾经雕梁画栋、流檐飞角。如今,乌黑的筒瓦上,年年青草,在风中招摇,仿佛陈旧的阁楼在维西小镇的建筑革新中大口喘息。一楼,今天是理发店、寿衣店、冰淇淋店、音像制品店。
春天时节,走在这条步行街上可以嗅到浓郁的兰花香。风尘仆仆的傈僳人沿街摆放着从深山密林中采集而来的兰花,等待出售。他们并不准确地了解这些绿草的价值,而是在估摸与猜测中完成与外来商人的交易。沿街木楼的一楼屋檐上,通常也摆放着阁楼的主人细心栽培的兰花。在陈年店铺中操着四川口音或者维西方言的女人们,整个上午都像一只只忙碌的蜜蜂。只有傈僳人返回群山,街道恢复了冷清,她们才打开二楼暗色的木格窗子,探出头来侍弄兰花,斜看黄昏。白色的云团低垂在她们暗色的屋檐上,流年光影从她们光洁的额头轻轻划过。她们正在与她们所栖身的建筑一道,成为时间之手素描的黑白影像。
十字老街的一头通往南门街,说是街道,其实是一些纵横相通的悠长巷子。有一条巷子通向一个寂静的沟谷,沟谷里流淌着来自西部的雪山之水,泉水滋养了茂盛高大的核桃林,林中栖息着鸣唱的布谷和飞翔的百鸟。核桃林巨大的华盖下面曾经有一口幽深的老井,砌老井的圆形卵石上长满绿色的苔藓。柔软的苔藓静静摇摆在水中,清澈的井水映照天空,像一枚泛着微光的银币。老井边是人们乘凉的好去处,几个神情坦然的老者,放下拐棍,坐在丢弃的石头磨盘上,叼着烟斗,漫谈江湖,犹如放牧时间的浪漫居士。老井的另一头曾经是地主的神秘宅院,如今只剩残破的断壁。走在这段安静的巷子中,随时可以遇见几个像花一样灿烂的少年。他们仍然居住在黑瓦黄墙的房屋里,他们的房屋通过秘密的巷子连成一片,成为城中幽静的村落。从远处望去,整个村落苍劲的人字形屋顶与远山的秀色相连,仿佛白云下面荡漾的暗色微波。
十字老街的另一头是青龙街,这是一条倾斜的巷子,通往永春河谷上纳西人的村庄。维西小镇上神色自若的纳西人多数从这里出入。从衣着和外表看来,他们与居住在小镇上的汉族人并没有什么区别,除非他们开口,说出刚毅有力的纳西话。小镇上有重大节庆的日子,纳西女人们也会穿出她们青白相间的服装,像一只只展翅的青蝶,谈笑着穿过安静的青龙街巷子。
在我接触的纳西人中,居住在维西小镇附近的纳西人说的纳西语是最有力度的,语言节奏和质感与别处的纳西语有着很大的差别。我曾经认真聆听过他们的对话,一种刚毅的发音和节奏,似乎熟悉,又似乎陌生,仿佛我在某个遥远的年代与他们相遇过,却又虚幻得令人捉摸不定。纳西人有着超强的应变能力和惊人的勇敢习性。我注意到几乎每个纳西人的头顶都散发着祖先的智慧光环和坚定的生活信念。数百年来,他们与生活在维西小镇上的汉族人相濡以沫、情同手足,就连建筑风格与生活习惯也形成了看似相同的格局,不同的是纳西人仍然相信他们的丁巴什罗圣祖,仍然相信他们的祖先来自东方草原。
小镇附近的纳西人更多的时候躬耕在永春河谷的田野,晨耕暮息、奉读诗书,有时也煮酒欢歌、通宵达旦。他们在流光淡扫的永春河谷留下快乐或者悲伤的往事,也在永春河谷的农耕文明中留下了斑驳的足印。
每年初秋,小镇附近的纳西人收完稻谷,在明波闪动的永春河谷留出一片金色的空地,维西的各族人会在田野上举行盛大的聚会。小镇上的人们把它叫做“交流会”。交流会其实是为了方便商品交易而举行的商业性聚会。维西大地的雪山峡谷之间盛产骏马肥牛,常年奔走在深山密林中的马群和牛群野性未消,交易只能在开阔的田野上进行。这个时节,小镇之外的傈僳人、藏人、彝人,停下手中的劳动,赶着他们的牛马,来到维西小镇。成千上万的马匹和牛群云集田野,仿佛一首首悠长的牧歌在永春河谷中蔓延开来。来自大理的回族人似乎都是精明的商人,他们通常会选中体格健壮的黄牛,贩卖到遥远的大理。而生活在雪山高原的藏族人骑马而至,更多的时候是为了寻找善于奔跑的骏马。小镇附近的纳西人买走强壮的公牛,则是为了耕耘他们富饶的土地。在庞大的牛马交易中,傈僳人通常是主要的出售者。小镇里生活的汉族人,因为远离了游牧生涯,在骡马交流会场搭上摊子,凭着他们精湛的手艺,出售鲜美可口的食物。参与骡马交流会的各族人等,为等待商机,通常会在广阔的田野上搭起帐篷席地居住七天之久。从远处看,骡马会场青烟袅袅,像是一个游牧部落在闪光的河谷中等待迁徙。
交流会的七个夜晚,是各族情人的狂欢派对。维西小镇的十字街在夜幕降临之际,禁止一切车辆通行,空出水泥路面唱歌跳舞。人们踏着天边绯红的流霞之光,不约而同地来到十字街口。看一看,天色尚早,三五成群钻进沿街小店,喝酒漫谈,等待着露天舞会的开场。黑夜到来,天上的神灵洒下一把跳舞的豆子,舞蹈和歌唱之神降临维西小镇。黑压压的人群以族为界,烧燃篝火、围成圈子翩翩起舞。傈僳人的阿尺木刮、瓦器,纳西人的阿里里,藏族人的锅庄。傈僳人的舞蹈狂热奔放、纳西人的舞蹈优雅细腻、藏族人的舞蹈端庄整齐,小镇上的汉族人有时也会在舞场边缘的安静地带对唱几段优美的维西山歌。顷刻之间,十字街成了歌的海、舞的浪涛。在海洋中,我们来不及赞叹维西人与生俱来的艺术天赋,便会被一些帅男靓女拉进激情汹涌的舞场。不同圈子的舞蹈犹如不同的部落在围火狂欢,随着舞步起伏的头颅们沉浸在各自优美的韵律中。不管澄净的夜空是否星移斗转,狂欢的人群犹如众神在跳跃,直到启明星在高高的山顶升起来。
维西河谷的时间碎片
桂树开满白色的花,站在秋天中央,风吹过,偶尔有花落下来,像雪。整个村庄弥漫着沁人的花香。
村庄里这棵唯一的桂树是父亲从土司家的果园里偷偷拔来的。
可能是1941年的春天,父亲望着土司果园里这棵绿色的树苗,以为是黄果树,想起秋分时节挂在土司庄园里那些沉甸甸的金色果实,父亲咽下了口水,忍不住偷偷拔走了一棵树苗,种在村庄的一个隐秘角落。这棵树在阳光和雨水中渐渐长大,奇怪的是这棵“黄果树”越长越不像它的同类,既不开花、也不结果,只是一直生长碧绿的叶子,四季常青。
某一年秋天,土司庄园的黄果树上又接满了金色的果子。村庄傍晚的空气中传来一阵又一阵隐秘的花香,并且日益浓烈。人们终于忍不住从屋子里走出来,沿着花香传来的方向寻找香味的来源,最终发现了那个隐秘之所居然有一棵开满白花的树。原来是父亲偷来的那棵“黄果树”在一夜之间开起了芳香的繁花。常年行走在山谷流霞中的傈僳山民,并不知道这棵盛开了扑鼻香花的树,到底是什么。以为它既然开出如此浓烈香味的花朵,也应该会结出鲜甜可口的果子,就静静地等待着。然而,等到繁花在秋风中一朵接着一朵落下来,最终散尽,也没有结出哪怕是一颗小小的果实。第二年秋天,当人们在村庄的傍晚嗅到一阵又一阵的花香,就知道了这是那棵安静的“花树”在散发它的隐秘芳香了。
流年迟暮的土司是一个女人,她并没有追究在1941年所丢失的那棵树的去向。或许她根本不知道她大片的黄果树苗里,曾经隐藏着这样一棵与众不同的花树,因为在她细心耕作的庄园,除了金灿灿的黄果树外,人们从来没有看见过一棵芳香的桂树。
清澈的水流滋养了不太宽广的永春河谷,土司夫人居住的这片庞大庄园在这片谷地上升起来之前,维西境内的傈僳人,在永春河谷的光影之中狩猎、采集和农耕,过着慕天席地的部落生活。某一年,忽必烈的蒙古军队席卷了青藏高原,沿着横断山脉的大地阶梯一路向下。岌岌可危的大理帝国驻守北方的臣邦,面对势如破竹的元朝大军,在金沙江南岸的石鼓镇放下了武器。元朝大军由此进入大理平原。一马平川,大理帝国土崩瓦解。从此在云南西北,成就了丽江木氏土司漫长的统治时代。生活在金沙江、澜沧江两岸以及永春河谷的傈僳族部落,连同维西这片大地,卷入了土司时代领地争夺的血腥战争之中。长达400年的战争之火,也造成了傈僳民族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的迁徙。他们在傈僳族军事将领刮木必的带领下,脱离纳西人土司与藏人土司长年战争的历史夹缝,先后到达怒江流域,然后在夕光中翻越高黎贡山,沿独龙江而下,最终聚集在缅甸的密支那。
大部分傈僳人的出走和战争的创伤使维西河谷留下了大片的空地。丽江木氏土司派遣他的纳西军团从维西永春河谷开始,一路向北,经过澜沧江岸的叶枝、康普,最后到达了藏地德钦,沿途留下了大大小小的土司衙门。然而,留守在维西高山峡谷的土司们在漫长的战争之后,发现没有了傈僳人的领地日复一日地荒了下来,他们毫无意义地空守着人烟稀少的广阔土地,便又遣使者从遥远怒江说服一些傈僳人,希望他们回到自己的领地居住。由于世袭制度的影响,当年从温暖的丽江深入维西不毛之地的纳西军队和他们的后裔,在维西大地上繁衍生息,最终融为维西土著的一部分。纳西人就这样分散居住在了永春河、澜沧江沿岸,成为维西土司时代的遥远背影。土司夫人的庄园就是这样在时间之上缓慢升起来的。在我父亲偷走桂树的那一年,不知道维西最大的叶枝“莫刮”(纳西语,意为土司)已经承袭了多少代,只知道1941年的土司是传说猛虎化身的王嘉禄。在漫长的时间河流中,叶枝小镇也因为这些土司的世袭流传而成为维西近代历史的隐秘核心。
父亲说的这个土司庄园,并不在叶枝,而是坐落在维西小镇北方7公里处的永春河西岸。这个土司的豪宅今天的行政划分上属于维西县永春乡拉日村腊普湾社。这是一座典型的大理四合院建筑,比起那些低矮的木垒房,一度显得气势恢弘,庄严气派。居住在里面的人,说的全是纳西话。经过数不清的世代世袭之后,在我父亲偷走桂树的那年,这所房屋的主人是一个孤独的女人,她的丈夫是居住在这所房子里的最后一任钱氏土司。有一年,由于洋人传教士在他领地上的傈僳人中传播基督教,信仰藏传佛教的土司与洋人传教士多次干涉没有结果,便把洋人告到了维西县衙。然而,对于处理中国与外国这样的关系,维西县衙门的级别无论如何实在是太低了,钱氏土司和洋人的官司便打到了丽江府衙门,传说最后闹到了省府昆明。官司不知所终,他却在返回维西的路途中神秘失踪,留下了土司夫人寂寞空守大片领地。土司夫人与她的丈夫膝下无子,他们的一生只生育了四个女儿,其中两个女儿早年夭折。另外两个女儿在1941年的时光中是两个八九岁的小女孩。我的父亲和从密支那、怒江返回维西的部分傈僳人一样,由于战争余光的震慑,对这两个小女孩和她们忧郁的母亲心怀敬畏。
1941年的土司夫人有17条老式步枪,有常年居住在家里的长工,和在她属地上耕作的傈僳人佃农,他们喂养和放牧土司家的马匹,耕耘土地。第二年,她应叶枝土司王嘉禄的要求,派遣她的马夫带着武器和30多个傈僳人充当民夫加入“福碧泸练抗日自卫队”远到怒江守土抗战。这个女人从此成为维西境内唯一没有武装的土司。据说这个孤独的纳西女人,能说一些日常的傈僳语,比如:“喂马,吃饭,唱歌,跳舞”等。那个年代,其实土司已经不叫土司,但是由于传统习惯,人们仍然称呼她为土司。而在深山丛林中奔走的傈僳人和她的家仆,必须尊称他们为“阿弓扒、阿弓玛”,那是傈僳语里“天神”和“女神”的意思啊。因此,遇到土司家族的人,人们必须低着头,让到路下,请他们先通过。这两个看似简单的名词,奴役了几代傈僳人一生的思维、剥夺了他们一生的劳动,也决定了一个女人一生的幸福与苦难。
每年的大年初四,是土司豪宅里最热闹的时光,四村八寨的傈僳人必须拿着他们的山货、药材到土司家里拜年。由于傈僳人生活在“土司的领地上”,万物皆属土司所有,因此按规定,无论是田间耕作的收成还是在深山密林中捕获的猎物、仰或采集到的山珍有一半是要进贡给土司的。父亲说这个迟暮的土司夫人比起其他土司来,似乎有着一副好心肠。因为她在正常的赋税之外,并不在意人们在春节期间进贡的物品有多少,只要来人就行。即使你一无所有,就带一双筷子给她,她也毫不在意,但是所有人都必须前来跪拜请安,以此警示人们不要忘记她在这片土地上的高贵地位和无上尊严。这个寂寞的女人空守在时间深处,也许是太寂寞了,所以她有一个唯一不得不实现的要求,那就是每年的大年初四晚上,必须给她带来一场盛大的傈僳舞蹈。这却是傈僳人的拿手好戏了。傈僳人在得到土司家的仆人分给的一块肉、一碗饭之后,等待着天黑。天若黑下来,他们就在土司家宽阔的院子里,烧起大火,吹响笛子、弹起四弦木琴、拉起弦子载歌载舞。土司夫人穿着干净的衣服,站在朝西的二楼扶着木栏杆,像一个安静的观众观看舞场里纵情狂欢的傈僳人。她的两个女儿和她们的纳西伙伴,在傈僳人的舞场里追逐嬉戏……若干年后我走进这座安静的院落,抬头看见四合院二楼暗色的木质栏杆,仍然能够感觉到父亲讲述的那个纳西女人穿着绣花的暗色唐装,站在那里静静地看着我。而四合院中央地坪上铺满的鹅卵石光洁的表面,似乎还有傈僳人赤脚跳舞时留下的余温。
1949年初,革命的风暴席卷维西河谷。维西地下党组织人民进行武装暴动,如风卷残云,在一夜之间推翻了国民党政权。那年春天,当土司夫人的黄果开满花朵的时候。维西人民武装自卫队处决了盘踞维西上百年的叶枝土司最后一个承袭者——所谓的国民党“三江总司令”王嘉禄。维西土司政权体系由此逐渐瓦解。这个被农民自卫队武装处决的“刀枪不入的猛虎”其实也是土司夫人的女婿,她的大女儿阿吕,在此之前不久成为王嘉禄的小妾。由于王嘉禄命丧黄泉,阿吕辗转穿过春天的迷蒙烟雨,从澜沧江边的叶枝小镇返回了永春河岸的家乡。
那年初秋,维西农民自卫队奉命赴外地作战。11月,王嘉禄手下悍将他西打着为王嘉禄复仇的旗号,率领千余武装沿澜沧江而下,进入维西境内。
当他西的武装经过不太宽广的永春河谷,到达腊普湾土司夫人的领地时,在时局风起云涌变幻莫测的风口浪尖,因为他西与王嘉禄土司的特殊关系,土司夫人接待并放行了他西武装的一部。他西率领武装于11月20日攻陷维西县城,烧毁了县城附近的一片纳西人村庄,维西局面更加趋于复杂。土司夫人领地上的一部分傈僳人为躲避战火又走进了山林,或者重返怒江,甚至远走缅甸。
好在他西与农民自卫队的战斗由于人心向背,实力悬殊,并没有像以往争夺维西河谷的战争一样成为漫长的拉锯战。1951年,维西农民自卫队在人民解放军边纵三十三营的支持下重返维西,他西的武装在三江峡谷与雪山之间溃散,一个“清匪反霸”、清算历史责任的时代来临。
由于数百年来腊普湾钱氏土司与王嘉禄土司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复杂关联,土司夫人成了这个世袭百年的钱氏土司家族最后一个牺牲品,这个寂寞一生的女人被自卫队员押赴刑场,站到了她的“子民”的枪口下。传说,由于她的一生没有杀过人,对领地上的人民也不太苛刻,后来又改判了她的罪刑。但是,当一骑飞骑拿着改判文书到达刑场的时候,她已经倒在血泊之中,清脆的枪声结束了她的生命历程。也许命该如此,她的前辈们所犯下的罪行和自己做下的一切,在一颗子弹的呼啸中,都由她全部承担了。
厌倦了战争的傈僳人在听到维西河谷的枪声逐渐平静之后,才从他们栖息的高山密林中走出来,回到田野上,他们看见了一个完全崭新而又陌生的时代。
几年后,土司的豪宅被分配给村庄里最贫穷的傈僳人居住,满院金色的黄果也成了父亲和他的朋友们唾手可得的食物。那些曾经在属于土司的田野起早贪黑地进行劳作的傈僳人,坦然自若地站在了属于自己的土地上,晨耕暮歇,煮酒欢歌。土司夫人的两个女儿也分别嫁给了他们所爱的人,成为大地上质朴的劳动者。
父亲从土司庄园里拔来的桂树,成为村庄里不可缺少的风景和人们的共同“财产”。年复一年在秋天开满白色的花朵,不喧嚣、不动摇。风吹过,偶尔有花落下来,像雪。村庄里生活的每个人,都能够嗅到它散发的沁人芳香。在阵阵隐秘的芳香中,父亲似乎又想起他们那一代人经历的艰难和恐惧。
如果世界上的每个人、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放下贪婪和欲望,像这棵安静的桂树,活在属于自己的土壤、阳光、空气和雨水之中,周身散发爱的香气,人类就可能得到了真正的幸福。
本文插图为埃舍尔作品
责任编辑:玉波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