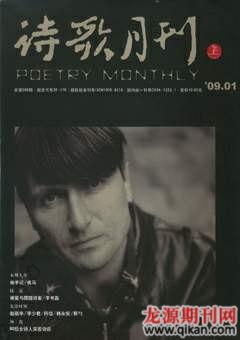八零的诗(12首)
八 零
今世歌
鬼魂们也有错把阳间
当作阴间后院的时候
趁着没有阳光的时刻跳下来
他们的腿太细了,类似于一根大头针
他们从不敲阳间的门
只打孔机那样在门前的杨树叶上留下记号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知道这一点。
阳间的人啊太忙了
已好长时间没回家
姿态
我逐渐认识到
我身上存在这样的毛病——
走路时脚向一边撇
站立时屁股一边倾
坐着的时候四肢是斜的
入睡之后身体是侧的
与情人相会,心歪
面对领袖大师,脸歪
与吵闹的庸常生活相处,肩歪
没一处是正着的。
“瞧你这生前坐立不规的坏毛病!”
上帝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这老家伙,
还不快把盒子端正了,
免得把自己撒的到处是……”
有感
有一天一个朋友
突然从我身后赶上来
"哇,你的后脑勺上
长了不少白头发呀!"
我知道他口气有多轻松
就像在说一个玩笑。
我知道这是事实,可能说什么呢?
生活总喜欢对我这样——
打背后突然袭击我一下
从我的脑后向我发抛来白眼
白花花的凉意顿时
在后脑上燃起
写一首心平气和的诗
早晨是令人神清气爽的
只有一个人的童年那样一小段时光。
早晨的女人是利落的,
我总盯她们的耳朵看
她们的扣子像牙齿一样齐
路口干净,警察还没有把白皮带扣在腰上
急救车停在我路过的大院,
经过时有意将脸在车玻璃上照一照
我到外面吃早餐,
早晨的包子又白又软
像一些小小的愿望,含着汁水。
如果我一边吃一边看报纸
就一定会看到这样的新闻——
“一名儿童正在迅速成长
即将步入烦恼的青春期……”
与子书
我的胃里住着三个兄弟
一滴水 一滴酒 一滴血
但是他们从来没有拥抱过
我不是一个合格的父亲
他们从来不愿表现地亲密一点
我不指望他们养我的老
只希望有朝一日他们在空中相遇
一小缕混合的蒸气,
经过我的尸骨
辰光
墙壁上留下整座城市
三流艺术家们的大幅国画
许多只鸟飞烁其间
这是惟一的希望啊——
今天早晨当我一边骑车经过一面无心观赏时
墙外的树枝上正有两只鸟在相互啼叫
世界如此虚假,
仍有真实声音在侧
时光
不是因为寒冷
而是因为孤独通体长出亮晶晶的小疙瘩
通常是这样,
早晨五点开始战栗
从落满榛叶的林子里走过
到河的那边去
黄昏时走回来
过了河,生长告一段落
战栗停止
躺下,从榛叶丛中
打几个滚出来
每个疙瘩上,
都插着一根松针
通常是这样,再回到闹市的时候
耳边总响起这样的赞叹
“瞧,快瞧呀
一只大个的卡通刺猬”
锋利的童年
我和三个玩伴
小C,小M,小H
同时爱上了储集车站光溜溜的铁轨
我们心怀鬼胎
其实不过是一路货
各揣着一枚大铁钉
相约来到下午的铁道边
猛烈的震动过后 我们心跳停止
大铁钉被飞驰的车轮
扎成了小扁刀 远远地甩在一边
刺眼的太阳光下
光亮,锋利,带着铁轨的热度
冰凉的空气里
我们四个后来前程不一的伙计
各握着心爱的的刀子
并肩从高高的路基上走了下去
路边一棵大叶杨的根部
留下一排
歪歪扭扭的大名
瞬间的孤独
突然之间
产生这样的恐惧——
当我把这个月的最后一张日历
翻过去的瞬间
心猛烈地
沉了下去
这恐惧啊自然不是来自对时间流逝的恐慌
而是我突然意识到
站在我这边的东西
正被一点点拿走
如同一位人民的领袖所担忧的那样——
所有热爱他的人民
转念之间
把他丢在了一边
我在做针尖上的事情
在游戏厅
开始我打斯诺克
球小,洞口也小
可我打的并不赖
后来打八球,
球大洞口更大的那种
却失误频频
以至于前几日踢个头更大的足球
面对宽敞球门
竟屡屡打飞
由此看来——
我不是个善于应对大事物的人啊,
阿基米德说给他一个杠杆
可以翘起地球
我想说的是 给我一个针尖
我要在上帝的睡袋上
扎个小孔
命运如此真实
我看到死神
在同上帝打球
隔着前排无数观众
隔着他们嘴里
升腾的雾气
视线朦胧,看不出是羽毛球
乒乓球还是网球
白色的影子
伴着急促的呼吸跳来跳去
时不时滚到界外
滚到观众的脚边
从我们中间
寻找一名球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