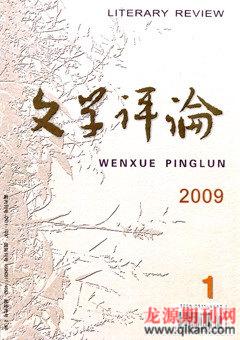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
邱江宁
内容提要本文所做的,是元代文学史的一段补阙工作,主要阐述三方面的问题:一是奎章阁文人与元代文坛重要人物的深密关系。二是奎章阁文风对于元代文坛的贡献。三是奎章阁文风对于元代中晚叶的文坛格局以及明初文风的深刻而又广泛的影响。
现有的元代文学研究中,很少有人整体地关注过“奎章阁”文人及其对于元代文坛的巨大影响。元代的奎章阁学士院于元文宗天历二年(1329)三月设立,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罢,1341年改为宣文阁,后又改为端本堂。奎章阁存在的时间虽然十二年不到,但由于它汇聚了元中叶以来最优秀的文人群体,在元代文坛有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对于元代文学的鼎盛和文风确立居功至伟,并对后世文学产生了不可磨灭的重大影响。要把握元代文学鼎盛时期的文风和发展方向,无法绕越奎章阁文人圈与元代文坛的关系。
一奎章阁学士院与奎章阁文人圈
奎章阁学士院设立于天历二年三月。二月,元文宗才登基。其实元文宗尚在金陵潜邸时,就向当时在上都的明宗提议建奎章阁,并命人将拟入阁的人员名单送给明宗批示。奎章阁是为帝王万机之暇读书游艺而设,是昭代之盛典,更是国家、社会拨乱反正,兴隆文治之所需。虞集《开奎章阁奏疏》云:
……将释万机而就佚,游六艺以无为,此独断于睿思,而昭代之盛典也。乃俾臣等,并备阁职。感兹荣幸,辄布愚忱。钦惟皇帝陛下,以聪明不世出之资,行古今所难能之事。以言乎涉历,则衡虑困心艰劳之日久;以言乎勘定,则拨乱反正文治之业隆。
奎章阁文人得到了元文宗相当的礼遇和尊重,“益优礼讲官,既赐酒馔,又以高年疲于步趋也,命皆得乘舟太液池,径西苑以归”,最高统治者如此用心笼络和礼遇文人,怎么不能令“闻者皆为天子重讲官若此,天下其不复为中统、至元之时乎?”恰如清人秦惠田所云,“元之文宗可称右文,然其时奎章阁诸臣如虞伯生、欧阳原功、揭曼硕、黄晋卿辈,乃一时能文之士,以检校图籍等事为上所宠礼……”,的确,居奎章阁中者皆为能文之士,且为元代文坛中坚力量。他们与同时期的文坛俊彦以及之前的大德、延祜文人和之后元末文坛主导者、明初开风气者,有着广泛且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间或师或友、亦师亦友或为同僚,交相唱和、赠答,形成了一个以奎章阁文人为中心的多级文人圈。为讨论的方便,本篇将奎章阁文人圈根据人物的生卒年,分为四个时段制成表格,凡奎章阁文人皆加黑体、下划线标明。表格中人物的排列顺序以人物的生年先后为准,如果人物的生年相同,则以人物的卒年先后为顺序排列(见附表格)。
根据表格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奎章阁文人主要集中于表格中间两列,而左右两列无论是13世纪70年代前还是14世纪初,奎章阁文人都很少。这样一个时间段的分布非常有意思,表格第一列人物的主要活动期在元朝统一后,文治渐趋繁荣的大德、延祐时期,表格第四列人物的主要活动时期多为元朝晚期、明代初叶,而奎章阁文人的活动期在中间,正代表着元明文坛承上启下和鼎盛时期的力量。因此,把握清楚奎章阁文人的成长氛围、交游圈子以及风格成因及其影响,将有助于描画清楚整个元代文坛——尤其是中、晚叶时期的面貌。为便于讨论,本篇将表格的中间两列即13世纪七、八、九十年代命名为“奎章阁时代”,将表格第一列命名为“大德、延祜时代”,而奎章阁时代影响波及期已为元末以及明初,故第四列以俗称“元明之际”命名。
纵观元代文坛,无论大德、延祜时期文人圈还是奎章阁文人圈以及元明之际的文人,他们之间多迭相师友,共为同年、同学,时有唱酬,是一个生态环境相当优越的良性循环圈。
首先,迭相师友。所谓迭相师友,是指以奎章阁文人为核心考察的元代文坛,文人间的关系并非纯粹单向的师生关系,他们往往由于仕途际遇、才能高下而构成多向的师生关系、师友关系。由于奎章阁文人“非尝任省、台、翰林及名进士不得居是官”,大德、延祐时期的文人之于奎章阁文人来说,多为前辈,有导引与擢拔之功。对于奎章阁文人圈来说,正是大德、延祜时期文人不具私心的赏鉴和不遗余力的擢拔,年轻的奎章阁文人才得以崭露头角,走向文坛。作为同时期文人中的优选者,奎章阁文人迅速与大德、延祜时期文人混溶一体,互相切磋,互为友朋。如奎章阁灵魂人物虞集早年以契家子从吴澄游,25岁入京师后,即“赫然以文鸣于朝著之间”。虞集与大德、延祐时期文人,尤其是那个时期的年轻辈关系融洽。虞集与袁桷、元明善、贡奎、王士熙、马祖常、盛熙明等时有唱和,“论者以为有元盛世之音也”,其中与袁桷关系尤密,其《祭袁学士文》云:
于时,同朝多士济济,公独我友。尚论其世制作,讨论必我与闻,或辩或同,有定无谖。公泰而舒,我蹇疐跋,三十余年,亦多契阔。
这种良性循环的文坛环境,对于文坛写作风格的确立与审美风尚的形成是深有影响的,时人谓“作为古文论议,迭相师友,间为歌诗、倡酬,遂以文章名海内,士咸以为师法,文体为之一变。”再如奎章阁另一重要文人揭傒斯,在20来岁的年龄登上文坛。其援引者,乃大德、延祐时代著名文人程钜夫。程钜夫颇奇揭傒斯之才,不仅收揭傒斯为门生,且将堂妹嫁与揭傒斯。而后著名作家卢挚因爱重揭傒斯之文,将揭傒斯推荐于朝廷。李孟、王约、赵孟頫、元明善等亦深赏揭傒斯之才,推荐不遗余力。延祐元年(1314),揭傒斯即由布衣入翰林,为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为程钜夫门人,深感程钜夫见知之恩,而赵孟頫缘于程钜夫的搜访与引荐而为朝廷重臣,故终身师事程钜夫。而赵孟頫之于揭侯斯则亦师亦友亦同门。揭侯斯入馆阁之际,与邓文原、袁桷、虞集以及后来加入的范柠、杨载等交游甚密,当时以及史上著称的“元诗四大家”即在其时逐渐形成,影响愈广:
方是时,东南文章钜公,若邓文肃公文原、袁文清公桷、蜀郡虞公集,咸萃于辇下。公(揭傒斯)与临江范椁、浦城杨载继至,以文墨议论与相颉颃,而公名最为暴著。
这种迭相师友关系更表现为奎章阁文人与前辈、同代以及后生晚辈间的师友关系。80年代生的奎章阁文人欧阳玄,年少时期即为卢挚所欣赏。据载,卢挚见到相貌堂堂的欧阳玄,即已心喜,后又观览欧阳玄文章,“大器重之,相与倡和,留连不遣去”。虞集父亲虞汲看过欧阳玄的文章之后,大为吃惊,写信给虞集,认为年轻的欧阳玄必将与儿子的名声相当,虞集由此而荐举欧阳玄入朝,欧阳玄的成就果然印证虞集父亲所言。而90年代生的苏天爵更是转益多师。他早年即从元著名儒学家安熙处接受刘因理学思想,后入国子监受学,其时虞集、吴澄、齐履谦同为老师,之后又得到诸多馆阁名臣的赏识与荐拔,史载:
(苏天爵)初官朝著郎,为四明袁公伯长(袁桷)、溶都马公伯庸(马祖常)、中山王公仪伯(王士熙)所深知。袁公归老,犹手疏荐公馆阁,马公谓‘公当擅文章之柄于十年
后,而王公遂相与为忘年友。
可以说,年辈颇轻、资质较浅的欧阳玄、苏天爵等通过这种师承、友朋关系迅速融入既有文人圈,受到荐拔与重视,从而更加壮大既有圈子的力量,扩大其影响。
其次,奎章阁文人多以“名进士”入选,故除迭相师友外,同年关系、读卷官与进士的关系对于奎章阁文人圈的构建影响非小。有元一朝,历来被史家、文臣诟病者,即该朝科举废止多年,即便实行,亦时有间断。但必须承认,元代头几届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历来被称“得人”。例如元仁宗延祜二年(1315)科考,这一年元明善任读卷官,张起岩为状元,一起登科的还有杨载、欧阳玄、许有壬、黄(氵晋)、马祖常、陈泰、干文传、王沂、杨宗瑞、刘彭寿、韩涣、杨景行、张翔、赵簧翁、杨晋孙、李朝端、李希贤、梁宜等等。欧阳玄、许有壬被选入奎章阁,杨载是元诗四家之一,黄(氵晋)为元文四大家之一,亦为儒林四杰之一,马祖常、张起岩更是声名赫赫。无怪人称“设科得士,不得不以延祜之初为盛也”。延祐五年(1318)科考,袁桷为会试、殿试读卷官,是年进士著名者如谢端、祝尧、虞盘(虞集之弟)、汪泽民、霍希贤等。奎章阁文人宋本乃至治元年(1321)状元,其时,袁桷任会试考官,同年登进士著名者还有:泰不华、程端学、吴师道、杨彝中、廉惠山海牙、杨梓、张纯仁、林兴祖、伯笃鲁丁、林以顺等。到1327年科考,监试官为王士熙,读卷官为马祖常。是年中进士著名者如萨都刺、杨维桢、黄清老、胡一中、刘沂、燮理溥化、郭嘉、张以宁、李黼、蒲理翰、观音奴、索元岱等,一批元晚期重要文人都笼络其中。元代科考起于元仁宗延祐初年,“昔者仁宗皇帝临御天下,慨然悯习俗之于文法,思得儒臣以图治功,诏兴贡举,网罗英彦,故御史中丞马公首应是选,人翰林为应奉文字,与会稽袁公(袁桷)、蜀郡虞公(虞集)、东平王公(王士熙)以学问相淬砺,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仁宗时期选拔出来的人才,后再转为人才选拔者,层递关系显然。而奎章阁文人群体得以形成,则得益于延祐以及之后的泰定年间的科考人才选拔。
另外,奎章阁学士院作为皇帝特设的文化机构,置大学士五员并知经筵事,侍书学士二员,承制学士二员,供奉学士二员并兼经筵官幕职,置参书二员,典籖二员并兼经筵,参赞官照磨一员,内掾四名内二名兼检讨,宣使四名,知印二名,译史二名,典书四名。奎章阁学士院下辖群玉司、艺文监、博士司、授经郎、艺林库、广成局等部门和机构,这些职能部门和机构笼络了大量优秀的文人供职其中,如前所举虞集、欧阳玄、揭傒斯、苏天爵、宋本、泰不华外,再如柯九思、王守诚,以及杨瑀、毕申达等人,他们共事一处,常诗文往来,共襄文坛盛业。为藻饰文治,奎章阁学士院成立半年不到,1329年,元文宗命翰林国史院同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依据唐、宋会要体例,修撰《经世大典》,命赵世延、赵世安领纂修,虞集为总裁,这一大型文化撰述事业为大批优秀文人的聚集与交往以及壮大奎章阁文人圈提供了非常的便利:
……天历二年冬,有旨命奎章阁学士院与翰林国史院参酌唐、宋会要之体,会萃国朝故实之文,作为成书,赐名《皇朝经世大典》。……至于执笔纂修,则命奎章阁大学士、中书平章政事臣赵世延,而贰以臣虞集与学士院艺文监官属分局修撰。又命礼部尚书臣库库择文学儒士三十人给以笔札而缮写之。后来,由于《经世大典》久未功成,翌年二月,以纂修事专属奎章阁学士院,同时虞集又向文宗提供一份名单,这份名单中人亦可谓代表了除奎章阁文人外,元中叶文坛之最优秀者,而这些最优秀者亦为奎章阁文人圈中之人:
礼部尚书马祖常,多闻旧章,司业杨宗瑞,素有历象地理记问度数之学,可供领典;翰林修撰谢端、应奉苏天爵、太常李好文、国子助教陈旅、前詹事院照磨宋襞、通事舍人王士点,俱有见闻,可助撰录。
综上所论,奎章阁设立之后,以奎章阁文人为中心的文人圈在上联系着大德、延祐乃至世祖时期的重要文人,向下笼络着元晚期以及后来在明初文坛有着举足轻重力量的一批年轻人,至于与他们同时代的人们,则以奎章阁文人为风向标,翕然影从,元代文坛遂成为奎章阁文人群体为中心并发生着深刻影响的文坛。

二奎章阁文人圈与奎章阁风格
既然奎章阁文人圈联系着元代文坛诸多显要力量,并产生深刻影响,那么奎章阁文人圈的具体创作风格和审美风格就非常值得探究与讨论。
奎章阁文人们的创作审美风格首先与他们的职业习惯密切相关。关于奎章阁学士们的职责,四库馆臣指出:“元置奎章阁学士专掌经史及考论帝王之治,犹唐之北门学士,称为内相者是也”,表面看来,确乎如此。元文宗曾诏谕奎章阁诸学士云:“朕以统绪所传,实在眇躬,夙夜忧惧,自惟早岁跋涉艰阻,视我祖宗,既乏生知之明,于国家治体,岂能周知。故立奎章阁,置学士员,日以祖宗明训,古昔治乱得失陈说于前,使朕乐于听闻。”实质上,“文宗御奎章阁,虞伯生(虞集)为侍从,日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一旦奎章阁文人希图在政治上有所建议,则会遭到文宗的反感,更会遭致权臣们的猜忌与排挤,正如清人秦惠田所云,“元之文宗可称右文,然其时奎章阁诸臣……一时能文之士,以检校图籍等事为上所宠礼,与古启心沃心之道殊矣。”因此,切实说来,奎章阁文人只是元文宗豢养在馆阁中,用来粉饰政治的文学弄臣。所以奎章阁风格首先即代表着元代馆阁风格。这种馆阁风格确切而言即为“宗唐复古”风格。当然这种馆阁复古思潮并非一朝而成,一成不变的。总体说来,有元一代复古思潮首倡于元世祖时期的姚燧、程钜夫、赵孟頫等,次为邓文原、元明善等接续,至虞集、揭傒斯,元文四家以及马祖常等定型,再接而为欧阳玄、许有壬等贯穿,传而为苏天爵、陈旅等“擅文章之柄”,再到元明之际,杨维桢变化,宋濂、危素等承接开启。奎章阁文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着承上启下,使之定型成熟的角色。
姚燧受学于元初大儒许衡,(《元史》评价姚燧曰:“由穷理致知,反躬实践,为世名儒”,姚燧为文宗韩愈,工散文,当朝三十年间,名臣勋戚的碑传多出其手,文风“闳肆该洽,豪而不宕,刚而不厉,春容盛大,有西汉风。宋末弊习为之一变。盖自延祐以前,文章大匠,莫能先之”。另外,程钜夫、赵孟頫辈亦“躬负宏博之学”,又身处“隆平之期”,故而行文往往从容大雅,有气格,少蹇促艰涩之态,颇有北宋馆阁余风。又由于程、赵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其“词章议论为海内所宗尚者四十年”。到邓文原、元明善等主持文坛之际,以温醇典雅为尚。邓、元一辈注重学有本原,文风上追秦汉风气,以六经为本涵泳,诸子百家为背景敷衍,力求发声为言,皆出于己。大德、延祐之际,除邓文原、元明善外,还有袁桷、贡奎辈左右之,“操觚之士响附景从,元之文章于是时为极盛”,到这一代馆阁文人,元正统文坛才开始确立自己的文风。不过,无论邓文原、元
明善,亦无论袁桷、贡奎等,增点气象、倡导荐拔之功有过,而使文风定型成熟,则未免才力有欠。须等到以虞集、揭傒斯等为中心的奎章阁文人群体的崛起,方完全确立起“雅正”为核心的创作与审美标准。这种“雅正”风格是以经学为基础,学问为涵养,以实用为目的。所谓“学有以致其道,思有以达其才”,秉性情之正,文辞章法规矩,力斥浮辞虚饰,“外无世虑之交,内无声色之惑”,力求养德于内,硕学于外,文势浩然正大,气韵丰沛从容,可以黼黻时代盛业。
毫无疑问,元代较宋代国力远要雄厚,国家气势声威直逼唐朝,甚而过之。生在这样的时代的人们是容易生出雍容、正大且开阔的心胸与气度的。与前辈相比,奎章阁时代的文人们首先都儒学修养相当深厚,元文四家“虞、揭、黄(黄(氵晋))、柳(柳贯)又被称作“儒林四杰”,即缘于是。四家中,虞集少年时代曾以契家子身份从吴澄游,吴澄乃有元一朝与刘因、许衡并列的三大学者之一;揭侯斯曾游学著名儒学家许谦之门(许谦乃著名儒学大师金履祥弟子),与欧阳玄、朱公迁、方用以羽翼斯文相砥砺,时称“许门四杰”;而黄(氵晋)、柳贯则皆为浙东婺学宗师。其它奎章阁成员如苏天爵乃安熙弟子(后者为刘因及门弟子),又曾授业于吴澄、虞集。便是赵世延、泰不华等西域子弟亦皆为学有本源,皈依儒家。其次,学问极其弘博,经史百氏,无不贯通。揭傒斯在奎章阁中乃七品授经郎,才学丰富且深受元文宗欣赏。史载:“(文宗)时幸阁中,有所咨访,……恒以字呼之而不名。每中书奏用儒臣,必问曰:‘其材何如揭曼硕?间出所上《太平政要策》以示台臣曰:‘此朕授经郎揭曼硕所进也。”揭傒斯的情况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元文宗非常喜欢有才学的大臣,奎章阁乃其精心营建的文化机构,入选其中的人必然要才学过人;第二,元文宗对文人们才学的爱重态度,势必致使同时期的文人都致力于学,形成良性学术氛围。事实上,考察奎章阁时代的文坛风云人物,无一不以硕学鸿儒而称著当时。奎章阁时代的人们由于博极天下之书,又有理学涵养作根底,故文章风格雅正,往往文辞上规矩谨严,言必有据,同时又俯仰雍容,堂堂正正,坦然、蔼然令人敬慕。其时文风所尚恰如人们评价其核心人物虞集文风所云:
主之以理,成之以学,即规矩准绳之则,以尽方圆平直之体,不因险以见奇也;因丝麻谷粟之用,以达经纬弥纶之妙,不临深以为高也。陶镕粹精,充极渊奥,时至而化,虽若无意于作为,而体制自成,音节自合,有莫知其所以然者。比登禁林,遂擅天下,学者风动从之,由是,国朝一代之文,蔼然先王之遗烈矣。”回实质上,以虞集为领军人物所代表的雅正文风还是秉承姚燧复古之风,以经学为根本,讲究经世实用,贬斥搞章绘句,迥然异于金末宋季雕琢辞章、气韵萎弱的文风。
关于奎章阁风格取合,很有必要以马祖常的一段批评来讨论。1330年他为苏天爵《滋溪文稿》所作序言表达了其文风取舍标准:
……祖常延祜四年,以御史监试国子员,伯修试《碣石赋》,文雅驯美丽,考究详实。当时考试礼部尚书潘景良、集贤直学士李仲渊置伯修为第二名,巩弘为第一名。弘文气疏宕,才俊可喜,祖常独不然此,其人后必流于不学,升伯修为第一,今果然。而吾伯修方读经稽古,文皆有法度,当负斯文之任于十年后也。
马祖常文风取向及审美追求实质亦代表了奎章阁文风和审美追求,体现出强烈的复古追求。虽然,马祖常没有任职奎章阁,但却是奎章阁文人圈中的重要人物。如前所述,他与袁桷、虞集、王士熙等以学问相淬砺,更唱迭和,金石相宣而文日益奇矣”,他们的文体意识与创作追求很相近。而马祖常又与欧阳玄、许有壬、黄(氵晋)、杨载等为同年,一手荐拔奎章阁年轻辈俊彦苏天爵,还是杨维桢、萨都刺的座师。更重要的是,马祖常的文章元文宗非常喜欢。马祖常文风取向尚古,“非三代两汉之书不读,文则富丽而有法,新奇而不凿”、“每叹魏晋以降,文气卑弱,故修辞立言追古作者。”(《滋溪文稿》卷九)“务刮除近代南北文士习气,追慕古作者。与姚文公燧、元文敏公明善实相继后先,故其文词简而有法,丽而有章,卓然成家。”缘于这样的背景,古雅、考究详实的苏文,符合马氏尚雅、尚正,文气须充实的审美追求,而巩文浮华虚饰,文气卑弱,大逆马氏口味,遂不为马祖常所取。果然,苏天爵迅速获得马祖常、虞集、王士熙等馆阁文人们的欣赏与奖掖,后来更成为奎章阁授经郎,终以“一代文献之寄”著名,既印证了马祖常对苏天爵的期许,又显明了奎章阁文风的衣钵承传。
奎章阁文人在文风上讲究一本于理,言必有据,正经从容,而他们在诗风上虽秉持^陛隋之正”的理念,但风格则多明丽清雅,与其文风颇异。《四库全书总目》评价揭傒斯《文安集》云:“其文章叙事严整,语简而当。凡朝廷大典册及碑版之文,多出于其手,一时推为钜制。独于诗则清丽婉转,别饶风韵,与其文如出二手。”且引揭侯斯诗、文比较之:
《与萧维斗书》
……仆性分麄谬昏戆,绝不通时事,与入交不计隆薄能否,辄以古道相期,待俗下诟病,日甚不止,终不愧悔,今复妄有谒于阁下焉。惟天生贤哲,常旷数百载不一二见,及有其人,或又废于庸主,格于谗忌,尽于懦怯畏慎,弗克卒其大业,仆甚痛之。自来京师,目睹耳听,口诵心语,惟公全才学富,义精仁熟,谦让克谨,去就有节,名与实侔,位与德称,有古大贤之风。束帛之聘,累光丘园,每聘必增其秩,每召必优其礼,其尊德乐道,右贤尚能,崇信慕向,若汉高帝之于四皓,可谓隆矣。然四皓不出则已,一出则能割至尊之爱,定天下之本,建万世之名,翛然而来,浩然而归,来不见其所难,去不见其所穷,何其裕哉?且今天下非汉高之草创,皇太子聪明仁孝过于惠帝,上亲信笃爱,无高帝之惑溺。昔之储贰不得与国家之政,今则无所不领,宜若公者,知无不言,言无不从。……
萧维斗即萧科,元著名学者,《元史》称他,“博极群书,天文、地理、律历、算术,靡不研究”,关辅之士,翕然从之。读书终南山下,三十年屡征不应。揭傒斯这封书信即代表朝廷邀请萧维斗出山。揭傒斯自1314年入朝为翰林编修之后,元文宗开奎章阁,置授经郎,他首获其选,以后又参与修撰《经世大典》,任《辽史》、《金史》的总裁官之一,直至死前,一生大量的时间都在修撰辽、宋、金三史。职业要求与职业习惯要求揭侯斯行文必须措辞概要精当,不以个人是非为转移。所著行文雍穆大气,文势浩然凌厉,有古作者风,且文法森严,运笔稳沉,殊无卑弱逶迤之气。再看揭侯斯的诗,揭侯斯擅长七言律诗,且援引其一首律诗如下:
《送蔡思敬还豫章有怀辽阳李提举》
来日能同去不同,独携别恨向秋风。眼看乱叶浑无定,心与浮云并一空。黄独山中归自断,玉梅溪上梦先通。莫嗤留滞京华者,更有辽阳送断鸿。
这首诗的风格确如虞集评价揭傒斯诗风所云如
“三日新妇”,清鲜明丽,略微还能看出一些如新妇般的生涩与矜持。正如四库馆臣所评“神骨秀削,寄托自深,要非嫣红姹紫,徒衿姿媚者所可比也。”但终与其文风迥然有异。
诗、文创作如出二手的情形不仅仅是揭傒斯,可以说奎章阁时代的文人大多如此,亦可谓为奎章阁诗风。元人以复古方式来贬斥宋、金,往往是通过学唐以上追于汉魏、秦汉。奎章阁文人以雅正为风格追求宗旨,文风上宗唐,乃不离韩、柳的古文运动路线,诗风上宗唐则主要学盛唐,盛唐诗风普遍意象明丽可观。当然,一方面,奎章阁文人日常的工作即承担着朝廷各种制诰、典册、碑铭以及正史的撰写任务,像虞集、揭傒斯、欧阳玄等文坛大家,他们的个人集子被大量的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文章所充溢,其雍穆古雅的文风既是职业习惯使然又是一朝风气所尚。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以及文坛影响,这种文风又进而为天下时人所尚。另一方面,元文宗对待奎章阁文人的态度实以文友相看,虽然他诏谕奎章阁文人,要求其职责是讲述祖宗治法,实际上,“文宗御奎章阁,虞伯生(虞集)为侍从,日以讨论法书、名画为事”,著名画家柯九思由于善画亦擅长鉴赏,为元文宗所深宠。奎章阁得以建立,柯九思的影响非小,因此柯九思亦由一介布衣擢拔而为五品官。而且元文宗本人“恰情词翰,雅喜登临”,善画,亦能作诗,画风、诗风颇宗盛唐。因此,日日伴随文宗左右的奎章阁文人多精通书法,擅长名画赏鉴。奎章阁时代,题画诗相当繁盛。像虞集就作题画诗一百七十多首。这种由奎章阁文人引领而起的题画诗风气,至元末大量著名画家参与,风气更盛。像元末文坛领军人物杨维桢、李孝光、顾瑛等人的集子中都有大量题画诗。题画诗的盛行也导致奎章阁文人们的诗歌创作讲求画境,诗风清丽、秀雅,透明如画。而无论是文风的古雅有则还是诗风的明丽如画,其审美追求核心皆为“雅正”,即养德于内,硕学于外,秉陛情之正,务排放浪性情,虚饰言辞,而这也是奎章阁文人所认可的古风。
奎章阁文人的复古雅正风气中,最动人的是他们的江南书写。江南自六朝以来即为文人墨客所盛情书写,盛唐文人作品中多有对江南风物的细腻描写。奎章阁文人创作中倾向于江南书写,既有复古思潮的影响,更有奎章阁的建立者元文宗的推动。元文宗在做怀王时期,潜邸金陵,对江南风物颇熟悉,亦深有好感,由其现存的几首诗词中可以看出其审美倾向与创作意识中对江南意象的喜爱。奎章阁文人中像虞集、柯九思、雅琥、揭傒斯、欧阳玄等皆为南方人或长期居住江南,颇易与文宗的这种倾向达成共识,所以奎章阁文人的审美倾向与创作风格中,“江南书写”成为一大特征。“江南书写”同样是奎章阁宗唐复古追求的一部分,但更形象可感。且看元文宗的两首诗词:
《自集庆路入正大统途中偶吟》
穿了毯衫便着鞭,一钩残月柳梢边。二三点露滴如雨,六七个星犹在天。犬吠竹篱入过语,鸡鸣茅店客惊眠。须臾捧出扶桑日,七十二峰都在前。
《望九华》
昔年曾见九华图,为问江南有也无。今日五溪桥上见,画师犹自欠工夫。
上引两首作品,对江南典型意象的描摹把捉,以及直接由眼前景道及江南景,颇能想见作者对于江南风物的熟悉与深切眷念。而能将这种“江南书写”发挥到极致,并为天下所宗,成为风尚的,还得数虞集词《风入松》最典型:
画堂红袖倚清酣,华发不胜簪。几回晚直金銮殿,东风软,花里停骖,书诏许传官烛,香罗初翦朝衫。御沟冰泮水援蓝,飞燕又呢喃,重重帘幕寒犹在,凭谁寄、锦字泥缄。报道先生归也,杏花春雨江南。
这首词是虞集1332年寄赠给退居吴下的奎章阁鉴书博士柯九思的,柯九思非常喜欢,“书《风人松》于罗帕作轴”,而且这首词因“词翰兼美,一时争相传刻,而此曲遂徧满海内矣。”这首词所以被人们广为传唱最胜出的地方就在于词作中“杏花春雨江南”这样一个简明却典型的江南书写,它剪切妥帖,明朗雅丽,很有魅力。当然,若论创意,与盛唐张志和《渔歌子》相比,并不能出其右。但此词成功的关键之处在于,整首词的抒写紧扣归意,将江南正面书写成为秀雅、雍正的形象,使江南摆脱以往明丽冶艳却有些不上台面的形象,成为具有文化品格,温暖而惬意可以抚慰心灵的世界。这种表达代表了时尚,却又深情蕴藉,故而深切地感动了元中、晚叶的文人,从此“杏花春雨江南”成为文人们报道江南、表达江南、寄念江南的风标,甚至一直流行至今。而元末吴中成为诗歌繁盛之地,其作者能驰骋文坛,奎章阁文人们对于江南的大力书写不能不说是一大激励。
综而论之,奎章阁文人圈接过元初以来掀起的复古大旗,以雅正风格为主,文章雍容有气势,文法规矩谨严,力求追摹古作者风气而别于宋末金季萎弱风格。尽管元代散文成就在整体上并未超越唐宋古文运动的传统,如杨维桢所云“我朝古文殊未迈韩、柳、欧、曾、苏、王,而诗则过之”。奎章阁文人诗词与文章创作有区别,总体上以明丽秀雅,讲求画境为式,其创作中江南书写特征颇值得一提。与前辈馆阁文人相比,虞集一代奎章阁文人圈大家辈出,风格更趋成熟定型,实际上他们是元代文坛的真正代言人,影响遍及天下,雅正风格不仅代表了奎章阁文人的文风创作与审美追求,也引导和代表了一个时代的风尚。
三奎章阁文人的文坛影响
奎章阁从成立到废罢再到更名宣文阁,虽有十二年时间,实际其鼎盛繁荣时间只有元文宗在金陵潜邸1328年9月筹备奎章阁到元文宗1332年8月驾崩,前后五年时间不到。1333年,元顺帝即位,而奎章阁文人圈的核心人物虞集谢病回到江南。在此之前,1332年三月到六月,以权臣燕帖木儿为首的监察御史机构对奎章阁深受文宗宠爱者雅琥、童童、柯九思多次弹劾,意欲通过这种清君侧方式,清算元文宗。即使在元文宗极力庇佑的时代,奎章阁文人亦是屡屡遭到权臣们的猜忌与排挤,根本不能在政治上有所施为,所以曾发生奎章阁首席文人们联合辞职之事。《元史·虞集传》载:
时宗箔暌隔,功臣汰侈,政教未立,帝将策士于廷,集被命为读卷官,乃拟制策以进,首以“劝亲亲,体群臣,同一风俗,协和万邦”为问,帝不用。集以入侍燕闲,无益时政,且娼嫉者多,乃与大学士忽都鲁都儿迷失等进曰:“陛下出独见,建奎章阁,览书籍,置学士员,以备顾问。臣等备员,殊无补报,窃恐有累圣德,乞容臣等辞职。”
当奎章阁文人们的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受到多重限制之后,奎章阁文人沦落为为皇帝提供提升汉文化修养的教导与娱乐意义、才识超诣的御用帮闲。这种尴尬的政治地位对于饱读经书,深受儒家正统思想影响的奎章阁文人来说是深有挫败感的。基于这样的身份,奎章阁文人为人处事相当谨慎低调,对后进好学之士态度平和谦恭,这使得乡野僻壤的学子可以更便利地接近他们,同时又更平易温和地接受他们的影响。例如陈旅,乃
奎章阁时代相当活跃的诗文家。其以一介布衣游学京师,虞集见到他的文章,“慨然叹曰:‘此所谓我老将休,付子斯文者矣。即延至馆中,朝夕以道义学问相讲习,自谓得旅之助为多。”奎章阁大学士赵世延极力荐举陈旅于朝廷,奎章阁授经郎苏天爵辑《国朝文类》,“其时作者林立,而不以序属诸他人,独以属旅,殆亦知其文之足以传信矣。”陈旅亦深受虞集等奎章阁文人复古思想影响,“为文典雅峻洁,必期合于古作者”(《四库全书总目》)。再如傅与砺,同样以布衣至京师,以·奎章阁文人为代表的馆阁文人欣赏其才,援引不已。其诗集,范柠、揭侯斯、虞集等皆为序。至其死后,苏天爵亲为墓志铭。傅与砺学诗法于虞集等,乃虞集晚辈,虞集作为文坛耆老,为傅与砺诗集作序,却态度谦卑,情文并茂,令人感慨动容:
嗟夫!上林千树,岂无一枝以栖朝阳之羽哉!而一官领海之不厌,何也?前数年诸公相知者多散出于外,今明良一廷,无所忌讳,清涧之蒲,海湾之水,不足以久烦吟咏也,必矣。书其别后稿如此。迟其北还,则沉郁顿挫、从容温厚有可起予者,何幸于余生亲见之哉!
可惜,陈旅、傅与砺英年早逝,竟皆死于虞集之前,枉负虞集等的期许之心。不过,由虞集这种谦卑的态度,兼其文坛地位、社会地位,可以想见其所倡导和代表的创作风格与审美追求的普达。
以奎章阁文人为核心的馆阁文人们对诗文创作的热衷和对后进才学者的荐拔奖掖很容易刺激民间对于诗文创作的热情。有元一朝诗文成就虽不能与之前的唐宋、之后的明清相比肩,但创作却颇为繁荣,尤其是元代中叶以后,诗文创作曾一度十分繁兴,除出现为数众多的作家外,编选本朝作者作品的集子亦大量出现,这些集子的刊印显然是既有存一代文献之意,更有为满足大量学者之心。蒋易就说“易尝辑录当代之诗,见者往往传写,盖亦疲矣,咸愿锓梓,与同志共之。”由这些集子的编选标准,依然能清晰地看到奎章阁文人为核心的复古思潮的影响。且不论奎章阁文人苏天爵编选的《国朝文类》是怎样深切著明地彰显了奎章阁文人的雅正审美倾向,即便中下层文人傅习、孙存吾、蒋易等前后编选的《皇元风雅》亦表明了与奎章阁文人雅正审美倾向一致的取合标准。蒋易1337年作《皇元风雅集引》曰:
……因稍加铨次,择其温柔敦厚,雄深典丽,足以歌咏太平之盛,或意思闲适,辞旨冲淡,足以消融贪鄙之心,或风刺怨诽而不过于谲,或清新俊逸而不流于靡,可以兴、可以戎者,然后存之。盖一约之于义礼之中而不失性情之正,庶乎观风俗、考政治者或有取焉。是集上自公卿大夫,下逮山林闾巷布韦之士,言之善者靡所不录,故题之曰《皇元风雅》。第恨穷乡寡闻,采辑未广,乌能备朝廷之雅,而悉四方之风哉!
缘于一致的审美标准,所以这些集子所选作家作品也自然以奎章阁文人圈文人及其作品为主体,蒋易《题皇元风雅集后》曰:
易始于怀友轩得观当代作者之诗,昌平何得之(何失)、浦城杨仲弘(杨载)、临江范德机(范柠)、永康胡汲仲(胡长孺)、蜀郡虞伯生(虞集)、东阳柳道传(柳贯)、临川何太虚(何中)、金华黄晋卿(黄(氵晋))诸稿,典丽有则,诚可继盛唐之绝响矣。自是始有意收辑,十数年间,耳目所得者已若此,况夫馆阁之所储拔,声教之所渐被,此盖未能十一耳。信乎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人才。呜呼盛哉!(见元张氏梅溪书院刻本)
值得注意的是,奎章阁核心文人虞集分别于1336年、1339年为傅习、孙存吾《皇元风雅》12卷、蒋易《皇元风雅》30卷作序。尤其是前者,虞集还参与校选工作,其前集题:“旴江梅谷傅习说卿采集,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奎章学士虞集伯生校选”,后集题:“儒学学正孙存吾如山编类,奎章学士虞集伯生校选。”(见《元风雅》卷首)这样一来,以奎章阁文人为代表的复古雅正审美倾向与创作意旨便由宫廷馆阁便捷地走向山野乡间,好学后进之士,则渐为其风气所染。
还有一点,元文宗佞佛好道,对方外之士颇信重,这使得奎章阁文人与方外人士的交往、唱和相当密切,因此,奎章阁风格还藉由这些方外人士广泛披靡。最著名者如张雨。他年二十,即弃家遍游天台、括苍诸名山,后从开元宫真人王寿衍入京师,与赵孟頫、范柠、杨载、袁桷、虞集、黄(氵晋)、揭傒斯等有交往,晚年与倪瓒、顾瑛、杨维桢等人深相投契,互有唱和。张雨的交游对象几乎关联了元代中上叶到元末的所有重要文人。至正十年前后,张雨将这些文人与他酬唱、赠答的作品编成集,名为《师友集》,黄浯为之序:
……属当文明之代,一时鸿生硕望、文学侍从之臣,方相与镕金铸辞,著为训典,播为颂歌,以铺张太平雍熙之盛。伯雨周旋其间,又皆与之相接,以粲然之文,如埙鸣而篪应也。逮伯雨倦游而归,入山益深,入林益密。并游之英俊多已零落,而伯雨亦老矣。后生晚出,如春华夕秀,奇采递发。欲一经伯雨之品题者,无不挟所长以为贽,而伯雨皆莫之拒,虽细弗遗……
由黄潘之序可看出,张雨周旋于虞集等文学侍从之臣,深受其浸染,在那些交游俊彦相继凋零之后,张雨又继续影响后生晚出者。类于张雨者颇多,这些人同样颇为忠实地将奎章阁文人为代表的复古雅正风气传播布达,不仅是同时代者,还及于元末文坛,并影响元末文坛格局的构建。
1344年,揭侯斯去世,而虞集则已近失明,奎章阁文人主盟文坛的时代渐趋终结,以杨维桢为核心的时代来临。由前文所述,杨维桢为1327年进士,那年的监试官是王士熙,读卷官是马祖常,从根本上说,杨维桢的创作与审美思想仍是元初以来逐渐形成的文学复古思潮的继续发展。杨维桢散文创作地位如时人云“元继宋季之后,政庞文抚,铁崖务铲一代之陋,上追秦汉,虽词涉夸大,自姚、虞而下,雄健而不窘者,一人而已。”相较于文,杨维桢更大的贡献在于诗。在诗歌创作上,杨维桢同样主张复古,但风格变异,别于虞、揭、范、杨诸家,以乐府诗作为突破口,终成一派,取得超越前者的突出成就。杨维桢《玉笥集叙》曰:
我朝习古诗如虞、范、马、揭、宋、泰、吴、黄而下,合数十家,诸体兼备,独于古乐府犹缺。泰定、天历来,予与睦州夏溥、金华陈樵、永嘉李孝光、方外张天雨为古乐府,史官黄(氵晋)、陈绎曾遂选于禁林,以为有古情性,梓行于南北,以补本朝诗人之缺。一时学者过为推,名余以铁雅宗派。……(《杨铁崖先生文集全录》卷四)
由杨维桢本人的这段话可以看出,杨维桢认同和接受奎章阁文人圈的复古思潮,只是为补其缺而兴古乐府之创作。杨维桢学生章琬亦很明白地指出杨维桢古乐府创作力追雅正之风,而求补奎章阁文人诗歌复古创作之缺:
我朝诗体备矣,惟古乐府则置而不为。……名目《铁崖先生复古诗集》。此集出,而我朝之诗斯为大备。红紫乱朱,郑卫乱雅,生于季世,而欲为诗于古度,越齐梁、追踪汉魏而上,薄乎骚雅,是秉正色于红紫之中,奏韶濩于郑卫之际,
不其难矣哉。此先生之作,所以为复古而非一时流辈之所能班,南北词人推为第一诗宗,此非琬之言也,天下之言也。(《复古诗集》序)
杨维桢的古乐府创作取得巨大成功,杨维桢本人成为元末文坛领军人物,某种程度上必须承认,奎章阁文人圈力量影响了元末文坛格局。其实,奎章阁文人圈中文人早在元四家鸣盛一时之际,即有染指乐府诗创作,例如王士熙、马祖常、宋襞等即有创作。尤其值得一说的是李孝光。1328年,已名满天下的李孝光与年轻的杨维桢在吴下相与唱和古乐府辞,李孝光对杨维桢的欣赏和肯定,使年轻的杨维桢终于有信心正式打出复兴古乐府的旗帜,此后杨维桢对李孝光异乎寻常的推重,其《陈樵集序》中举元代作者四人,李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李孝光亦可谓奎章阁文人圈中人物,与奎章阁文人关系密切,有着深切的馆阁情结。他曾与柯九思同受知于怀王潜邸,怀王即位为元文宗之后,柯九思被召为臣,李孝光亦汲汲于馆阁召用,常常出入奎章阁侍书学士赵世延家,奎章阁典签泰不华曾学诗于李孝光。李孝光与杨维桢吴下的那场相聚唱和好比天宝年间李白与杜甫的相遇唱和,四库馆臣认为杨维桢对李孝光的称誉并不过分,但李孝光倘若不是在满身光环之际,仍能与杨维桢亲切唱和,杨维桢当不至如此感重和推崇李孝光,或许杨维桢的复兴古乐府行动也会有其它的变化。因此,奎章阁文人圈之于文坛的影响和意义不仅仅之于他们提出和倡导某种文风或审美倾向,更在于他们是一种力量和磁场,作用于文坛,影响其方向与格局的变化。
元末文坛除杨维桢等,诸如贡师泰、揭泫、余阙辈亦算挺然秀者。这些人则可谓是奎章阁文人圈之后续力量。贡师泰乃贡奎之子,揭泫是揭傒斯之子。像贡师泰“少承其父奎家学,又从吴澄受业,复与虞集、杨载、范柠、揭傒斯游,故文章具有源本。其在元末,足以凌厉一时。诗格尤为高雅,虞杨范揭之后,可谓挺然晚秀矣”(《四库全书·玩斋集提要》)。
元明易代,文坛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当推宋濂,乃“开国文臣之首”,“一代礼乐制作,濂所裁定者居多。”宋濂为文转益多师,与奎章阁文人渊源亦深。宋濂1381年所作《欧阳公文集原序》对奎章阁文人欧阳玄文章推崇备至,称其文“意雄而辞赡,如黑云四兴,雷电恍惚而雨雹飒然交下,可怖可愕,及其云散雨止,长空万里,一碧如洗,可谓奇伟不凡者矣,非见道笃而择理精,其能致然乎?”并将欧阳玄的文坛地位提升至与欧阳修的相等。而且宋濂还自称深受欧阳玄影响:
……濂也不敏,自总角时即知诵公之文,屡欲裹粮相从而不可得。公尝见濂所著《潜溪集》,不我鄙夷,辄冠以雄文,所以期待者,甚至第以志。念荒落学识迂疏不足副公之望,况敢冒昧而序其文哉?……(《文宪集》卷七)
宋濂与奎章阁文人圈中黄(氵晋)、柳贯、胡助等皆有交往、师从关系。再有危素。危素以再事明朝为人所鄙,其文章实则“欧、虞、黄、柳之后,屹为大宗。其文演迩澄泓,视之若平易,而实不可几及……”(见《四库全书·说学斋稿提要》)。危素与奎章阁文人圈关系尤密。曾学经学于吴澄,吴澄赞其学问,以同辈之礼相待,所著之书多请他一同参订,吴澄年谱即由危素编撰,吴澄学生虞集等亦待危素如吴澄,与危素多有题跋唱和之作。危素又曾学书法于康里蠖,擅楷、行、草三体,尤精楷书。危素史学造诣得欧阳玄指点,欧阳玄对危素期许甚高,危素自称其“宦学京师,尝从公(欧阳玄)于史馆,晚辱与进尤至,谓可以承斯文之遗绪”。可以说,当奎章阁文人圈在元代文坛势力如日中天之际,诸如宋濂、危素等地方俊彦即以其文为范式、楷模,而奎章阁文人们亦以斯文遗绪相期许,一旦宋濂诸人成名,以其政治影响与文学影响双向推动,更兼明初对程朱理学的推崇,奎章阁文人所形成的以理学为宗,以史学为底,以学理见长的稳健充实的雅正文风在明初依旧大行其道,影响一直波及到明代中叶。
综上所论,奎章阁文人及其活动、交游的圈子,在审美追求与文体风格上,确立了元初以来即掀起的复古思潮的正宗地位,确定了宗唐、宗汉魏的深醇雅正风格,力铲宋末金季以来萎弱风格。其社会影响与文坛影响极其广远,不仅直接、间接地促成了元中叶至末叶诗文的繁兴,也影响了元末文坛格局的建构和明初文风的形成。所以奎章阁文人及其圈子应是元代文坛尤其是中、末叶文坛最不容忽视的力量,任何关于元代诗文的研究,他们都将是绕不过去的话题。
责任编辑李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