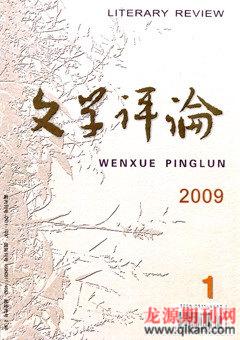晚周观念具象述论
饶龙隼
内容提要晚周人的心智浑朴初开,其主体性尚未全然凸显。这使得人们感知成象,既不再是原初的具体,也不会是高度的抽象,而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具体而观念地把握事物。当然人们还注意到了,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要认识事物的形质界别,最简明的办法就是类比。将众多事物一一进行类比,可超越对单个事物的感知,进到对同类事物的认知,从而把握物类的共同特性,形成特定属性的物类观念。而物类的观念一旦形成,就可以反观具体的事物,识取事物的同类属性,辨别事物的异类属性;还可在物类间进行类比,超越对单个物类的感知,进到对更大物类的认知,终至领悟世界万物本体,从而确立同类相推原理。晚周成象机制就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式,遵循同类相推的原理,识取物类属性的同异,以对事物制名指实,从而实现感知成象。这样的成象机制,由其同类相推的思维形式而言,可称之为推类取象,由其观念形态的物类属性而言,可称之为观念具象。若换个更简便的说法,也可浑然称之为类象。观念具象有自身的规定性,主要呈现为三大形制特征:(一)观念具象的基本形质是观念联属,其观念属性大致经由三条途径来生成;(二)观念具象是一种自由灵便的用象,表现为人工作用和自由自足程度提高;(三)观念具象主要凭借语言媒质传达,引发名实、文质、言意三对关系范畴。基于这样的用象形制特征,观念具象就可以以组合构形。亦即在具体语境中,一或多个观念具象,依凭三大形制特征,建立新的观念联属,而成完形自足、相对独立之表形。其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单元型组合构形、复合型组合构形和叙事型组合构形。在晚周谈辩述学的背景上,诸子即以三种类型为组件,作更高位更宏通的观念联属,创设出体制更巨的表形集成,从而表现为独特的风神肌理。
晚周是指春秋晚至战国末这个时段。此时的用象形态是特异的,即如《荀子·劝学》首二章所示,其中所蕴涵的用象形制,既不同于早前的程式拟象,也不同于更晚的气感取象,这里称之为“观念具象”。
一观念具象的原理
晚周人的心智浑朴初开。人们能知晓事物是一实在,如《庄子·达生》云:“凡有貌象声色者,皆物也。”但这种认识尚未全然开露,因它还浑然地视人为一物,如《庄子·秋水》云:“号物之数谓之万,人处一焉。人卒九州,谷物之所生,舟车之所通,人处一焉。此其比万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马体乎?”其结果就使万物不能外在于人,而人也未能独立于万物。既然人未从万物独立,其主体性便无由凸显。这决定人们感知成象,既不再是原初的具体,也不会是高度的抽象,而是在具象与抽象之间,具体地对事物作观念把握。
这是一种有限的知识能力,人们能够直观事物之实在,却难以探究事物的本原。如《庄子·知北游》云,若有实体先于天地,可决定万物的生长,那这实体便不是物;既然这实体能生万物,那它就不会先于万物,而仍然是物之一种。如此,天地万物只能是实在,而没有产生的本原;故有人断言:“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周易·序卦》)正是“唯万物”这一断制,限定了时人的知识阈界。认识能力所能达到的,只是感知万物的形质,即所谓“物与物何以相远?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庄子·达生》),以及认识事物间的界别,即所谓“物物者,与物无际;而物有际者,所谓物际者也:不际之际,际之不际者也”(《庄子·知北游》)。
当然人们还注意到了,事物不是孤立存在的,要认识事物的形质界别,就需辨识事物间的差别;而弄清事物间的差别,最简明的办法是类比。类比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大约有两重思想进路。首先是物与物对比,将甲物与乙物比较,寻找两者的同与异;将甲物与丙物比较,寻找两者的同与异;将乙物与丙物比较,寻找两者的同与异……众物的同与异弄清楚了,人们便可能进而发现,某些事物具有共同特性,可以归并为同一类,某些事物没有共同特性,应该分属不同的类。这样对比就上升为类比,超越对单个事物的感知,进到对同类事物的认知,从而把握物类的共同特性,形成特定属性的物类观念。而物类观念一旦形成,人们就可以反观具体的事物,识取事物的同类属性,辨别事物的异类属性;还可以物类之间进行类比,超越对单个物类的感知,进到对更大物类的认知。这样,感知就由细微趋于宏大,进而可依循物类的大小,从多个层位来认知事物。如《墨子·经上》79条将事物分为三个层位,《经说上》79条解释云:“名:物,达也,有实必待文[之]多[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又如《荀子·正名》云:“故万物虽众,有时而欲遍举之,故谓之物。物也者,大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则有共,至于无共然后止。有时而欲偏举之,故谓之鸟兽。鸟兽也者,大别名也。”这将物类分为两个层位来认识,而实际隐含了“私”名的层位。
随着类比活动深入,人们不断积累经验,逐渐形成某些通识。关于同类质性相同,时人已能分析若干条理,如《墨子·经上》88条云:“同:重、体、合、类。”《经说上》88条解释云:“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关于异类质性不同,时人也能分析若干条理,如《经上》89条云:“异:二,不体、不合、不类。”《经说上》89条解释云:“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而类同、类异的条理化,又引出同异的形上之辨。如《墨子·经上》90条云“同异交得。”《经说上》90条更以十三例证明之。又《墨子·大取》云:“有其异也,为其同也:为其同也,异。”这是说同异相互依存,此物与彼物的相异之处,恰在于彼此有相同之处,所有类异都根基于类同。若循此理推阐到极至,战国中期惠施更断言“人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庄子·天下》)就这样,晚周人借助简明的类比,经由对事物同异之推阐,达至对万物本体的领悟。
类比思维既能达事物本体,它便具有了普遍的适用性。《邓析子·转辞》云:“抱薪加火,燥者必先燃,平地注水,湿者必先濡;故曰动之以其类,安有不应者。”这是说事物以同类而相应。《论语·阳货》云:“性相近,习相远。”这是说人类的质性相近同。《孟子·告子上》云:“故凡同类,举相似也。”这是说同类事物质性相似。《墨子·经下》165条云:“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台[似]也,说在方。”《经说下》165条解释云“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台[似]也。尽类犹方也,物俱然。”这是说方法相同之物类似……此从多层面讲明一个原理,即同类事物都能以类相推。至战国末荀况更阐发说,同类相推乃古今通理:“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荀子·非相》)同类相推原理一旦确立,就成了认知的必要手段,人的思维活动离不开它,否则会陷入无知与虚妄。
比如《邓析子·转辞》云:“进退无类,智不能察是非,明不能审去就,斯谓虚妄。”此指出不懂推类将导致虚妄。又如《公孙龙子·迹府》载:“惠子曰:‘夫说者,固以其所知,谕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无譬,则不可矣。”这指出不用譬类将导致无知。于此可见,同类相推是普遍必要的。
基于同类相推的普遍必要性,人们进而探讨它的操作原则。如《墨子·经下》提出同类相推三原则:其一“类以行之”,要求推类只能在同类事物中进行:反之“异类不比”,规定推类不可在异类事物间进行,例如下列四项类推就行不通:“木与夜孰长?智与粟孰多?爵、亲、行、贾四者孰贵?糜与霍孰高?”《经说·下》107条再一“类之大小”,要求推类限在同范围的物类进行,例如“四足兽,与牛马、与物,尽与大小也。此然是必然,则俱[误](为糜)。”(《经说下》102条)这是正面提出的原则,要求在推类时能遵循。反过来,对不合原则的类推,人们也能注意规避。如《孟子·告子下》嘲讽“不揣其本而齐其末”,《墨子·经下》141条警示应答要“通意后对”,同书166条指斥“狂举不可以知异”,《荀子·非十二子》指斥孟子“僻违而无类”等,都是推类活动的反面训诫。不过也应该切实估量,上述原则或经验之谈,作为推类实践的总结,仍是初级具体的,远未达高度抽象。
这样的性状决定了,同类相推既有规则可循,又不至教条化,犹然粗疏浑朴之中,蕴蓄知识生长机能。依循同类相推的原理,人们不仅能认知事物的实体、处所,而且能认知事物的属性、关联。对此,《墨子·大取》云:“以形貌命者,必智[知]是之某也,焉智[知]某也。诸以形貌命者,若山、丘、室、庙者皆是也。长人之与短人也同,其形貌同者也,故同。指之人也与首之人也异,人之体非一貌者也,故异。将剑与挺剑异,剑以形貌命者也,其形不同,故异”;“不可以形貌命者,虽不智[知]是之某也,知某可也。荀是石也白,败是石也,尽与白同。诸非以举量数命者,败之尽是也。是石也虽大,不与大同,是有便[使]谓焉也”;“诸以居运命者,苟人于其中者,皆是也,去之因非也。诸以居运命者,若乡、里、齐、荆者皆是”。“形貌”是指事物的实体,“居运”是指事物的处所,“不可以形貌”、“非以举量数”是指事物的属性或关联。这表明,时人能从多层面辨别同异,以把握对象物的客观因素。至于事物同异的主观因素,时人多避而不谈,任其茫昧;唯荀子稍加明敏,似有朦胧的认识。
他尝探讨同异的主观依据,云:“然则缘何而以同异?曰:缘天官。凡同类、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所以共其约名以相期也。形体、色、理以目异,声音清浊、调竽、奇声以耳异,甘、苦、咸、淡、辛、酸、奇味以口异,香、臭、芬、郁、腥、臊、洒、酸、奇臭以鼻异,疾、养、沧、热、滑、铍、轻、重以形体异,说、故、喜、怒、哀、乐、爱、恶、欲以心异。心有征知,征知则缘耳而知声可也,缘目而知形可也:然而征知必将待天官之当簿其类然后可也。”(《荀子·正名》)“天官”即天生的感官,包含耳目鼻口体和心。前五项是谓“五官”,似乎不具有能动性;唯心一项具有能动性,即谓“心有征知”。所谓“天官之意物”,就将“天官”引入感知领域,添注了认知的主观因素,植入知识生长的新机能。至谓“天官之意物也同”,又引“天官”入同类相推,提供一种新的认知理据,即“天官之当簿其类”。“类”就是物类;“当簿”就是对应接触。所谓“当簿其类”,是指五官与物类的对应接触,即杨惊注“可闻之物耳之类,可见之物目之类”云云,以及“心”对五类对应接触的认知。这种思致确实是新进的,标志着晚周的认识高度。
但仍应该切实地估量,“天官”唯“心”有能动性,表明人的心智犹然浑朴初开,其成象机能是很有限的。故《正名》下文退守曰:“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征之而无说,则人莫不然谓之不知。此所缘而以同异也,然后随而命之。”这就是说,认知援“当簿其类”之理,始终不出同类相推的范围,其目标仍是别同异一名实,即所谓“制名以指实”:“同则同之,异则异之。单足以喻则单,单不足以喻则兼,单与兼无所相避则共,虽共不为害矣。知异实者之异名也,故使异实者莫不异名也,不可乱也,犹使异[同]实者莫不同名也。”这就是晚周感知成象的基本内涵,苟子更概称之为“制名之枢要”。“制名”即感知成象,“枢要”即成象机制,它包含三个层面的规定:一是“约定俗成”(即普遍认同),所谓:“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名无固实,约之以命实,约定俗成谓之实名”;二是“径易不拂”(即简明易晓),所谓:“名有固善,径易而不拂,谓之善名”;三是“稽实定数”(即质性不变),所谓:“物有同状而异所者,有异状而同所者,可别也(谓之一实);状同而为异所者,虽可合,谓之二实;状变而实无别而为异者,谓之化,有化而无别,谓之一实”。只有遵循这三项规定,才能“辨异而不过,推类而不悖”,避免“用名以乱名”、“用实以乱名”、“用名以乱实”之惑,从而实现对事物感知成象。关于此一成象机制,时人还有另类表述,如云.“天地与其所产者,物也。物以物其所物而不过焉,实也。实以实其所实而不旷焉,位也。出其所位非位,位其所位焉,正也。其正者,正其所实也:正其所实者,正其名也。”(《公孙龙·名实论》)这意思也是说,只有“不过”、“不旷”、“位其所位”,亦即遵循同类相推的原理,人才能正确认知事物,实现对事物感知成象。
故而即便如上述荀子所论,给认知活动增添主观因素,却不至改变晚周用象质性。因为说到底,晚周成象机制是采用类比思维的方式,遵循同类相推的原理,识取物类属性的同异,以对事物制名指实,从而实现感知成象。这样的成象机制,由其同类相推的思维形式而言,可称之为推类取象;由其观念形态的物类属性而言,可称之为观念具象。若换个更简便的说法,也可浑然称之为类象。
对这种观念形态的类象,战国时人似有朦胧认识。《周易·系辞上》云:“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拟诸其形容”,指用卦体拟象事物,“物宜”即物义,指物类的观念属性;“象其物宜”,指用卦体拟象事物的观念属性。故韩康伯注举例说:“乾刚坤柔,各有其体,故曰拟诸形容。”这指出,乾坤诸卦拟象的不是事物的具体形貌,而是刚柔等观念属性。此所论虽是特殊形式的易象,却也揭示了类象的成象机理。且这种观念形态的类象,在晚周有大量施用实例。例如诸子论学所用“水”,就是典型的观念形态类象。对于这样的用象性状,黑格尔从思辨的角度,恰巧有过类似的描述:“个别自然事物,特别是河海山岳星辰之类基元事物,不是以它们的零散的直接存在的面貌而为人所认识,而是上升为观念,观念的功能就获得一种绝对普遍存在的形式。”朱光潜为“观念”一词作注云:“观念
(Vorstellung)指意象,即对于一类事物所获得的一种总的印象,但还不是抽象的概念。”既超越实物形式,上升为观念形态;又未成抽象概念,仍存留物类属性,这正暗合晚周观念具象。
二观念具象的形制
基于上述感知成象的原理,观念具象便有自身规定性。它表现出三大形制特征:(一)观念具象的基本形质是观念联属;(二)观念具象是一种自由灵便的用象,(三)观念具象主要凭借语言媒质传达。
(一)观念联属
作为观念形态的类象,观念具象蕴涵两重性。它既超越实物形式,呈现为观念形态,又未达纯粹抽象,具体为物类属性。这两重性也可简括为观念属性。据晚周各种资料显示,这种观念属性之生成,主要经由三条途径:
一条是,由程式拟象的介质属性转化而来。观念具象转接早前的程式拟象,转释《易》象、《诗》兴象、礼仪象等的程式内涵,使之义理化为观念属性。比如《礼记·玉藻》云:“笏,天子以球玉,诸侯以象,大夫以鱼须文竹,士竹本:象可也。”这是周礼完好时的情形。及至晚周礼制废弛,服饰等差无所依托,其仪制便转化为天子、诸侯、大夫与士的政治等级观念。
再一条,直接从某种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这一生成途径,亦谓“取象”,为晚周人常用。.比如《荀子·礼论》云:“上取象于天,下取象于地,中取则于人,人所以群居和一之理尽矣。”此描述晚周人从天文、地理、人事诸物类抽取观念属性的情状;故章学诚说:“战国之文,深于比兴,即其深于取象者也。”(《文史通义·易教下》)不过也应看到,时人从物类抽取观念属性仍很拙朴。一方面,他们能够识取物类属性的同异,明了推类不悖之通理,另一方面,他们只能获取物类的部分属性,尚无法做到全然把握。因而,他们往往依据物类的现象与关联,直感而偏至地抽取观念属性。例如,孔子所论“静”、“寿”、“动”、“乐”诸观念,就是出自对山水的直感而非抽象(《论语·雍也》)。又如,有若所谓“出类拔萃”,就是从物类中偏取其最,以凸显孔子圣明的观念。(《孟子·公孙丑上》)。
又一条,将此物类的观念属性旁推彼物类。例如君子比德于玉,孔子曰:“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润而泽,仁也;栗而理,知也;坚刚而不屈,义也;廉而不刿,行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并见,情也;扣之,其声清扬而远闻,其止辍然,辞也。故虽有珉之雕雕,不若玉之章章。”(《荀子·法行》)此将玉的七重观念属性旁推君子,显示了玉观念属性的衍生功能。时人所谓“引而申之,触类而长之”、“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周易·系辞》上、下),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观念属性生成的三条途径,也有某种内在的逻辑关联。第一条途径意味着,程式拟象转型为观念具象,原有的介质属性被转释、转换为新质的观念属性,摆脱了操持程式约束,使用象更显自由灵便;而用象之自由灵变,就使第二条途径,即从物类抽取观念属性成为可能;且观念属性之抽取,又为物类联属创造条件,因此第三条途径,作为更繁密之生成,便上升为观念联属。可以这样说,第一条途径是物类观念属性的原始发生,第二条途径是物类观念属性的自然滋长,第三条途径是物类观念属性的人工推衍。其结果是,凸显了观念具象的基本形质,激活了物类的观念联属功能。
在晚周的用象活动中,这种观念联属被普遍运用,以至于“无譬则不能言”(《说苑·善说》录惠施语),甚至有人引发理论认知。例如(《论语·雍也》云:“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此用“仁”观念来联属己与人,即所谓“能近取譬”。“近”即近类,指物类的观念属性相同;“譬”即比譬,指同类间实行观念联属;“方”即方法,指物类观念联属之通则。再如《墨子·大取》云:“凡兴利除害也,其类在漏壅。”此用特定辞式“其类在”表达观念联属,标示了对这一通则的运用。又如《公孙龙子·迹府》所云“假物取譬”,则已是简明的理论表述。
(二)自由灵便
观念具象是较自由灵便的用象形态,这可以描述为两个方面:
一方面,观念具象的自由程度提高,原有的操持程式脱落,人工的因素显著增强,人的能动性有所激发,不仅可从物类中抽取观念属性,并且可在物类间进行观念联属。
人工因素增强、能动性被激发,这是用象自由灵便的实质。它既呈现在观念具象的生成与调用上,更集中体现在“象”义变迁中。“象”是古今用象的共名,因而透过“象”义的变迁,可以考测用象的自由程度。“象”义演变可描述为.最初,它是指大象这动物。殷墟卜辞“象”字,均为大象之象形,反映了殷人服象习俗。后来,“象”的词义虚化,增加了动词一义,不单指这种巨型动物,而且指对事物的描摹。再后来,“象”义进一步虚化为共名,泛指描摹事物形貌的成果。如《尚书·说命》“乃审厥象”、《左传》僖公十五年载韩简侍所论“龟象”、同书昭公二年载韩宣子聘鲁所见“易象”。盖自周初以至春秋前期,典章文物中的程式拟象均为“象”,正如王夫之所云:“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周易外传》)及至晚周时期,“象”词义分化,添加“亻”字旁,而衍生出“像”。其结果是,“象”字仍被沿用,既指称象这种动物,又指称描摹事物形貌的成果;而“像”指称描摹事物形貌之行为。之后转释引申,“象”泛指感知事物所成的观念具象,“像”则指从物类抽取观念属性之行为。
关于“像”义的这个性状,《韩非子·解老》描述云:“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故日‘无状之状,无物[象]之象。”这解说的是《老子》十四章,旨在探究“道”观念之由来,指明是由“意想”而生成的。所谓“无物[象]之象”,是指无迹可寻的“道”体,亦即“道”这个观念具象。循韩非理路,也可解析为:活象、死象均为“象”,按死象骨骸而意想的活象也是“象”,而这种意想行为则是“像”。以此类推,“道”之本体是“象”,“执其见功以处见其形”的行为是“像”,经由“像”的作用所想见的道体也是“象”。在这个理路中,明显灌注了人工因素。正是由于人工因素的作用,“象”义才分化出“像”,抽取观念属性才成为可能;所以“像”义的产生,标志着人工因素激增。
另一方面,观念具象的自足程度提高,大体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况:第一,物类的观念属性相对恒定,物类与属性形成稳定连接,致使人们提及某一物类,就会联想它的观念属性。比如,说起鲲鹏,就联想到自由逍遥,随意所适;说起天,就联想到清明在上,无所不覆;说起地,就联想到广厚无边,无所不载。这种性状的发生,大约有两重因缘:其一,物类的观念属性是固有的,
不需外力强加,即所谓“物类之起,必有所始;荣辱之来,必象其德……物各从其类”(《荀子·劝学》);其二,物类的观念属性是自足的,不受时空拘限,即所谓“类不悖,虽久同理”(《荀子·非相》)。这样,物类就超越实物形式,虚化为一种观念实体。当人们调用这些观念实体,即使不去想象具体的物类,而只在观念层面进行连缀,也不至于引起隔阂与歧误。
第二,某一物类蕴含多种观念属性,这些观念属性可以是相关的,也可以是不相关的。这种性状的发生,大约有两重因缘:其一,事物质性是复杂多面的,大们从中抽取观念属性,不可能做到圆融而完备;故而在一定用象情境下,物类观念属性是片面的。比如时人辩论“离坚白”,就因石有坚硬与色白属性,而感知者又有所偏执。其二,人的感知能力往往有差异,又受多种外在因素的影响。人们感知同一物类,甲某偏重其这一面,乙某偏重其那一面;即便是同一感知者,此时此地他敏感这一面,彼时彼地又敏感另一面。这样难免偏取物类的观念属性。比如时人辩论“白马非马”,就出于偏取物类的观念屙陛,而感知者又适己所好。
第三,不同物类可以呈现同一观念属性,反过来也就是,同一观念属性可以呈现在不同物类中。其性状是,观念属性仍从物类抽取,并由该物类来具体呈现;而不是先有某种观念,再附加到各种物类中:更不是脱离具体物类,而成纯粹的观念形式。这种性状的发生,大约有两重因缘:其一,世间物类繁多,难以搜求穷尽;且在一定的时空中,人的感知总有局限。因此,物类与观念属性未必一一对应,可能是某一观念属性与多个物类分别配对,或者是多个物类分别与某一观念属性配对;其二,尽管心灵不受外物拘限,但在具体的时空中,人的感知往往是受动的。此时此地,遇见此一物类,受此一物类触发,便从中抽取此一观念属性;彼时彼地,遇见彼一物类,受彼一物类触发,便从中抽取彼一观念。这样抽取的观念属性,可以是不同的,也可能是相同的。当它们相同时,就表现为不同物类呈现了同一观念属性。如《老子》、《庄子》所述“道”近同,而其所抽取的物类却多种多样,或抽取自“冲”、“深”、“湛”等水的蕴蓄形态(《老子》四章),或抽取自“蝼蚁”、“梯稗”、“瓦甓”、“屎溺”等低下猥亵之物(《庄子·知北游》)。
(三)语言媒质
晚周用象既然凸显观念属性,就脱落早前用象的程式内涵,而不再依附操持程式,主要凭语言媒质传达。这样,语言的功能便明显增强,由辅助上升至主导地位。有人依托孔子云:“天下有道,则行有枝叶;天下无道,则辞有枝叶。”(《礼记·表记》)由“行有枝叶”到“辞有枝叶”,隐约揭示了言辞开露之实况。语言既然日渐开露了,就成用象的有效媒质。晚周用象的提示词,诸如“若”、“譬”、“谓”、“如”、“道(说)”、“名”、“曰”、“辩”、“言”、“喻”、“谕”、“说”等,大多从口从言,显示了语言与用象之共生,也突出了语言的立象功能。对此荀子更阐述日:“故辨说也:实不喻然后命,命不喻然后期,期不喻然后说,说不喻然后辨。故期、命、辨、说也者,用之大文也,而王业之始也。名闻而实喻,名之用也:累而成文,名之丽也;用、丽俱得,谓之知名。名也者,所以期累实也;辞也者,兼异实之名以论一意也。辨说也者,不异实名以喻动静之道也;期命也者,辨说之用也;辨说也者,心之象道也。”(《荀子·正名》)“辨”通“辩”,指言语谈辩;“道”通“导”,指传达媒质。辩说是战国中晚期流行的语用方式,其包含的命、期、说、辩等项,正是传达观念具象的具体环节;所以荀子说语言是“心之象道”。
但也要切实估计,晚周语言媒质只是相对独立,还未发展为纯粹的语言形式。受观念具象形制的约束,它大致呈现为两种倾向:一是实用功利倾向。晚周观念具象之调用,多在修身、议政等场景,附着了浓厚的政教色彩。受外加的功利因素影响,语言的本体就难以凸显。因而人们多关注言语的德义规范,却相对淡忽语言的本体内涵。孔子提山“慎言”主张,而以周礼作唯一标准(《论语·子路》);墨子主张言有“三表”,也是从功利目的着眼(《墨子·非命上、中、下》)。尽管时人谈辩述学,也能暗合形式逻辑,如遵从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充足理由律等;但那多是感性经验的适用,并非逻辑论式之抽象。二是物象中心指向。作为晚周用象的媒质,语言主要指示物象一边,亦即偏向观念属性所抽取的物类方面,而疏离抽取观念属性的人工方面。这就形成语言媒质的物象中心倾向。人们很少像后世文人那样直抒胸臆,而是大量调用观念形态的类象;并以“若”、“犹”、“譬”等提示语,来显示物象与观念的类比联想。正是受这种类比思维制约,语言也依循同类相推原则,其向心不在所联想的观念,而在于引起联想的物象。所谓“传言以象,反舌皆至”(《大戴礼记·小辨》依托孔子语),描述的正是这个情状。这样就强化了物象的中心指向,而弱化了语言的达意功能,使纯粹语形式难以发育。
基于上述晚周的言用状况,语言理论也得到相应发展,孕育出如下三大关系范畴:
其一,名实之争。名实命题肇论于孔子,他首倡“正名”之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所谓“名不正言不顺”,是指旧名与新实不同一:以此反观,若依旧名与旧实之同一,则原本是“名正言顺”。从“名正言顺”变得“名不正言不顺”,正是程式拟象转为观念具象的语言表征。要改善名实乖离状况,就应强化语言的功能,复归“名正言顺”,达成新的名实同一。其途有二,或依从旧名来矫正新实,这是当时孔子修复周礼所期待的;要么依从新实来确定新名,这是后来荀子创设王制所期待的。”不论是复古还是创新,其所引导的名实之争,均在于达成名实同一。故而晚周诸家所论,大都沿此导向展开。
其二,文质之分。文的本义是修饰,相反,未加修饰就是质。质又常被称为野。文质是对关系范畴,其发端可推寻很远。早在春秋中期以前,文指礼文,修饰对象是人的行为(含言语行为)。人的行为(含言语行为)符合礼仪规范就是文,不符合礼仪规范就是质(野)。例如,郑国攻打陈国,子产献捷于晋,依据礼法辩说,辞顺而无所难。对此,孔子评论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此所谓“文”、“文辞”,是指对外交辞令之修饰。及至春秋战国之际,文指身文,修饰对象是人的品行(含言语态度),人的品行(含言语态度)符合礼义要求就是文,不符合礼义要求就是质(野)。例如,孔子论品行修养:“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大约到战国中晚期,文指言文,修饰对象是人的言语(含语言论式),人的言语(含语言论式)符合听受指向就是文,不符合听受指向就是质(野)。例如,群臣为齐景公抚疡,晏子所言极尽文饰,较高
子前说之鄙陋,其文雅与质野迥然;所以景公日:“吾不见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七章)此事应出自纵横策十的缘饰,反映迎合听受者的言辩风习。”总的来说,此三种文质形态都侧重修饰内容的外加规范,而忽视修饰对象的自身要求。这就阻滞了纯粹语言论式的成熟,诱导着言语实用的发展方向。
其三,言意之辩。言意这一对关系范畴,主要探讨言能否尽意、言如何尽意之类问题。在晚周用象背景下,它有三种理论倾向:一是主张言能尽意,以儒家、墨家和法家为代表。孔子尝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其本意是肯定辞能达礼。《墨子·小取》云:“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这对言能尽意表示充分信任。二是言不尽意,以道家和名辩家为代表。《老子》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这是从体道引发的看法,认为言语仅仅是工具,不能传达对道的体认。后来庄周学派转释之,将道扩展为一般的意,而得出言不尽意论。如《庄子·秋水》云:“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论,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三是折中的看法,在言不尽意前提下,融摄了言能尽意论。这又形成两种论调:一种出自《易》传,在言、意之间添加象,以为言不尽意,但立象能尽意:“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不过,此所谓象是特指《易》象。另一种出自庄子后学,只肯定言的有限功能,但主张得意就要忘言。如云:“荃[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蹴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庄子·外物》)
三观念具象的表形
基于上述用象的形制特征,观念具象就可以自由组合,形成多种多样的构形,具有更强的表义功能。所谓组合构形,是指在具体语境中,一或多个观念具象,依据自身形制特征,建立新的观念联属,而成为完形自足、相对独立之表形。在晚周谈辩述学的场景,观念具象极少孤立出现,而往往落实在特定语境中,以组合构形的方式被调用。这或可以说,组合构形是调用观念具象的基本形式,主要有类型、结构、形义等多种表形。
从形质层面考察,观念具象组合构形有一定规则。一方面依循人类用象的发展规律,它与早前用象(如《诗》兴象等)应有演化关系;另一面基于观念联属等三人特征,它比早前用象(如《诗》兴象等)更加适用随意。在晚周特定的语境中,既可调用单个观念具象来组合构形,也可调用多个观念具象来组合构形。而调用多个观念具象又有两种情形:一是多个观念具象组构为理据关系,二是多个观念具象组构为叙事关系。这样就有三种基本类型,即单元型组合构形、复合型组合构形和叙事型组合构形。此三种类型,虽都以观念具象为基本元件,但不是观念具象的简单叠加,而升为更高层位的用象结构,且具有相对独立的表义功能。
(一)单元型组合构形
所谓单元型组合构形,是指在一定语境中,调用单个观念具象,并遵循同类相推原理,而成完形自足之表形。例如《论语·八佾》云:“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木铎”是铃的一种,金体而木舌,属周代礼器。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它作为诗乐演述的名物,必须依附特定的操持程式;因而,“木铎”只是程式拟象的媒介,尚不具备独立自足的形义特质。及至孔子的时代,因礼乐制度废坏,“木铎”的程式内涵脱落,其所暗示的政教内涵凸显,转化为呈观念属性的物类,从而转型成一个观念具象。所谓“以夫子为木铎”,即对二者实行同类相推:孔子有感于天下无道,因以修复周礼为己任;而“木铎”作为周礼遗物,变为蕴涵政教观念的类象。这就调用了观念具象“木铎”,依其政教内涵来进行观念联属,而成相对独立的表义单位,且表形为单元型组合构形。此可直观表示为:[孔子]—→[政教观念]←—[木铎]。”再如,《庄子·人间世》两处调用社树,也都是单元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社树本是原始崇信物,而在周代诗乐演述中,它转化为起兴的名物,用以引发《诗》兴象。即如《诗·唐风·秋杜》首章,以社树“秋杜”起兴,寄寓着宗族父兄之思。及至晚周时期,诗乐演述的体制废弛,社树的程式内涵流失,其宗族父兄之思脱落,其某些属性反而凸显。比如,社树不合材用,不材而可不夭,不天而终天年;这样,就可抽取不材而寿考(无用乃大用)的观念,从而实现社树由程式拟象向观念具象之转化。《人间世》中调用社树这个观念具象,即依不材而寿考(无用乃大用)属性,而与散人(神人)的生存理念相类推,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联属,其表形仍为单元型组合构形。此也可直观表示为:[社树]—→[不材而寿考(无用乃大用)]←—[散人]。这两例都遵循同类相推的原理,且暗合形式逻辑同一律;因而能结体完形、形义自足,组构成相对独立的表意单位。
(二)复合型组合构形
所谓复合型组合构形,是指在一定语境中,调用多个观念具象,并遵循同类相推原理,而成完形自足之表形。例如《荀子·法行》所载曾子训子语:“大鱼鳖鼋鼍犹以渊为浅而堀其中,鹰鸢犹以山为卑而增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饵。故君子苟能无以利害义,则耻辱亦无由至矣。”这里调用了鱼和鸟两类观念具象。鱼鳖鼋鼍堀居渊中、鹰鸢增巢山上,这样的生活习性出于安居远害;但此二类不抵饵食诱惑,终致遭受祸害。曾子从二类中抽取共有的贪利害性观念,而使鱼和鸟这两个类象具有相同的属性。正是凭借这相同的观念属性,鱼类和鸟类才能被连缀一起,构成了一组复合型观念具象。它被引用到曾子训子语境中,即可依鱼鸟的贪利害性观念,来与世人的贪利害义相类推,从而建立一个新的观念联属,表形为复合型观念具象组构,以反推“无以利害义”之诫。此可直观表示为:[世人)—→[贪利害义(性)]←—[鱼鳖鼋鼍]+[世人]—→[贪利害义(性)]←—[鹰鸢]。这个表形也遵循同类相推原理,且暗合形式逻辑同一律;因而也结体完形、形义自足,组构成相对独立的表意单位。
值得玩味的是,复合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自有来源,与复合型《诗》兴象等有同构关系。如《诗·豳风·九罭》用“鳟鲂”“鸿”,两物共引发三次起兴,所成兴象聚合一篇中,构成复合型《诗》兴象,可直观表示为:[鳟鲂]—→[网大鱼需九罭(兴起)迎贵宾需尊礼]←—[周公]+[鸿]—→[飘飞渚陆失所(兴起)被疑避居东都]←[周公]。若将此一表达式与前一表达式相比照,则可发现,[网大鱼需九罭]与[迎贵宾需尊礼]、[飘飞渚陆失所]与[被疑避居东都]未能泯合无间,其构成复合型兴象必须《诗》篇演述的“兴”程式来衔接。但除此环节不同之外,两式的表形大体同构。
由此可知,复合型观念具象是复合型程式拟象(如《诗》兴象)的自然演化,它摆脱操持程式的约束,而主要凭语言媒质传达。由于脱落了程式内涵,其观念属性就被凸显;故而可在观念层面,更自由随意地组构。
(三)叙事型组合构形
所谓叙事型组合构形,是指在一定语境中,调用若干观念具象,既表述人物叙事关系,又遵循同类相推原理,而成完形自足之表形。例如《庄子·至乐》所调用:“昔者,海鸟止于鲁郊。鲁侯御而觞之于庙,奏九韶以为乐,具太牢以为膳。鸟乃眩视忧悲,不敢食一脔,不敢饮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夫以鸟养养鸟者,宜栖之深林,游之坛陆,浮之江湖,食之鳅鲦,随行列而止,委蛇而处。彼唯人言之恶闻,奚以夫譊譊为乎!”此即鲁侯养鸟寓言,其中心物类是海鸟。另据相关文献的载述,海鸟亦作爰居、燕等。燕作为程式拟象的起兴物,义见《诗·邶风·燕燕》。燕原是先民鸟图腾崇拜的表象,如今因“兴”程式的介入,而演述成一个《诗》兴象,明显附着了某种程式内涵。而在《庄子·至乐》中,海鸟厌恶九韶、太牢等礼仪,暗示它将从礼乐程式中解脱,由程式拟象演变为观念具象。这样,海鸟就脱落附加的程式内涵,而凸显顺乎天性的观念属性。此外,该寓言中除了海鸟,还有鲁侯这个物类。鲁侯不懂海鸟习性,强“以己养养鸟”;从中抽取违逆天性的属性,而成反衬海鸟的观念具象。如此,海鸟与鲁侯就组合构形,建立一种新的观念联属。这种新的观念联属,不仅表述为一定长度的叙事过程,而且呈现出同类相推的逻辑关联,因而为叙事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这可直观表示为:[海鸟栖止于鲁郊]——[鲁侯以己养养鸟]——[海鸟厌饮食而死]+[海鸟→以鸟养养鸟(顺乎天性)]←→[以己养养鸟(违逆天性)←—鲁侯]。这个表形虽增繁为叙事过程,却仍遵循同类相推原理,且暗合形式逻辑排中律;因而也结体完形、形义自足,组构成相对独立的表意单位。
由此便可以说,寓言是用象制度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其表形就是叙事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在晚周谈辩述学的语境中,寓言表现出自身的规定性:一方面,作为相对独立的表意单位,它可供晚周诸子适时调用,却未发育成纯粹文章体式,因而不同于当今寓言故事;另一面,作为观念具象的衍生产物,它有观念联属等形制特征,其寓意是从物类中抽取的,因而绝不是理性的感性化。
若更从观念具象的演进历程考察,上述三种组构类型又有时段表征。既然观念具象由程式拟象转化而来,那它作为晚周新兴的一种用象形态,便有孕育、成形、增长与纯熟进程,而其总的态势是由简单渐趋于繁复。其表征是:春秋晚期,以单元型组合构形为主,开始出现复合型组合构形,叙事型组合构形几未产生;战国前期,以复合型组合构形为主,单元型组合构形渐次式微,开始出现叙事型组合构形;战国中期,叙事型组合构形剧增,而复合型组合构形仍有优势,战国晚期,以叙事型组合构形为主,而复合型组合构形渐次式微。这就是晚周观念具象表形的总体特征。
在晚周谈辩述学的用象背景上,人们又以三种类型组构为部件,进行更高位更宏通的观念联属,从而创设体制更巨的表形集成。通观晚周诸子的著述,其一般的形义表征是:在一篇或一段文字当中,除了一些推论式的文句,其余便是这种表形集成。这种观念具象的表形集成,照样遵循同类相推的原理,并且依据内在结构之关联,而表现出独特的风神肌理,灵动多变,意态繁富。兹仍以(《荀子·劝学》首二章为例。若依其内在的结构形式来切分,这段文字包含十二个表意单元;每单元都是观念具象组合构形。其表形与结构可示例如下:
第二表意单元:“木直中绳,鞣[揉]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曝,不复挺者,鞣[揉]使之然也:故木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其表形为复合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木揉为轮]→[曲中规(知明而行无过)]←[君子博学自省]+[木受绳]—→[正直(知明而行无过)]←[君子博学自省]+[金就砺]→[锐利(知明而行无过)]←[君子博学自省];其形式以“+”为标识,而成三段式并列类比结构。
第三表意单元:“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其表形为复合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不登高山、不临深溪]→[不知天之高、不知地之厚(不知学问之大)]←[君子不闻先王遗言]←→[登高山、临深溪]→[知天之高、知地之厚(知学问之大)]←[君子闻先王遗言];其形式以“←→”为标识,而成两段式正反类比结构。
第六表意单元:“南方有鸟焉,名日蒙鸠。以羽为巢而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系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日射干,茎长四寸,生于高山之上,而临百仞之渊;木茎非能长也,所立者然也。”其表形为叙事型观念具象组合构形:[蒙鸠为羽巢]——[编之以发]——[系之苇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蒙鸠为羽巢而编以发、系于苕]—→[风至苕折卵破子死(不知学问而危身)]←[人而不学]←→[射干生高山上]——[高临百仞之渊]——[立高而身加长]+[射干高临百仞]—→[立高而身加长(增益道德学问)]←[君子以学润身];其形式以“←→”为标识,而成两段式正反类比结构。
以上描述了晚周用象制度。它表明,晚周人感知成象很独特,其用象形态已自成一格。人们基于有限的认知能力,采用简明的类比思维方式,遵循浑朴的同类相推原理,建立事物之间的观念联属,并主要靠语言媒质来传达,而成自由灵便的观念具象。晚周诸子谈辩述学,大量调用观念具象,将之进行组合构形,以成三种表意类型,进而创制表形集成,从而独具风神肌理。这也表明,观念具象颇有效用性,其形义显得完形自足,能达成对世界的把握。而可叹的是,近世以来人们似乎遗忘了这种用象形制。
责任编辑胡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