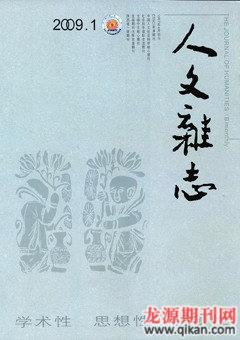先周历史与牵牛传说
赵逵夫
内容提要牛郎、织女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广大农民的象征。男耕女织、自给自足是农业社会的基本经济形态。牵牛(牛郎)的原型是周人的先祖叔均。《山海经》中两处记载叔均“始作牛耕”,一次记载其抵御了旱灾,因而后世以为“田祖”。牛用于农耕是远古时期的伟大发明。周人在远古时代各部族中农业最发达,农业生产上贡献最大。后稷弃、叔均是其杰出的代表。周人因叔均在始作牛耕上的重大贡献以“牵牛”的名称将其命为天汉东侧一颗星的名称。《诗经》中的《甫田》、《大田》即周入祭田祖之诗。叔均的父亲“台玺”,“玺”为名,“台”表其部族,即《诗·大雅·生民》中“即有邰家室”的“邰”,本姜螈之国,后稷生处,在今陕西武功、宝鸡一带。求“台”、“邰”之本义,也即有牛之处。叔均的“叔”表排行。后代传说中牛郎有兄,也与此有关。
关键词牛郎织女牵牛叔均《山海经》田祖先周历史
[中图分类号]1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47-662X(2009)01-0087-11
一、《牛郎织女》传说的蕴含与流传的广泛性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时间最久、产生时代最早、最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征,在海内外影响最大的一个。无论从拿一个方面说,这在世界民间传说中都是少见的。说它孕育时间最久,因为它的两个主要人物的名称和身份特征分别来自原始社会末期秦人和周人的两个祖先;说它产生时代最早,因为它的故事产生于秦汉之际,定形于汉代末年;说它最集中而典型的反映了中华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特征,因为故事的两个人物牛郎、织女事实上是我国从史前时代直至近代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社会特征。中国长久的农业经济在世界上是比较典型的,而《牛郎织女》的传说故事正反映了这一特征;故事中的王母或玉帝既是家长的象征,又是国家政府的象征,又是神灵的象征,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说:
“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
那么,《牛郎织女》故事中的玉帝或王母,便是政权、族权、神权的代表,是中国农民几千年中所受压迫力量的象征。相对来说,夫权的统治在广大劳动人民中不象上层统治阶级中那样突出,因为在农业劳动中男女双方都从事劳动,因而在家中也都有发言权。而且,劳动人民是热爱自由的,所以在这个故事中,不但没有男子对妇女的压迫、歧视的情节,而是表现出他们共同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进行不懈努力的状况,反映出对爱情的无限忠贞。这种精神,同大量民歌中所反映的精神是一致的。而且,这个传说还反映出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对所谓“门当户对”的门阀制度和门第观念的批判;作为农民形象代表的牛朗以王母的孙女为妻,也反映了上层社会中妇女没有地位,男子对女子缺乏真诚爱情,因而青年妇女更希望以淳朴的农民为妻的实际。这些都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中深层的问题,已涉及对整个封建制度、封建礼教的批判。说它是我国民间传说故事中流传最广的一个,因为它不仅在从南到北,从西到东的广大地区,包括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中广为流传,南方的苗、瑶等少数民族中也有他们的流传版本,同时在日本、韩国、越南、东南亚地区也广泛流传。比如日本不但牛郎织女的故事广为流传,而且有不少诗歌作品歌唱这个故事,据我们初步掌握,就有100多首。而且,在日本的仙台,七月七日是一个十分盛大的节日,带动了仙台的旅游文化。说它影响最大,因为它形成了流传两千多年,涉及好几个国家的“七夕节”。由此产生了无法统计的诗、词、曲、赋、文作品和小说、曲艺、戏剧。历代咏牛郎织女的诗作数不胜数,我国的各个剧种中也都有《天河配》、《牛郎织女》的剧目。
二、八十年代以前关于《牛郎织女》起源的探索
以往在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中,对《牛郎织女》的研究是最少的,关于它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更少。
对《牛郎织女》传说真正说得上研究的是钟敬先生刊于《民众教育季刊》1933年第1期上的《中国的天鹅处义故事》,这篇论文从母题的角度对这个故事母题的“本来形态”、牛郎织女传说的基本情节要素及流传中由于改削、增益、混合等而形成的分化情况作了细致的分析。但这篇论文牵扯到故事产生的部分只能说是从民间文学形成和情节的基本模式方面所作的推断,还没有能从其题材本身,即素材的方面去进行考察。民间文学研究中的“母题”,实际上只是情节类型上的模式,并不关系到题材本身。
1949年以后,在这方面影响最大的一篇论文是范宁先生发表于1955年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一文。文章说:“传说织女最初是天上水神,后来由于她和凡人农夫发生过恋爱关系,恰巧天上的两个星座结在一起,被想象成为一对夫妇,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到六朝时这对夫妇的美好生活在传说中有了变化,据说遭受到外力的破坏,扮演了爱情悲剧的角色。”范宁先生以为《牛郎织女》的传说同牵牛星织女星没有关系,后来才被联系到一起;依据张华《博物志》所记有人浮搓至天河见到牵牛的故事,认为在晋代之时牛郎织女故事中他们的生活是富裕的,也是美满的,到六朝时(按:据上引文字宁先生之意思是说到南北朝之时)这对夫妇的美好生活在传说中有了变化,才变成了悲剧的情节。范先生引述材料过于随意,忽略了一些时代较早且可靠的材料,而依关系不大的间接材料进行推论,故难以成立。但成书于上世纪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辞源》的“织女”条就基本上采取了范宁先生的说法。此后二十多年中,基本上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
八十年代末学术界对于我国文明的起源问题,越来越多的关注,地下考古发掘的一些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也引起人们对传统文献的从新审视,对神话传说民俗资料的意义,也有了新的看法。尤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礼县大堡子山发现了大规模的秦先公先王陵墓群,使我对长期流传在西和、礼县一带的隆重、盛大的乞巧风俗和礼县盐关镇历史悠久的骡马市场的起因产生了兴趣。我回顾清理了历来有关“七夕”节和“牛郎织女”传说的材料,以时间排比,按其地域分布加以分析,分其先后,辨其源流,认真考索。我研究的结果,“牛郎织女”的情节要素在汉代已形成,这个传说故事中两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形成同我国从史学时代开始的农业经济特征有关,而其悲剧结局的形成又同我国封建专制制度,封建礼教对男女青年杂七杂八婚姻上的迫害有关。我认为织女先是秦人的祖先女修因善织而命为星名“织女”,到战国时代人们慢慢忘记了它原来的含义,而
同天汉另一侧的“牵牛”星联系,形成了一个人间同天上相交结的天人恋爱故事。我写了两篇论文,在1990年发表,一篇《论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与主题》,一篇《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郎织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我在这两篇论文中对范宁先生的说法进行了辩驳,这里不多说。
关于牛郎,即牵牛,最早我以为是由商人祖先王亥而来。因为《山海经》、《世本》、《楚辞·天问》中都说到王亥事迹同牛有关。但后来联系我国史前农耕文化的发展的实际,以及史前和夏商、西周时期各部族活动同汉水的距离远近等进行思考,更重要的是发现了《山海经》中两处写到周人的先祖叔均发明了牛耕,而且被尊为“田祖”,我认为天上的牵牛星,本是指周人的先祖叔均。因为《山海经》中明确说后稷的后人叔均用牛耕,成田祖,而文献中记载王亥同牛的关系只是“服牛”(或作仆牛),大约是指以牛为运输工具,而非用于农耕。关于这个看法我已在《汉水与西礼两县的乞巧风俗》、《寒水、天汉、天水——论织女传说的形成》两文中论述过。我们在后面对此问题再加论述。
在此前也有过两篇文章,一篇是刊在杭州大学中文系办《语文战线》1980年7月第43期“资料”专栏所刊《牛郎织女故事的产生、流传和影响》,吕洪年辑,约五、六千字,用综述的形式所述,大体皆人们常见的《诗·大东》、《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等材料和此前论文和民间故事集中提到的几个不同传说,材料中包括一些唐宋诗词,一直至毛泽东《送瘟神二首》,对这个传说产生的根源并未作探讨。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引述了《北朝鲜游记》所记述的一个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化版本。
另一篇是刊在安徽省文学艺术研究所出版《艺谭》1981年第3期“大学生论坛”专栏中的《牛郎织女故事的源流》,作者是安徽劳动大学杨果、范秀萍,其行文方式同吕洪年文章差不多,但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提到明代《渡天河牵牛会织女》杂剧和清代的《天河配》剧目,二是将《牛郎织女》传说同董永的故事联系一起进行考察,尤其后一点所用篇幅占全文一半。
可以说,这两篇文章都未对《牛郎织女》传说的根源和产生时代、产生地域、传说要素的形成转化过程等进行考察。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有四篇论文专门探讨《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问题。
一篇是姚宝瑄的《牛郎织女传说源于昆仑神话考》。论文说:“二星的名称源于人间的生活、劳动,即地上有了专营织帛的女子,天上才有织女星,人间有了专职牧牛的人,天上才有了牵牛星。”而“我国养蚕缫丝源于有史以前,传说最早发明推广育蚕技术的是黄帝的元妃西陵氏女嫘祖”。而商周时代纺织业有不断发展,并举出甲骨文中有“女蚕”、“蚕示”(蚕种)的文实。关于牵牛星,论文说:“奴隶主拥有大量畜群,并有专职放牧的奴隶,但放牧者却难得有一条自己的牛,于是‘牵牛的命名便完成了。其形式除牧牛一职外,奴隶主外出乘车,牧牛人便成了牵牛或御车之人”。论文中还引了《诗·豳风·胡》中诗句说:“可知古豳地是我国最古老的蚕区之一。又‘冬民即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当时妇女们日夜忙于纺织,一个月做了四十五个工。这些产品无疑为奴隶主吞并,以至奴隶们发出怨愤,以‘织女、‘牵牛喻西周,实乃更事出有因。”(按:其中引文出《汉书·食货志》)。论文进一步说:“周族是源于昆仑山、祁连山一带的皇帝、嫘祖之苗裔,最早的‘织女便应当是嫘祖”
这是一篇研究深入,很有份量的论文。其意义主要在以下几点:
(一)指出“牵牛”、“织女”二星的名称源于人间的生活、劳动,将以往只从《牛郎织女》情节方面探求这个传说的起源引向以“牵牛”、“织女”这两个名称的形成为起点进行探索。
(二)肯定了“牛郎织女”传说同上古西北民族有关,尤其指出了同周民族有关。
(三)论文第三部分在论述见于句道兴本《搜神记》的“田章天女”故事时,提到这个传说同西王母的关系,指出后世神话故事中的王母实由‘西王母转化而来。
(四)第二部分引了《拾遗记》卷一中一段文字,言皇娥乘桴而昼(原引文误作“画”)游“时有神童,称为白帝之子,降乎水际,与皇娥燕戏,秦便娟之乐,游漾忘归”,后皇娥生少昊,号穷桑氏。(按原文末注明出处,引述也不甚准确,然可以肯定出于《拾遗记》只是转引自他处)。
认为“漾为汉水,值得注意”。(文中言《左传·昭》有关少吴建立鸟王国的美丽神话,当指《左传·昭公十七年》所载郑子的一段议论)。还引了汉女与郑玄甫相会于汉水之滨的故事,第三部分归纳为“‘汉女型神女”,认为洛水女神宓妃故事中,也应注意到“洛水出秦国北部向东南人黄河”。尽管论文对织女传说同汉水的关系尚缺乏有力的论证,但作者注意到“牛郎织女”传说同汉水有关,并引《说文》:“汉,漾也”,《辞源》“汉,水名,即汉水,又系天河。”这是很有必要意义的(作者之所以将织女的传说同皇娥加以牵合,也应是由于这个原因)。论文中又说:“‘汉地乃西周初农桑发达之地”,“所以,追寻‘织女踪迹还要在昆仑神话统治的时间内,在其管辖的区域里看”。其表述虽然欠确切,但都道出了部分的真理。
论文还对《牛郎织女》传说同董永的故事,句道兴本《搜神记》所载田章的故事的关系有所探索,有一定的意义,这里不多说。
但这篇论文也存在若干问题。这些问题影响到其结论的成立和论述的可信程度,这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织女”之名显然指一个以织布帛出名或在织布帛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女子,但论文却追溯到最早养蚕的妇女嫘祖的身上。此同织女的传说并不相合。同时,嫘祖传说一开始就是指传说中一个善养蚕或发明了养蚕缫丝的妇女,而不是指一个由未婚的女子,到结婚生子的女子。这一点似也不甚切合。
(二)上古星名的命名,除了同原始宗教、神灵相关的星名(如“天门”、“天蹲”、“天田”、“天纪”、“天枪”、“霹雳”、“雷电”、“腾蛇”之类),和依照人间帝王宫廷、京都的设置取的一些名称(如“帝座”、“宗正”、“牵道”之类)外,总是传说中部族的首领(如柱、轩辕、造父),或杰出人物(如傅说、王良)或传说中在某方面作出了贡献的人物(如奚仲)。因为给星命名,总是掌握文字工具,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物来完成的(古有专人掌“天官”,为世职,以观察天象,记载灾异、制定历法)。随着社会的发展,各部族文化交流的频繁,原有的一些星名被流传广的星名所替代,甚至统一王朝根据自己的政治需要,对一些星重新命名(“天大将军”、“土司空”之类当属此类),不可能是由奴隶们给星命名,成了古代通行的,见之于竹帛、传之后世的星名。所以,论文第一、第二部分以嫘祖为“现实中‘织女”,以皇娥为“神话中‘织女”的论证,都不能成立(其实嫘祖也
是传说中人物,同皇娥差不多)。
(三)认为牵牛(牛郎)是由“牧夫型”人物而来,第四部分同“牛郎织女”故事长期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特征的国家流传,事实上也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发展成熟起来的,实际状况不相符合。牛郎实际上是几千年中一直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化身。
(四)在文献的征引方面颇多疏失。第三部分倒数第二段说:“在此前将牵牛织女为并称的功绩归于班固”临乎昆明之地,左牵牛而右织女,自《春秋元命苞·初学记二》、《淮南子·俶真》始谓织女为神女,至魏曹植《洛神赋》止,三百几年,由曹植立案判定将人世间汉女型神女送入长天,与牵牛结为夫妻。这一小段话中有几个问题:
1《淮南子》、《春秋·元命苞》均在班固之前,而文中以为在班固《两都赋》后。
2曹植《洛神赋》中只“叹瓠瓜之无匹兮,咏牵牛之独处”二句同“牛郎织女”传说有关,但也只是借以表现自己的孤寂之情,对“牛郎织女”传说并无发挥或论断,文中所说之语无着(论文结尾部分也说“曹植将上天‘织女、‘牵牛二星结为夫妻”,实则《两都赋》、汉乐府《迢迢牵牛星》都早于曹植之作)。
3《春秋·元命苞》公布于东汉初年,《初学记》成书于唐玄宗之时,二者并无关系,而文中误以后者为前者中之一部分。
行文中诸如此类的疏失还有一些,如文中引了《诗经·小雅·大东》后说:“可知,早在西周初年”云云(第17页),而实际上《大东》一诗产生于西周末年,殆无异议;注《诗·生民》作《民生》,言此诗中反映“奴隶主有大量畜群,并有专职放牧的男奴隶”(18页),引《拾遗记》卷一大段文字未注明出处(19页),引《汉广》文字,以“其中《汉广》载有”领起,所引却非原文,而是译文(20页),与全文因述体例也不相符;但无论怎样,我以为这篇论文在“牛郎织女”传说研究中还是一篇有思考、有新见、思路开阔,具有一定启发性的论文,是应该予以充分关注的。
八十年代末,《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刊有徐传武《漫话牛女神话的起源和演变》。这篇论文行文严谨,引文规范,论证也较严密,又有新见,是比较重要的一篇论文。这篇论文明确将“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其证据主要是论述了我国黄河流域从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已出现了农业,到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农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作物除栗之外,已开始种植麻,先民们已掌握了较多的天文和生产季节知识,这些社会发展方面是故事形成的合理条件。
值得注意的是,论文对《荆楚乡时记》中“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同样话语也见于明冯应景《月令广义》所引南朝殷芸《小说》)。杜甫《牵牛织女》中“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两句诗众所周知言牵牛、织女两星方位同实际相反的问题作了解释。论文引了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三章的文字:“据计算,公元前2400年,河鼓(牛郎星)在织女西”,因而说:“牛朗织女为神话的创始年代是与牛、女二星方位相合的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这是很新颖的看法,尽管公元前2400年前后正是黄帝时代,那时的星象情况能否传到南北朝以后,很值得怀疑;且古人都随时观察天象以知时节,其不论当时星象实际而用三千年前的星象位置,必难以置信,但这一点毕竟是将来继续探索的一个新线索。
这篇论文同吕洪年文章一样将织女传说追溯到传说中的黄帝之妻嫘祖,同时论文中说:“我认为原始的牛女神话的主角是两个‘女织男牧(或耕)的劳动的‘平民形象,显示着当时社会的男女劳动的两大分工,或者说是劳动者在创作神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形象和天上的星宿联系起来”(45页),这一点也同史前社会的实际情形并不符合。以前人们误以为母系氏族社会末期至父系氏族社会人们都是完全平等,权利、义务完全均等,其实并非如此。在父系氏族社会中期以前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氏族、部落首领无太大的特权,但社会分工还是有的,氏族、部落有集中大家意见和首先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力,氏族、部落的首领是人们公认的杰出人物,有领导才能,其贡献比一般人大,是理所当然的,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是氏族或部落的代表人物,他们的行为、组织、领导、决策常常决定了部落的历史,这也是可想而知的。因此,认为一般的氏族部落人员,或者笼统的所谓“平民”被命名为星名,这也是不可能的。它的形成总是有一个代表人物的活动或事迹而引起的。
其次,论文认为“至秦汉时代国家出现了大一统一的局面,君主制政体确立,织女星才被说成天帝的孙女(一说帝女,或曰帝子)。”认为天孙或曰帝女的身份同上古神话完全无关,这一解释也比较勉强,既然这样都是平民,牵牛为什么被说成天帝的孙子或儿子?
再次,认为“牛郎织女”的神话起源于母权制度向父权制度过度的时期(43页)或日中国原始氏族社会母权制时期,都估计太早。应该说是在父系氏族社会末期。这样一来才能同原始社会末期的估计相一致。事实上,公元前2400年也正是我国父系氏族社会时期。
以上两篇论文的成就是大大打开了“牛郎织女”传说的思路,不是像有的学者一样只在秦汉以后有关材料中去寻找“牛郎织女”传说形成的线索,而是由“牵牛”、“织女”这两个名称的形成去探索它最早的胚胎。因此,应该说这是“牛郎织女”传说形成演变研究方面的两篇重要论文,应该予以重视。
近年来,由于国家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各地又都在开发旅游资源,《牛郎织女》的传说在全国各地、包括少数民族地区都有流传,在日本、韩国、东南亚一带也有流传,七夕节也是一个全国性节日,在亚洲很多国家、地区也都比较兴盛,所以,一些人在宣传七夕文化旅游活动的同时,也联系当地的某些地名、传说,对《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发表了一些看法。但实际上,真正进行了认真研究的论文并不多。《襄樊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4年刊有杜汉华的一篇《牛郎织女流变考》的论文,提到几种说法。除上面已论述过的姚碹莹提出的昆仑神话说之外,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山东沂源县旅游局网上的《招商项目》中介绍说,当地有始建于唐代的芝女祠、牛郎庙等古建筑,因此有人认为此处即牛郎织女的传说产生地。其实沂源织女祠、牵牛庙的传说是由于《诗经·小雅·大东》中说到“牵牛”、“织女”,据《诗序》,此诗是谭大夫为讽刺周王朝的沉重徭役而作,西周时间谭围其地在沂水上游,故后来当地附会而建有牵牛、织女庙,又有什么织女祠。诗中实际上是用牵牛、织女来比喻周王朝和周王朝的卿大夫,说他们居于高位而不关心民众。此说反映了他们同周地有关。再者,诗中在提到这两个星名之前先说“维天有汉”也恰恰说明了他们同“汉”(天汉、同汉水相应)有关。
(二)2004年农七月初,首届中国七月七爱情节
在鹿泉开幕。当地有关于牛郎织女的传说,这是不用说的。弘扬传统节日中利于精神文明,利于建立和谐社会的精神,这是一件大好事。“牛郎织女”的故事表现了青年男女为爱情的忠贞、为争取自由幸福的生活、不屈于家族、政权的压迫的精神,不追求豪华、富裕、高贵的生活而共同劳动、勤俭持家的优秀品质,在今天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对一些人热衷鼓吹西方的“情人节”,夫妻感情淡漠,追求物质享受而忽视充实幸福的精神生活的现象,也是一种抵制。我以为全国各地都应重视“七夕”节的教育作用,都应致力于挖掘它当中所包含的积极的思想、精神资源。
但有人一定要在当时找到一个同牛郎织女传说相关的地名,结果附会上了当地的抱犊山。但“抱犊”名称只能说同牛有点关系,同牛郎的传说并无关。而且“抱犊山”这个名称也产生在南北朝以后。《元和郡县志》卷十七萆山:“今台抱犊山,韩信伐赵,从间道草山而望。后遂改为草山。后魏葛荣之乱,百姓因山抱犊而死,故经以为名。”则此山在汉代名萆山,名抱犊山为公元527年之后的事,但牛郎织女的故事在东汉时代已形成情节。实际上此处同牛郎织女的传说联系起来大体也就是近二三百年的事。
(三)《中兴江苏新闻网》2004年5月24日倪敏毓的《900年前中国的情人节起源于太仑南码头》根椐宋代《中吴纪闻》和《吴郡志》的有关部门文字,认为900年前的北宋末期已形成的有关节俗起于太仓。《吴郡志十三·祠庙下》载,昆山县东三十六里有一黄姑庙,其地也名黄姑,“父母相传,尝有牵牛织女星精降焉。女似以金簪划河,河水涌溢,今村西有百沸河,乡人异之,立其祠。旧留牛、女二像,后人去牵牛,独祠织女。”按“河鼓”本牵牛星异名,而误中误作“黄姑”,又设黄姑庙,后来又解“黄姑”为织女,正如赵翼《陔馀丛考》卷十九《湘君湘夫人非尧女》一文《蓼花洲闲录》中一个事实:“杜拾遗讹为杜十姨,而以之配伍子胥(讹为须)也”。古代南方淫祀,往往因音假想,即奉为神、清初诗孙枝蔚有《乌鹊桥》七绝一首,其前后二句云:“乌鹊桥今存茂苑,黄姑庙却在昆山。”诗后注云:“黄姑即牵牛星,繇“河鼓”讹也。父老言此精尝降于此,因祀之。同《吴郡志》所记一致,都是言河鼓星精虽降于此地,讹成黄姑,又误为织女。宋代其地有过七夕节的习俗,完全可信,但其地同“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完全无关。
(四)《四川文史》2003年第4期刊有重构的《七夕炎黄二帝通婚的故事》,将《山海经》中有关文字同牵牛织女的传说相比附,认为牛郎织女的传说起于山西、陕西、内蒙的黄河河套一带,其说颇为牵强。然而认为“牛郎织女”的故事起源于北方,也最早流行于北方,则从大的方面说,较为近理。
(五)杜汉华本人认为银汉古称汉、云汉,《诗经》二“南”之地孕育了《汉广》和“郑交甫会汉水之神”等诗歌与传说,《牛郎织女》的传说应产生于湖北襄阳。
以上这五种说法,本来都缺乏较扎实、严密的论证,很少有人注意到,但因为杜汉华这篇论文被收入一本名为《名家谈牛郎织女》的书中,一下被很多人所注意到,一般人也并未见到原文,不知其究竟是如何论证的,因而均视为一说。其实,杜汉华同志所列几说,有的发言者并不以为自己是在论“牛郎织女”传说的起源,只是对当时的“牛郎织女”传说及乞巧节的形成和传播作一解说而已。杜汉华同志的文章还提到日本祸岗说,我以为这也是猎奇以求惊人,不值一提的。
关于汉水同牛郎织女传说的关系,我在刊于《北京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上的《连接神话与现实的桥梁——论牛女故事中乌鹊架桥情节的形成及其美学意义》和刊于《西北师大学报》1990年第4期上的《论牛郎织女故事的形成与主题》两文都从不同角度作过论述和论证,杜汉华同志的文章也持这个看法,我们的看法一致。但其产生在襄阳的说法,证据却不充分。《汉广》一诗和“正玄甫会汉水之神”的故事同“牛郎织女”的传说毫无关系……上世纪五十年代范宁先生著文说“传说织女是天上的水神”,依据是唐代《开元占经》引《巫咸》语。而《开元占经》乃是星占家因很少有星在银河边而附会出来的,我于上面提到的论文中已予辩驳。
以往寻求牛郎织女的产生地,都是根据文献上的某些记载或某些有什么相关地名、祠庙可牵合处去论证是否是其地。我以为这种方法用于研究其他的民间传说鬼使神差的起源是可以的,用于研究“牛郎织女”这个产生时代早、流传十分广泛、其人物,情节又有极高概括性、典型性、代表性的传统故事,是难以达到目的的。这是因为:
(一)它孕育时间久,是我国古代、包括上古时代社会经济及礼俗制度等的概括反映,很难说产生于某一地。其中的两个人物,有可能是不同两个部族代表人物的原型发展而来。
(二)它的孕育形成可能经过了几个较长的历史阶段,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都可能在其中留下了印记,也很难说这个传说明确地起于何时。因此,从不同的角度上看,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我以为,《牛郎织女》的传说反映了我国从氏族社会晚期形成的农业经济社会中“男耕女织”的结构特征。耕而食,织而衣,衣食足而有礼义。男耕女织不仅是我国几千年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经济的基础,也是我国氏族社会晚期大部分地区经济的基本形态。牛用于农耕是农业发展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而我国封建社会中家长和宗族权力对男女青年爱情、婚姻生活的控制与破坏,造成无数的悲剧。然而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生活、追求婚姻自主的努力与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这样具有概括性典型性的题材,这样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人物,这样丰富而深刻的主题,要在某一个地方找到它的产生地是难的。
三、探索这个问题应遵循的原则
我以为要考察“牛郎织女”传说的形成。
(一)应突破忽视传说形成的时代,先考察“牵牛”、“织女”这两个人物的形成,再看几时形成它的基本情节。
(二)应从我国早期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去考虑,而不要只着眼于后代某些地方形成的传说,因为“牛郎织女”故事流传十分广泛,全国所有地方都有关于它的传说,而且故事中的情节,提到的事物,总是同当地的风俗相一致。这是民间文学的一般规律。
(三)关于其基本情节的形成应联系我国古代社会思想文化的发展历史,不能根据个别材料孤立地去下论断。
(四)应充分重视早期的文献、在文献的引述上尽可能作到去伪存真,也不能本未倒置,以产生迟的文献为依据而根据某些产生很迟的材料随意下结一论。
(五)充分重视时代很早的遗物遗迹与地下新出土的材料,包括文字材料和实物。
自然科学的研究有定义、定理、公理、公式,严格按照这些已经被证明了的定义、定理等进行推算、推理或实验鉴别,就难以出错。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也有一些被证明的真理、规律、原理,有一些被前代学者所证明是正确的基本做法。但有的人认为社会
科学是软的,由人说了算,人文学科更具主观性,完全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没有规律可言。这些看法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客观事实的唯心主义的思想。连人的心理活动也是有规律可以认识的,人对一个事物的看法会有差异,但总有共同性;个别人对某些事物的看法比较怪异,但大部分人的看法总是相近的。我们从事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研究,也应遵崇客观规律,尊重前人已确定并被证明为正确的研究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够得到正确的答案,即使得不到答案或明确最终的结果,也会靠近真理一步,而不至于言人人殊,永远争论不休。
我根据上面的原则,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研究、思考“牛郎织女”故事、人物、情节、主题等方面的问题,寻找形成牵牛织女是由秦人的始祖女修而来。
关于牵牛,上面提到的1990年刊出的两篇论文中认为是来自商先公王亥,因为《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据《世本·帝系篇》和《史记·殷本纪》此“胲”既“亥”之借,指殷先公王亥。《天问》中也说:“该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终弊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又云:“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王亥在殷先公王中显得很重要,祭祀特别隆重,后王有时向他求雨,求半年。《吕氏春秋·勿耕篇》说:“王冰作服牛,”“王冰”也为“王亥”之误。《山海经》中说:“王亥托于有易,何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郭璞注引《竹书纪年》:“殷王孩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这“王孩”也即王亥。《山海经》和《竹书纪年》中对王亥的事迹记述得更为详细。我当时确定牵牛是由殷先公王亥而来的原因有三:
(一)王亥是殷先公中十分重要的一位,有被殷人以象征性称谓命为星名的可能。“轩辕”(黄帝)、“柱”(神农之子)、“王良”、“造父”(皆秦人远祖)皆杰出的部族领袖,“奚仲”、“傅说”(上古的杰出人物)。王亥因服牛而出名。商人大约避伟直呼其名,而以“牵牛”命为星名。
(二)王亥服牛,是我国古代最早利用牛力的记载。《山海经》、《天问》为我国古代神话的渊薮,其中曲折地反映了我国上古以至远古的历史。《竹书纪年》、《世本》为记载先秦时历史的史书,皆从五帝开始,《吕氏春秋》也是吕不韦组织一些博学文人在各种先秦典籍的基础上编纂而成,而这五部书都记载了王亥的事迹,写到他服牛之事,可见其影响之大。
(三)殷人已敬奉王亥,视之为有神灵的人物,问他乞求丰年,长久流传中有可能转化为神话人物。
(四)司马迁在《史记·殷本纪》中说商祖契被封商,在《六国年表序》中又说:“或曰‘东方无所始生,西方物之成熟,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毫,周之王也,以丰镐伐殷秦之帝用雍州兴,汉之兴自蜀汉。”认为商祖契被封之地在西北。《史记集解》引郑玄说:“商国在太华之阳。”又引皇甫谧说:“今上洛商是也。”许慎《说文解字》中也说:“毫、京兆杜陵亭也。”《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商州东八十里商洛县,本商邑,古之商国帝喾之子(契)所封地。”上洛即今陕西省商县,本西周邑,战国时属魏、后属秦。这样,商人早期的关于牵牛的传说有可能同秦人关于织女的传说结合,而形成“牛郎织女”的传说。
在当时,我认为这个结论是比较可靠的。但后来觉得其中有两个疑问:
(一)从各方面看,商人早期是以畜牧业为主,并非农耕民族,这同后代牛郎(牵牛)的身份与形象特征不太符合。
(二)根据近年考古学上发现的文物分析,陕西商地区的西毫(或称杜毫)说已很少有人赞同,而大部分学者主张在冀南、豫北及豫东、鲁西地区。这样一来,同秦文化的融合就要迟于周代,而《诗经·小雅·大东》中牵牛、织女已本联系在一起说,尽管当时都只作为星名,但这两星都在天汉边上(天汉实由汉水而来),则牵牛的原型应产生于汉水流域或距汉水不远之处。
由于以上这两个原因,我放弃了牵牛来自商先公王亥之说,根据我国早期农业发展的状况及各部族对自己早期历史的重述,以及从氏族社会末期至商周时代各部族的分布,认为他应来自周先祖叔均。
四、叔均事迹与周人的发祥地
《山海经·海内经》中说:
后稷是播百谷。稷之孙日叔均,是始作牛耕。
《大荒西经》中又说:
有西周之国,姬姓,食谷。有人方耕,名日叔均。帝俊生后稷,稷降以百谷。稷之弟日台玺,生叔均。叔均是始代其父及稷播百谷,始作牛耕。
《史记·周本纪》云:“封弃于邰,号日后稷,别姓姬氏。”所谓“有西周之国”云云,是据周人后来所建国而言之。又《大荒北经》中述黄帝蚩尤之战中“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畜水。蚩尤请风伯雨师,纵大风雨。应龙乃下天女日魃,雨止,遂杀蚩尤。”其下云
魃不得复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后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为田祖。
看来叔均不仅发明了牛耕,而且曾组织人民抗旱,度过大旱。至于将叔均领导人民抵御旱灾变为向天帝请命的神话及将此事同黄帝蚩尤之战牵合一处,则是流传中形成,可以不论。《大荒西经》中说叔均为后稷的侄,《海内经》中言为“孙”。从其父称为“台玺”看以作弃之“孙”为是。因为古人之名一般为单字,应名为“玺”、“台”乃是地名,表示其与台地有关。“台”即“邰”。《史记索隐·周本纪》引毛苌说:“邰,姜螈之国也,后稷所生。”《诗·小雅·生民》“即有邰家室”句,《毛传》:“邰,姜螈之国也。”其地望《水经注·渭水注》云:“渭水又东迳县故城南,旧邰城也”。《括地志》云:“故城一名武功城,在雍州武功县西南二十二里,古邰国。”旧说据《生民》诗中“即有邰家室”一句以后稷被封于有邰。其实,此句意义应是指弃取母家氏族之女为妻室。此两千多年来之误解,今当加以更正。因为在今武功一带发现的文化遗址都大体在先周中晚期,当古公直父、季历及文王迁丰之际。则叔均可能是古公之前的氏族首领导。周人应当在豳地其间早在周人建国以前很久,称“邰”犹称周,因为玺也是周人中很著名的人物,故其前加“台”。“稷之弟日台玺”的稷应指弃的后代之袭稷之职者,《国语·周语上》“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旧注:“父子相继日世。”则任稷之官者非一人。这也同《史记·周本纪》所言“不窑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窑以失其官”的记载一致。
周人是农业民族。我们由《诗经·大雅·生民》可以知道,从后稷开始,已播种多种粮食作物,并选择良种(嘉种),除杂草,对作物的生长有细致的观察,讲究耕作技术(有相之道);但后稷之时耕作完全用人力,至叔均而发明了牛耕,大大节省了人力,提高了耕作速度与质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叔均最重要的事迹是发明了牛耕,所以在周人的远古传说中,他的事迹就同牛联系在一起。牛作为运输工具时是人赶着牛,作为交通工具时是人骑着牛,而用为耕作工具时是一人牵着牛,另有一人在
后面扶犁。牵牛而行于畎亩之中,是牛耕的象征,故周人以这位杰出的氏族首领为星名之时,名之为“牵牛”。
关于周早期活动地点的问题,专家们有过深入研究与探讨,提出过好几种说法。但根据近几十年考古发掘的情况看,旧说中有的说法显然缺乏证据,有的则有欠确切。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的形成》一书中加以全面总结,作了概括说明:
目前已知的先周文化遗址分布,主要在陕西中部泾渭流域一带,大致范围:北界达甘肃庆阳地区,南界在秦岭山脉北侧,西界在六盘山和陇山东侧,东界在子午岭西侧至泾河沿岸一线。
书中说就遗址分布密度言,明显成为三大群,一群在泾河上游与甘肃接壤的陕西长武县一带,时间最早;一群在岐山、扶风、武功一带,次之;一群在长安丰镐一带,时代最晚。这正与周人早期居豳、公宜父迁岐、文王都丰及武王都镐的文献记载相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还说:
长城遗址群中,碾子坡先周文化遗址的发
现,乃成为探索先周文化起源的突破口。书中还说:
自这一带逆泾河,再循支流马莲河而上
100多公里,为甘肃庆阳地区,传说周先公不宙“奔戎狄间”即在此。
这马莲河即《水经注·渭水注》中所说流经不窑城的马岭水,民俗以音称“马莲河”,今以俗称为正。据《中国古代文明与国家形成研究》一书所说,“文献所谓公刘迁豳,不是一个点,当为一个地域范围的‘面,所迁豳的最后定点,不是一代一次完成,其间当经几带周人在此‘面上的自北而南逐步迁徙与壮大。”这样一来看来,甘肃庆阳地区属于古代文献中所说的豳地的范围之中,是周人的发祥地和早期活动地区。
叔均大体相当于商代后期。因为《史记·周本纪》中说:
后稷卒,子不窗立。不窗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窗以失其官而罐戎狄之闲。不窗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
稷是夏商时代官名,也是夏商时代所奉农神之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载晋史官史墨云:“有烈山氏之子柱日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则“稷”非一人。被周人奉为始祖的后稷(“后”犹日“王”),自然是指《诗经·大雅·生民》一诗所写之弃,但其在夏代继任“稷”之职者,却不止一个。上古的职务多为世职。因为那时候的“官”实不主要在行政管理,而更重要在技能方面,土地、建筑、天文、农耕莫不如此,家传其业,世有能者。邰玺和叔均究竟为弃至不宙间的人,还是鞠以后的人,有待根据其他问题的解决作进一步研究。总之,他同甘肃庆阳地区至陕西武功这一片地方有关,后稷和叔均正是这片黄土地上发展起来的先进农耕文化的杰出代表人物。
五、叔均与牵牛(牛郎)的传说
古所谓“伯”、“仲”、“叔”、“季”表示在同胞兄弟姐妹中的排行,周人也是如此。如《史记·周本纪》:“古公有长子日太伯,次日虞仲。太姜生少,子季历。”(按:古公指公直父。司马迁误读了《诗·生民》中“古公室父”一句,“古”实犹言“昔”,表追述,司马迁误以“古公”为号)。太伯、虞仲、季历中的“伯”、“仲”、“季”即表排行。所以,我以为周先父中的“叔均”也应表排行。其非长子可知。因为非长子,继承酋邦首领地位的可能性就小(有兄终弟及的制度者,也有因长子死、病而由弟继父亲位置者,但也有直接由季子继承者,如季历;同时也有其他例外)。所以,叔均有可能是后稷弃至不窑之间的人物,也有可能是不窑之后已知周先公中某一位,但也有可能是不窑之后来未继承公位的人物。总之,他并非长子。这一点,同今日流传的各种《牛郎织女》传说中牛郎都有哥哥的情节相合。
钟敬文先生作于1932年的《中国的天鹅处女型故事》一文引述了赵景深、赵克章所记述的《牛郎》的内容:
据说,从前有弟兄两人,弟弟心肠忠厚,哥哥却很狡猾。弟弟因常赶牛的缘故,被人叫做牛郎。弟兄分家,弟弟只得了一辆破车和一只老牛。一天,老牛对主人说,某处河里,有许多仙女在洗澡。倘他能取得她们中间任何人的衣服,便可以得她做妻子。第二天,他跟了老牛出发,果然看见许多正在洗澡的仙女。他抱了一堆衣服上车(牛车)就走。结果便带回了一个仙女做妻室。她就是织女。织女和牛郎生下一对男女。一天,她用巧语骗得了自己以前被取去的衣服,便乘云而去。牛郎忙担了他的儿女,穿上牛衣(这是老牛死时所嘱咐的),急赶是去。谁晓得慌忙中少穿了一只牛腿,使他不能立即赶上织女。正在追逐的当儿,忽来了王母。她用金簪划成一道天河,把他们两人分开。牛郎托了燕子去说合,不意被误传了日期,所以后来永远只能一年一会。
钟敬文先生在概括叙述了其梗概之后说:“这个故事,没有记明所由采集的地域,但附注中有‘北人称妻室为媳妇的一句话,也许是我国北部的哪一省所流传的吧,虽然两记者都是西部四川地方的人。”根据钟先生对这个采集本中语言特征和作者籍贯的说明,这个故事采集于西北部的可能性为大。赵景深和赵克章记述的这个《牛郎》的故事,是现代民间文学工作者记述的最早的采录本。
钟先生的文章中还引述了洪振周记述的一篇流传在奉天的题为《牛郎》的故事,情节与上一篇差不多,说“有一个叫王小二的孩子,依着坏心肠的哥嫂过活,一天在牧场看牛,忽然黄牛对他说起话来,等等。牛是黄牛,其反映的故事自然也是以北方为背景。”
钟先生引述第三个故事是郑仕朝采集于浙江永嘉,说:“有个看牛的孩子叫牛郎,一天,他正要回家的时候,他的老黄牛,忽然向他说起话来。”情节大同小异。而牛是黄牛,也反映着这个故事较原始的情节要素特征。
这几个采录较早的本子,只有孙佳讯采录于江苏省灌云地方的《天河岸》,那帮助牛郎的牛是老水牛,可以看出这个故事在南方长久流传之后发生的变异。
可以看出,牵牛织女的传说最早产生于西北。这同叔均的传说,在《山海经》中只见于《海内经》和《大荒西经》、《大荒北经》是一致的,《大荒西经》中是在北部,《大荒北经》中是在其西部。总之是在西北。
当然,这些流传在南北不同地方的《牛郎》之类的故事,有一些共同点。比如都是说织女在河边洗澡时牛郎抱了衣服,使得织女不得不跟了他去,以后婚姻生活很美满。第一、三、四都是生了两个孩子(第一、四都明确说是一男一女)。这自然同天上的牵牛星由一大星和两小星组成有关(牵牛星是一大星在中间,两边各两小星,织女星也是一大星两小星,但两小星在其前面);故事中说牛朗带着两个孩子追到天上。第一、第三、第四个都是织女离去时牛郎听了老牛的话追去,而且是靠了牛皮的法力才得腾空而行;都是用金钗划出了一条天河,将他们隔开。唯第一、二为王母所划,第三、四为织女所划。看来,较原始的情节应是王母所划,流传到南方之后,才演变为由织女自己所划。
至于各种关于《牛郎织女》的故事采录本中,都有织女在河中洗澡的情节,以及都是有一条河将他们二人分开。这同织女星、牵牛星是在天河边上有关。七月中织女在河西,牵牛在河东。但银河古称汉、天汉、银汉,同地上的汉水有关,应没有问题。秦人发祥于今天礼县东部为中心的一大片地方,因而以其祖先织女之星在天汉边上,而此以东,便是陕西省的岐山、武功(先周时邰)和甘肃庆阳及陕西的长武、旬邑、彬县(先周时豳地)。则牵牛传说同甘肃庆阳有关,应无疑问。
更值得注意的是庆阳各县也有些关于《牛郎》一类的故事传说,还有不少同牛郎、牵牛有关的地名、祠庙,尤其是自古有着丰富的农耕习俗和牛文化。我国几千年经济的特征是以农业为主,而陇东的庆阳由于气候适宜,土壤肥沃,又便于挖窑居住,故农业发展最早。而在上古,牛耕的发明是农业发展历史上最重要的发明,至今大部分农民仍由之而获其利。
《牛郎织女》的传说是我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中孕育时间最长、流传最广泛的传说,其中有丰富的内涵、需要我们去发掘,而陇东的农耕文化、牛文化及其同牛郎传说的关系也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应者力于去掺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