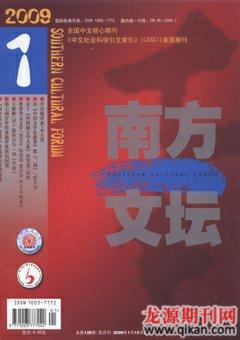有“大作品”无“大作家”的当代文学
从1978年到现在,“新时期文学”已经发展了三十年。对这三十年来的当代文学如何评价,已经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无论是认为现代文学三十年(1919—1949)的成就更为突出,还是强调当代文学早已超越了现代文学的辉煌,我认为都是一种将问题简化的判断。2008年4月,在上海作家协会召开的“新时期文学三十年”学术研讨会上,张清华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他认为“现代文学有伟大的作家,但几乎没有伟大的作品,而当代文学虽然几乎没有伟大的作家,但却几乎出现了伟大的作品”①。不管这一论断是否能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它都提出了一
个试图整体比较和评价中国新文学的命题,而这也是一个引人思考的和有意思的问题。
关于“伟大”文学的标准
有没有“伟大的作家”或者“伟大的作品”?争论的起点和焦点常常集中在对这两个基本概念的界定上,即什么样的作家、什么样的作品能够堪称“伟大”。它们的标准和尺度分别是什么,包含哪些要素。对于这两个概念,虽然古今中外的大师、名家都根据自己的理解有所阐述,但从实际情形看,它们要么过于笼统,有些大而空泛,如哈金所定义的“伟大的中国小说”②,要么虽然深刻、独具见地,但却只是冰山的一角,如米兰·昆德拉所认为的“小说的精神是复杂性”③。而那种将所有的真知灼见和标准汇总起来的对“杰作”和“大师”的定义,已经类似于文学判断上的操作指南。也就是说,只有具备了一二三四,甲乙丙丁俱全,才能确定作家和作品的质量。这种技术层面的操作,看似科学严谨,实则机械。文学分析和判断,当然要依靠逻辑和理性,那是最基本的思路。但是一部作品首先击中人们的,一定是心灵和情感,然后才是沉浸其中的思想。如果人们为了使头脑更加明晰和深刻,肯定不会首先选择小说。说这番话的意思是,文学(无论是作家还是作品)有它的特性,在借助典律、法则来进行判断时,不妨也相信一下我们的眼睛、心灵和直觉。就如同打量一匹马,你只要看到了它的奔跑,就能大致知道它是一匹什么样的马,而不需要去仔细检查一下它的牙口和腿脚,然后做一份鉴定报告。
研究者已经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伟大的小说”和“伟大的作家”的界定和争论上,各执一词者都认为自己在坚持真理,在捍卫文学的纯正和高贵。而大多数的情形是,判断一部作品的好坏,需要的往往是一些常识,这些常识几乎是不言而喻的,从而成为一种判断上的本能反应。一部作品的优劣,肯定不是通过别人的提示和解释而
确认的,一定是阅读本身告诉我们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伟大的小说”,可以认为是文学史上的“经典”,如《古船》、《九月寓言》、《红高粱》、《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或者是备受争议的《废都》;也可以认为是大众喜爱、畅销不衰的《平凡的世界》。文学判断绝对不会有一个符合所有人愿望的统一标准,为什么要明晰出一个确定的名单呢?我相信对于某一些作品,大多数人认同它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之作。这个大多数不仅是指专业的文学研究者,也应该包括普通读者在内。这些作品在人类精神领域探索的广度和高度,以及小说的形式之美,是令人难忘的,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与现代文学完全不同的审美经验和感受。
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存在着某些共性的,它们在理论上的意义同时吻合人们的心灵感受。它们体现出的共性在哪里?王国维论词,认为“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的生命,是真切自然。他眼中的“大家之作”,具有“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特点。其中,“真”是基础,它不仅是指反映生活时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也指“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④;“深”是思想认识,面对事物的理解之深,必然会引出境界的广博和苍茫。只有体会到了“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况味,才会“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由“真”而“深”而“广”,这应该是“伟大的小说”的基本特点。当代文学三十年中有没有这样的作品?根据我们的阅读体会,这样的作品肯定是存在的。
为什么会有“伟大的作品”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从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谈起。当代文学三十年有没有“伟大的作家”?人们对此持保留的态度可能更多一些。王晓明在评价资深女作家王安忆时,也只肯小心地说:“她真有一点大作家的气象了。”⑤也只是“气象”而已。人们对当代的知名作家,始终不肯轻易地冠之以“大师”的称谓,这不是出于文学评价上的贵古贱今,而是当代作家确实存在着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
同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相比,当代作家在文化修养、天分和精神世界的含量上,显然不能与之同日而语。且不论徐志摩、闻一多、冯至等人深厚的西学功底,就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来说,当代作家中能否找出一人堪与茅盾、郁达夫、冰心等相提并论。而现代作家中的很多人又是学贯中西的,更有一批人集翻译家、编辑、作家的身份于一体,在文化的多个领域游刃有余、各有建树。今天的人们看到现代作家的肖像,能确切地体会到“腹有诗书气自华”的准确性。当代的大多数作家,则“术业有专攻”,是“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阿Q,论起城里乡下可以各有嘲笑,一旦握住毛笔便画不成一个圆,“一抖一抖的”“画成瓜子模样了”。除了文化修养上的不足,当代作家中具有大天分的并不多。沈从文所受教育有限,萧红的文字在勃勃生气中难掩其粗粝,但他们的天赋却无可比拟。同样成长于东北,萧红透视问题的深刻,其价值大于迟子建对人与自然的温情。善良与温情可能是一种精神气质,但观察和体会的深刻却是一种本领。最后一比,关于作家的精神世界,2005年4月,王蒙在中山大学演讲时,在回答记者的提问“中国作家为什么不够伟大”,他调侃道“是因为自杀的人太少了”。老舍算是自杀的当代作家,但他心灵世界的淳厚质朴,处世的热忱认真,都与现代作家更近。在当代作品中,我们很少能看到像《骆驼祥子》、《月牙儿》、《四世同堂》那样对人的处境的深刻理解与同情。老舍先生善良的天性与悲悯的情怀,甚至形成了他作品中特殊的气质与感染力。同样,如果没有曹禺先生对蘩漪深刻的同情,便不会有压抑与爆发的《雷雨》;如果没有巴金先生对“大哥”和“鸣凤”的泪水,就不会有沉重悲愤的《家》。相比之下,当代作家似乎更多理性。除了张炜、张承志等作家容易在作品中热血沸腾之外,大部分作家的神经像钢铁一样坚强。他们中的一些也许并不缺乏悲悯,但却往往表现得稳重而得体。一个奇怪的现象是,现代作家几乎不怕在作品中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脆弱或极端的天性,但当代作家的倾向却是将忧愤以人性的坚韧和高贵表现出来,成熟得体往往是以世故为代价的。
面对当代作家的种种不足,为什么当代文学三十年仍然出现了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佳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当代文学的资源问题。“文革”结束后,“解放思想”成为一个重要口号,但真正有解放思想的社会空气,要从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于当代历史的反思,对于中国社会的再认识,成为知识分子不倦的话题。可以说,当代历史的复杂与沉重,造就了当代文学的深厚与广博。《芙蓉镇》、《古船》、《受活》,甚至是像《灵旗》、《人面桃花》这样以现代革命史为背景的小说,也离不开当代目光对“革命历史”的再认识。对于一个世纪以来的历史生活,当代的大多数作家都是以批判的目光来再现与感受的。不管当代作家们是有意而为还是无意识地呈现,这都是一种充满了意识形态意味的写作。现代作家们虽然也同样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封建帝制崩溃,资本主义民主初步确立。但从历史经验来看,封建主义同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似乎远远没有“新民主主义”时期“民主与专制”之间的矛盾来得激烈。后一时期历史生活的残酷性堪比中世纪,而它的复杂性则在具有现代意味的同时,也引起人们更多的反思。在现代作家那里,对人的处境的思考,其实超过了对社会问题的解剖。深刻如鲁迅,他也只表现“皇帝坐了龙庭了”普通人的惊慌和复归于平静,也只表现病人对于“人血馒头”的渴望,而并不给中国革命或民生问题开“药”。萧红也只表现中国人的“生死场”,说出“我恨日本人,更恨中国人”的大实话,但她也并不分析中国社会的来龙去脉,她呈现的是花开花谢的人生景观。而当代作家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是超过了对“人”的。个人的命运总是和历史联结在一起,坚韧如《活着》、超逸如《长恨歌》,它们都是在历史的潮汐中,描述个人的浮沉,中国独特而复杂的历史生活是这些小说广阔的舞台。这种丰富性,正如余华所说:“一个西方人活四百年才能经历这样两个天壤之别的时代,一个中国人只需四十年就经历了。四百年间的动荡万变浓缩在了四十年之中,这是弥足珍贵的经历。”⑥ 这种历史生活的丰富性,成就了三十年来当代小说的基础和表现空间。而其中具有或者抛开意识形态色彩的历史呈现,都使小说具有厚重扎实的思想含量。现代作家中的大多数似乎更倚靠作家自身的感知,他们的表达和发现也更感觉化和个人化。这是当代小说与现代小说之间的明显不同,也是当代写作在资源上的优势。也可以这样说,当代小说更能以材料取胜,而材料本身所具有的思辨性质为作品的思想内容提供了复杂性。
当代文学的另一个优势,是它用西方现代哲学丰富了自己看问题的方法和角度。同时,它对外国文学艺术中的理念和表现技巧进行了借鉴。本土资源和民间经验当然是巨大的财富,但如果没有对西方现代哲学的吸收,当代文学的内涵会单薄许多。残雪、余华、格非至少他们早期相当一部分作品的意义,是借助于小说形式对某些哲学理念的演绎。当余华、格非将这些哲学理解同本土经验相结合的时候,才有了产生伟大作品的可能。鲁迅是个伟大的作家的前提,在于他首先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也受外来哲学的影响,比如早期的“进化论”,但是他能以深刻的洞察力逐渐形成自己对人和世界的理解,形成自己复杂、矛盾的世界观。他的目光是辩证的、怀疑的,他无所依傍,卓尔不群。在当代那些重要的作家中,我们还看不到一位是在对外来经验毫无依仗的情形下,逐步确立了自己的哲学的。当代作家的作品内涵,也因此更多人类哲学的普遍性,而少个人感受和思考的独特性。如格非的《人面桃花》将个人命运和中国历史表现得阔大、细致而优美,但在对革命、历史和乌托邦叙事中,我们仍能找到它们各自的哲学老家。同时,对于外国文学技巧的借鉴,也因为“有意味的形式”,而丰富了作品的内涵。《白鹿原》壮阔丰厚、含蓄从容,与魔幻现实主义在作品中的自在运用有直接的联系(魔幻现实主义似乎也特别适合表现古老土地上的沧桑动荡与文化的神秘)。对外来文化成果的吸收,有助于当代文学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在思想性上深厚而强大,其中的一些理念无疑是人类精神探索的精华。它们的质量直接影响了这些作品的质量。在自然科学领域中牛顿的名言:“我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的”,对于认识当代文学的成就,同样适用。但是这种登高而远,无损于当代文学的价值。只要是它融入了血液中的,我们就可以认为是与它自身一体的。它的成就一定是作为整体来完全体现出的,而不是从一个相对的高度。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点,当代作家在文化修养上可能整体落后于现代作家,但他们凭借写作资源的优势,也可以创造自己的辉煌。一个世纪以来历史经验的独特性,以及对现代人类文明的吸纳,都足以形成当代文学在内容上的磅礴与深度,在形式上的别致和圆熟。
我们并不缺少文学事实,而是缺少面对现实的客观和直陈它的勇气。正像张清华所指出的那样:“我总是担心,我们对最近三十年文学的评价过低了。但当代的批评家不敢,也没有勇气说最近十年,或者至少从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新世纪初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是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是汉语新文学诞生以后的最辉煌时代。”⑦
大师的距离
当代文学并不缺乏思想与才情兼备的作家,他们中的一些人不仅禀赋出众,而且勤勉过人,是严肃而认真的作家,但人们在承认他们的艺术成就、尊重他们的努力的同时,也很少能认为其中有大师存在。在对当代作家的认识上,汉学家顾彬对王安忆的评价可能具有代表性,“她是个好作家没有问题,但她是不是一个大作家就很难说”⑧,这与王晓明的观点不谋而合。
究竟什么是“大作家”,或者更甚一步“伟大的作家”?他们的标准和尺度是什么。这些问题同鉴定什么是“伟大的作品”一样足以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关于当代写作出现的问题,也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进行过分析和陈述,这些观点不可谓不精辟,但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所考察的对象往往是笼统而宽泛的。当代作家是一个很大的概念,从不同的目的地出发,是可以兵分几路的,诸如为市场写作、为奖项写作,包括严肃作家的职业化写作。这些虽然人数众多,但他们肯定不能代表当代文学真正的力量,若干年后留下的,也一定不是他们。当顾彬指责马原“他为什么不在上午写他真正要写的作品,下午和晚上写剧本”⑨ 的时候,正在写电视剧的马原其实已经不能算作当代写作之列了。只有在那些已经写下了重要的作品、同时值得人们期待的作家身上,他们所呈现的问题和局限,才是最值得人们关注的。这些问题也才是当代文学的瓶颈所在。
离“大师”最近的称谓是“大家”,在能被人们尊之为“大家”的有限的人当中,贾平凹大概要算一个。他在传统文化领域兴趣广泛,修养较深,他的作品不仅内蕴沉厚,耐得住时间的打磨,而且他勤于琢磨,有一套自己的世界观与小说艺术观。从各方面来看,他都是最具有大师潜力与气度的。但是,他的创作又显然是有问题的。贾平凹身上的一个突出特点是,他在如何使小说这活儿做得漂亮上,下了比别人更多的工夫。他的颖悟使他比大多数作家更早也更深地参透了艺术的奥妙和规律。往往在别的作家所忽略的地方,他品出了价值;别人不屑一顾的,他视若珍宝。但在这位灵慧过人的作家那里,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贾平凹的创作美学是“实用”多于“无用”的。
文学艺术除了陶冶性情之外,其实是最“无用”的,即便是面对“无限江山,流水落花春去也”,也只能慨叹一声:“天上人间!”但这就是绝唱。凡是以“隔江犹唱后庭花”来影射“亡国恨”的,凡是用字、韵律、布局重于直抒胸臆的,都不可能成为上乘之作。对于艺术创作而言,“抱负”和“技巧”只能是第二位的,作家个人的灵魂永远第一,而灵魂常常是无用的。
贾平凹在文学上的“实用主义”体现为两点,其一是创作动机,其二是表现技巧,而这两点是前因后果的关系。归结为一点,就是“为什么写作”的问题。人们毫不怀疑,贾平凹视文学为生命,写作对他而言就是日常的思考和说话,是存在的最根本意义。但贾平凹绝不是一个书生式的作家。他有俯仰宇宙之心,吞吐天地之志。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着大追求、大抱负的作家。这直接影响到他对写作的认识。他认为当代的文学创作“在境界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的东西,在行文表现上一定要有中国的做派”,“现代意识可以说是人类意识,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思考什么,你得追寻那个东西”⑩。
关于“西方的东西”和“中国做派”,其实不仅仅是内涵和风格技巧的写作问题,它还是作品的阅读接受和影响问题,也就是作品怎样尽可能地被最广大的人群所接受。而关于作品的焦点和思想性,贾平凹关心的是“地球上大多数人在想什么,思考什么”。且不论“大多数人在想什么”的“人类意识”是否就是“现代意识”,只就一个作家而言,如果他不能听凭自己内心的召唤,去探究那些痛苦的、难解的、像梦魇一样纠缠着自己的问题,而去捕捉“大多数人在想什么”,那他只能是被自己的聪明误到了家,他充其量只能是一个投机的、附庸的作家。这样的评价对贾平凹并不过分。他写作《秦腔》时,旨在为日益凋敝的故乡“树一块碑子”,他用近乎原生态的描写呈现了日益衰败的乡村。但他宏大的文学意图显然超过了他的文学准备,他面对现状,“不知道是该赞颂还是该诅咒”,只能说一句“我不知道”(11)。虽然事实有时可能比看法重要,有时事实本身就是一种看法,但客观的目光同审视的目光之间,终究是能显出高低的。“宏大叙事”的愿望、“树一块碑子”的理想,使沉淀于思考根本就没有足够的时间和心态。
当人们惊讶于贾平凹写了一部以农民工进城为素材的《高兴》时,作者这样解释他的初衷:“在这个年代的写作普遍缺乏大精神和大技巧,文学作品不可能经典。那么,就不妨把自己的作品写成一份份社会记录留给历史”(12),为此,作家几番去捡破烂的人群中体验生活,收集素材。这种敬业精神当然值得赞叹。但作家是否本末倒置了。书写历史记录是否是作家该干的活儿?我们也无法想象,一个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作家忽然去体验生活,以便能使他笔下的生活像真的一样。
《秦腔》和《高兴》的写作反映出来的是同一个问题,它们都是作者用心打造出来的“史”,是作者立意要为故乡树起的一块“碑子”。这块“碑子”不仅记录了农民进城以及进城之后怎样,也是贾平凹在文学史上以作品的形式所能留下来的,它有太多“工作”、“使命”、“业绩”的涵义。所以,它是“作文”。我们不否认作者在这两部作品中所付出的气力,所投入的思考和感受,但它们是“气力”和“构造”大于“心灵”的。无论是文学事业的需要,还是社会的需要,都不能成为文学的需要。唯一能成为写作的理由的,只能是“我”的“心灵”的需要。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会有这样一个认识:在那些大家身上所反映出的缺陷,正是作家普遍状况更深层的反映。贾平凹在文学事业上的进取心、希望最大限度地被社会承认的心理,在一般作家那里只是表现为更世俗的市场意识和功利性。二者虽然有境界的大小和高低之分,但都可归于迎合的、有意而为的写作。
当代文学的其他问题,也能从别的优秀作家那里体现出来。比如,作品思想性的薄弱,这是以深刻著称的余华也无法避免的。余华被认为是“同时代作家中写作字数最少的作家之一,但他也是废品最少、被研究得最充分的作家之一”(13)。余华不仅以他的聪慧和颖悟,解决了中国当代小说的形式问题,《活着》、《许三观卖血记》自然、优美、精巧,它们将先锋的精神与赏心悦目的形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同时它们的内容和气质又是中国式的,这是当代文学最重要的成就之一。不仅如此,余华超出了众多作家的地方,在于他能在纷纭的世相当中一眼看到本质,也就是直接指向事物中心的能力。他所揭示的真相和事物的实质,他的准确、透彻和力度,常常是令人震惊的。如果说,贾平凹这样的作家能够代表当代文学的宽广和复杂,那么,像余华这样的作家则代表了当代文学的深度和高度。
余华具有透视事物本质的才能,他对自己的认识非常自信,表达得有力而强劲。但与此同时,他放弃了对事物复杂性的认知。余华迄今为止的所有作品,都传递出这样一种信息:他见识过人,但毫无困惑。他能够深刻地理解他看到的一切,没有什么能够纠缠着他,使他寝食难安。比如,余华的大多数作品都反映了人类巨大的灾难、人性的丑恶和存在的残酷,但是这一切都是可以化解的。面对灾难和不幸时,福贵用的是坚忍,许三观用的是苦中作乐,而到了《兄弟》则是煞有介事中的嘲讽,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消解的。这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姿态和方式。世界真的是这样纯粹而绝对的吗?人们有必要想起福克纳的提醒,他说:“当今从事文学的男女青年已把人类内心冲突的问题遗忘了。然而,惟有这颗自我挣扎和内在冲突的心,才能产生杰出的作品,才值得为之痛苦和触动。”(14)如何使作品的思想性更深刻,使作品的精神境界更博大,这是当代作家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而在基本的写作技巧上,当代小说也不是没有问题。从1985年的“方法”热开始,经过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等等写作训练,当代作家的艺术表达已经颇为娴熟精到了,但写作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又以其他形式表现出来。以深孚众望的作家王安忆为例,她对写作的认识无疑是独特的。她致力于发现日常生活的审美性质,在由物质世界构建“心灵世界”的过程中,她极其重视其中的合理性,每一步都是通往最后景观的台阶,绝不跳跃和含混。当余华谈到尤瑟纳尔小说中的一个细节:被斩首的人复活了,他的脖子上仿佛围了一条奇怪的红围巾。余华对此非常赞赏,认为它显示了一个作家出色的把握细节的能力。但王安忆却提出疑问,认为“有点太写实了,我觉得必须在真实的材料和变形之间找一个衔接”(15)。这种对于自我写作理念的执著,已经近乎机械和固执。
正是这些,限制了当代作家的发展,虽然他们曾经产生过伟大的作品。他们完全有可能做得更好。■
【注释】
①⑦ 傅小平:《当代文学:有大作无大师?》,载《文学报》2008年4月24日。
② 哈金这样定义“伟大的中国小说”:“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从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见徐江:《我们需不需要“伟大的中国小说”?》,载《北京日报》2005年7月5日)这个定义稳妥而全面,但那只可能是一种想象中的完美。
③ 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4页,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④ 王国维:《人间词话》,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
⑤ 王晓明:《从淮海路到梅家桥——从王安忆小说创作的转变谈起》,载《文学评论》2002年第3期。
⑥ 余华:《活着·后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⑧⑨ 顾彬、何映宇:《我和中国作家无话可说》,载《文学报》2008年3月6日。
⑩ 贾平凹、黄平:《贾平凹与新时期文学三十年》,载《南方文坛》2007年第6期。
(11)贾平凹:《故乡啊,从此失去记忆——〈秦腔〉后记》,载《收获》2005年第2期。
(12)贾平凹:《我和刘高兴》,载《当代》2005年第6期。
(13)谢有顺:《余华的生存哲学及其待解的问题》,见《先锋就是自由》,171页,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14) 《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374页,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15)余华:《文学不是空中楼阁——在复旦大学的演讲》,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2期。
(张晓峰,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