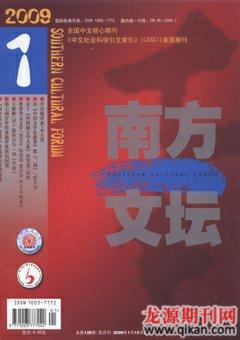钱谷融“学术回应模式”解码
夏 伟
钱谷融高寿,与五四同龄(1919— ),在学界享誉甚隆,甚久。海内外专家至今谈及这位文学长老,仍不忘赞叹他在半世纪前写的那些惊动历史的文章:《论“文学是人学”》和《〈雷雨〉人物谈》。那时,钱谷融正当才子盛年,1956年始撰《论“文学是人学”》时三十七岁,1962年首刊《〈雷雨〉人物谈》时四十三岁,很快便达到其学术生涯的巅峰状态。
诚然,若稍知“文革”前十七年(1949—1966)的大陆气候,你或许会庆幸钱谷融恰巧撞上了两个难得的时代节点——这就是颁布“双百方针”的1956年,与“七千人大会”前后出现的“小阳春”1962年——这才使作者能在公开表白自己对文艺的真诚见解的同时,流露其醇厚的人道情怀。这儿用“撞上”一词,是为了呈示历史的偶然性。这就是说,假如国史不给出“1956”和“1962”这对时代节点,很可能,钱谷融也就不愿动笔述学或不便公布天下,于是也就成不了学术史上的“钱谷融”。但历史又有必然性:钱谷融的文字及其名字所以早早进入学术史,是因为他本就才情兼具,学思兼至;不仅如此,根子或许还在于他的心灵特质——正是这种可称之为“学术回应模式”的心灵特质,才是激励作者凝聚其才情、学思来介入历史的内驱力。千万不要忘记:在“1956”与“1962”之间,还夹着一个难熬的“1957”呢。这似可用来解释:同样面对“1956”和“1962”,为何当年另些地位更高、名声更大的文学教授,却未能持续写出钱谷融那样的力作,反倒让华东师大的这位中年讲师独领风骚呢?①
这段史实给人如下启示,即大凡读文学史,至少有两种读法:一曰“文献学”读法,旨在弄懂某家、某成果为学术史提供了什么;二曰“发生学”读法,随即追问某家为何能为学术史提供先哲或时贤不曾提供的创见,亦即探询这一学术创新赖以发生的心理动机何在。前者是回答对象“是什么”,后者须追究对象“为什么”。或曰,前者可满足于“知其然”,后者更注重“知其所以然”。这段话其实已表露笔者的意图:本文所以要从“发生学”角度来解读《〈雷雨〉人物谈》,重点是想弄懂当年驱使钱谷融撰写此稿的心灵动机,即其“学术回应模式”到底为何物?为何其《论“文学是人学”》明明已在“1957”涉险,五年后他仍于心不甘?进而论述这一“学术回应模式”在其写作心境是如何运行的?而笔者更大的心愿当是“窥一斑而见全豹”,想通过实证型个案解码来表明,在学术史研究领域,从“发生学”角度去深究学人是怎么创造历史的,或许要比从“文献学”角度去浏览学术史是什么,更发人深省。
一
鉴于本文的路径,是凭借对《〈雷雨〉人物谈》的发生学解读,以期析出作者的“学术回应模式”,故暂且不说该模式赖以构成的诸心理元素及其交互关系,而先着眼于钱谷融对剧本《雷雨》的那份近乎亲缘的向心力。
在中国当代学者中,钱谷融似乎是一个更愿意沉浸于私人阅读的隐逸者,以至于惹人质疑其成果的数量与“大学者”的名号不尽相符。钱老知道这点,曾不止一次地坦诚自己“太懒”,言语中颇多自责。对于这“懒”,当然也有另种解释:只有那些真正激荡过钱谷融内心的作品,才拥有让他不得不动笔的力量。《雷雨》无疑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它抓住了钱谷融的心,他才会“情不自禁地要深入下去,把自己的感受写出来”②。但让人回味的是,《雷雨》作为曹禺的处女作暨中国现代话剧奠基作,早在1930年代、钱谷融少年时便轰动文坛,为何事隔三十载,中年钱谷融依然对其情有独钟呢?用“情有独钟”来描述钱谷融对《雷雨》的倾心并不夸张,因为是《雷雨》才使疏于纸笔的他再度勤奋(首度勤奋是写《论“文学是人学”》),且一发难收,在1962年便接踵刊发三篇“人物谈”(依次为“谈周朴园”、“谈蘩漪”、“谈周冲”)。且不说为一部戏剧的每个角色立章评析③,此类文体在百年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是否首创,单就钱谷融的学术生涯而言,肯定是唯一。
于是,问题就来了:钱谷融为何对《雷雨》如此青睐?或倒过来,《雷雨》是靠什么打动了钱谷融的心?
我想从蘩漪谈起。钱谷融曾坦陈:“我是对她有所偏爱的”④,这“‘偏爱包括对她的同情,自然也倾注了自己的某种切身感受”⑤。请关注“切身感受”这四个字。这是否表明,蘩漪在剧本中的角色境遇及其命运,的确触动了钱谷融心中颇为柔软的那部分,所以他才会对蘩漪产生共鸣?但疑问犹在:钱谷融究竟在哪一点上与蘩漪特别有共鸣呢?
是孤独感吗?
钱谷融曾在读大学时如此抒怀:“我的孤独和寂寞,实在是出奇的,你很难在任何一个群众场合发现我,我常是独处而无伴的。而那难耐的寂寞,则不时戳刺着我寒冷的心房,几乎使我时时要为痛极而放声号哭。”⑥ 相比之下,他眼中的蘩漪则寂寞得近乎绝望:“就是这样一个女人,落进了周朴园的魔掌,把她软禁在这个仿佛是与世隔绝的周公馆里,已经一十八年了。寂寞枯淡的生活,沉重窒息的空气,把她闷得气都透不过来,本来她已经不存什么希望,只安安静静地等待死亡的到来了。”⑦
蘩漪的孤独当令人同情,但读过《雷雨》原著的人明白,曹禺笔下寂寞的人物远不止她一个:周朴园表面威风霸道,内心却怀念侍萍,与儿子相处亦颇隔膜,他也孤独;周冲活在梦幻里,又单恋四凤,同样孤独;侍萍嫁给了并不相爱的男人,与女儿分居二处,对周朴园更是爱恨交加,很孤独;即便是鲁贵,在嬉皮笑脸卑躬屈膝的背后,忍受着儿女的白眼,肯定也不免孤独。既然如此,钱谷融又为何对蘩漪特别怜惜呢?
诚然,蘩漪绝不仅仅“有孤独感”而已,她的孤独,是属于最珍贵的心爱被剥夺后所体验到的那种极度空虚和绝望。
周朴园再“孤家寡人”,事业上总还“一帆风顺”;周冲虽单相思,但仍不乏梦想的慰藉;对侍萍来说,女儿若能活得幸福,将是最大的满足。他们都还有生的目标和希望,蘩漪的境遇则不一样。
蘩漪作为角色,曾是有钱人家的小姐,有着“对诗文的爱好”⑧,这样的女子,往往最期待爱情,而她的这份期待显然没有在周朴园身上得到兑现;此外,蘩漪虽已为人母,儿子也近成年,但外表看上去还是颇年轻。女人到三四十岁,这又是个亟须性爱的季节,恰恰在这方面,周朴园似难以胜任,以至于在逼蘩漪吃药时被反戈一击:“你忘了你自己是怎样一个人啦!”⑨ 总之,对蘩漪最重要的两样东西——爱情和拥抱,她都没有得到。
如果是活在当下,蘩漪或许不必那么痛苦,但《雷雨》所设定的戏剧情境,是一个阴晦的、死气沉沉的、等级森严的旧式家庭,对如此家境中的妻子而言,丈夫是“天”,是一切,相处好了,会是唯一的朋友和伴侣;相处不好,那就成为永远都逃不脱的铁笼子,因为女人一旦出嫁,就很难有二次选择的权利。所以,并不相爱的丈夫就像厚重的乌云,始终笼罩着蘩漪,郁闷,痛苦,找不到出路,一旦连希望都变得渺茫,孤独和痛苦就会被无限放大。这种压抑得令人窒息的戏剧氛围,在舞台上就被物化成一间蘩漪的小阁楼,阴暗、逼仄。
爱是女人的宗教,是其生命中的重中之重。假如说,蘩漪之孤独,是缘自其爱在大屋檐下枯萎;那么,对学者钱谷融来说,是何种揪心失落,会诱发他返身体认蘩漪式的孤独呢?
青年钱谷融常常“因为找不到一个可与对谈的人”⑩、一个像他那样痴迷美与艺术的人而唉声叹气。近似洁癖的爱好让钱谷融难觅朋友,别人聚在一起“热烈地谈论着政治、经济以及各种社会问题”(11),他却“对此毫无认识”(12),只愿独自背诵“‘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骑马倚斜桥,满楼红袖招之类的美丽的诗句”(13)。他有很多话想说,却很难找到倾听者,只能埋在心里,间或泻于笔尖,“像一只受伤的小鸟”(14) 般“抚摸着自己”(15)。可以说,钱谷融早在读大学时便初尝了孤独的味道。
毕业后,钱谷融任职交通大学文科教员不久,已是1949年了。应该说,他已经如愿接近文学圈,但他在圈子里依旧找不到归宿感。问题是出在艺术观念大相径庭。在钱谷融看来,艺术首先应该是美的:一切艺术品都是“艺术家心中的意向”,“造成这意向的……是艺术家心灵的美”(16),而在当时主流语境,唯一拥有话语权的文学研究方法是阶级分析法。所谓“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然一旦落实到具体作品评判,则往往“政治标准第一”也就转为“政治标准唯一”了。在“你死我活”的阶级论的刚性框架,当然容不下风花雪月,也没有嬉笑怒骂,甚至连“人性”一词也不宜说,谁说“人性”,谁就是“资产阶级人性论”者,那就近乎有政治嫌疑。事实上,自1949—1956年(“美学大讨论”前),大陆学界也很少人探讨钱谷融所神往的“美”。
钱谷融爱文艺,首先爱的是文艺之美,但他一旦开口谈文艺,却又不得不遵循阶级分析法,而阶级分析法又恰恰是忽略美、压抑美的。可以说,当时语境对钱谷融追求美、谈论美的权利的无形剥夺,就好像蘩漪被剥夺了爱情一样(17)。
找不到归宿的钱谷融于是就在孤单中沉默。自1945—1956年“双百方针”颁布前,整整十二载春秋,他几乎没写过一篇论文,直到1957年早春二月,《论“文学是人学”》问世。关于此文的诞生,钱谷融说:“现在回想起来,如果不是在那时刚宣布不久的‘双百方针的精神的鼓舞下,如果没有当时那种活泼的学术空气的推动,单凭一般的号召和动员,我也不一定会写……”(18)我愿意相信,钱谷融在动笔前曾犹豫过,这犹豫或许出于政治顾虑,也可能仅仅源自惰性,但他一落笔,就写了三万五千字。
三万五千字,对于勤奋者尚不算小数目,对于整整十二年疏离纸墨的钱谷融来说,更难能珍贵。何况这三万五千字,决不是扭扭捏捏的三万五千字,而是犹如洪水破堤、飞流直下的三万五千字!可以想象,此文在被钱谷融泼墨纸帛之前早已成竹在胸了。或许在那漫漫十二年间,在每一个辗转反侧的不眠之夜,此文的运思已断断续续地像渗透岩隙的幽泉,不绝如缕,点点滴滴串成涓流,汇成碧潭,有朝一日,终于迎来沉默后的爆发。
颇为相似的是,当蘩漪被寂寞逼迫得透不过气的时候,也曾望见过希望的火光,那是周萍给她的爱情。面对这份感情,蘩漪或许也犹豫过,但当周萍声称痛恨父亲周朴园,愿他死,为了她,就是犯乱伦的罪他也干时,女人被爱情俘获了。可是转眼间,周萍抛弃了她,还骂她是“想不到的一个怪物”、“一个疯子”(19) ……蘩漪在《雷雨》中所经历的、有如从天堂跌落地狱的那种角色绝境,又委实像极了钱谷融的“1957”:《论“文学是人学”》发表不久就遭遇全国“大批判”,连他器重的学生也恶语相向……周萍的绝情遗弃,当是蘩漪拼死也挣不脱的梦魇,“1957”对钱谷融来说,又何尝不是让他痛苦到“难以想象”的梦魇呢。
这叫“因痴而辱”。这儿有两个关键词:“痴”和“辱”。“痴”作为心理状态,是指人对目标的精神投注乃至身心执着已臻极限,近乎入魔;“辱”则指人因无端承受外力欺凌而积郁的道德痛感。正是这点,我愿推测,“1957”烙在钱谷融心头的那道“因痴而辱”的记忆,或许会让他将自己视作活在《雷雨》剧外的另个“蘩漪”。虽然她是为爱而“痴”而“辱”,而他是为“人道—艺术理念”而“痴”而“辱”,但将两者置于体验形态类型水平而论,则彼此调性相近,“同病相怜”,不足为怪。记得福楼拜当年写完《包法利夫人》时曾说“爱玛就是我”。理由同一。
二
我承认,“因痴而辱”是可能呈示作者写《〈雷雨〉人物谈》的动机之一,也是钱谷融“学术回应模式”赖以构成的第一心理环节,但这是必要条件,远非充分条件。事实上,他与蘩漪的“同病相怜”,只能使他在面对《雷雨》诸角色时,更偏心蘩漪一些,但这点还不足以让他非写“人物谈”不可。再说得透彻些,在1957年后,蘩漪所以吸引钱谷融的更大原因,恐怕不在“同病相怜”,而在于蘩漪的“雷雨”性格。
曹禺曾说,原想在剧中加一个名为“雷雨”的好汉,但最终没能实现。钱谷融对此颇有己见,认为他“还是写进去了。那个人就是蘩漪。在《雷雨》初版本的序言中,曹禺曾说蘩漪是一个最‘雷雨的性格。其实,照我看来,蘩漪不但有‘雷雨的性格,她本人简直就是‘雷雨的化身。”(20)
曹禺和钱谷融都认同蘩漪是“雷雨”的化身,那么,“雷雨”这个意象究竟在隐喻什么?
《雷雨》的剧情安排在夏天,曹禺说那“是烦躁多事的季节”(21),而雷雨更会渲染这躁动不安:即使乌云暂未压城,但皮肤已能感受低气压的不适了,随着云层越聚越厚,气压越来越低,呼吸也会愈发吃力。雷雨在大气中的酝酿过程,也是人的烦躁不断郁积、耐性不断耗散的过程。这是蘩漪追求爱情反受侮辱的过程,也恰是钱谷融寻找知音却成为众矢之的的过程。更要命的是,一个普通人,若置身于这无助的困境,除了隐忍,几乎别无他法。
蘩漪却不愿忍气吞声一辈子,她将自己化作了“雷雨”。雷雨很痛快,磅礴而落,酣畅淋漓,能把所有烦闷都冲刷干净;但雷雨本身又是悲剧,因为在“痛快”之后,世界还是那个世界,它自己却烟消云散了。蘩漪在剧中的爆发有如雷雨一般澎湃,也有如雷雨一般悲哀。一方面,正是她的“豁出去”才推动了剧情,影响了其他人物的命运:“死命地拖住周萍不让他离去的是她,把侍萍(她好比是个定时炸弹)招到周公馆的是她,关住四凤的窗户使周萍被鲁大海与侍萍发现的也是她,最后在周萍与四凤要一同出走时,又是她叫来了周朴园,打乱了原来的局面,完成了这出悲剧。”(22)另一方面,“她自己后来也渐渐意识到她所做的种种努力,不过是一种徒劳的挣扎。但是,像她这样的性格,是绝不能忍受别人的欺负玩弄,绝不能安于失败的命运的。她一定要反抗,要报复”(23)。
现在,我总算可以回答“雷雨”是什么了。“雷雨”是隐喻某种巨大、原始、不顾一切的破坏力,这破坏力往往是由那些经历了巨大失落的人所引爆——毕竟对他们来说,最珍贵、最心爱的已被剥夺,所以,自己可以无所谓了,因为不会再失去什么了,只想本能地释放不满乃至仇恨。鉴于“雷雨”性格的这一“非理性”特质,曹禺常用另一个词来指称它,那便是“蛮”。
当钱谷融说蘩漪是《雷雨》中最“雷雨”的人物时,我想他已真正读懂了《雷雨》,也真正读懂了曹禺。因为曹禺曾表白,写《雷雨》就是自己“蛮性的遗留”(24),而那么多戏剧人物,“最早想出来的,并且也较觉真切的,是周蘩漪”(25),他还坦白:“喜欢看蘩漪这样的女人。”(26)曹禺曾如此描述这个女人:“她也有更原始的一点野性:在她的心,她的胆量,她的狂热的思想,在她莫名其妙的决断时忽然来的力量。”(27)很明显,曹禺所喜欢的,也正是繁漪的“野”或“蛮”。
钱谷融为何会对曹禺笔下的“蛮”如此动心呢?我想先说清曹禺与“蛮”的关系。
曹禺虽然写了繁漪这个戏剧人物,但他本人却并没有“她的胆量”、“她的决断”,相反,曹禺似像钱谷融一样沉默,忧郁。曹禺曾这么描述自己的少年时代:“生活上一点都不苦,但感情上是寂寞的,甚至非常痛苦,没有母亲,没有亲戚,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交谈的人,家里是一口死井,实在是闷得不得了。”(28) 面对这口“死井”,曹禺只能“躲到自己的房间里去读书”(29),而当他无法从书本得到心灵的宁静,就只能动笔“发泄着被积压的愤懑,诽谤着中国的家庭和社会”(30)。作家往往是通过虚构人物的戏剧冲突来疏解内心的情结,就像歌德非得让少年维特毅然结束无聊的生命,自己才能够继续忍受现实世界一样,曹禺恰恰是因为缺乏蛮性,才将舒缓郁闷寄托在“豁出去”的繁漪身上。繁漪是舞台上的行动家,创作了“繁漪”形象的曹禺在生活中却不是。
钱谷融在生活中也不是行动家,他在大学时代只懂得用文字表达哀愁,连那些文字也大多显得细腻而柔弱,它们能够记录青年钱谷融“成长的烦恼”,却无助于从根子上排遣。所以,可以想象,当《论“文学是人学”》遭遇“围剿”,钱谷融就其习性来说,也只得默默隐忍乃至规避,“因痴而辱”足足五年,而未能像繁漪那般“因辱而蛮”。
我说过,在“因痴而辱”层面,钱谷融可与繁漪心有灵犀;那么,在“因辱而蛮”层面,钱谷融为何迟迟不仿效繁漪奋起抗议呢?除了书生文弱之外,另一个原因是时辰未到。这是百年学术史上颇具国情特色的文化现象:学人述学得讲究选择时间(时代节点),何时宜?何时不宜?这不是学术,却有“学问”。关键是在“述学”之“述”,不仅指私人空间的悄然低吟,更是指在公共语境的独立言论。这就意味着,在“1956”写的话,当不宜搁到“1957”去说;但鉴于历史常常拐弯,于是,不宜在“1957”说的话,放到“1962”又变得可酌情出笼了(31)。我讲不清这是历史的狡猾?学术的无奈?还是生存的智慧?我只看到“1962”,当大地微妙地回暖,冰河稍有解冻,万物便竞相摇曳春色,被幽闭五年的钱谷融重新出山,学界惊喜地披阅《〈雷雨〉人物谈》一篇、一篇、又一篇……
由于我不曾读到钱谷融对“人物谈”撰写背景的自白,故不免纳闷:钱谷融究竟是何时才真正读懂了繁漪的“蛮”,不仅心动,而且诉诸行动,理智地、不无执拗地用学术来回应时势对他的误解与不公呢?但这无碍我推测:即使钱谷融早已领悟了繁漪的“蛮”,也恐怕只有到“1962”,此领悟才能转为可让学界瞩目的白纸黑字。所以,要害并不在于,到底是繁漪唤醒了蛰伏在作者心底的“蛮”的渴求呢?还是作者内心本就有曹禺式的“蛮”的种子,才不难深味繁漪“蛮性”之三昧?重要的是,钱谷融“学术回应模式”已经启动。
“学术回应模式”作为学人应对时势的价值心理动力定型,当是一个制动学人角色行为的内在意向结构机制,它不是只有单一价值意向(动机)环节,它要靠两个意向(动机)环节的有机链接,才能促使学人有所作为,近似“情动于中而形于外”(只是此“情”不会单纯得像孩童)。这落实到钱谷融身上便是:“因痴而辱”作为始初动机,固然是间接诱引作者写“人物谈”的心理基因,但显然只有“因辱而蛮”这继起动机,才是直接策动作者写“人物谈”的心理动因(当然尚需外因)。由此,我敢说,繁漪之“蛮”对在“1962”酝酿学术回应的钱谷融
来说,不啻是意念层面的“启示录”,亦是行为层面的“兴奋剂”。
三
当我说在“因痴而辱”、“因辱而蛮”层面,钱谷融皆像是活在《雷雨》剧外的另一个“繁漪”,这仅仅是修辞格,并非是把钱谷融简单地等同于繁漪。以“蛮”为例。繁漪之“蛮”,固然激活了钱谷融写“人物谈”以回应时势的心志,但当“人物谈”切实地化为墨痕,学界从字里行间读出钱氏之“蛮”,却毫无繁漪的暴戾气、挑衅性与尖酸味。钱谷融对时势的学术回应,若不是设身处地地还原现场,时隔近半个世纪,你几乎读不出那个“蛮”,因为其“人物谈”纯粹是学理的,建设性的,犹如在大学课堂,面对洗耳恭听的满座学子娓娓道来,同时又在期盼对象的理解或善待——全然不像繁漪对其所置身的家族背景是仇视的,势不两立,冰炭不容,非理性乃至无理性可言的。繁漪的“蛮”是失控的破坏力的爆发,是将整个舞台乃至世界(连同自己)掀翻、颠覆、炸毁也不足惜的,否则不足以平息其复仇狂焰。相比较,钱谷融却“蛮”得那般温文、平实、雅谦,简直太有风度了,不妨命之为“蛮而有度”。
“蛮而有度”作为钱氏“学术回应模式”链型结构的第三意向环节,可谓从整体上设定了“人物谈”的回应力度、幅度及其限度。这可从他“谈周朴园”时看得很清楚。
最能见出“谈周朴园”一文的回应力度的,体现在作者坚执周朴园对侍萍的种种缅怀,并非全系虚伪、作秀、“故意装出来的”,“做给别人看的”(32)。钱谷融没有否认周朴园的基本性格是专横、威严而伪善的,但珍视日常人伦体验的他更愿意相信,即使阶级属性从整体上规定了周朴园“他只能是虚伪的”,“但也并不等于完全否认”或“排斥周朴园对侍萍可以有某种程度的真正的怀念”(33)。其理由极具说服力,不妨录下——
侍萍年轻时是很美的。他确曾喜欢过她,何况她又是周萍的母亲,怎能不常常想起她呢?一个人对于已经失去的东西,总是觉得可贵,特别感到恋念的。尤其是他做了那样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我们记得,他是为了赶娶一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逼着刚生下孩子才三天的侍萍,在年三十夜冒着大风雪去跳河的),总不能毫无内疚。现在,侍萍既已死去(他一直以为她已经死了),对他就不再有什么威胁、不利,他就更容易想到她的种种可爱处而不胜怀念起来。这种怀念,又因为他的灵魂的内疚,又因他的补过赎罪之心而愈益增加了它的重量,以至于他自己都为这种“真诚的”怀念所感动了。他觉得自己虽然“荒唐”于前,却能“补过”于后,就仿佛也是个“道德高尚”的人了。这样,他对侍萍的怀念就做得愈益认真起来,并且还以此为豪,以此来教育周萍,来树立家庭的榜样。这样做,在他主观上可能的确是很“真诚”的,并无故意骗人的存心。(34)
很质朴,很周正,很合乎人之常情,又很辩证,几乎无懈可击。
判断周朴园形象是否一味虚伪一案,原本仅仅是个有涉人物造型的“文学”命题,尚未提升到哲学意味的“人学”层次。就人物造型而言,西方文学史曾有过两种范型。一是法国古典主义,以莫里哀为代表,其喜剧人物大多是“类型”,堪称是人的单一习性之寓言,就像钱谷融所说的:“吝啬汉有的只是吝啬,残暴的人任何时候都是残暴的”,未免“简单化”(35)。另一种则是英国莎士比亚所示范的“性格”造型,“性格”化之核心是要表现人物个性的复杂,“而个性,则总是比较复杂的。吝啬汉可以慷慨于一时,杀人不眨眼的人有时也会大发善心”(36)。这就把人物写“活”了。显然,钱谷融在“文学”上是器重人物造型的“性格”化的,他认定周朴园就是这么一个被写“活”了的“性格”。
人物塑造,应走“类型”路子,还是走“性格”路子?这是见仁见智,各有所爱的。但钱谷融在“文学”上如此推崇“性格”人物,则有其“人学”的理由。第一,在钱谷融眼中,周朴园作为一个资本家,无论其宗法意识有多偏执,首先,无法否定他也是个“人”;第二,既然周朴园是“人”,则其身上也就有“人性”,只要其“人性”还未被剥削者的“阶级性”(诸如专横、威严、伪善等)吃掉或泯灭殆尽,那么,他身上依然有“残余的人性”,比如他对侍萍的不无诚意的怀念,在无损其在家族的绝对威势的前提下,是有可能在他内心滋生的,这是合乎日常人伦逻辑的;于是,第三,不难得出如下看法,即只要不把阶级论绝对化,不把阶级分析法形同“贴标签”,比如具体评价某人,不是言必称家庭出身、阶级成分,进而以此为终极尺度将人一棍子“打闷”或“打死”,那么,对人物做个性化的人性论分析,并不有悖于对人的阶级论分析。用钱谷融的话说,便是“个性的复杂性并不否定或削弱个性的阶级性,而恰恰是更生动,更丰富地体现了它的阶级性,更充分、更深刻地揭示了他的阶级性。如果我们不估计到个性的这种复杂性,不去具体的观察研究这种复杂性,那么,我们对他的阶级本质即使也可能有正确的了解,但这种了解必然是抽象的而不是具体的,是肤浅的而不是深刻的。因为这种了解,只是挪用了一个无可争辩的现成结论的结果,而并非自己实地观察的结果”(37)。钱谷融这番话说得很学理,很严整,也很有潜台词。其潜台词是:有人所以在“人学”层面将周朴园简化为纯粹虚伪的“类型”而无视其个性的复杂,是因为他们在“人学”层面是有绝对化倾向的阶级论者,当他们认定人在阶级社会只有“阶级性”而无“人性”,一般“人性”是抽象的、空洞的,只有“阶级性”是具体的,实在的,每个人身上的“人性”就这样被“阶级性”武断地、无条件地挤压了,置换了,注销了,当他们用这一眼光去审阅周朴园,周朴园也就难免从“圆型”人物沦为“扁型”人物。
“蛮而有度”的钱谷融“谈周朴园”确实谈得很妙,妙就妙在:此文未用一字去正面回敬“1957”对其《论“文学是人学”》的政治误判(被打成“修正主义毒草”),但他分析周朴园“个性的复杂性”的每一个词,无形中都成了辩护其“人道—艺术理念”的美学证词,虽然迂回,委实有力。若有人愿将“谈周朴园”读成是《论“文学是人学”》在现代文学论域的个案化学理延伸,大体不错。
更妙的地方还在于:“1957”打压《论“文学是人学”》的理论无疑是绝对化的“阶级论”,但其“谈周朴园”却不刻意回避“阶级论”,甚至在方法论层面不无尝试:即欲探索能否让“人道—艺术理念”在“阶级论”为主导的思维空间占一席之地,虽尊卑有序,但无碍彼此间互渗与互补,既使自己的建树能有机融入现实语境,同时又从方法上限制了“阶级论”被滥用。这就像一株痉挛、顽强而又委婉地从乱石缝中爬出的兰花,虽然活得很艰涩,很卑微,但仍梦想着绿叶舒卷、迎风飘逸的自由天地,它无须大,只要不失却独立性就好。对这一点,不论钱谷融有否足够的自觉,他“谈周朴园”时所展示的、着意让个性论与阶级论对接、并渴求两者融合的心迹,是有案可查的。这难免会让钱谷融付出学术代价(嗣后有机会当专论)。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问:如此温文尔雅地、有节制地“谈周朴园”,何“蛮”之有?充其量,“痴”而已,仅仅是在悄悄地守望五年前被废黜的《论“文学是人学”》。
我只想说:一个人能在“1962”换一种语式,继续说出“1957”不让说的话,容易吗?毕竟,“1962”与“1957”的差别只是数量的,而非性质的,绝不像“1978”已公认“历史反思”是时代呼声,可堂堂正正地响彻大地。坊间至今有此传言,“1957”之后中国知识分子不敢讲真话了,“1959”之后执政党内的正直者也不敢讲真话了。但钱谷融愣在“1962”以“学术回应”方式,将“1957”不宜讲的话又讲了一遭。记得王瑶曾在1980年末有此妙语:“不说白不说,说了也白说,白说也要说。”一时被尊为“学界傲骨”。殊不知钱谷融早在60年代初已以其“人物谈”这般做了。虽谦卑,却高贵。虽文弱,却尊严。你说这是“痴”,还是“蛮”呢?能在“1962”毋忘“1957”之“痴”,此“痴”即“蛮”。
四
“谈周朴园”与“谈周冲”皆体现了钱谷融学术回应的“蛮而有度”,但“度”的内涵不一:假如说,前者表现了作者对其“人道—艺术理念”的守望,颇具理论力度;那么,后者则沉潜到生命关怀层面揣摩一个周冲式的“梦想者”在现实中的生存路径,故更具思想幅度。
周冲作为梦想家兼大男孩走上舞台,确实与剧本中那阴郁的、压抑的、咄咄逼人、针尖对麦芒的氛围,显得不协调。当时就有评论家对此不耐烦,并质疑曹禺:“要他干什么,仅仅就是作为一个陪衬吗?”(38)
钱谷融当然不认为周冲因仅仅处于戏剧冲突的边缘,因只起“陪衬、烘托和渲染方面”(39)的角色功能,就被宣判为“多余的人”,就应被逐出舞台。但钱谷融也确实同意“周冲似乎是所有人物中最无足轻重的一个了。如果单纯从结构的观点来看,即使把这个人物精简了,也不至于对事件的进程有多大的影响,不至于使剧本的基本面貌有所改变”。是的,若考虑到《雷雨》的戏剧结构,大体是走法国古典主义的“三一律”路子,它讲究要在同一时间、地点演绎同一情节,即以紧凑凝练取胜,那么,周冲在《雷雨》中的存在理由,委实不无争议。但钱谷融旋即又强调,这个人物“是断乎少不得的”(40)。不然,剧本“给予观众心头的冲击力,也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强烈,现在这样的深沉了”(41)。
钱谷融这么说,是源自他对剧作家的深挚体认。理由有二。
一、周冲“是曹禺的宠儿,曹禺是以他整个的心灵来哺育这一人物的”。周冲的追求,曹禺“当然知道不过是一个孩子的天真的梦想罢了。但毕竟,在他看来,这又是多么美丽的一种梦想……他并不因为这种梦想万无实现之望就舍弃了它,倒正是因为它的不能实现而更加倾向于它,更加执着于它了”(42)。
二、周冲“是天真,善良,而富于正义感的。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的幼稚,就是他对现实的完全的无知。然而这并不是他的罪过,而正是他的不幸,对于这样一位天真未凿的孩子……谁能不给予同情,加以爱抚呢?”(43)然而,当“丑恶的现实不但摧毁了周冲的美好的梦想,并且还吞噬了周冲的年轻的生命”,这定将激起观众的愤慨:“这是个什么世界呵!曹禺正是通过周冲这一形象来表达他对丑恶的现实的沉痛控诉和严正抗议的。周冲这一形象的意义和力量就在这里。”(44)
三篇“人物谈”,无疑是钱谷融对曹禺作“同情之理解”的结果,但细心品味,仍可辨析出作者对三个角色的微妙差异。“谈周朴园”时,钱谷融酷似神情淡定的放射科大夫,透过荧屏,他很清楚患者的症结何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不枝不蔓,言简意赅,冷静客观,是把周朴园放在“他”的位置。“谈繁漪”时有变化了,钱谷融的眼神有温情溢出,似怜香惜玉,从心底愿为她的每次冲动与火星四溅的反诘寻找理由,恨不能上前与她推心置腹——亦即是把繁漪置于“你”的位置。那么,“谈周冲”呢,无须说那角色身上既活着青年钱谷融曾有过的梦想,同时又牵动着中年钱谷融对现实境遇的不无哀感的生存忧思。钱谷融是置周冲于“我”的位置。
这样说有依据吗?有。请读钱谷融的自白:“像我们这些从旧社会生活过来的人,在孩子时代,谁没有做过周冲式的美梦呢?”(45)所谓“周冲”式的美梦,钱谷融有一个解释:也就是“他对真善美的乌托邦世界的无限的渴望和对丑恶的现实社会的极端憎恶”(46)。切实落在剧情中,则显现为周冲“对周朴园的否定,对鲁大海的同情,乃至于四凤的爱慕”(47),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出自周冲所信奉的“平等、自由、博爱”(48)等价值准则。这里须说明的是,据笔者对青年钱谷融的研读,他对如上准则的体认更多地是落在对神往艺术与美的诗意个体人生层面,而不像周冲那样要在日常人际探求群体性社会公正——但这两种理想皆可从上述价值准则中衍生出来则无疑。
这就有助于解释:为何钱谷融会一再感慨年轻演员想要演好周冲,很不容易了。因为在钱谷融眼里,周冲有两面性:一方面,他纯真,善良,像孩子那样憧憬未来;另一方面,他毕竟十七岁了,十七岁竟有时还“天真”得奶声奶气,这就不是“美好”,而变成了“幼稚”,所以钱谷融说周冲的台词往往显得“不自然”、“矫揉造作”。
十七岁是这样一个年纪,将近成人,却又差那么一点儿。所谓成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青少年不断走向社会、面对世界的过程,或者说,是其梦想不时与现实碰撞,从而在解读世界的同时,更真切地体认自身,学习担当责任的过程。当周冲迈向第十八个年头,他不应看不到自己身处的世界并不如想象中那般美好。他应该懂得,梦幻在现实面前往往显得无力而无助。但周冲依旧稚气满满,这其实是一种倔强——他不愿轻易妥协,就算梦不能实现,也要尽量让自己和自己所爱的人活在梦里。但周冲追逐梦想的努力终于一次次化为乌有,被周朴园训斥,被鲁大海嘲笑,甚至连四凤都只把他的憧憬当作儿戏,一笑了之。表面上,周冲只活在自己的梦中,但其灵魂却在梦想和现实的夹缝里挣扎。曹禺写周冲,就是为了表现这种梦想被现实不断碾压所必须承受的无力的阵痛。
正因为钱谷融看到了周冲在美梦幻灭后所忍受着的煎熬,所以他说:“要一个年轻的演员,能把周冲灵魂上所承担的深重的负载,所尝受到的钻心刺骨的痛苦,完满地、恰如其分的表现出来,委实是很困难的。”(49)
周冲的痛苦,年轻演员无法体会,就连专业评论家也未必能够体悟,为什么钱谷融却能够相惜甚契呢?
别忘了,相对于现实语境,钱谷融也曾揣着“夏天里的一个春梦”,这便使他在1949年前后也屡屡成为“一个奇异的存在,一个‘不调和的谐音”(50)。且不说他年青时因痴迷文艺而难觅知音;人到中年,脱稿于“1957”早春的《论“文学是人学”》,进入夏季就被铺天盖地的“大批判”所轰毁。所以,在1957—1962年间他阅读周冲的过程,难免是他不断地咀嚼自己痛苦的过程。而相对周冲,他的痛苦当有过之而无不及:周冲是出于孩子气的倔强而拒绝与逃避现实,进而陷入孤单;钱谷融则是无意间成了靶子而被孤立,所谓“因痴而辱”,几乎连退路都没有,只能一滴一滴地独咽苦酒。所以,当钱谷融“谈周冲”,他不仅仅能设身处地,感同身受,甚至还会无意间放大那些痛苦,更确切地说,是把自己内心得不到释放的哀感嫁接到了周冲身上——请阅“谈周冲”的尾声:
周冲是生活在梦想中的,他的梦想是这样的美好,真是纯洁无瑕、纤尘不染。但现实却是这样的丑恶,到处布满污秽,遍地散发出腥臭。这两者是万难并存的。结果是……人们所喜爱的受虐杀,人们所憎恶的在逞威;无辜遭难,罪人逍遥;美丽永逝,丑恶长存:这是个什么世界呵!(51)
不难体会,钱谷融在写这些句子时已进入了亢奋状态,心底似有一汪泉水在汩汩泻涌,参不透的酣畅、华美与凄婉。遥想当年曹雪芹为林黛玉撰葬花词,其心境或许便近乎此。
钱谷融不讳言自己有过“周冲式的美梦”,但他又很清楚自己不是周冲式的梦想家。他说过,与周冲相比,“我们的睡眠并不怎样酣甜,入梦也并不太深沉,只要一点略大的声响,一丝意外的惊扰,就会使我们醒觉过来。因而梦醒后的失望、悲哀,也就并不是怎样的不能忍受了。周冲却是真格的生活在美丽的梦想中的人,一般的声响,普通的惊扰,轻易不能使他觉醒。……可见他的睡意之浓,入梦之深;可见他对现实是如何的隔膜!”(52)
由此可见钱谷融对自己的生存定位,既不像繁漪“蛮而无度”,豁出去与现实拼个鱼死网破;也不像周冲“对现实彻底隔膜”(53)——相反,钱谷融在理智上是愿意把现实当“教科书”来拜读的,把自己所忍受的苦难当“严酷的导师”(54)来尊重的,用他的话说,便是:“一个对社会完全隔膜的青年,本来是必然要处处碰壁,必然要受到现实的无情的打击的。而也只有在一次次的碰壁,一次次的打击下,才能使他慢慢的清醒起来,聪明起来。”(55)
那么,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变得比周冲“清醒”而“聪明”呢,记得在评述曹禺为何塑造周冲时,钱谷融曾言:“至于应该怎样从现实出发来制定他的理想,特别是应该怎样为他的理想的实现,而作一些切实有效的斗争,他就很少考虑到;或者说,这还不在他当时的能力范围之内。”(56)就在同一页,钱谷融还说:“只有新的才能挤走旧的,只有树立起了新思想,旧思想才不得不离开你。曹禺当时还没有树立起比这更高的新的理想,即还没有掌握住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准则,当然也就不能完全抛弃这种理想了。”(57)上述“这种理想”,大体上接近周冲式的梦想。
这就是说,十七岁的周冲在剧本中所不曾有的,二十三岁的曹禺在写《雷雨》时所不曾赋予周冲的那种“先进的、科学的思想准则”,到了“1962”他仿佛发现了。这就解释了:为何钱谷融能够忍受梦境幻灭后的悲哀,因为他似乎找到了一条调整自己与现实关系的“切实有效”的路,既无须鄙弃梦想,又不沉湎梦想,而是尝试将自己这枚“不和谐音”整合进“主旋律”。这落实到钱谷融的学术回应,那就是在《〈雷雨〉人物谈》里,谦恭地让植根于人性论的“个性论”在“阶级论”为基调的奏鸣曲里发出柔和的低吟。即便是在咏叹受辱者的哀怨,也大体可唱得“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此即中年钱谷融在《〈雷雨〉人物谈》中所定格的“学术回应”形象,既是风度,也是限度。■
【注释】
① 钱谷融1951年自交通大学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任职讲师,至1980年直接晋升教授。
②④⑤(18)(20)(22)钱谷融、殷国明:《中国当代大学者对话录:钱谷融卷》,455、457、457、29、456、457页,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③ 1979年5—7月钱谷融续撰“谈侍萍”、“谈四凤”、“谈大海”、“谈鲁贵”。
⑥ 钱谷融:《散淡人生》,37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⑦(23)钱谷融:《“最残酷的爱和最不忍的恨”——谈繁漪》,见《文学的魅力》,396、403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⑧⑨(19)(27)曹禺:《曹禺作品精选》,45、9、157、45—46页,且夫选编,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
⑩(11)(12)(13)(14)(15)(16)钱谷融:《散淡人生》,21、39、39、40、21、11、61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17)据亲历者说,1957年春,当一身西装革履的钱谷融在华东师大文史楼宣讲《论“文学是人学”》时,便戏称此文是其“情人”。参阅曾利文、王林主编的《钱谷融研究资料选》,389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08年版。
(21)(24)(25)(26)(28)(29)(30)曹禺:《曹禺自述》,63、63、63—64、64、5、4、60页,京华出版社2005年版。
(31)学界传说当年主掌《文学评论》杂志的何其芳,在读完钱谷融来稿《“你忘了你是怎样一个人啦!”——谈周朴园》后曾说,味道有点怪,但还是发。参见缪克构的《钱谷融:从容是一种气度》,载《文汇报》2008年7月21日。
(32)(33)(34)(35)(36)(37)钱谷融:《“你忘了你是怎样一个人啦!”——谈周朴园》,见《文学的魅力》,385、386、386—387、386、385、38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钱谷融:《“夏天里的一个春梦”——谈周冲》,见《文学的魅力》,427、429、420、420、420、429、430、420、421、425、425、423、420、430、420—421、421、430、430、426、426页,山东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夏伟,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2006级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