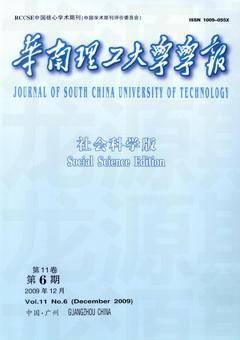喜马拉雅条款效力的扩张
崔起凡
摘要:在2004年Kirby案中,美国最高法院在一张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能否赋予“铁路公司”责任限制权利的问题上,沿用了第三人利益合同理论,但确立了比以往判例宽松的解释标准。而在另一张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能否约束“Kirby公司”的问题上,美国最高法院创设了“有限代理理论”,进而同样得出肯定结论。美国最高法院扩张喜马拉雅条款效力的实用主义态度,有利于鼓励海运业及多式联运业的发展,为我国立法和司法在处理类似问题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喜马拉雅条款;美国;kirby案
中图分类号:D99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5X(2009)06—0039—06
随着海运业的不断发展以及多式联运的兴起,越来越多的主体参与到整个运输的各个环节。在这些主体之中,除了订立运输合同的承运人之外,还会有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甚至是独立合同人,如港口经营人(以下统称“履行辅助人”)。当运输途中货物出现了灭损,货方可以基于合同或提单起诉承运人,基于海上特殊风险的考虑,公约及各国法律一般都规定了承运人的免责、责任限制等权利。另外,货方也可以以侵权为由起诉直接造成货物灭损的履行辅助人,这时,如果履行辅助人不能享有与承运人类似的权利,很可能使承运人的免责和责任限制等法定权利落空,因为履行辅助人赔偿货方后一般会向承运人要求补偿。如果得不到补偿,对于经济实力一般相对较弱的履行辅助人来说,责任过于沉重,不符合公平原则。
在海运实践中,承运人常常会在提单中订立喜马拉雅条款,即在提单中约定了履行辅助人可享有免责和责任限制等权利的条款。但是,作为提单所包含或证明的合同中的一项内容,认可喜马拉雅条款对提单外当事人的效力需要克服“合同相对性”这一理论障碍。为解决喜马拉雅条款问题。“海牙——维斯比规则”和“汉堡规则”及部分国家的国内法,直接规定了履行辅助人的免责和责任限制等权利,即喜马拉雅条款法定化。而美国相关立法并没有将喜马拉雅条款法定化,它参加的“海牙规则”也没有涉及喜马拉雅条款问题,因此判例法是其处理该问题的主要法律渊源,其中美国最高法院对2004年Kirby案的判决代表了美国判例法在这一问题上的最新发展。
一、Kirby案简介
(一)案情
2004年,澳大利亚的Kirby公司和无船承运人International Cargo Control(以下称“ICC公司”),签订了从澳大利亚运到美国的运输合同。ICC公司签发了一套全程提单给Kirby公司(以下称“ICC公司提单”)。ICC公司又把运输安排给了海上承运人Hunburg Sued公司(以下称“HS公司”),HS公司给ICC公司也签发了一套提单(以下称“HS公司提单”)。
两张提单都记载悉尼为装货港,美国Savannah为卸货港,交货地为内陆城市Huntsville。另外,两张提单分别规定了首要条款和喜马拉雅条款:ICC公司提单约定了海运部分适用美国1936年海上运输法中的责任限额(每件500美元),陆路运输部分适用海牙维斯比规则中的责任限额(每件666,67特别提款权或每公斤2特别提款权),而且责任限制扩及承运人的受雇人、代理人或其他人,包括任一独立合同人;HS公司提单规定了美国1936年海上运输法的责任限制,并延伸适用至所有代理人也包括内陆承运人、所有独立合同人。
货物在Savannah卸船后,HS公司和NorfolkSouthern铁路公司(以下称“铁路公司”)签订合同,将这批货物从Savannah继续运送到目的地Hunts—ville。货物在铁路运输途中发生了事故,损害达150万美元。Kirby公司起诉铁路公司,铁路公司依据两张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主张责任限制。
(二)判决
地区法院经简易程序认定了铁路公司责任适用HS公司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第11巡回法院推翻了上述判决,它认为在两张提单下,被告铁路公司都不能主张责任限制。但最高法院又完全推翻了第11巡回法院的判决。
(三)Kirby案的焦点问题
该案两张提单中的喜马拉雅条款的效力,构成本案的两个焦点问题:第一,ICC公司提单中喜马拉雅条款能否赋予第三人铁路公司责任限制的权利?第二,HS公司提单中喜马拉雅条款是否约束第三人Kirby公司?二、喜马拉雅条款赋予第三人权利:
宽松标准的确立
关于Kirby案的第一个焦点问题,在试图得出结论以前,首先回顾以往判例。
(一)判例回顾
1,herd案:第三人利益合同理论的运用
1959年Herd案①是由最高法院处理的第一个喜马拉雅条款案件。在该案中,装卸公司由于过错导致货物损失,虽然提单中的责任限制条款未约定适用承运人以外的第三人,装卸公司仍然主张责任限制。
美国最高法院认为,装卸公司既不是运输合同的当事人,运输合同也没有约定装卸公司是受益人,因而不能享有提单规定的责任限制权利。
美国最高法院进一步指出该案涉及的是一个第三人利益合同问题。第三人享有免责或责任限制的前提必须是合同中订立了喜马拉雅条款,而且该条款必须具备两个有效条件:第一,使第三人受益的合同意图(intent)应严格解释并仅适用于“意向中”受益人(intended beneficiary);第二,该合同意图应以“明确的语言”(clarity 0f language)表述。美国最高法院同时强调代理理论不能适用:该案不是代理问题,因为装卸人对于运输合同来说是“完全的陌生人”。
2,宽严不一的解释标准
在Herd案之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喜马拉雅条款的受益第三人的认定存在宽松解释或严格解释两种倾向,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是“严格解释”和“明确的语言”。Herd案明确了喜马拉雅条款的两个有效条件:“严格解释”和“明确的语言”。但Herd案并没有进一步阐释“明确的语言”的认定标准以及如何“严格解释”。各法院虽然都以第三人利益合同为理论基础来解释喜马拉雅条款,但标准不一。比如,20世纪70年代之前,“独立合同人”的描述一直被认为足够明确,但此后又被认定为不明确。
二是海运服务(maftime service)。装卸人的装卸和港站经营人的仓储保管等在实践中习惯上被看作海运服务。但对于在内陆提供服务的第三人而言,情况就不同了(原因似乎是非海运服务与海运服务具有不同的风险)。司法实践中,有些判例拒绝承认喜马拉雅条款针对内陆承运人的效力,如Sony Chemicals案。但更多的判例认可其效力,如Mori Seiki案③。
三是另一个“合同相对性”。在参与运输的多个履行辅助人之中,有些不仅仅是和托运人没有合同关系,和承运人也不具有“合同相对性”。这种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