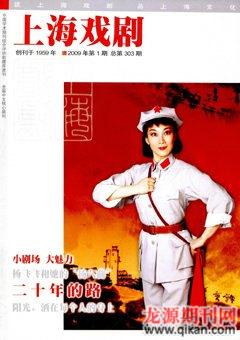人生与艺术之海的探索者
刘明厚
诗剧《浮士德》是18世纪德国大文豪歌德(1749-1832)用了60年时间创作出来的杰作。1831年8月31日,歌德终于为他的这部不朽之作划上了句号,此时的他已是83岁高龄。这部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完美结合的诗剧,以德国民间传说为题材,以文艺复兴以来的德国和欧洲社会为背景,描写了一个新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满现实、竭力探索人的自由和人生意义、挑战神的权威的故事。
得知该剧是由中国最有影响的导演、中央戏剧学院教授徐晓钟执导,兴奋与期盼涨满了我的心怀——说了多少年的事情,如今终于兑现了,浮士德终于穿越了历史的尘埃,第一次从德意志走上了上海的舞台。
浮士德:人本欲望无限扩张的悲剧
在《浮士德》中,歌德以其飞扬的激情洋洋洒洒地写下了约12000行诗句。该剧分为上下两部,此次上演的是上部,也是最富有舞台戏剧性和动作性的一部。
序幕表现了天主对人的信念与魔鬼靡菲斯特对人的怀疑与否定之间的冲突。在靡菲斯特看来——
如果不是赐于他们理性的天光,
他们也许还可能活得自在。
如今有了这个“理性的天光”,
他们却变得比野兽还要野兽。
天主并不认为这样。在天主看来,浮士德是他“忠实的仆人”。三位大天使赞美天主的伟大、宇宙的和谐,于是设定了全剧的神性框架。浮士德则欲冲破神性(或者说是宗教)的羁绊与束缚,借助靡菲斯特的魔力来实现自己的欲望,追求人的自由。他主动与靡菲斯特签约,从此在魔力的帮助下打开潘多拉的盒子,踏上了欲海旅程。
浮士德曾饱览群书,求知若渴,哲学、法学、医学、神学涉猎甚广。但这些中世纪的陈腐知识却使这位年老的博士痛苦地发现,这些知识“解释不了宇宙、说明不了世界、认识不了人间”!他觉得自己虚度了光阴,一事无成,这是人类知识欲的悲剧。因此,他决定走出书斋、走进生活、解放自己,这是他与靡菲斯特一拍即合的思想基础。他们俩建立了主仆关系——浮士德为主人,靡菲斯特为仆人。靡菲斯特听从主人的调遣,满足他的一切欲望,包括可能的和不可能的,直到他的欲望满足为止;而浮士德则以自己的灵魂作为交换的条件。
对自己背离神性秩序、追求人的自由的冒险之旅,浮士德心里是很清楚的,用他的话说,是——
有两个灵魂藏居住我的心底,
一个总要和另一个分离。
一个怀着强烈的情欲,
像吸盘一样紧紧抱住凡尘;
另一个却要超脱俗世,
向那崇高的灵境飞驰。
在经历了内心挣扎之后,他以叛逆者的姿态诅咒神圣的基督教教义:“诅咒希望!诅咒信仰!特别要诅咒忍耐和谦让!”这些话,意味着浮士德要公然与上帝(天主)挑战了,他不再愿意匍匐在上帝面前、服从他的意志,他要按自己的意志重建人的秩序、建立浮士德的世界,凡是赋予人类的一切,他都要亲身加以体验,从个人世界扩大到整个人类。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对靡菲斯特说道:
你不必担心我会把条约破坏!
条约的内容,本来就是我永恒的追求。
让我投身到人世的洪流,
不管痛苦和享受。
失败和成功如何交替,
唯有大丈夫才会有不息的追求。
此时的浮士德是豪迈的,他把人与神对立了起来,一旦做出自由的选择,就连魔鬼都不能阻拦。浮士德与清纯少女格蕾青在大街上偶然相遇,立刻被强烈吸引,向格蕾青大献殷勤却被拒绝。此时,他便当即命令靡菲斯特当晚就把她“搞到手”。然而,就连魔鬼都觉得格蕾青太清白、太稚嫩而不忍心下手,可浮士德却不依不饶地威胁靡菲斯特说:“如果今夜不能搂在我的怀里,那么午夜时分,我们就各奔前程,两下分手!”他欲火中烧,对美女的强烈占有欲使他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先前靡菲斯特对人类的评价:“人类比野兽更野兽。”
浮士德和格蕾青的故事是全剧最为引人的亮点。在淫欲支配下,浮士德向少女发起了强攻,两次送上珍宝示爱。不谙世事的格蕾青完全被迷惑住了,她深深爱上了浮士德。但是,为了这份爱,她却付出了可怕的代价——母亲、哥哥、刚出生的孩子和她自己四条人命!是浮士德一手造成了格蕾青的悲剧。为了能进入少女的房间,他给格蕾青一瓶所谓的安眠药水,结果却毒死了格蕾青的妈妈;他借助靡菲斯特之手杀死了格蕾青的哥哥;他玷污了格蕾青的床榻又离她而去,使她在失恋、悔恨和痛苦中走向疯癫,溺死了自己的儿子,继而不得不独自承担起全部的罪责。
残存的良知,使正在与魔女狂欢做乐的浮士德突然想起了格蕾青,他带着靡菲斯特赶到牢房,要救出为他牺牲了一切的少女。但格蕾青拒绝了与魔鬼作伴为伍的浮士德,她选择了死,她要以死赎罪而重返上帝怀抱。她对浮士德说——
我害怕你,我又替你害怕!
格蕾青替浮士德害怕什么呢?她害怕他在魔鬼的牵引下,在背离天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人的大欲的无限扩张,会导致人类的毁灭。格蕾青就是浮士德不可抑制的情欲下的牺牲品。美,就这样残酷地被毁灭了。
但是,浮士德没有就此回头。他依旧和魔鬼如影相随,继续他的人生探寻之路。在德国文学中,有人类借助魔力使自已的欲望得到满足的传统。作为德国狂飙突击运动的积极分子,歌德继承了这一传统,他笔下的浮士德要以理性的光辉借助科学和超自然的魔力,跟着靡菲斯特去追求人本更大的自由,满足自己更大的欲念,直到最终魔鬼要拿走他灵魂的时候被上帝所拯救。
徐晓钟:无边艺术大海的坚韧探索者
“无边大海的‘苦行者”,这句话出自徐晓钟的导演阐述,他以这句话来概括《浮士德》这部戏的形象种子,可谓精辟而形象。作为学者和教育家,徐晓钟总是能用最简洁、最朴实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一如他的为人,平和而谦逊。在我看来,这句话其实也同样适用于他——徐晓钟,一个无边艺术大海的坚韧探索者。为了这部戏,为了完成前辈黄佐临的嘱托,徐晓钟在他80高龄时专程从北京赶到上海执导《浮士德》。事实上,多年以来,他对《浮士德》的研究从未间断,他研读了所有《浮士德》的中文翻译版本,资料和笔记积案如山。在排练场,在剧场,每一个人都能感受到他对全剧的成稳驾驭和在表现形式上的智慧追求。
徐晓钟是一位非常严肃的、有深厚学术功底的导演,对于这部18世纪的经典诗剧,他首先是站在忠于原作的立场上,然而再用现代人的眼光去审视、解读。2008年8月29日徐晓钟作导演阐述时,他对剧组全体演职人员说道——
我们排演《浮士德》,肯定会有我们自己对这部伟大作品的解读。但是,我们首先是向我们的观众严肃、忠实地介绍歌德的这部作品,严肃地向观众介绍歌德对人性,对人类的哲思和他的艺术特点,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发挥我们的创造。
这一席话,表明了徐晓钟对于经典和戏剧的严肃态度以及他对剧作家的高度尊重。
徐晓钟曾与这部《浮士德》演出本的翻译者余匡复一起反复切磋,对原著冗长的诗句进行删节。在研讨合作中,二位学者目标一致,相互尊重,为戏的成功上演夯实了扎实的文本基础。由此,我们所看到的这台《浮士德》,不是某位导演个人的《浮士德》,而是最接近于歌德的《浮士德》。
原著《浮士德》采用了多种表现手段,大大突破了在欧洲统治了200年之久的古典主义创作法则。才华横溢的歌德走笔若飞,上天入地,从天堂写到地狱,从人间写到鬼域,从大自然写到工业社会,可谓气势恢弘、浪漫飘逸。其中最吸引人的,是浮士德与女巫在炼丹灶房和浮士德试图解救被判死罪的格蕾青两场戏。
幻想,既是歌德的翅膀,也是徐晓钟的翅膀。徐晓钟并未专门设置“女巫的炼丹灶房”这一写实场境,而是用虚拟的魔幻手法展现出女巫变幻莫测的鬼蜮伎俩。靡菲斯特带着浮士德进入到神秘、恐怖的女巫灶房,这个见不得阳光的地方寓意着一个淫荡、肮脏的性欲世界。靡菲斯特与女巫是主仆关系,他们之间谈吐举止粗俗不堪。在表现女巫的妖术和她的炼丹仪式时,导演运用了灯光和音效手段,营造了一个怪诞诡异的魔鬼世界。浮士德接受了女巫的忘川水汤药,刚放到嘴边时,舞台灯光变红, 象征浮士德已开始欲火中烧。他立即为镜像中的美女玉体所诱,因此一旦他回到正常的现实社会,便心急火燎恨不能马上把软玉温香抱满怀。
导演让观众见识了一个具有魔幻、诡谲的女巫世界。他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并借此告诉观众——在这个独特的规定境遇里,浮士德就此打开大欲之门,完全抛弃了圣经里的清规戒律,与神性逆向而行,从此走上了一条一发而不可收拾的新的冒险之路。浮士德今后会遇到什么样的故事,导演为观众设置了一个巨大的悬念。
戏到这里,浮士德已把靡菲斯特看作是他的“再也离不开的伙伴”,为了能在情欲享受中燃起更强的情欲,浮士德对后者言听计从。他们之间的主仆关系时常是模糊的,既相互依存又各自独立。对浮士德来说,靡菲斯特这个魔鬼既是外在的,又是内在的,是自己内在自我和大欲的外在表现。

而后来的“瓦普几司之夜”,徐晓钟再次调动了艺术想象力和表现力,同是鬼域世界的再现,但与前一场完全不同。此时,舞台上凸显的是魔鬼们的狂欢,他们群魔乱舞,乌烟瘴气,浮士德在其中再一次迷失自我。这场喧闹的、动感十足的戏,与紧接着表现格蕾青在死牢里即将告别人世的凄美悲剧形成鲜明对比。
怀着对美的欣赏,导演通过格蕾青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而突出了女主角的善与纯真,并在她最后一场戏中提升到一个美的高度。从一开始不理会浮士德的调戏,到第一次收到贵重礼物时的惊喜,从爱的情弦被拨动,到天真地玩“数花瓣”游戏从而确定这从天而至的爱到底是真是假,以及面对浮士德的强有力的山盟海誓:“我要完全为你献身,永生永世,永无尽期。”此时,格蕾青才接受了浮士德的爱,天使般的纯洁无邪被层层展现出来,非常甜美,非常诗意。
在这个过程中,导演运用了多个对比手法来刻画美的化身——格蕾青。如她与欲火难忍的浮士德,她与风骚的邻居大婶玛尔太,她与粗俗放荡的魔女、女巫,她与爱嚼舌的小市民姑娘等等。稚嫩、纯洁的格蕾青与这些人在一起,是那么的与众不同,她的美、她的微笑、她的羞涩就像是天使来到人间般超凡脱俗。在场面与场面的对比中,导演以动与静、美与丑、善与恶、圣洁与放荡、光明与阴暗、寻常与离奇、崇高与卑劣、幻想与真实等各种对立因素置放在一起,将格蕾青升华的一个至善至美的高度。
格蕾青确是值得怜爱的。当衰老的浮士德以贵族美少年的面目出现在她面前,格蕾青对这位魔鬼附身的人的进攻自然难以抵挡——她以为她和爱情不期而遇了,于是为了爱而委身于浮士德,结果却遭受到毁灭性的惩罚。全剧的高潮落在死囚牢房这场戏,在这里,导演细腻地开掘出了女主人公在罪与罚这一规定情境中的微妙而复杂的心理活动,那是彻骨的苦痛、忏悔和对死亡的恐惧。浮士德眼中的格蕾青,像一头受了惊吓的小鹿浑身颤抖,她神经质,有点疯癫;而格蕾青眼里的浮士德也变得陌生起来,他不再可爱了,他的嘴唇是冰冷的,他的语气也不再像从前那么坚定有力。导演同时站在男女主人公的角度去看待对方、表现对方,这种审美视角与歌德的原著精神是极其贴近的。
在“活着,还是不活”的艰难选择中,格蕾青最终受制于神性秩序,她选择了对上帝的皈依:“这是主的裁判!主啊,我已把自己交付了你!”格蕾青和浮士德的分道扬镳,不仅是生与死的分离,更是她和浮士德在道德观与宗教观上的分歧,从本质上看,他们不可能达到一致。导演将这场戏处理得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将男女主人公的灵魂冲突演绎得一浪高过一浪。最终,格蕾青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浮士德跟随靡菲斯特而去。此时,剧场上空久久回荡着格蕾青的最后一声呼唤:“亨——利!”这一声绝望的呼喊,揭示出这位不幸少女对浮士德、对现实社会的深深失望,也同样激起观众对格蕾青悲剧命运的思考,以及对浮士德这个艺术形象的反思。
如果说格蕾青是一只迷途的羔羊,那么浮士德则是抵抗上帝意志,追求人的自由和理性的勇士和自我解放者。他要借助魔力进一步解放自己,创造新的世界,实现他一个又一个理想,也包括各种人本体的大欲。在尾声里,导演把《浮士德》的第二部做了个引子——浮士德醒来,在阵阵涛声中孤独而义无反顾地向茫茫大海走去。这一尾声预示浮士德的不屈的意志,引起观众对浮士德最终命运的期待。
纵观全场,我们可以感悟到徐晓钟对诗性和哲思的审美效果的追求。他坚持用诗的语言取代多少年来中国舞台上那种日常口语化的台词,这对演员和观众来说,都是一个考验。他刻意保存着这部诗剧中的哲思性诗句,这对爱看故事情节的中国观众来说也是一个挑战。然而,他并未过于迁就观众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而是坚持尽可能还原原著的导演原则。同时,他在表现形式上下了许多功夫,以追求形式上的美感和诗意。
细心的观众会注意到,全剧所有的场景或远或近都与大海相关联——酒店是大海附近的酒店,浮士德与格蕾青相遇的大街是海边的林荫道,女巫的炼丹灶房也是在海边的山洞里……阵阵涛声几乎伴随着每一场场景的转换。“大海”,是徐晓钟语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大海是人类无法控制和驾驭的,它变化莫测,时而风平浪静,温柔可爱;时而波涛汹涌,粗暴异常;时而又大雾朦胧,令人迷茫。导演把故事场景都放在海边,是有他的寓意的,这是为了强化人物内心冲突的“海浪化”的可能性。当即将被处死的格蕾青向上帝呼救时,导演用剧烈的电闪雷鸣、滚滚的海浪声外化出赎罪者内心的极度恐惧和悔恨,同时也凭借这些声、光、影等舞台效果来营造悲剧诞生前的那种毛骨悚然的死亡气氛。这场高潮戏的“海浪化”的舞台处理,使观众的心灵也得到震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