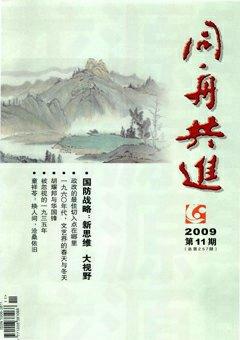延安时期的“跨国婚姻”
宗道一


【李德与肖月华、李丽莲】
延安时代的“跨国婚姻”并不鲜见,最为著名的要数李德和李丽莲。上世纪30年代,共产国际向中央苏区派出军事顾问李德,即奥地利人奥拓·布莱恩(笔名华夫)。李德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失误众所周知,这里只说他生活上的“毫末细节”。
李德到江西苏区时正值三十出头,自然有正常的生理上的需求。据美国著名专栏作家、《纽约时报》副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称:“李德于1933年10月抵达中国时,满以为红军与其他军队一样,他指望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他睡觉。但是苏区没有妓女。”(索尔兹伯里《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解放军出版社2005年版,下同)“李德寓所离共青团机关的宿舍不远。当时共青团的一位领导人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妻子。李德对这位年青妇女垂涎欲滴,想与她同枕共眠。他主动给她送礼……那位丈夫很快就意识到他在搞什么名堂。李德的不‘检点很快传到了领导层面,这是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但听任洋顾问如此放肆,影响确实也不好。一些同志,可能还包括翻译伍修权在内,采取措施挽救了局势。”最终组织上找到了一位名叫肖月华的年青农妇。
肖月华是出身贫苦的广东姑娘,长得虽不怎么漂亮,但为人厚道,当时在少共中央局秘书长胡耀邦身边工作。肖月华也是一位老革命,17岁那年由海丰县妇女协会执委、彭湃夫人蔡素屏介绍入团。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肖月华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正如朱德夫人康克清所言:肖月华是把李德看成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与李德一起过了。也是据索尔兹伯里所言,著名女作家丁玲对肖月华嗤之以鼻:“她充其量只不过是个乡巴佬!”其实,丁女士此言差矣!这种有违人权和婚姻道德,由组织上定夺的婚姻“配给”,在中国,特别是在部队,一直持续到上世纪50年代。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观念,肖月华随李德到了延安,甚至在他的指导下学会了烤面包。当肖月华给李德生了个皮肤黝黑的儿子后,连毛泽东也调侃李德:“这可无法证实日耳曼民族优越的理论了。”后来,毛泽东还一直记得李德、肖月华夫妇这个儿子。王炳南的德国夫人王安娜(安娜利泽,中共长江局国际宣传组成员)随夫婿抵达延安,毛泽东初次见面便问王安娜:“你儿子(王黎明)的头发是金色还是黑色?眼睛像妈妈一样吗?是蓝色的,还是黑的呢?”“皮肤是白色的,还是接近中国人的颜色?”毛泽东不顾王安娜脸上的惊愕神色饶有兴味地寻根刨底。当王安娜明确表示儿子是“黑头发、黑眼睛”,“接近中国人的颜色”以后,毛泽东才抚掌笑曰:“这真有趣!”“你的同胞李德的太太是中国人,他们的孩子也是黑头发、黑眼睛,肤色也和中国人一样。一般说来,你们德国人总是以德国的强大而自豪;可是,似乎怎么也敌不过我们中国人!我们的人种好像比你们强呢!”(王安娜《中国——我的第二故乡》,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版)
但是,这种组织上介绍乃至一手包办的婚姻十之八九是悲剧。果不其然,在李德移情别恋投奔延安的上海影星李丽莲之后,肖月华最终找到了毛泽东。听完肖月华的哭诉,毛泽东说:“博古那时把李德奉若神明,言听计从,要什么给什么,需要女人,就将你提供给他,实在是荒唐,造成这场婚姻悲剧。”不过,毛泽东最初也想做“和事佬”,毕竟这是桩涉外婚姻,尤其还与共产国际、与苏联人有牵连。但肖月华去意已决,经调解无效,边区政府民政厅同意离婚。
肖月华解放后任职湖南省交通厅(办公室主任),尔后调回部队,授大校军衔。1983年11月3日病逝。
而令李德情有独钟的李丽莲身材颀长,俏丽动人,更兼天生一副好歌喉。1937年与后来成为毛泽东夫人的江青一起离沪来延安。由于李丽莲不仅能演戏,还能歌善舞(为上海“天一”影业公司演员,曾在胡蝶主演的《皇后的新婚》等片中配唱),很快担任了延安鲁艺音乐系助教。离婚后的李德与李丽莲正式结婚,李德也转为中共党员。但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李德便于1939年8月奉命返苏,留给李丽莲的是无限惆怅与清泪涟涟。新中国成立后,李丽莲大部分时间从事民间外交,曾参加国际民主妇联理事会并历任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副秘书长、全国妇联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1965年4月在北京病故。定居民主德国的李德则于1974年去世。
【郑律成与丁雪松】
另一对“跨国婚姻”是丁雪松和郑律成。1918年生于重庆巴县的丁雪松是新中国第一位女大使,20世纪70年代末先后出使荷兰和丹麦,此前历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朝鲜处副处长、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秘书长等职。
丁雪松幼年失怙,父亲丁开科英年亡故,家中生活十分清贫,主要靠母亲做手工活、摆小摊苦度光阴。丁雪松早年就读于教会学校重庆文德女中,她才华出众,唱歌、弹琴、舞蹈无师自通,成绩名列前茅,屡获教师好评。丁雪松于1937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年初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学习。在中国女子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时任学生会副主席、俱乐部主任。她是在“抗大”这座革命大熔炉里与同龄的异国青年郑律成相识并相爱的。丁雪松说:“1938年初,我到了延安。那是一座充满了青春活力的歌咏之城,到处回荡着嘹亮的歌声。”“那年春天的一个傍晚,我和‘抗大女生队的几个同志到延安北门外散步,初次见到一个体型瘦削,腰杆笔挺,眉宇间显得英俊而刚强,身穿黄色军大衣的人。他是我们队长赵玲的客人郑律成——来自朝鲜的一个革命青年。后来在我担任队长以后,又常常看到他活跃的身影。他有时穿着灰色的军装,有时穿件褐色的茄克。当他在晚会上出现的时候,他的节目很独特,嘴里吹着口琴(用铁丝把口琴系在头上),怀里弹着曼陀铃,脚下踏着打击乐器,一身而三任。我想这也许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但在当时延安这样简朴而热烈的晚会上,不正需要这些来自四面八方、有着各种艺术才能的青年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以活跃大家的文娱生活么?有时他引吭高歌,那宏亮抒情的男高音,具有一种感人的魅力”。
1918年生于韩国全罗南道一个贫寒家庭的郑律成,原名郑富恩,是著名作曲家,国际主义战士。郑律成的3个哥哥,都参加了朝鲜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1933年春,15岁的郑律成和一批青年志士从朝鲜木浦登上了“平安九”轮船,来到中国南京,进了朝鲜在华抗日团体所办的“朝鲜革命干部学校”。1937年9月,郑律成在李公朴等人的帮助下,和爱国青年—起奔向延安。他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88年经邓小平签署命令,被中央军委颁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郑律成的另一代表作品是《延安颂》,正是这首被誉为“用心抒写世界上所有争取和平的人们”的作品,成了他和丁雪松喜结良缘的“媒人”。1937年秋,到延安不久的郑律成,就想写一首优美、战斗、激昂的歌曲来歌颂延安。1938年春天的一个傍晚,延安城里大会结束后,郑律成和“鲁艺”的几位朋友站在北门外山坡上,眼前是唱着歌、呼着口令的青年男女踏着整齐的步伐奔向各自宿地。嘹亮的歌声和口号声响彻云天,传遍山野田间,郑律成的心和整个延安城一起沸腾,他要求身旁的女诗人莫耶给他写个歌词:“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 丁雪松这样回首往事:“在延安的一个晚会上,我见到了郑律成,他和女高音唐荣枚同志合唱他刚谱就的《延安颂》……郑律成当时是抗大的音乐指导,我任抗大女生队队长,他常到我们队来教唱歌。我们就这样结识了,以后,我们常在一起漫步、聊天,无话不说。”(丁雪松《〈延安颂〉和〈八路军进行曲〉》)
丁雪松于1941年12月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秘书,差不多同时,她与郑律成结婚。此前,郑律成一度在政治上受到某些人的“怀疑”(怀疑为“特务”)。由于他写了《延安颂》等有影响的歌曲,才保留了党籍。抗日战争胜利后,经中央批准,丁雪松与郑律成去了朝鲜工作。中朝正式建交后,丁雪松和郑律成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丁雪松加入朝鲜国籍并转为朝鲜劳动党党籍,长期留在朝鲜工作;二是两人分手,从此各奔东西;三是郑律成随丁雪松回中国。后经周恩来批准,并征得金日成同意,两人相继回到中国。1950年9月初,郑律成不愿在祖国受难的时候离去,他的心情十分矛盾,最终他让丁雪松带着7岁的女儿先行回国。1950年9月中旬,美军在仁川登陆,人们纷纷撤离战火笼罩的平壤,郑律成扎上干粮袋,装上火柴和盐,准备背着77岁的老母亲撤离平壤。此时,我国驻朝鲜大使馆政务参赞柴成文同志,派吉普车把郑律成母子送过了鸭绿江,随后乘火车匆匆赶到北京。郑律成于 1976年病故,丁雪松现已是91岁高龄。
【李敦白与魏琳】
由李先念、王震介绍,经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五大书记批准加入中共的著名国际友人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先后娶了两位中国姑娘。他在延安则是和张家口新华广播电台、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英语播音员魏琳结婚。魏琳原名蒋琳琳,重庆中央大学外文系肄业,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熟悉鲁迅先生《日记》和《书信集》的朋友都会依稀记得一位名叫蒋抑卮的人物,他便是魏琳的祖父,与鲁迅有长达30年的交往情谊。正因为蒋抑卮是鲁迅留日的挚友,于是有人穿凿附会地将魏琳说成是“浙江绍兴东浦人”。其实,蒋抑卮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从蒋抑卮到魏琳,蒋家在杭州已繁衍5代,实为杭州郡望。
虽然出身金融巨贾,但由于战争,魏琳的生活依然颠沛流离。1942年她从上海著名的教会中学中西女中毕业考入沪江大学。据魏琳回忆,这时,她“对共产党的认识还是模糊的”。1943年那个酷热的夏天,不满20岁的魏琳终于迈出了第一步。她这样写道:“出于反对日寇占领上海这样一点非常浅薄的爱国想法,更主要的是为了脱离大家庭,逃避现实、追求新鲜,追求所谓的‘不平凡、不空虚的生活,我离开了生活了19年的家到国民党区去了。”“1943年,我经江西到成都。又于1945年3月到了重庆,上国民党的中央大学。在外文系二年级借读”。在这里,魏琳读了《新华日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社会科学基础教程》等一类报刊书籍,对社会发展规律、国民党的统治及解放区的民主生活都有了一些了解,“以后就被吸收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社”。
1946年2月25日,由美国、国民党、中共三方代表组成的军事三人小组委员会签订《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简称《整军方案》)。中共方面急需大批英语翻译人员,周恩来指示:要在半个月内从重庆、成都的大学中挑选100名左右政治上可靠、有一定英文水平的大学生,作短期培训后,准备在有美方人员参加的国共整编军队时担任中共方面译员。“因为是要给美国人当翻译,坐的是美国人的飞机。登机前,我们都改了名字。我原名蒋琳琳,改了母亲的姓,叫魏琳。飞机经过北平飞到张家口,聂荣臻同志接见了我们”。魏琳这样回忆道。
在张家口的晋察冀军政干部学校外语干部训练班里,学员享受营级干部的生活待遇。训练班学员编成几个小组,自学为主,教员辅导,并请国际友人李敦白、美国记者库莉训练听力,还邀请聂荣臻、罗瑞卿、姚依林、马辉之、杨春圃等领导同志到班上作报告。
李敦白出生于美国南卡罗来纳州, 1945年夏天,他随美军踏上中国大地,来到西南边陲云南省昆明市。从那一刻起,24岁的青年李敦白便开始书写自己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李敦白成了中国共产党唯一的美籍党员,他曾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众多中共高层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毛泽东称他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纽约时报》亲切地叫他“中国女婿”,“四人帮”则诋毁他是“美国特务”。在华35 年间,李敦白曾两次入狱,在狱中度过了近一半的时光。1949年1月21日李敦白因“斯特朗间谍案”在西柏坡入狱,他被指控“接受美帝国主义指示,破坏中国革命”,1955年4月4日获释,毛泽东、周恩来向李敦白当面道歉。然而,后来中国人再次犯错,而且是同样的错——
“文革”初期李敦白身为北京外国人造反派组织“白求恩—延安造反团”的领袖人物,一度在北京“红得发紫”,但却被四人帮诋毁为“美国特务”、“国际间谍”而遭逮捕。1967年8月底,“中央文革”派人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将李敦白软禁。1968年2月21日,又以“美国特务”罪名被送至秦城监狱关押,于1977年11月19日出狱,前后监禁长达9年8个月零1天。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著名新闻访谈节目《60分钟》主持人迈克·华莱士称:李敦白“曾利用与邓小平的亲密关系,说服邓接受了我的60分钟采访。这在西方新闻界的来往中,是唯一的一次。”(《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李敦白在昆明时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处理民间事务。这使李敦白有机会看到中国社会的黑暗腐败,听到底层百姓的痛苦呻吟,并对中国共产党人和传颂一时的“朱毛”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二战结束,李敦白却不想回国,他想方设法让自己滞留中国。李敦白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通过地下党的帮助,李敦白在上海结识了宋庆龄的秘书、廖承志的姐姐廖梦醒(英文名辛西娅)。未几,宋庆龄先生介绍李敦白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简称“联总”)任职,负责把粮食送往受灾地区,从此脱离美军。廖梦醒点燃了李敦白的“延安梦”:“别回去了,与我们在一起。留在中国,到延安去。”于是李敦白奉命前往武汉“联总”办事处报到,并从那里往北进入大别山区。在此期间,李敦白利用职务之便给了中共一份丰厚的“见面礼”:1946年春,李利用美国记者的特殊身份,从美方代表白鲁德那里弄到了准确情报,将国民党军队准备对中原解放区首府宣化店发动进攻的机密告诉了中共。后来,见到周恩来时,李敦白投奔延安的想法还得到了周的支持。按照周恩来的意见,李敦白将和纽约一个救济组织的代表普莱丝小姐一起奔赴北平,准备从那里搭乘美军军用运输机进入延安。但此计划却遭到了美军的拒绝,连叶剑英出面也无济于事。叶剑英提议让李敦白去张家口,那里的新华广播电台正在筹建英语广播,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协助工作。当地最高指挥官聂荣臻也要求李敦白留下。
李敦白与魏琳的爱情种子便是在张家口播下的。在贫瘠的黄土地上,爱情种子顽强地发芽并开花结果。李敦白与魏琳是名副其实的“师生恋”。李本是有妻室之人,只是1945年离开美国时,他的第一次婚姻便因妻子红杏出墙而临近崩溃。李敦白毕竟是洋人,在昆明时也“鬼混过几次,与一些吉普女郎搂抱亲嘴”。尽管适逢燕尔之喜的老朋友李先念将军在延安已经豪情满怀地向其承诺:“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后,我就是武汉市的市长,到时候你就可以过来生活,我帮你找个当地最漂亮的女孩做老婆。”但是李敦白似乎等不及,他也无法习惯没有女人的日子。在收获爱情果实的秋季来临之前,即便是对魏琳动情之后,李敦白在感情上也一再“出轨”。 他首先迷上了刚回延安不久的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养女孙维世:“在延安,我迷上了孙维世,她非常迷人,我第一次见到她时是在周恩来的窑洞,当时周恩来正在接受斯特朗的采访,我对她一见倾心。她有张非常甜美的脸,漂亮的头发,大眼睛充满了幽默和智慧的光芒。她善良机智,红润健康,又有点男孩子气。我怕她拒绝,所以尽力与她建立起脱俗的柏拉图式的友谊。”与孙维世同岁的李敦白倒还算有点自知之明,不敢造次唐突。李敦白哪里知道,这位后来成了著名表演艺术家金山的夫人的孙维世,连青年林彪都为之心旌摇荡,足见其风采魅力。孙维世是革命烈士孙炳文长女,著名话剧导演艺术家、戏剧翻译家,李敦白第二次身陷囹圄时,孙维世亦于1968年10月14日惨死狱中,年仅47岁。
李敦白的感情漂泊,直到魏琳对其最后“锁定”才宣告结束。从相爱到波折、到花好月圆,两人终成眷属,李敦白在回忆录里写得很翔实:
那时,每天晚上我都从电台送她回家,一路欢声笑语。我一直不知道自己已深深爱上了她,直到她突然割断我们之间相恋的可能。“我们不能再接近了”,她说,因为她在等未婚夫从布拉格回来。于是我的自尊心阻止我再做进一步的表示。不久我便离开张家口,远远离开了她。但就在我动身去延安的那天,我察觉到,其实在她内心深处,并不像外表所表现的那般抗拒。她在我床头放了一副亲手织的手套,还附上一张深情的字条:“这副手套是我为你织的”,她用英文写道,“我会永远珍惜我们的友谊”……
我还是很难做到不露声色……魏琳终于递给我一张小纸条。其实我一直在等着她某种形式的拒绝,因此当我看到她那张挽成结的纸条上写着“我们必须谈一谈”时,心立刻沉了下去。我几乎可以肯定,她要告诉我的是:我们之间必须保持距离……
那天吃完午饭,我便按照她的指示,忧伤地坐在房间里等她。她进门后,径直走到房内另一头的椅子上坐下。我坐在炕上,等她开口。“我们必须谈谈”,她说,“我再也受不了这样子下去,对我们的工作也不好”。这正是我最害怕听到的,“怎么了?”我问。她哭了起来,大颗的泪珠从圆脸上滚下来。她用手捂住泪眼,啜泣着说:“我从来没想到我会同时爱上两个人。”
……
当我们手牵手走出那个小房间时,似乎没有人对此感到惊讶……一旦魏琳改变心意,爱情便势如破竹。
1947年10月,我和魏琳结婚。
按照规定,我们向组织提出申请……婚礼很喜庆。一帮朋友自发布置了我的房间,婚礼就在那里举行。廖承志发挥漫画天分,画了一幅巨大的画像:一个戴眼镜的外国人对魏琳丰满的身姿垂涎欲滴,上端还题了两句打油诗:“洋人何必忧天,有情必成眷属”。
后来,李敦白入狱后的第3年,也就是1952年,苦苦等候的魏琳申请离婚。李敦白杳如黄鹤,魏琳选择再婚,并与新的夫君携手至今……
(作者系浙江财经学院中国外交人物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