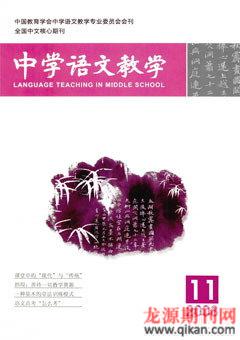“情境教育”对语文教学现代性问题的启示
冯卫东
什么是教学的“现代性”?我个人理解,大致有三层含义:一是时代性,从一定意义上说,教育教学是时代与社会的一种表征,有什么样的时代与社会,就应该(大致)有什么样的教育教学,“桃花源式”的隔膜和落伍行为是“去时代性”的。自然更谈不上“现代性”;二是规律性,那种紧紧“追风”,与时代和社会“同辙合振”,纯粹成了时代和社会的“晴雨表”却缺乏应有批判力、独立性及超越精神的行为,由于违背了教育教学自身的规律,因此也很难说是具有“现代性”的。譬如“文革”时期为政治和阶级斗争服务的教育教学,如果有人以为它还具有“现代性”,一定会贻笑天下;三是先进性,这其实也是对前两者的“集大成”,同时又是一种提升——现代性应该是“先进教育(教学)生产力”的一种本质特征,是任何一个时代与社会的教育教学都应致力追求的目标或方向。
中学语文教学必须具有鲜明的现代性,我们应该为此付出许多“前无古人”的努力和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到达现代性的“河流”中,我们是“空游无所依”的鱼儿;相反的,语文教学界无数前人、前辈及其创造和积累的丰富的教学资源、经验、思想与智慧正是我们实现现代性的重要凭借和“镜鉴”,如果没有这一些,那么,所谓的“现代性”就必然是无源之水,是空中楼阁。也毋宁说,是他们和我们的传承与“接力”,才使现代性成为一种可能,最终成为一种现实。
“情境教育”就是其中一份弥足珍贵的财富。要言之,“情境教育”是让儿童(学生)置身于某种优选或人为优化的情境(渲染了、弥散着浓郁情感色彩或情意氛围的环境、景象)之中,主动地、愉悦地、有效地进行学习,从而获得情智和谐发展、人格健全成长的一种教育模式。以上述关于“现代性”意涵之理解来衡量它,完全可以说,“情境教育”是强烈彰显语文教学现代性的一面旗帜:它“是对当代人类教育中困惑和危机的回应,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情境,时代的话语”(朱小蔓);它“为了儿童研究儿童,易于找到规律”(李吉林);它“从20年前就在代表当代、当代教育来解决一百年来没有解决好的教育难题”(朱小蔓)……《语文课程标准》先后七次提到“情境”,可见它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关键词,这自然是对“情境教育”思想的肯定、吸纳和弘扬,也从一个侧面“确证”了它的现代性意义与价值。
学习“情境教育”的思想与精神,应该成为中学语文教学的一种自觉行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们强化语文教学现代性乃至达成语文教学现代化的一条必由之径。
“情境教育”较早、较好地解决了一系列“教育难题”,学术界将之概括为五个关系问题,即符号与经验的关系,逻辑化认知与情感化认知的关系,学科与生活的关系,学科与统整的关系,自发自然与引导的关系,不难发现,这些“难题”不唯小学语文教学才有,中学语文教学同样有,甚至更为棘手,更加迫切需要加以解决。
为了解决这些“难题”,著名语文特级教师李吉林努力“促进‘儿童-知识-社会的完美建构”:她从儿童立场出发,“我,长大的儿童”,“用儿童的眼睛看世界”,面对种种禁锢儿童个性的行为,她说,“看出了问题不碰它,我实在是坐不住”,所以“从儿童的需要来设计我们的教学”:她不是孤立地、抽象地、生硬地把“知识”灌输给儿童,而是把它有机地“镶嵌”到特定的情境中,尽力让儿童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内心情感的驱动下,“不容自遏地学”;她切实做到“语文学习的外延等于生活的外延”,经常带领儿童到“蓝天下的学校”,读“大自然三百页的书”,让儿童在“完整的生活”中度过……
由此反观中学语文教学现状,反观其中的种种弊端,可以看到,恰恰是在“儿童(学生,也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儿童)立场”上,我们有所缺失,有所偏颇;在知识呈现上,我们有所片面,有所割裂(知识之间以及知识与生活之间的联系);在社会关怀上,我们有所漠视,有所隔膜。
不是吗,在许多教师那里,何曾有过“人的发现”?那一个个本应充满勃勃生气的“儿童”只不过是等着填食的鸭子,是等着答题的机器,是等着“渔利”(学生自己及其家庭、教师之功利)的工具。“目中有人,心中无人”,这时的“人”实际上已经是人或人格的异化、沦落、丧失。他们没有主体主动性,却有被动“反射性”(如对各种试卷“熟能生巧”的“条件反射”);没有个体感受性,却有群体盲从性;没有心灵成长性,却有精神萎缩性(随着年级的升高,童心和创造冲动等在不断地“塌陷”、湮灭)……
不是吗,在许多课堂之内,何曾有过知识的激活?学生也许会背诵不少名诗佳句,却体味不出它的意蕴和妙处;也许能对各种文意的概括法、阐述法等等说得头头是道,却无法独自“解读”一段普通的文字:也许对种种作文构思技巧了如指掌,却不能写好一篇简单的应用文……时过境迁,但他们却可能“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所以在其理解中,《我的叔叔于勒》只能是揭露资本主义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玛蒂尔德也只能是虚荣心的化身,等等。(当然,这些未必是学生自己的见解,但他们知道“保险”的重要性。)怀特海所批评的“死的知识”“无活力的概念”仍充斥于今天理当最有活力的语文课堂中!
不是吗,在许多学生的学习生活当中,何曾有过对社会的真正“介入”?社会被学校(包括语文教师)任意疏离化、碎片化,从而使学生不能进入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不能汲取社会的源头活水,使他们所面临和接触的“社会”只是从“完整社会”中割离出来的一些片段。难怪他们写《心中有春光》一类作文,奋笔疾书;而面对《初夏的季节特征》(上海市某年中考作文)之类的标题,却束手无策……因为对于前者,他们有着许多“写作知识”(词语和技巧)可供套用;而对于后者,却缺乏必要的“社会认知”。
这里,不能不说到另一种对社会“抄捷径”式“介入”的情形。如,一位教师上澳大利亚作家泰格特的小小说《窗》(写人性的美丑与善恶),却大谈“八荣八耻”;一位教师上杨绛的散文《老王》(对弱势者寄寓同情和敬重),却大谈“‘感动中国人物”。毫无疑问,这样的“介入”是强拉硬扯,是牵强附会,是向往日曾经有过的庸俗的“意识形态化”教学倾向的倒退。如果说它也能加速学生社会化进程,那无疑只会有助于矫情、媚俗、功利等畸形“社会人”的形成,而不利于清新真诚、活泼刚健的“现代人格”的发育。
无视儿童(学生)、孤立知识、隔绝社会,这大概是当下中学语文教学中林林总总的“非(反)现代性”现象的总体症候,也是其根本症结所在。这样的症候或症结只要有一天还普遍存在,是一种“常态”,那么,不管社会进入了怎样的“现代”“后现代”,我们的教学都仍将停留于遥遥无期、令人窒息的“前现代”,陷入美国学者W.奥格本所说的“文化堕距”(或“文化滞差”)之中而无法自拔。
所以,谈“现代性”固然要谈到技术更新、方法优化、路径选择等问题,但这些毕竟是“治标”之举,而若要“治本”,就必然绕不开“儿童-知识-社会”这三个维度,少不了对“儿童(学生)观”的厘清,对“知识观”的矫正,对“社会观”的调整。这些问题,恰恰为李老师及其30年持之以恒、心无旁骛地实践与探索着的“情境教育”所精彩演绎。从这个意义上说,学习“情境教育”,不仅是“治本”之需,也是“返本”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