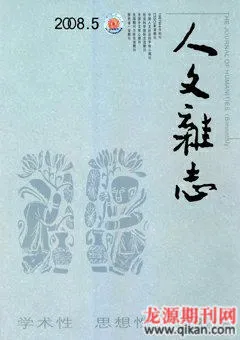吏胥幕随与明清廉政
内容提要 在明清时期,吏胥幕随在政府运作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吏胥幕随即六房书吏、四班衙役、师爷宾客、跟班长随。他们人数庞大,把持地方政务,甚至要挟长官,在衙门中
形成相互依赖、相互牵制的关系,他们的行为方式,带有鲜明的中国传统特色,充满了非正式的和私人的因素。相形之下明清法规制度和管理措施对这四类人员监控薄弱,束手无策,致使其对廉政带来了巨大的消极影响。
关键词 吏胥幕随 政治制度 地方政府 廉政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161-05
在明清时期,吏员、胥役、幕友、长随四种人,在地方官府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他们的腐败,则是廉政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明清时期,各级官府中有大量的吏员和胥役,这些人没有国家官员的身分,但却具体经办各项行政事务,在官场上和地方上有着广泛的联系和很深的根基,离开了他们,庞大的国家机器就无法运转。这些人不从国家正规俸禄中获取报酬,而是凭衙门的陋规生活。地方官员不同于中央官员,单枪匹马来到一地,面对着大量熟悉公务、盘根错节的吏胥,只得重用自己的私人幕友和长随,这些人不是官府人员,有的甚至不能进入衙门,但却是长官的亲信,借此而操持政务。明清以前的廉政制度,主要针对目标是“官”而不是“吏”,国家法律制度对这些非官非民而又亦官亦民的特殊人物约束力很小,致使在廉政方面留下了很大的空档。清代在雍、乾年间,才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但其时已经遗患无穷。明清廉政制度的这一特点,同前代有着很大不同。
一、明清廉政建设中的吏员问题
官与吏之别,在唐代就初露端倪。刘晏称:“士陷赃贿,则沦弃于时,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廉洁,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注:《文献通考》卷三五《选举八》,中华书局,2006年)从宋代起,吏员就成了官吏管理中的难题。元代重吏,是其政治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到了明清,腐败成为政治制度乃至政治体制的一大侵蚀剂,著名学者王夫之甚至在遗训中告诫后代:“勿作吏胥,勿与吏胥为婚姻。”(注:《船山遗书》卷四六,北京出版社,1999年)随着科举人数的增多,社会的发展和人Eu9xPXVmrRo0kTumx7hFow==口的增加,明清逐渐形成了一支庞大的吏胥队伍。
吏员即官府中的掾史、令史、书吏、司吏、典吏,以及提控、都吏、承发、狱典等等,各以衙门的政事繁简确定吏员编制,由各衙门长官自行辟除。长期以来,吏员在官场形象不佳,但是,各衙门办事又少不了吏员。因此,有关吏员入仕的制度,在明清廉政建设中具有特殊地位。明初规定,吏员任职九年,经考核报吏部,按所在衙门级别授予正式官职。最高者一品衙门提控授正七品出身,依次递降,至三四品衙门典吏授从九品出身。不够迁转流内品秩的吏员,则依次迁转更高级吏员和不入流杂职。这样,吏员的迁转入流速度较慢,形成官尊吏卑的定势。但明初吏员入仕后尚不受歧视,确有才能者亦能重用,如况钟以吏员出身,九年考满授礼部仪制司主事,后一直升至苏州知府。到永乐年间,吏员不得出任科道官。洪熙元年(1425年),尹崧上书言事,称:“今所任多以吏员,虽循资格出身,而其人素非良善,廉洁者少,贪鄙者多,生民被害,政事疏违,虽遣官分巡考察,而贤否岂能周知。”(注:《明宣宗实录》卷六,上海书店,1990年)宣宗自己也道:“比者御史考察官员,阘茸不称职者多由吏典出身,盖初用之时失于慎选。”(注:《明宣宗实录》卷九,上海书店,1990年)宣德三年(1428年),宣宗又道:“每一次选官,吏之冠带者三四百人,何如是之多?”“古人戒用吏,今日多用吏,民之不安,率由于此。”(注:《明宣宗实录》卷三九,上海书店,1990年)“吏部近年每奏选官,其间吏员冠带,率数百人。虽是循用旧章,亦当严加简择。分布列郡县,道理不通者有之,文移不谙者有之。贪污鄙猥,比比皆是。求其才用,百无二三。以望理民,其何能济!”(注:《明宣宗实录》卷八八,上海书店,1990年)自此,吏员入仕大受限制,即使入仕也难以重用。有的学者查阅明代中期以后的地方志,没见到一处记载有吏员做到府州县正官的,连任佐贰官的都极少,大多为杂职官(注:见赵世瑜:《两种不同的政治心态与明清胥吏的社会地位》,《政治学研究》1989年第1期)。这种对吏员入仕的限制,肯定具有澄清吏治、促进廉政的积极意义。
清代吏员有京吏外吏之分,京吏为供事、儒士、经承,外吏为书吏、承差、典吏、攒典。清代除沿用明代中后期对吏员入仕的限制外,还加强了对选任吏员本身的控制。录用吏员称著役,旧例以捐而录,按纳银多寡分送各衙门办事。康熙二年停止捐纳吏员,改为召募。康熙十四年准外省地方衙门照旧例捐纳,唯在京及奉天各州县衙门仍行召募。吏员由捐纳得之,这一选择方法本身就承认了吏员之职可以得利,开了腐败之源。但改捐纳为召募,其中弊端更多,应募者“有一等游手好闲无业贫人”。黄宗羲称吏职为“无赖子所据”(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清人牟原相则说得更明白:“唐宋以来,士其业者不为吏胥,为吏胥者则市井奸猾、巨家奴仆及犯罪之人,以是吏胥贱。吏胥既贱,为之者皆甘心自弃于恶行,己若狗彘,噬人若虎狼。”(注:《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四,牟原相:《说吏胥》,文海出版社,1972年)对于这种弊端,清朝无法根本革除,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把其弊端设法控制在一定程度内。具体做法是缩短和控制吏员的任期。大凡吏员在一职上充任多年,熟悉衙门事务,就容易产生各种弊端。因此,顺治五年规定,吏员任职以五年为期。康熙七年定各衙门吏员数目,从编制上裁汰了一些吏额。雍正元年谕令:“各衙门募设书办,不过令其缮写文书,收贮档案。但书办五年方满,为日已久,熟于作弊。甚至已经考满,复改换姓名,窜入别部,奸弊丛生。更有一等缺主名色,子孙世业,遂成积蠹。自后书办五年考满之后,各部院堂司官查明,勒令回籍听选。如有逗留不归者,饬令五城司访官稽查遣逐。”(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五四,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乾隆五十二年,针对有些书吏五年任期满后改名换姓、继续当差的现象,令在京衙门供职书吏无论服役已满未满,均不准改籍归宗,更名覆姓,以杜弊端。同时对任满书吏考试录取者,将年貌籍贯三代姓氏造册存吏部,不取者姓名籍贯亦送部备案,以杜重考。嘉庆五年(1800年),又下令禁止书吏以经手事务未完为理由留任。“书吏五年役满,即行报明开缺。倘各衙门以该吏经手事件未完暂请留办,概不准行。”⑩《清朝续文献通考》卷八九,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年)道光时,御史姜梅又曾奏请役满书吏应随时勒限回籍。咸丰元年,御史周有簋再奏请饬查孥拿已满已革书吏之在京逗留者,文宗准其奏而下令严查。
吏员五年任满后,经考试入仕,但品秩低微。清初,吏员考试录用后授八品以下至未入流杂职。乾隆五十二年规定吏员录用后只能授从九品或未入流杂职。考试由各堂官各督抚于每年七月进行,自行录取,录取比例在京不超过十分之七,在外不超过二分之一。因之,吏员已登仕途者虽非永无升转之日,但却必须从最下层干起,论资计俸,著有能声,方准升转。至晚清,因书吏在衙门轻车熟路,致有以捐纳、保举授知县者。同治元年(1862年),通政使于凌辰奏请禁止书吏捐保知县,建议“凡系派书吏差使,永不得层递保至正印官阶,以示限制,而杜冒滥,庶于国体官方两有俾益。”⑩
明清时期,对吏员的弊端批评极多。明代张居正曾说:“人之所以畏吏而必欲赂之者,非祈其作福,盖畏其作祸也。如兵部袭职官,功次系于首级,一颗一级,令甲至明也。昔有吏故将一字洗去,仍填一字,持以告官曰:字以洗补,法当行查。俟其赂已入手,则又曰:字虽有洗补,然查其贴黄,原是一字,无弊也。官即贷之。是其权全在吏矣。欲毋赂之,可乎?”(注:张居正:《张太岳集》卷一八《杂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顾炎武针对晚明政治弊端说:“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弊,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子,兄以是传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注:顾炎武:《日知录》卷八《吏胥》,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清人阮葵生曾言:“唐宋以来,以制举取士于文采声华,而士乃不习民事;吏习民事,而不得美仕。吏日下,士日尊,判然两途。而士之子恒为士,降而为吏,即为隳其家声。于是吏益以无赖。朝廷兴一利,吏即随所兴者滋百弊。欲革一弊,吏即随所革者滋他弊。自知罪大,则纵火去其籍,使茫然莫知其颠末。且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更名而不更人,更人而不更其所守。夫以他州外郡之人,为来往无常之官。官一而吏百,又皆文采声华不习民事之官,以之驾驭百十为群、熟悉风土、谙练事故、作奸犯科无赖之吏,于此能奏循绩焉?沿习既久,如久病之人,转以病为命,一旦悉去此辈,则百司茫然,一步不可行,势不能以终日。”(注:阮葵生:《茶余客话》卷七《论吏道》,中华书局,1959年)对这种弊端,连皇帝也心知肚明,如雍正就曾指出:“各部之弊,多由于书吏之作奸。外省有事到部,必遣人与书吏讲求。能饱其欲,则援例准行;不遂其欲,则借端驳诘。司官庸懦者,往往为其所愚;而不肖者,则不免从中染指。至于堂官,事务繁多,一时难以觉察。且既见驳稿,亦遂不复生疑。以致事之成否,悉操书吏之手,而若辈肆无忌惮矣。”(注:《清朝文献通考》卷一九八《刑四》)
明清的书吏用于衙门的各个部门。以县衙为例,书吏被安排在六房和承发房(收发)、柬房(通信)、库房、仓房等处。其职责是草拟公文、填制例行报表、拟制案卷备忘录、填发捕票传票、填制赋税册籍等。起初,书吏尚有薪水,清代前期,书吏一般有六到十两的年薪。康熙元年起,所有书吏薪酬全部取消。书吏的实际收入来自陋规和馈遗。陋规也有规矩,纸笔费书吏独享,其他陋规书吏和衙役分享。凡是同下级衙门打交道或同老百姓打交道的事项,每项都要收费。但收费有惯例额度和较为固定的名称,各部门不一,各地也不一。陋规的收入为朝廷默认,不算贪赃。
但是,书吏是衙门里的贪赃好手。书吏贪赃,是指在陋规之外贪污或勒索。如借报销索贿,借司法勒索当事人(贼案开花之类),征税中的掉包,税票中的重号、大头小票、催比中的贿赂,这些统统被称为浮费。值得注意的是,书吏为了贪赃方便,往往形成一个巨大的运作网,牢不可破。以县衙为例,六房书吏不仅包办行政事项,而且普遍与县城的各个粮行老板、保歇(客货栈主兼保人)勾结,用他们作中介,甚至让自己的父兄家人当保歇,开店铺。所有要到衙门打官司、交赋税、办理事务者,一般都要通过这些保歇,其油水之大,致使继任者要向退役书吏付款买缺,称“缺底”或“顶头银”。有的特殊岗位“顶头银”达上千两银子。黄宗羲称:“京师权要之吏,顶者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后而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胥吏》)
二、明清廉政建设中的胥役问题
胥役又称衙役,其地位低于吏员,没有官方身份,属于服役性质,习称皂隶。他们负责衙门的站堂、缉捕、拘提、催差、征粮、解押等事务。以清代州县衙门为例,胥役分为四班,即皂、捕、快、壮班(由于壮班为良民,所以往往不计入胥役,而称三班衙役)。皂班负责站堂执役,捕班与快班负责缉捕人犯。快班又可分为马快、步快。壮班负责站岗守卫。各班均有班头,或称头役,统领本班。四班之外,还有零星杂役,包括门子、禁卒、仵作、库丁、仓夫、斗级(收粮掌斗)、轿夫、伞扇夫、鸣锣夫、吹鼓手、灯夫、更夫、伙夫、马夫、铺兵(邮驿)等等。衙役也有定额编制。如清代大兴县衙役定额为:门子2,皂隶16,马夫12,禁卒8,轿夫与伞扇夫7,灯夫4,库卒4,仓夫4,民壮50。但实际上的衙役数量,都大大超过了编制。一般来说,一名正式衙役,手下往往有三四名“白役”。通常,小县有衙役数百人,大县上千人甚至数千人。
衙役数量之所以悬殊,在于衙役职能的弹性。皂隶的职责是前驱护卫和仪仗,并作为刑讯拷笞的执行者。马快和步快的职责是巡夜、传唤、逮捕,问案时到庭供县令驱使,派出到乡下催征赋税。捕役的职责是缉捕盗贼,也巡夜,押运官银时当护卫。民壮的职责是守卫粮仓、金库和监狱,护送官银或罪囚,也充当杂差。门子掌管仪门(衙门中正门与正堂之间的门,正官升堂办公,须关闭仪门),叫升堂,喊人犯,掌管发令竹签。衙役的服役期限为三年。
衙役的身份分两种:民壮、库丁、斗级、铺兵为良民,皂、快、捕、仵、禁卒、门子为贱民。这些贱民同倡优奴婢同列,其中捕役社会地位最低,几乎被看作准罪犯。贱民衙役的子孙都不能参加科举,为士绅所不齿,有些家庭严禁子孙从事衙役。但是,除了官户儒户,衙役可以豁免或逃避徭役。各种衙役在清朝可以得到三至十二两年薪,平均每天薪水在两文左右,为一顿饭钱。衙役的主要收入来自陋规。多数衙役的规费,属于书吏和衙役分享。只要派差,就能得到规费或贿赂(例如,一桩杀人案,各种规费可达数万钱)。一般州县也认为,衙役的车费驴费和饭费属于正常,但不准勒索敲诈。捕役主要从娼妓户和宰牲户收取陋规,因而,小地方的捕役,缺乏规费来源而生活像乞丐,但大城市的捕役,则规费花样繁多而十分滋润。
衙役的贪赃,主要通过强行代交赋税而要求加息偿还。其次是对逮捕或传唤者的勒索,虐待囚犯以获贿赂等等。
吏与胥身份不同,但是,在衙门里,书吏办理文书,胥役具体操作,二者密不可分。所以,吏胥的管理以及其中的弊端,人们往往合并论述。时人对吏胥在国家政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曾形象地描述道:“仕官有如传舍,而吏胥生长子孙;仕官素不谙习,而吏胥熟知典故。朝廷一举一动,必不能出若辈之手。于是天下遂为若辈之天下。”(注:吕留良:《四书讲义》卷三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天下惟胥吏最难安顿。后世上自公卿,下至守令,终不能出此辈圈子。刑狱簿书出于其手,典故政令出于其手,甚至兵机政要,迟速进退,无不出于此手。一刻而无此曹,则宰相亦将束手矣。”(注:梁章钜:《制义丛话》卷六,上海书店,2001年)吏胥把持官府,从好的方面讲,便于政务。“吏胥生长里巷,执事官衙,于民间情伪、官司举措,孰为相宜,孰为不宜,无不周知。”(注:陈宏谋辑:《在官法戒录》卷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从坏的方面讲,则易于舞弊。“国朝胥吏,偷窃权势,舞弄文莹,高下在下。实以黑衣下贱之流,而操天下之大柄。”(注: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庚集,商务印书馆,1920年)由于吏胥大权在握而约束甚少,有官之权而无官之责,控制措施相对薄弱,因之弊极大而利极小,上害主司,下害庶民,实为清朝政治一大患。仅以州县吏胥假司法以害民而论,名堂极多,前所未闻。嘉庆时礼部侍郎罗国俊奏湖南州县之状道:“以讼事入乡,先到原告家索需银两,谓之‘启发礼’,次到被告家,不论有理无理,横行瞒诈,家室惊骇,餍饱始得出门,由此而入族保、词证各宅,逐一搜求,均须开发。迨到案时,不即审结,铺堂散班之费,莫可限量。盖各有所挟,积渐之势使然也。是以贼盗蜂起,不敢申报。报则枉费银两,不为缉获。获则受贿放去,毫无裨益。谚云:‘被盗经官重被盗。’”⑥赵翼、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97年)御史程次坡奏四川州县之状道:“间遇有窃案呈报之后,差役将被窃邻近之家资财殷实而无顶带者扳出,指为窝户,拘押索钱。每报一案,牵连数家,名曰‘贼开花’,乡曲无知,惧干法网,出钱七八千至十数千不等。胥役欲壑既盈,始释之,谓之‘洗贼名’。一家被贼,即数家受累。如此数殷实者亦空矣。有鲁典史者刻一联,榜于堂。联云:‘若要子孙能结果,除非贼案不开花。’此川省之弊蠹,正恐不独川省为然也。”⑥清朝始终未能找出肃清吏胥之良法,听任其患政害民,使其成为吏治腐败的一大病源。
三、明清廉政建设中的幕宾长随问题
明代晚期在地方官员中逐渐兴起了幕宾,到了清代,地方衙门的幕宾成为定制(中央衙门无幕宾)。幕宾又称幕僚、师爷、西席,主要负责衙门的刑名、钱粮、承发、稿案,其中以刑名和钱粮最为紧要。例如,在司法中幕宾安排审案的各种文件和细节,但不能出庭;在财政中幕宾审核关于税赋的所有文件,并监督相应票据和记录,但在钱谷管理上不接触现金,实际运作与账房互相牵制。幕宾介于学者和官僚之间。一般幕宾种类有:钱谷、刑名、征比、挂号(登记)、书禀(通信)、朱墨(红黑誊录)、账房(簿记)等。地方长官事繁者有上十幕宾,事简者也有二三幕宾。幕宾系地方官高薪聘请,以友相待,主持相应公务,督察下属吏员。幕宾的身份、地位与吏员不同,但在政务处理和事务操作上基本属于一类,尤其在监控吏员方面是长官的左右手。中央衙门的部分书吏,则在一定程度上也承担着幕僚职能。各级官署中的幕僚、宾客越来越多,致使明清出现了绍兴师爷遍天下的奇观。
幕宾主要来源于落第书生。许多幕宾是待考的秀才甚至举人。幕宾地位较高,官员必须待以宾礼,友之敬之。如称呼只能称字而不能直呼其名,官员自称教弟,幕宾则自称晚生,官员称幕为先生,幕宾称官为东翁,私下互相以兄弟相称。幕宾由官员聘任并自付薪水。有许多大官出自幕宾(如左宗棠、王杰等名人,都从幕宾起家)。而且陕西韩城的王杰能够在科举殿试中夺魁,还得益于其幕宾经历。王杰幼年丧父,家贫,中举后一直给两江总督尹继善、江苏巡抚陈宏谋当幕宾,奏章多为其缮写。“乾隆二十六年,成进士,殿试进呈卷列第三。高宗熟视字体如素识,以昔为尹继善缮疏,曾邀宸赏,询知人品,即拔置第一。”(注:《清史稿》卷三四○《王杰传》,中华书局,1977年)由此而成为清代陕西籍惟一的状元。但绝大多数幕宾不像王杰那样幸运,他们多数一直以幕宾为生,或捐取官职。幕宾的聘金从几十两到几百两不等,最高可达两千两。但是,幕宾不能分享陋规,这也正是幕宾能够有效监控吏员的奥秘所在。
长随是官员的私人仆役。州县到任时,要提防书吏和衙役,可依赖的就是长随和师爷。官员任职期间,则要依赖长随对书吏和衙役形成监督牵制。一般来说,长随是主官信赖之人,主官用长随监督书吏衙役,执掌官印,商议公事。尤其重要的是,没有一个中高级官员会亲自受贿,长随的贿赂中介人角色不可缺少。所以,凡惩治腐败,往往要从长随身上打开缺口。
长随人数一般不多,通常有负责把门的司阍(或称门上),负责文书签转的签押(或称稿案),司仓,管厨,跟班。有的还有公堂值勤的值堂,负责通讯的书启,掌管印信的用印,负责税收的钱粮,负责监所的管监,负责驿站的管号,负责杂税的税务。通常一个州县长官有十几二十名长随。长随的职能有:监督进出衙门的人员,充当州县与书吏衙役的中介,收发公文并监督公文处理程序中的各个环节,监督案件审判的准备情况,参与案件审讯,处理审案琐务,监督狱卒和囚犯,查看税册,解送税款和漕粮,监管仓库和驿站,办理相关杂差。“长随非在官之人,而所司皆在官之事。”(注:徐栋辑:《牧令书》卷四)总之,长随协助处理日常公务,以减轻长官负担,协调衙门各部门各类人员关系,监督吏胥运作。
长随的地位与衙役相同,也属于贱民,本人和三代之内子孙无权参加科考。其来源主要是官员的家仆和亲友推荐。有趣的是,明清时期,票号经常向读书人或捐买官职者提供贷款,当官后票号债主可推荐一名长随,对方必须接受,用这种方法使票号的财力与官方的权力勾结起来。长随的收入,主要是同书吏衙役分享规费。有些规费属于长随独占,如门包。另外,长随常常从所经手的款项中克扣一定比例,替长官受礼时收取“小费”等,其贪赃方式与书吏衙役大致相同。有区别的,在于长随能够在贿赂中介的经手过程中中饱私囊,而吏胥没有这种收入。州县用长随监督吏胥,而长随与吏胥勾结往往又是他自己的收入来源。所以,长随又往往同吏胥勾结欺骗长官。与吏胥不同,长随必须得到官员的信任才能得手,官员可以明确表示对吏胥的不信任,而长随却必须以取得长官的信任为自己的作弊前提。所以,为了防范弊端,有的州县甚至规定:长随不准与吏胥交游、饮酒和赌博。
吏员、胥役、幕宾、长随等人,在明清官场构成了一个庞大的集团。而且能量极大。从整体来看,明清对这部分人员的管理相对薄弱,尽管有一些廉政制度涉及到他们,但力度和范围都有较多疏漏。明清的吏治腐败,往往同这批人有直接关系。因此,了解这些人的状况,对于深化廉政制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