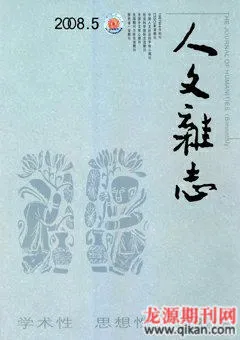阴阳哲理与儒家政治思想的命题组合结构
内容提要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思维方式和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从“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政治方略论、“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等诸多层面,说明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方式。
关键词 儒家 阴阳 政治关系 命题组合 思维方式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139-07
儒家政治思想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命题组合”的理论结构。有关阴阳关系的哲学思辨是导致这种理论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揭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审视与评价儒家政治思想的本质、特点、功能及其历史价值。本文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典型例证,说明由阴阳哲理导致的命题组合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其思维逻辑。
阴阳论是儒家政论重要的哲学依据。《周易》为儒家重要经典之一。马王堆帛书《易之义》记有“子曰:易之义,谁(唯)阴与阳。”在《周易》及其历代注疏中,每一种阴阳关系命题都势必引申出相应的君主与臣民关系的命题。儒家内部对阴阳关系、君臣关系的认识存在差异,而在本文所列举的五个基本点上又有大体相同或相似的思路。这就为认识命题组合结构提供了便利。
一、“阳尊阴卑”与“君尊臣卑”的政治等级论
理想社会模式为何?儒家认为,它的基本特征是:上下有序、尊卑有别、贵贱有等,每个社会成员都自觉恪守礼的规范。简言之,即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礼”是儒家政治思想的核心概念。孔子及其后学主张“为国以礼”
①。礼的本质是“分”,是“别”,是“伦序”,是“等差”,是“亲亲”、“贵贵”。礼的制度与秩序要求贵贱有等,君臣有别。因此,在先秦诸家中,儒家政论的特色在于“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 ②。国以君为至尊,家以父为至尊,妇以夫为至尊,这是儒家学说的基干。历代大儒多方论证人类社会实行等级秩序的必然性、合理性,其重要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阳尊阴卑”。
《周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儒家认为,道(天道、天理)是宇宙本体,阴阳是道的体现。
物之有形者皆根于道(理)而生于阴阳(天地)。作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重大项目(项目批准号:05JJD840005)。
① 《论语•先进》。
② 《史记》卷一三O《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73年,第3290页。
为实体,阴阳化生万物;作为属性,阴阳遍布一切事物之中。大凡先后、始终、动静、晦明、上下、进退、往来、捭阖、盈虚、消长、刚柔、尊卑、贵贱、表里、隐显、向背、顺逆、存亡、得失、出入、行藏等,都是“一阴一阳”的具体表现。天之道曰阴曰阳,天地是一大阴阳;人类社会中的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皆为阴阳关系。依此类推,“一阴一阳”可以解释自然、社会、人生的各种对立统一现象。这样一来,阴阳成为为各种事物定位、定性的理论依据。
儒家以尊卑论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上下。作为这种政治观念的哲学抽象,势必以尊卑论天地,论阴阳,论乾坤。一旦具有“尊阳抑阴”特质的阴阳论形成,它又反转过来成为论证人世间尊卑等级的哲学依据。朱熹说:“乾坤阴阳,以位相对而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言,乾尊坤卑,阳尊阴卑,不可并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母终不可以并乎父。兼一家亦只容有一个尊长,不容并。所谓‘尊无二上’也。”
(注:《朱子语类》卷六八,中华书局,1994年,第1683页)就自然属性而言,阴与阳是平衡、并立关系;就社会属性而言,阴与阳是尊卑、主从关系。在儒家看来,天与地、阴与阳、乾与坤的基本关系是天尊地卑、阳尊阴卑、乾尊坤卑。依据天地、阴阳、乾坤法则而确立的尊卑有别、贵贱有等的等级秩序是“天秩”、“天序”、“天地之别”。因此,“尊无二上”是最具一般意义的社会法则。
《周易》把天、乾、君、男、夫、父、兄等与地、坤、臣、女、妻、子、弟等分别划归阳与阴两大类别。这种分类方式已经将阴阳的尊卑关系固定化,使之具有了等级属性。《系辞》、《文言》、《说卦》以及《彖辞》、《象辞》等共同论证了同一个道理:尊者为阳,卑者为阴,阳尊贵而阴卑贱,这是社会的普遍法则。《周易•系辞上》有一个被广为引用的命题:“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礼记•乐记》亦称:“圣人作乐以应天,制礼以配地。礼乐明备,天地官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在历代大儒看来,天地至大,尚有尊卑之别、贵贱之位。因此,天地之象有高下,乾坤之体有尊卑,万物之位有贵贱。这就注定了人类必然实行尊卑有序、贵贱分明的君主制度和等级制度。换句话说,君主与臣民之间的尊卑关系是自然生成、先天注定的。阳尊阴卑,定位不移,因而君臣之分,贵贱有恒。臣民只能永远处于卑贱地位。
历代大儒都强调君臣之间尊卑关系的不可移易性。尽管孟子、荀子及其后学有时也言及并肯定一些现实中的君臣易位现象,诸如“汤武革命”之类。但是,在他们看来,汤武是受命新王,桀纣是独夫民贼。这种奉天伐罪的行动不可以用“君臣之义”来解释。孟子声讨“无父无君”(注:《孟子•滕文公上》)。董仲舒以尊卑不易之位来论阴阳。在他看来,“礼者,继天地,体阴阳,而慎主客,序尊卑、贵贱、大小之位,而差内外、远近、新旧之级者也。”(注:《春秋繁露•奉本》,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275-276页)扬雄认为,“阴以知臣,阳以知辟,君臣之道,万世不易。”(注:《太玄经》卷四《从迎至昆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48页)郑玄、孔颖达大讲“易简(易)”、“变易”,同时又强调“不易”,所谓“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
也。”(注:《周易正义》卷首,《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7页)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大讲变的恒而不穷,甚至大讲道有变有不变,而一从自然回到社会,从万物回到伦理,变的普遍性、绝对性就受到限制。他们认为道统是不变的,因而“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注:《朱文公文集》卷一四《甲寅行宫便殿奏札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在儒家学说体系中,作为一般法则的“君臣之义”是不容置疑、不可更易的。这是儒家全部政论最基本的前提。没有任何一个儒家思想家是脱离这个前提来论说民本思想的。
二、“乾健坤顺”与“君主臣从”的政治主体论
国家由谁来统治?儒家认为,国家必须由圣明的君主统治,天子是最高政治主体。自孔子以来,历代大儒都主张:君为主,臣为辅,民为基。他们从君主制度的起源、国家的政治结构和君主的政治功能等不同角度,全面论证了这个观点。“君之心,政之本”(注:《陆九渊集》卷三O《政之宽猛孰先论》,中华书局,1980年,第356页)。这种政治主体论可以称之为“君为政本”论。
儒家在理论上极力渲染道义、贤臣、民心在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而一旦论及政治中的决定因素,又将其归之于君。孔子认为,统治者之德犹如风,臣民之德犹如草,上行下效,风行草偃,君主克己复礼,才能天下归仁。儒家后学将这种政治思维方式发挥到极致。他们为这种政治主体论提供的理论依据之一就是天刚地柔、阳主阴从、乾健坤顺。
在《周易》中,关于乾的《卦辞》、《爻辞》及《彖》、《象》、《说卦》等,把乾与天、阳、龙、君及大人、圣人、君子纠结在一起。历代传注者皆据以论证君主制度的神圣、君主地位的尊高和君主德行的博大。简言之,君主为阳刚之体,纯一不二。与此相应,关于坤的解读则明确将其纳入乾的匹配者、辅助者、从属者的地位。阳为主而阴为从,乾为君而坤为臣。依据这种哲理,必然将君臣关系定位为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关系。
自先秦以来,许多大儒以“阳贵阴贱”、“乾健坤顺”论证君贵民贱、君主臣从。其基本思路有四:
一是阳为贵、富、尊;阴为贱、穷、卑,注定君主高贵,臣民卑贱。阴与阳的社会属性决定了君主与臣民之间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的地位。董仲舒说:“天下之尊卑随阳而序位。……贵者居阳之所盛,贱者居阳之所衰。……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注:《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36-337页)这类说法在儒家文献中很常见。
二是阳为(乾)刚、健、动;阴为(坤)柔、顺、静,注定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主导者为阳,从属者为阴,君主臣从,合乎天理。在政治生活中,臣民不能充当具有完全主体性的可以自作主张的主动者。《周易•坤卦》以“坤道其顺”、“地道无成”论为臣之道,指出:“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终也。”孔颖达的注疏认为:“臣不可先君,卑不可先尊”,因此臣下必须“不为事始”,“待命乃行”,“能自降退”、“事主顺命”、“上唱下和”,尽管也允许以柔正刚的谏诤,却又必须“不自擅其美,唯奉于上”(注:《周易正义•坤卦》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17-18 页)。柔顺、被动、服从是臣民的本分。
三是阳为纯一,阴为驳杂,注定君道无为,臣道有为。《周易•系辞下》以阴阳论君臣之道,孔颖达对此的注疏认为:君道为阳,“纯一不二”,所以“君以无为统众”,“委任臣下,不司其事”;臣道为阴,“不能纯一”,所以臣下“各司其职”(注:《周易正义•系辞下》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影印,1980年,第87页)。受君主指使,为君主服役,这是臣民的本分。
四是阳为善、仁、爱;阴为恶、戾、残,注定君主道德完善,臣民道德残缺。《周易•系辞下》以阴阳论“君子之道”、“小人之道”。历代儒者皆以“一阴一阳,一善一恶”论道德。董仲舒认为,予、仁、宽、爱为阳,而夺、戾、急、恶为阴。朱熹认为阳为刚、为明、为公、为义,属“君子之道”;阴为柔、为暗、为私、为利,属“小人之道”(注:《朱文公文集》卷七六《傅伯拱字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依据这个逻辑,臣民属于阴类,注定有道德缺陷,甚至是见利忘义的“小人”。臣民愚昧,先天注定,他们必须接受君主的教化。
对阴与阳的哲理历代儒者有不同认识,而他们普遍认为,阴与阳、乾与坤之间不仅是尊卑关系,而且是主从关系。这一属性见诸政治就注定了“君为臣纲”。以天地、阴阳、乾坤关系论证君臣、父子、夫妇的纲常关系是儒家学说的一大特色。由此而得出的“三纲五常”是一个影响极其广泛而又深远的命题。
许多学者认为,孔子不讲三纲,纲常之说是后儒编造的,它曲解了孔学(又称“原始儒学”)的真谛。其实不然,三纲的宗旨是确立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妻之间的主从关系,其条文定型于汉代,而有关的观念却源远流长。早在孔子所敬仰的西周时期,君臣、父子、夫妇的主从关系就得到周礼的确认和维护。《尚书•康诰》把“不孝不友”称作“元恶大憝”。在春秋时期,君父无贰命的信条获得广泛的认同。这类观念是后世纲常论的文化源头。孔子强调君臣、父子这两个基础性的社会关系,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以“无违”(注:参见《论语》的《为政》、《颜渊》等)论孝道。《周易》把男女、夫妇、父子、君臣视为四种基础性社会关系,并将男、夫、父、君归入处于支配地位的“阳”类,将女、妇、子、臣归入处于被支配地位的“阴”类。在儒家经典中,论证君臣、父子、夫妇之间主从关系的思想材料俯拾即是,主张维护纲常名教的思想材料不胜枚举。到汉代,董仲舒认为,“阴道无所独行。其始也不得专起,其终也不得分功,有所兼之义,是故臣兼功于君,子兼功于父,妻兼功于夫。”他把这概括为“王道之三纲”,并证明其“可求于天”
⑤《春秋繁露•基义》,见《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350-351、350页)。《白虎通》则以严谨的文字和阴阳的哲理论证了“三纲六纪”。汉唐儒者还把以维护三纲为宗旨的道德规范概括为“五常”。宋代理学诸子认为,“三纲五常”为天理之必然、王道之根本、民彝之大节。在他们看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是“人事之大经,政事之根本”《论语集注》卷六《颜渊》,见《四书集注章句》,中华书局,1983年,第136页)。经过他们的细密论证,关于“三纲五常”的理论登峰造极。由此可见,纲常论的基本思路是孔孟之道所固有的,在儒学发展史上,它可谓一而贯之。
《广雅•释诂》:“乾,君也。”以天与地、阴与阳、乾与坤等为君与臣、上与下定位、定性,这就为政治结构上的君尊臣卑和政治功能上的君主臣从找到了本体论的依据。它以“天道”、“天理”、“天秩”、“天序”的名义向人们宣示:君主永远处于尊、贵、刚、健、主的地位,臣民永远处于卑、贱、柔、顺、从的地位,这是天的规定、道的本质,是上帝的律令或自然的法则,任何人都不能违逆。这也是儒家政论最基本的前提。
三、“天地合德”与“君臣民一体”的政治关系论
如何调处各种政治关系?在论及这类问题的时候,儒家强调君、臣、民一体,臣民为国家之本,主张以仁义、中和、忠恕、礼让作为人际互动的准则。他们把君礼臣忠、父慈子孝、夫唱妇随、兄友弟悌等视为最理想的状态,而仁、仁义是这种道德关系的一般概括。其中君主以仁心行仁政又是最具关键意义的。如果礼是区分等级的制度规范,那么仁就是维系等级的情感纽带。仁之爱犹如一股和暖的春风回荡在森严的等级之间,沟通上下之间的情感,维系君、臣、民关系的和谐。在儒家看来,惟有礼与仁的结合,才能造就既有等差又有和谐的王道乐土,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注:《论语•学而》)
阴阳论也是儒家论证上述主张的重要理论工具。《周易•系辞下》:“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又说:“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乾卦》从阴阳相须互补的角度指出:“髙而无民”犹如“下无阴也”,会导致“亢龙有悔”。《屯卦》指出:阳贵阴贱,君贵民贱,而君主“以贵下贱”可以“大得民也”。因此,《周易》及其历代注疏者纷纷阐发天地和谐、阴阳相须、乾坤交感的哲理,然后以阴阳合德论证乾坤的合和、天地的合和、天人的合和、万物的合和,进而论证人与人之间的合和。董仲舒在“王道三纲”的框架内,大讲“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中,“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君臣父子夫妇之道,皆与诸阴阳之道”⑤。这类说法在儒家文献中很常见。
有关天地之和、阴阳合德的哲理对儒家的社会关系论和政治关系论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诸如《周易•咸卦》涉及男女、夫妇的合和,《周易•家人卦》涉及家庭内部的合和。这种宗法家庭的理想模式将男为阳、女为阴,夫为天、妇为地,父为乾、母为坤等作为最基本的构成法则。其基本特征是:父母在上(“家人有严君”),男女有别(“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各守其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据说“家道正”则“天下定”。儒家偏好以“天下一家”论天下国家,以“天下之父母”论君主角色,以“治家之道”论“治国之道”,因而由此推导出来的君臣的合和、国家的合和与男女的合和、夫妇的合和、家庭的合和属于同一模式。这也是儒家的“君臣民一体”论的重要的推导思路之一。这种合和观的本质是:在天高地卑、阳主阴从、乾健坤顺的前提下,强调天地交泰、阴阳互补、乾坤交感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具体而言,即强调在家庭和国家的构成、维系、发展中,君与臣、父与子、夫与妇等各种社会政治角色相须一体、不可或缺,彼此之间还有应尽的相互责任,诸如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听;长惠、幼顺;君仁、臣忠等。显而易见,这些有关相互责任的规范并不具有否定父子、夫妇、君臣之间尊卑、主从关系的意义。
《周易》将《乾卦》列为开篇第一卦,并以神妙的阳之德论龙之德,以刚健的乾之道论君之道,称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这就是说,“保合太和”缘起于乾,“首出庶物”归功于阳,“万国咸宁”取决于君。以这种阴阳观来论说君主与臣民的政治关系,决不可能脱离君尊臣卑、君主臣从的窠臼。换言之,儒家的君臣合和论是以君主与臣民的支配与被支配关系为基本前提的。儒家的君民一体、民为国本思想集中体现了这种政治关系论的思维方式和基本特征。
在儒家文献中,有许多与民本思想相关的命题。诸如《泰誓》的天为民而作君作师,《召诏》的“以小民受天永命”,《洪范》的“天子作民父母”,《五子之歌》的“民惟邦本”,《周易》的“汤武革命”,《论语》的“富民足君”,《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君舟民水”,《谷梁传》的“民为君之本”,《左传》的“利民则利君”等。《礼记•缁衣》所记载的孔子的一个观点最能体现儒家君民一体论的思路:“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本。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历代大儒对这些思想命题多有阐发。简言之,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
但是,一旦论及政治制度和政治主体,孔孟大儒及其传人又纷纷主张君权至上、君为政本。据《礼记•坊记》记载,孔子主张“天无二日,土无二王,家无二主,尊无二上”。《孟子》也有类似的说法。后儒讨论政体问题时大多引用这段话。据《论语•季氏》记载,孔子认为“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则为“天下有道”,否则为“天下无道”。后儒讨论“大一统”时常常引用这段话。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孔子主张“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后儒讨论君权的独占性时往往引用这句话。孔子把政治角色分为天子、诸侯、大夫、家臣、庶民五大类,明确规定其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严禁僭越擅权。这类思想也为后儒所继承。
乍然看去,“民为国本”与“君为政本”、“民贵君轻”与“君尊民卑”、“君以民为本”与“民以君为主”似乎是自相矛盾的。然而,孔孟大儒及其传人却将这两类命题交织在一起,巧妙地将二者圆融在同一理论体系之中。这种理论结构势必导致“民为国本”命题沦为“君为政本”命题的附庸。重民的主体是君主,民众只是政治的客体,是君主施治、教化、关爱的对象。正是这样的思维方式及相应的理论结构注定了儒家的重民之论与尊君之论难解难分,始终彼此扭结在一起。导致这种思维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具有特定内在结构的阴阳论,即以阳尊阴卑、阳主阴从为基本前提而大讲阴与阳的平衡、相须、互补与和谐。四、“刚柔迭用”与“宽猛相济”的统治方略论
君主如何治理臣民?儒家的回答是:实行礼治仁政。对于如何实行礼治仁政儒家有周到的设计。许多学者将其原创者归之于孔子,将其弘扬者归之于孟子。实际上,这类思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它长期居于统治思想的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推崇德治、教化的儒家主张宽柔之治、仁爱之政,反对刑罚之治、强制之政。其实不然。《周易•说卦》以阴阳之道论证“刚柔迭用”的哲理。历代注疏对这个哲理多有阐发。北宋五子之一的邵雍说:“阳者道之用,阴者道之体。阳用阴,阴用阳,以阳为用则尊阴,以阴为用则尊阳也。”张行成衍义:“道体常尽变。阳动而变,故为道之用。阴静而常,故为道之体。阳动阴静,阳尊阴卑。至于随时变通,则阳中有阴,阴中有阳,迭相为用。”(注:《皇极经世观物外篇衍义》卷七《河图天地全数第一》,见《皇极经世书》,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321页)依据这类哲理,儒家主张刚柔并济,宽猛随时,文武交替,德刑并用。一般说来,德为阳而刑为阴,因而儒家通常主张德主刑辅。但是,儒家不仅肯定“阴阳迭用”的必要性,而且主张在一定条件下以阳为用而尊阴。因此,儒家多有肯定“刑”、张扬“猛”、重视“法”的思想,乃至主张在必要时以强制、严刑为主。这种君主治理臣民的统治方略实际上以刚为主,以柔为辅,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将刚与柔、宽与猛、文与武、德与刑、礼与法等各种政治手段兼收并蓄。
儒家主张礼乐之治,而礼与乐也是一对相反相成的范畴。《礼记•乐记》及其历代注疏认为,礼与乐都属于德治的范畴。乐法天,礼法地;乐为阳,礼为阴;乐为动,礼为静;乐主和同,礼主别异。就施治手段而言,礼乐之“礼”是刚,礼乐之“乐”是柔。因此,“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在儒家看来,礼是“天地之序”,即依据“天尊地卑”确立等级秩序;乐是“天地之和”,即效法“阴阳相摩”实现社会和谐。“乐由中出,礼自外作”。礼是外在规范,重在“治躬”;乐是内心感应,重在“治心”。节之以礼,和之以乐,可以使社会既有静态的差异,又有动态的协调,既有森严的等级,又有人际的调整,既有冷静的节制,又有亲密的和谐,所谓“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礼与乐是一种刚柔并济关系,二者不能偏失,“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这是儒家统治方略的一个重要思路。
在儒家看来,礼以不齐不和为特征,别上下就是“齐”,守本分就是“和”,不齐不和的礼是实现齐与和的必由之路。孟子认为“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注:《孟子•滕文公上》)。荀子认为,“《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注:《荀子•王制》)但是,这类旨在“杜绝陵替,限隔上下”的措施,毕竟属于“体险之用”(注:《周易程氏传》卷二《周易上经下•习坎》,见《二程集》,中华书局,1981年,第845页)。因此,儒家以“刚”、“严”、“险”、“不齐”、“不和”等字眼来描述礼的基本特征。礼毕竟是以不齐求齐,以不和求和。为了避免过分强调礼而导致的偏执、偏颇,儒家以“乐”与“礼”并举,使之相互限定,相互补充。乍然看来,儒家的礼乐论更注重教化、协调的作用。实质上,乐是从属于礼的。“无礼之节,则无乐之和,惟有节而后和也。”(注:《朱子语类》卷八七,中华书局,1994年,第2253页)以节为本,以和为用,节而后和,这就注定儒家在骨子里更看重“刚”在政治中的作用。所谓以礼乐治国的实质是以刚为本,以柔为用,在维护森严的等级、刚性的规范的前提下,注重等级关系的协调与和谐。
在儒家的统治方略中,刚与柔、宽与猛、文与武、仁与义、礼与乐、德与刑都分别构成一种命题组合结构。刚柔并济、宽猛互补、文武交替、仁义相成、礼乐协调、德刑相辅等一批相关命题,构成了儒家礼治仁政思想的基本内容。在评价儒家的统治方略时,必须充分注意到儒家政治思维方式的这一特点。
五、“尊卑相正”与“正君以礼”的政治调节论
儒家以乾为阳、为刚,以坤为阴、为柔,讲究阳尊阴卑、乾健坤顺,这表明他们更看重阳与刚的价值。尊阳抑阴的阴阳论势必导致在政治上将君主置于主宰、主体、主导、主动的地位。但是,儒家也体味到阴阳相须、乾坤一体、阳中有阴、阴中有阳的哲理,因而重视乾坤和谐,期待阴阳互补,讲究刚柔并济。这类哲理也是儒家提出的各种政治调节理论的重要依据。
“尊卑相正”、“君臣相正”是《周易》的历代注解者常常涉及的话题。例如,《诚斋易传》卷八论《坎卦》上六爻,说:“君臣相正,国之肥。主圣臣贤,天下之盛福。”又如,《周易要义》卷八以“尊卑相正”论“阳卦多阴,阴卦多阳,分君子小人”。在这个意义上,有时“阳为君,阴为臣”,有时“阴为君,阳为臣”。在儒家其它经典及其注疏中也有这类思想。例如,《礼记•礼运》的“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又如,《尚书正义•说命中》孔颖达疏:“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尚书正义•无逸》孔颖达疏:“君臣以道相正”。
自孔子以来,历代大儒多有“克己复礼”、“正君以礼”、“格君心之非”、“致君尧舜”之论,他们主张君主体道、守道、行道,而臣下“以道事君”、“从道不从君”。为了防范王权走向极端而失控,他们提出一系列调节王权的理论。诸如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灾异谴告为基本思路的天谴论,以内圣外王、道高于君、以道事君为基本思路的从道论,以天赋君权、得民为君、吊民伐罪为基本思路的革命论,以立君为民、民为国本、政在养民为基本思路的民本论,以社稷重于君主、天下为公为基本思路的尚公论,以广开言路、集思广益、拾遗补缺、防范奸佞为基本思路的纳谏论等。这类思想是儒家政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着许多积极的因素。它们对中华帝制的统治思想和政治运作有极其深刻的影响,也曾为缔造中华古代文明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应当指出的是:以上五个层次的内容共同构成儒家的政治关系论的理论体系。在每一个大儒的思想体系中,这五个层次的内容彼此交织在一起。它们不可分割,同为一体,彼此之间是相辅相成、互补互证的关系。笔者只是为了便于分析而人为地分出层次。如果说天高地卑、阳主阴从、乾健坤顺与天地和谐、阴阳互补、刚柔相济等共同构成儒家阴阳论的组合结构的话,那么君尊臣卑、君主臣从与君臣一体、尊卑相正等便共同构成儒家政治关系论的组合命题。因此,在解读其中任何一个命题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这个命题在儒家理论体系中的地位、作用、价值和功能,否则就会得出有所偏颇的结论。
许多学者将儒家的民本思想等定性为“民主思想”。其中颂扬“儒家民主主义”、“儒家自由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和某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最为典型。仅从学术方法的角度看,这类学者犯了思想史研究的一个大忌,即脱离思想家的思想体系,特别是这个思想体系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各种命题的具体历史内容,单凭主观好恶去评说这个思想家的某个具体命题,乃至随心所欲地演绎发挥。
显而易见,在特定时代形成的特定思维方式和特定价值取向,注定了儒家政论有一种特定的理论结构,而这种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和理论结构又注定了儒家思想不可能属于民主思想的范畴。以儒家的君主与臣民关系论为例,它依据天尊地卑、阳刚阴柔、乾健坤顺、天地和谐、阴阳互补、尊卑相正等哲理,将君尊臣卑、君主臣从、君臣一体、君礼臣忠、民贵君轻、君舟民水等思想命题组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可以称之为“君为政本——民为国本”的理论结构。显而易见,君尊臣卑、君主臣从是这个思想体系的基本前提,其它的命题都处于这类命题的指导下。因此,不管思想家们将民为国本、民贵君轻之类的命题张扬到何种程度,他们也不可能明确提出治权在民的主张。以孟子的思想为例,他一方面憧憬“王道乐土”,主张“民无二王”,斥责“无父无君”,另一方面又倡导“仁义之政”,张扬“民贵君轻”,斥责“独夫民贼”。这就使“民无二王”之类的尊君之论与“民贵君轻”之类的民本之说共处于同一思想体系之中。依照这种思维逻辑,无论“民贵君轻”之类的命题包含多少积极因素,也不可能纳入民主范畴,而只能属于旨在以尊臣、重民来维护君主制度的政治调节理论。在君为“尊”的前提下宣扬民为“贵”,在君为“主”的前提下强调民为“本”,这类思路所能导出的政治主张不可能逾越“君仁莫不仁”的窠臼。因此,在评价这类命题的积极因素和历史价值时,必须把握恰当的分寸。
作者单位: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黄晓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