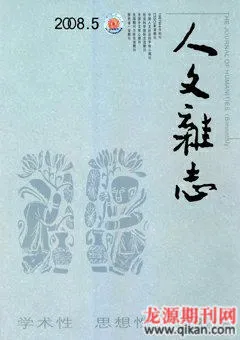为“真理”而建的桥梁:艺术作品的意义与存在论意义
内容提要 本文思考了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和意义之间的关系,探索了艺术作品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性与内容上的真理性之间的关系,提出作品的存在论意义该当建立在作品的意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以对存在论意义的反思取代对意义的探索,这正是海德格尔所犯错误的原因。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虽无益于作品意义的真理性建构,却对我们建构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和促成经验向审美经验的转化具有指引性。
关键词 艺术作品 真理 存在论 意义 海德格尔
〔中图分类号〕I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123-07
自海德格尔把存在论与艺术作品结合起来之后,艺术作品与最高存在的真理性的关系,或者艺术作品作为真理的显现方式这种观念又复活了!柏拉图和早期基督教美学曾经建立过这种关系,而后随着唯名论与经验论者的胜利归于沉寂;之后在德国的形而上学家那里这种联系又被建立起来,特别是谢林和黑格尔,“黑格尔的存在论再一次建立了美与存在的直接联系,这种联系在近代被认识论的兴起打断了,这就打断了美与真理之间的联系,使得美成为低于理性的愉悦,艺术成为制造这种愉悦的工具。而且,这一打断使得美陷入认识论的范式而丧失了存在论上的自立性”
(注:刘旭光:《黑格尔美学的存在论基础》,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6期);但随着唯物主义在美学领域内的崛起和具有实证倾向的艺术理论的成熟,把艺术与最高存在或真理联系起来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了,人们往往从认识论的视野中思考艺术作品的真理性,而不再是存在论问题。但海德格尔所引领的存在论的复兴把艺术作品再次从审美领域拉入到存在论中,并且给予其崇高的地位。这令审美主义者和艺术至上论者心醉,但也带来了一个令人痛苦的问题: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与艺术作品的具体的意蕴之间是否有联系?它的存在论意义是否有利于对艺术作品的鉴赏?
汤拥华先生的提问再次把我拖入到这一痛苦的问题之中。汤先生指责我在近年来的著作与一系列论文中,对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推重之至,但由于海德格尔的一个错误而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几乎完全否定了海德格尔的艺术之思”。对这个指责我作如此回答:我追随海德格尔是因为我认同他对“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的阐释;我背叛他是因为他无法解说“艺术作品的意义”。而我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能否在理论上跨越这二者之间的鸿沟。这个问题我、汤拥华先生、邓晓芒先生在各自的论文中都意识到了,但都没有集中而明确地把问题的症结找出来,也就谈不上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借与汤拥华先生的切磋来解剖这个问题,并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1、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
艺术作品是一个存在者,这是事实,而且这一存在者与其它存在者有存在论上的差异。和人相比,也就是和海德格尔所说的此在相比,艺术作品是“被创作存在”,用黑格尔的话说艺术作品“自在”而不“自为”,艺术作品不具备此在所具有的主体性。但是和普通器物相比,艺术作品又具有自己内在的意义世界,普通器物的存在和它的器具性之间是直接同一的,而艺术作品的存在并不直接依赖于器具性。更重要的是,艺术作品的意义世界是开放性的,就其意义的产生而言,它和接受者之间有一种对话关系,正是在这种对话关系中,它的意义才产生出来,因而就它所开拓出的意义世界而言,它具有相对独立性,它不但“接受”,而且“给予”。因此,艺术作品相对于普通器物,又具有“类主体性”。对于艺术作品的此种存在论性质的揭示源自海德格尔。
海德格尔诠释艺术作品的出发点,不是审美,也不是艺术理论,而是存在论。是借艺术作品来探寻非概念性的对于存在的源初体悟,进而借艺术作品来解说存在者之存在如何显现出来,这就使得艺术作品在存在论上具有了特殊意义。这符合德国美学的传统:一方面艺术作品是某种最高存在者的具体化或感性化;另一方面它也是“言说”最高存在的一种有别于哲学和宗教的方式。
就海德格尔自身的存在论思想来说,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此在”到“艺术作品”再到“物”这样一个过程(注:关于这一历程的详细解说,参看刘旭光:《艺术的存在论意蕴与生态存在论美学观的确立———从海德格尔的思想历程看艺术与生态美学观的关系》,《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那个被遗忘的“存在”按海德格尔的思路,在艺术作品仍保留着其源初状态,所以他是最初在《形而上学导论》中以解读诗的方式寻求关于“存在”的源始经验。在这部著作中,被海德格尔引述的诗人包括荷马、品达、索福克勒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阿那克西曼德、歌德等。为什么要从“诗”中寻求“存在”的意义呢?在《存在与时间》中有这样一段话:“如果要为存在问题本身而把这个问题的历史透视清楚,那么就需要把硬化了的传统松动一下,需要把由传统做成的一切遮蔽打破。我们把这个任务了解为:以存在问题为线索,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那些最初的、以后一直起着主导作用的存在规定就是从这些源始经验获得的。”(注: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太庆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26页)最关键的是这一句:把古代存在论传下来的内容“解构”成一些原始经验。海德格尔详细解构了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尼》中的第一首合唱诗(注: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熊伟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7页),并交待了这种解构的程序:一,首先得出构成此诗之内在纯真境界的是什么(这就是“存在”问题)而在语言应用中突出这一境界的又什么(这是指语言中所包含的对存在的经验);二,顺着诗的各段顺序走向诗所敞开的整个境界(无蔽境界);三,在这整个境界中找到了个立足点,从而明了人究竟是谁(或者说通过什么而言说存在)。这基本上就是海德格尔后来解诗(如对荷尔德林诗的阐释)的主要程序,这个过程也就是通过诗而切入存在的过程。在这里,海德格尔找到了一条通达“存在”和言说“存在”的新路——诗。
那么其它的艺术形式是否可能是对“存在”之“去蔽”?如果诗能作到,其它艺术形式当然能作到。结果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一文中,建筑、绘画、雕塑、戏剧等艺术形式也成为言说“存在”之源始经验的一种形式。艺术作品成为摆脱“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地位”的非此在式的存在者,从而成为存在之真理显现的一种方式。更为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对艺术作品“自身”的追问是在传达这样一种思想:存在者有其不关此在的本身存在。也就是在要非此在的存在者处寻求某种“主体性”,也就是对所谓“自身”的追问。对艺术作品自身的追问就包含着这样一种意味:把艺术作品从与此在的关系中解放出来,不从关系的角度研究艺术作品的性质与意义,也就是斩断艺术作品和自身以外的所有关联,这其中也当然包括审美关系,直接逼向艺术作品的作品性。而这个作品性,海德格尔认为是存在之真理的发生,是“世界”与“大地”的“源始争执”。
艺术作品的这种存在论意义在海德格尔的思想体系中具有桥梁性的作用,它让我们走出器具狭隘的工具性存在,走向聚合天地神人的“四方游戏”之境,引导我们从对世界的功利性要求中走出,去融入尊重万物存在,追寻生成与创造的自由、澄明之境。在海德格尔的思想旨归中,艺术作品借其存在论意义,指引我们走向一种新的世界观、新的人生境界,新的物我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层面上,“艺术就是从大道层面上得到思考的”②海德格尔:《林中路》,孙周兴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70页)。而作品是真理之置入,考虑的是“艺术就是人的创作与保存”②,这里的“人”按海德格尔所说,是指“人类”,当他思考艺术与真理的关系是,他考虑的是“人类”与艺术的关系!人类创作着艺术,而艺术保存着,言说着人类的存在。
我们来看海德格尔所举的例子。
“一个建筑,一座希腊神殿,没有摹写任何东西。在岩石裂口的峡谷之中,它纯然屹立于此。这一建筑包含了神的形象,并在此遮蔽之中,过敞开的圆柱式大厅让它显现于神性的领域。凭此神殿,神现身于神殿之中。神的这种现身是自身中作为一神圣领域的扩展和勾勒。然而,神殿及其围地不会逐渐隐去进入模糊。正是神殿作品首先使那些路途和关系的整体走拢同时聚集于自身。在此整体中,诞生和死亡,灾难和祝福,胜利和蒙耻,忍耐和衰退,获得了作为人类存在的命运形态。这种敞开的相联的关系所决定的广阔领域,正是这种历史的民众的世界。只是由此并在此领域中,民族为实现其使命而回归到自身。”④
海德格尔:《诗•言•思》,彭富春译,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42页。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看到一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这只是在神庙这件艺术作品中看到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
“建筑屹立于此,建立在岩石的基础之中。作品的这种道出了岩石那种笨拙而无所迫使的承受的神秘。建筑于此,建筑顶住了其上凶猛的暴风雨,同时也首先使暴风雨自身显现了其暴力。岩石的光泽和闪光,尽管它似乎只靠的恩惠,但首先使它光明的是白昼之光,天空的宽广和夜色的黑暗。神殿坚固和耸立,使不可见的大气的空间成为可见的。作品的坚固性反射碰上海潮拍岸的巨涛,而它自身的宁静则显出了海洋的凶猛。树木和野草、鹰和公牛、蛇和蟋蟀,首先进入它们研究的型态,因此显示出它们所是的东西。古希腊早先称这种在自身和在所有物中的出现和产生为Physis。它澄明和启明了人靠何和在何之中,建立其居住。我们称这种基础为大地。此词所说不相关于其它沉积的物块的观念,也不只是相关于行星的天文学观念。大地是一切敞开者向其敞开之地并且作为这样一种敞开者回归之地,在敞开者中大地作为庇护者而现身。④
一个非此在式的存在者——艺术作品,开启着世界,而且海德格尔用了四个“首先”,这似乎是说,“世界”只有通过艺术作品才被建立起来,也就是说,人类创造艺术并不是为了反映世界,而是创造世界!更何况“历史的民众的世界”(或译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只有借艺术作品才敞开出来。
这个结论很有诱惑性。以这种方式解读艺术作品,深沉而大气,超越于感性的审美之上而成为精神与艺术之间的交流,成为欣赏者与艺术作品这两个存在者关于某种存在的共同言说。这是一个成功的解说,这个解说没有借助外在于艺术作品的社会关联,在这个解说中,历史性民族的世界被开启了,而大地也展现了出来,“真理”发生了。不,这甚至不能用“解说”这个词,应当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倾听”,不是看者在解说什么,而是欣赏者在倾听艺术作品的“道说”。
从存在论的角度来说,艺术作品开启着,庇护着存在者之“存在”或“真理”,这就是为什么人类需要艺术。
但艺术作品中真得有这种“真理”发生,而且是“自行”发生吗?既然讨论的是艺术与人类的关系,那是不是说所有的艺术作品都具有这种存在论性质,在之中都可以听到这种“真理”?海德格尔回避了这个问题,他把自己对艺术的关注限定在“伟大的艺术作品”,因此刚才我们所说的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性质仅仅是伟大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性质。可问题是“伟大”的边界是什么呢?更麻烦的是,“谁”能听到这种言说?作品之“作品性”真得是自足的吗?如果说艺术作品中有“意义”发生,而且这种发生是必然的,这没错,这也是现象学美学想要导出的结论之一,但问题是,什么样的“意义”?海德格尔的理论之有效在于,艺术作品肯定有意义发生,这种发生以世界与大地的争执为基础,这是令人信服的。可是当我们追问到“什么样的意义”时,艺术作品总体上的存在论意义和艺术作品的“具体意义”之间就不是同一的。我们承认艺术作品存在着并言说着存在,而且从某种层面上说是自在存在,但同时它还是一个社会存在,一个时间性存在,一个“被创作存在”。
2、艺术作品的意义
艺术作品在存在论上的特性不应当被否定,形而上学家们在这个方面的探索不失为一种启示,毕竟,艺术作品有别于器具,也有别于此在主体,它的这种存在论性质应当是研究艺术作品的起点。但这并不是说,艺术作品就是独立于社会历史存在的。艺术作品所传达出的思想、情感、意蕴、它所借以表达内容的形式,我们笼统地称之为“意义”,都是具有社会历史性的。我们无法否认,艺术作品是一个社会存在,一个社会事实,而不仅仅是博物馆的某个角落中的自在存在。艺术作品源自人类的实践活动,而实践的社会性使得艺术作品本身只能是一个社会存在。这就意味着,艺术作品处在社会关系中,被社会所决定。
“社会性是一个可怕的字眼,它意味着,事物只有在社会关系网中,作为该网的一个环节才是现实的,才获得自身的规定性。社会性是对事物的功能与价值的要求,事物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是‘为它的’,而不是‘为己的’”(注:刘旭光:《作为社会产品的艺术作品——马克思主义艺术生产论再研究》,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艺术作品的社会性与自律性或自在性是矛盾的。艺术作品的社会性说明艺术作品的意义是被规定的,并且是不断被规定的,而艺术作品的自律性或自在性却想标榜艺术作品有其类主体似的独立性。就艺术作品的具体意义来说,它显然不是自在性能够解说的。艺术对于社会有一种虚假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的本源在于:艺术作品就其产生的源动力而言,是创作主体对现实的双重要求所致,首先创作主体会依赖于现实,作品的内容以现实的某一部分为内容,在二者间形成反映关系;同时艺术家也会和他所处的现实之间产生某种间离性的要求,这种要求使得艺术作品的内容会和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站到现实的对立面。有时艺术由于站在社会的对立面才成为艺术,也就是说超越于社会之外是艺术作品的社会性的表现方式。
艺术对现实的虚构性反映和艺术对现实的批判态度都使得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间接的,每一个现实的社会要求在艺术作品中都只能以间接的方式呈现出来。但麻烦的是,当艺术作品的内容和现实的这种直接或间接的关系由于“现实”在时间性的长河中不再具有现实性时,艺术作品就仿佛获得了对于现实的独立性。结果艺术作品的意义就显得具有某种超越时间性的持久性,这就会诱使人们去思考,艺术作品是不是有超越于时间之上的某种“作品性”。
但这种独立性是虚假的,因为艺术作品作为现实,是与现实的功利目的相结合的,艺术作品只是由于承担了某种功能才被创造出的,而功能的背后是需要,包括生物性需要和文化性需要。所谓功能意味着满足需要,人类在各种需要的刺激的推动下,不断地创造出新的文化要素并不断地扩大着文化要素的功能价值。无论是一根木杖、一支猎枪、一件祭器或一件艺术作品,只有充分理解它们在经济上、技术上、社会上及仪式上的功能或用处,才能对它的出现、传播及传播过程中形式上的变化做出合理的说明。
作品的意义就其现实存在而言,必有其本源,而其中最直观的本源,就是艺术家。艺术家创造艺术作品,艺术家赋予自己的情感、观念、认识、欲望、意识等生命因素以形式。艺术家言说着什么,而艺术作品就是他的语言。这一语言包括形式、质料、色彩、结构、节奏、形象等等构成艺术作品的诸多物质性因素,这构成艺术家的语言。就艺术作品的意义而言,艺术家是最透明的现象,艺术作品的意义可以被看成是艺术对他的心灵世界的表现、再现、传达、反映,研究,,这就形成一种理论上的模式,认识艺术作品的意义,就是去认识艺术家及其心灵的隐秘。
但麻烦的是,艺术家控制不住自己的语言,艺术作品相对于作家的独立性,使得艺术作品或许有其“本意”,但本意却不是它唯一的与现实的意义。艺术作品一旦被创作出,它就具有了相对于艺术家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体现着被艺术家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被有选择的“听”,甚至“误听”,它的线条,它的结构,它的色彩,甚至它的某一个局部,都可以被看作是某种“言说”,而艺术家人可能根本没有这样想过。这样一来,艺术作品的意义就有了第二个源泉:被“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看”。
这实际上把读者或接受着作为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第二个源泉,海德格尔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谈至真理的保藏时已经有这种意识,而伽达默尔则把它上升到“艺术经验里真理问题的展示”这一高度。而艺术史的事实正如伊格尔顿所说:“‘我们的’荷马并不是中世纪的荷马,我们的莎士比亚也不是他同时代人心目中的莎士比亚;情况很可能是,不同的历史时代出于自己的目的创造了‘不同的’荷马和莎士比亚,并在这些作品中找出一些成份而加以重视或贬斥,尽管这些因素并不一定相同。换言之,一切文学作品都被阅读它们的社会所‘改写’,即使仅仅是无意识地改写。没有任何一部作品,也没有任何一种关于这部作品的流行评价,可以被直截了当地传给新的人群而在其过程中不发生改变,虽然这种改变几乎是无意识的;这也就是为什么说被当作文学的事物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事件的原因之一。”(注: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4页)这也说明,艺术作品的意义是一个极不稳定的事件,读者以社会群体的形态必然改造着文本。
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第三个来源是在其在时间性存在中必然获得的历史性意味。时间在这里意味着,某个特定时代的艺术作品以自身的存在见证了这个时代的在场。当我们面对这件作品时,我们面对的是这件作品的创造者,是他的心灵世界与生活世界,以及沉淀在他的世界中的他所处的那个世界的某些碎片,我们借这件作品窥到了这些碎片,并且把这些碎片视为进入那个已经逝去千年的世界的道路,这件作品由于作为道路,或者作为道路的指引而超越了作品自身的审美性质,而成为一个窗口或者一个符号。这个符号让我们跨越时光而直面一个已经逝去的世界,这时这个时间跨度不是被忽视或者掩盖,而是被凸现出来,面对这件作品时我们所产生的喜悦,与其说源自对于它的美的欣赏,不如说源自对对它所凝定的时光的慨叹。因此,时间本身是一个内在于艺术作品因素,这个因素凝结的越多,就意味着作品之所包含的意蕴越深厚,越突出。这种时间性还体现在一个更专业化的方面,既艺术作品的创作技术上所体现出的历史性的意义,技术上是革新命名得艺术作品因此会具有一种超越于内容之上的时间性,而从创作技术出发,我们可以发现艺术作品的一切形式因素都可以因此而获得时间性的“意义”。
艺术作品本身的社会性和艺术作品之意义的三个来源说明,艺术作品的意义不是来自它自身,而是来自一些外在于艺术作品的因素,艺术作品就其所传达的意义来说,不是自律的。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难题:艺术作品就其存在论上的类主体性,它的存在论意义,和它的意义之间有关系吗?
3、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与意义
第一种回答:没有关系。这就意味着,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仅仅是把艺术作品作为一个特殊的存在者,考察这个存在者和其它存在者在存在状态上的差异,这个差异不关涉作品所传达的具体内容。但问题是,如果不关涉内容,一件艺术作品和一件器物如何区分开?这个回答海德格尔是不会同意的,因为在他看来“存在就是存在的意义”,因此,艺术作品的存在只能来自它的意义,艺术作品一定有与普通器物不同的意义世界,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把一把作为器具的锄头和一个作为艺术作品的石雕的锄头区分开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强调艺术作品的作品性在于真理自行转入艺术作品。但是他的矛盾在于,他一方面认识艺术作品中的真理是“自行”置入,也就是说“世界”和“大地”的争执“是源始的”,这种意义的发生无需作品之外的因素介入;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艺术作品的意义在于对存在者之存在的揭示,是艺术作品把它所描绘的存在者的意蕴世界的揭示出来。前者如他所描述的神庙,后者以梵•高的农鞋为例。前者把艺术作品的意义归之于它的存在论意义,把这种“真理的自行发生”视为艺术作品之为艺术作品的作品性;而后者引出了麻烦,也就是我所讨论过的他犯的错误。
第二种回答:有关系。这似乎是唯一的回答,因为如果不承认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与意义之间的必然联系,就没有办法把艺术作品和普通器物区分开来。所以这种联系对于艺术作品来说是规定性的东西。那么问题是,是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规定着作品的意义,还是作品的意义使得艺术作品才获得自己的存在论意义?存在论是没有具体内容的,它只标示艺术作品和其它器物在存在状态上的差异,而不是对艺术作品的规定性,它是建立在艺术作品的规定性之上的东西。那么回答只能是:是艺术作品的意义规定着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
现在我们理清的艺术作品的“意义结构”,艺术作品的时间性的“意义”,也就是其内容上的和技术上的意义是奠基性的,这个意义使得艺术作品获得自身的规定性,在这个规定性上,建立起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海德格尔以其在存在论上的深刻洞见,揭示出了艺术作品独特的存在论意义,并借这一存在论意义突破此在的基础存在论地位,从而走向天地神人的四方之境。但是,海德格尔颠倒艺术作品的“意义结构”,以“存在论意义”来规定“意义”,在面对艺术作品时,首先认定作品中有真理发生,存在者之存在被揭示了,这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而后为这个“真理”填充内容。他以这样的方式解读古希腊人的诗,建筑,戏剧,还有荷尔德林的诗,里尔克的诗,梵•高的画。
问题是,为这个“真理”填充内容的时候,填充物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何在?只有当这个填充确实具有“真理性”的时候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性质才有其根基。我在《当代美学对艺术真理性的几种理论与启示》(注:见《社会科学战线》2007年第1期)一文中,结合着围绕海德格尔所描绘的那幅梵•高的画所产生的争论,概述了艺术作品真理性的本源。海德格尔的错误在于,他往“真理”这个瓶子里放错了东西。
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是建立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之上的,而不是建立在“存在论意义”上,而这种真理性内容的复杂构成使得它只有通过反思才能被获得,而不是通过直观,这就构成了海德格尔无意间所面对的矛盾,他强调真理的自行发生,这意味着欣赏者似乎无需反思就能获得这种真理性内容;而艺术作品的社会存在使得它的真理性内容只能处在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中,因而真正需要面对的是艺术经验中真理性的“内容”是如何生成的,而不是借助于欣赏者本人的直观,欣赏艺术和欣赏美在这里是有本质差异的,前者奠基于概念性的反思,而后者直接通过直观。
但是引起我兴趣的还不在这里,是什么诱使海德格尔认为他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体验或者说感受就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 我在《谁是凡高那双鞋的主人——关于现象学视野下艺术中的真理问题》(注:见《学术月刊》2007年第9期)一文中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结论是现象学方法造成了把艺术作品的真理性的“本源”当作“艺术作品内容”的真理性的本源,这就违反了我们刚才得出的结论: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建立在艺术作品的意义之上。现象学强调在艺术作品中有意义“发生”,如果这一“发生”的必然性被视为“真理”的话,这一真理仅仅为存在论意义,却无法解释意义作品的意义。当海德格尔说艺术作品让存在者之存在显现出来,这没有错,可是当面对一个具体艺术作品时,也就是说,需要具体说明什么样的存在者的什么样的存在的时候,就必须研究这幅艺术作品的内容的真理性的本源,这就不是凭直观可以获得的了,而海德格尔恰恰是把自己在审美直观中关于艺术作品的审美想象当作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
意义的“本源”不能代替意义自身,对于艺术作品的存在论结构的研究不能代表对艺术作品具体内容的研究(英伽登);对审美经验的生成过程和审美经验的构成的研究,不能代替对审美经验的内容的研究(杜夫海纳);对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的研究不能代替对艺术作品的具体意义的研究(海德格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认为现象学的方法对于美学的适用性是值得怀疑的。现象学关注的是审美的形式,而不是审美的内容。当内容意义上的真理性是虚假的,那么“发生”(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性就是没有根基的。
无论汤拥华先生还是邓晓芒先生在讨论海德格尔关于“农鞋”的描述,都没有意识到海德格尔这种对作品的内容的描述所包含的方法论上的矛盾。而当汤先生如杜夫海纳般试图把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寄托给那些能够把艺术作品置入到艺术史之中的“能人”的时候,仅仅是想靠“能人”解决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真理性,这不是海德格尔关心的问题,也在实际上否定了海德格尔这种“非能人”解读作品的权威性。同时,由于没有意识到艺术作品在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性和意义(内容)上的真理性的区别,试图用“一个整体的艺术世界”来解决内容上的真理性也没有抓住问题的要害,关键是:有没有可能把艺术作品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性与内容上的真理性统一起来。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样把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上的真理性与意义上的真理性结合起来?也就是说,现象学的方法和现象学对于艺术作品与审美经验的研究方式对于我们对艺术作品的鉴赏有什么样的意义。海德格尔对神殿的阐释在美学上是令人满意,他对诗的诠释也让我们的鉴赏在超越性的解读之中获得一种“理性的愉悦”,只要我们能够容忍其中的牵强附会。追求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对待艺术作品的方式把我们从“直观”或者说“肤浅”的审美中解放出来,康德意义上的或者说本真意义上的审美由于把自己仅仅限定在“对象的形式的主观合目性”上,因而显得与存在论无关,与真理无关,甚至与内容无关。重建艺术作品与真理性的联系无疑是对抗这一形式美学或者说感性学意义上的美学的最有效的武器,因此,现象学从探求意义本源的角度来建设艺术作品的真理性是有价值的。真正的问题应当是,存在论上的真理性应当建立在内容的,或者意义的真理性上,而不是倒过来。
现象学们对艺术作品与审美经验的研究对于现实的审美活动来说,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性,艺术作品与审美经验的存在论结构对于艺术研究者与欣赏者来说,是给出了一个审美对象的建构性的过程,根据这个过程去建构“作为审美对象的艺术作品”和具体的审美经验,这是现象学美学在方法论意义上最大的启示,因为在这里现象学美学秉承了胡塞尔对于“描述”的执着,只要是描述,就体现着对过程的执着,一件作品以什么样的过程成为一个“审美对象”,和一种经验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审美经验”,这实际上给出了我们欣赏艺术作品和审美的意向性过程,这一过程是指引性的,就像英伽登的“四层次说”可以看作欣赏文学艺术作品的一个基本过程。
现在的问题是,“发生”意义上的真理性只有建立在意义的真理性之上时,才有说服力,海德格尔的错误的启示在于,如果他能以研究的态度弄清那是梵•高本人的鞋,而不是农妇的鞋,那么他同样可以借描述艺术作品而开启出梵•高的生存世界来,从而揭示出作品的真理性内容,把鞋和艺术家的生存世界联系起来,超越审美的直观性,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与理性反思结合起来,那么这种对于艺术作品的解读就是具有“真理性”的,也是深刻而具有建构性的。
很高兴看到汤先生和我思考的同样的问题:艺术作品的世界和艺术作品中的世界,可是我们俩的结论是相反的,汤先生认为海德格尔执着于艺术作品中的世界,而我认为海德格尔实际上是从存在论上认为艺术作品的世界具有发生意义上的真理性而把艺术作品中的世界随意化了。艺术作品开启着世界,这是他看重的,但艺术作品开启着什么样的世界,海德格尔的错误说明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欣赏者,结果就有了主观上的随意性。
揪住一个错误不放不是因为吹毛求疵,而是出于理论严肃性。作品的存在论意义由于建立起来了艺术作品与真理之间的联系而令人心醉,但这种联系如果不是建立在对艺术作品的意义的真理性探索上就是无效的。在前一篇文章(指《谁是凡高那双鞋的主人——关于现象学视野下艺术中的真理问题》)中由于现象学美学无益于作品意义上的或者说内容上的真理性而引起了我的疑心和戒心,在这里,我把这种戒心转化为一种思考的动力:我们应当如何在研究和欣赏中利用现象学美学的基本方法。必须在艺术作品的存在论意义与意义之间搭起一座桥,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只发生在这座桥上。作品的“存在论意义”如果没有“意义”的支撑,就是空洞的;作品的意义如果不能上升到存在论意义,就是琐碎而盲目的。我们崇敬艺术不单单是因为艺术美,而且还因为艺术作品的双重的真理性。这篇短论仅仅是为这座桥寻找基石,感谢汤先生的提问,提问让我认识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