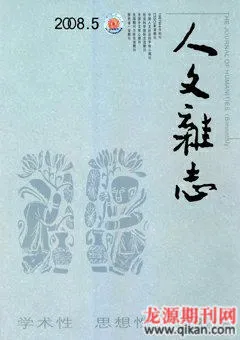比较语境与中国文学研究的自我意识
内容提要 徐复观力图在比较语境中对古典作出现代的阐释和研究,但他反对用西方的文学体系作为标准来衡量中国文学。他强调文学研究要走出进化论的观念,采取历史的整体视角。他认为,要以中国文学自身的传统为脉络来建立研究的基点,而避免那种以西方某种理论概念为先在体系的研究方法。基于这种学术的自我意识,他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实用性,将其作为传统文学的主要特征加以表彰,从而构建出与一般从纯文学角度出发建立的中国文学史观念。
关键词 徐复观 比较语境 自我意识 实用文学传统
〔中图分类号〕I0-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108-07
中国现代学术是在西学影响下形成的,是以西学作为参照系,或者运用其方法作为工具来分析中国的传统学术。现代传统文化研究里,西学是一个或明或潜的比较。对我们来说,比较是使中学获得新的意蕴的有效途径,现代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也是在比较视野下进行的。
一
在中国文艺研究中,徐复观自觉吸收西方的文艺理论,以之作为观照中国文学的一面镜子,他力图在中西的比较语境中对中国传统文艺思想作出现代阐释和研究。他说,“我常常有一个想法,希望能在世界文化的背景下来讲中国文化。所以我在东大开文心雕龙的专书以前,最大的准备工作,便是摘抄了约三十万字的有关西方文学理论批评的东西。”
①徐复观的中国文学研究贯穿了现代意识,他认识到中国文学的审美特性与特征只有在西方理论的参照下才能获得现代的阐释。应该说,西方文学理论的引入使得我们的眼界比以前更加的开阔,比如以往中国人重视的是诗歌和散文,对戏剧和戏曲并不重视,由于西方叙述文学的发达,让我们重审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小说与戏曲,对小说、戏曲的发掘可以说大大丰富了以往中国人的理解,更让传统的雅俗观念具有文学意义。但是,徐复观认识到,我们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必须符合中国文学自身的发展,我们必须在中国文学的历史语境中阐发它,从而凸现出中国文学自身的特性。西方理论作为参照可以启发我们打开视野,却不能代替我们对自我问题意识的研究。就文学研究而言,徐复观认为,在对具体的古代文学阐释中,西方的理论难以对中国文学进行有效的阐释,很难将中国文学的独特魅力展现出来。任何简单照搬西方理论,将中国文学纳入其中做比附的阐释方法,都是一种偷懒的行为,这忽视了中西文学的差异远比其共同性多。对西学理论的生搬硬套,其结果是使得中国文学经验被遮蔽,仅成为西学理论普遍性的一个注脚。
徐复观认为,我们应通过置身于历史情境之中来获得关于文学的具体感受,还原中国文学发生的本来面貌,从历史变化的角度来理解文学观念。这正是他一直强调的,思想史文学史的研究必须用“动的观点”来研究,所谓“动的观点”,就是说,任何的文学现象并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源有流的,它是文学历史的产物,带有历史的烙印。因此不能孤立的研究文学现象本身,而应该同时关注文学现象的历史根源及其发展,这样对文学研究才是动态的,符合文学现象的历史性。而现代许多“研究文学史的人,多缺乏‘史地意识’,常常是以研究者自己的小而狭的静地观点,去看文学在历史中的动地展出。不以古人所处的时代来处理古人,不以‘识大体’的方法来处理古人,也不以自己真实地生活经验去体认古人。常是把古人拉在现代环境中来受审判”。(注: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自序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因此,徐复观强调采用一种内部视角的方法,即从历史文本出发来阐发历史本身,用中国文论本身的话语来阐释中国文学,他极力避免用现代科学实证方法,他力图把握中国文学的内在特征,这正是徐复观对中国文学解释研究的核心所在。最能体现徐复观这种阐释方法的是他对“文学”概念本身的理解,因为这是任何研究中国文学首先遇到的问题:在中国历史文化的语境中,文学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如果要复活中国文学就必须对“文学”在其原初的语境中自身的涵义做出符合其自身的理解。
“五四”之后,中国文学研究较早开始了建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的现代学术化努力,可以说,中国文学的审美特征和特性是在西方艺术理论的启发下才作出了系统的理论化阐释,中国文学的价值和特征在这种比较的语境中获得较清晰的了解。但是这种启发又容易使得研究者有意无意之中将西方文学的发展模式以及艺术的审美趣味视为文学发展的普遍模式和艺术审美的最高标准。“五四”以来,西方文学理论中影响中国文学最深远的就是纯文学观念,用现代的纯文学概念来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成为之后的文学研究主流,一部中国古典文学史就是纯文学史。
但是,文学是一种生存的文化经验,它不应该存在任何先验的文学或者文学的本体理念,任何将西方文学经验视为文学普遍性的看法,就是已经将西方的文学经验和实践预设为文学的本体,从而成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先验理念。不同地域国家的文学实践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文学模式,中国的文学研究,中国文学的经验如果不仅仅是为世界文学提供一种新的地方性经验,而是丰富我们对文学的形态,文学性的理解。文学研究作为学科来说,也只能是经验性的,文学的概念应该由文学的实践中产生,文学的审美以及艺术的趋向也只有放在一个独立的文学系统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认同。正如比较文学的理论家迈纳所指出,文学理论体系产生于丰富的文学创作实践及其作品分析中,而“当文学是在一种特殊的文学‘种类’或‘类型’的实践基础上加以界定时,一种独特的诗学便可以出现”(注:〔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学的具体经验不是用来证明西学的正确与否,或者为其理论提供一个东方的注脚。即使从世界范围的文学发展来说,纯文学观念也不过是西方文学发展到近代以来才出现的,徐复观指出,所谓艺术的自觉,纯粹艺术的观念直到康德才出现。他说,“古希腊的艺术模仿说,一直支配到欧洲的十七世纪。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出,对美的成立、艺术的成立,才开始了真正地反省”。(注: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序》,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页)他较准确的把握住了西方美学的发展的史实。艺术自觉的理论渊源来自于康德,康德系统地阐发了审美活动的无功利性和相对独立性,为艺术划定了自我的独立地盘。而在19世纪中、后期欧洲的唯美主义运动中,“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更标明了以艺术自足性和独立性为特征的“纯文学”的艺术追求。
文学的观念与理论首先来自于具体的文学实践,先验的文学本体性并不存在。即使就西方文学而言,“文学”观念的形成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文学理论家乔森纳•卡勒指出:“文学就是一个特定的社会认为是文学的任何作品,也就是由文化来裁决,认为可以算作文学作品的任何文本。”(注:〔美〕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页)他说:“文学作品的形式和篇幅各有不同,而且大多数作品似乎与通常被认为不属于文学作品的相同之点有更多的相同之处,而与那些被公认为是文学作品的相同之处反倒不多。”在西方,现代的纯文学观念实际上也是迟至19世纪才诞生。乔森纳•卡勒指出:“如今我们称之为literature(著述)的是20个世纪以来人们撰写的著作。而literature的现代含义:文学,才不过200年。1800年之前,literature这个词和它在其它欧洲语言中相似的词指的是‘著作’或者‘书本知识’。……如今,在普通学校和大学的英语或拉丁语课程中,被作为文学研读的作品,过去并不是一种专门的类型,而是被作为运用语言和修辞的经典学习的。……比如维吉尔的作品《埃涅阿斯纪》,我们把它作为文学来研究。而在1850年之前的学校里,对它的处理则截然不同。”(注:〔美〕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1-22页)可以说,这种对文学的看法与中国古代对“文”的看法就比较接近。可见,纯文学观念只是现代西方文学发展的一种观念,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文学本身是一部流动的历史,文学的观念并不是不言自明的,文学的概念是在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形成的,文学的概念本身就表明文学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演化和建构的过程,它是在与其它知识的不断区分之中被表述出来的。纯文学的观念只有在科学、道德、艺术分治的现代性知识景观中才能建立和凸显出来。因此,所谓的“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只能是一定时期的产物,并不具有先验的合法性。既然文学的观念并不是先验的,文学在中西方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文学的观念随着文学的变化发展而逐步形成的。那么仅仅用今人的纯文学观念来衡量文学史的材料,以之贯穿文学史研究,其结果就是大量文学史上的文学作品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这样的文学史不过是一种单一观念史的产物,它不能对文学发展的历史情形作出真实的描述以及合理的评价。
二
徐复观认为以庄子影响的“为艺术而艺术”与以孔子影响的“为人生而艺术”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两种范型。徐复观对绘画和文学在审美上的分野,从美学上说,暗合于康德关于审美的论述,绘画(视觉艺术)是一种纯粹的艺术,比较接近康德所说的“纯粹美”;而文学艺术本身因为形式因素比绘画要弱,而作为“依存美”的特征比较明显,从康德那里以纯粹美为基础的审美论对文学的解释效用也就更低了。因此对这两种美的艺术,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审美理想,绘画是气韵生动的空灵之美,是神韵之美,是偏向虚的美;文学是偏向实的美,是充满了内容的美;这和康德美学有惊人的相似。钱钟书先生说:“中国传统文艺批评对诗和画有不同的标准,评画时赏识王士祯所谓‘虚‘以及相联系的风格,而评诗时却赏识‘实’以及相联系的风格。”(注:钱钟书:《七缀集》,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5页)钱钟书用美学的所谓“虚实”来区分中国文艺在文学和绘画上的审美区别,而这种审美区别,根源恐怕就是徐复观所阐述的,中国文学具有实用性的传统,这就使得中国文学的美学上偏于“实”;而中国绘画则是秉承庄学的精神,构成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一书对庄子影响下的中国绘画构成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精神进行了深度阐发,而他关于“为人生而艺术”实用文学传统的构建,则是贯穿其《中国文学论集》的文学观念核心。但在目前徐复观的文艺思想研究中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这主要是因为以往我们对文学的理解太狭隘,被西方的文学及其理论观念所束缚。而徐复观实用文学传统的提出,是建立在对“五四”以来文艺研究深入反思基础上的。
中国文学里面纯文学的概念实际上是“五四”运动以来新文化影响的结果,文学并不是先验存在的。在五四一辈的学者中,纯文学观念与进化论纠结在一起,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杂文学与纯文学,构成了古今中西,落后与进步的关系。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设置了进步与落后的文学设想,将古代文学设想为落后的文学,白话文为新时代文学的代表,终结了文言文学的时代,这种进步论的思想观念下,文学研究的核心中民间文学成了中心。在这种进步论的视野里,俗文学与纯文学成为文学研究的中心,它们体现了进步论中的文学性观念。但是这种中西比较,恰恰造成对中国文学特征的遮蔽。徐复观指出:“进化的观念,在文学、艺术中,只能作有限度的应用。历史中,文学、艺术的创造,绝对多数,只能用‘变化’的观念加以解释,而不能用‘进化’的观念加以解释。可是时下风气,多把个人的文学观点,套上未成熟地进化观念的外衣,无限制地使用,结果,文学史中十之八九的人和作品,都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变成了过时的肥料。”(注:徐复观:《中国文学精神•自序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由这种中国文学的自我意识出发,他重新评价了在纯文学视野下被贬低了的中国文学的非审美中心的散文,突出了实用性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的地位。我们不能够用现代文学的纯文学概念来规范中国文学的类别,不能将中国传统的文学中很多的样式通过纯文学这一概念被排除在文学研究之外。徐复观实际上通过对中国文学史一种实用的文学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以叙事小说为主体的文学史的论述,阐明了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与个体性特点。唯有如此才能阐明中国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正如海外华人学者刘禾指出,现代的“文学”这一概念通过把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视为“纯文学”,而把所有其他形式降到非文学的地位。在小说、诗歌、戏剧和散文被命名为“文学”的同时,其他古典文类则被重新分配到“历史”、“宗教”、“哲学”以及其他的知识领域,而这些知识领域本身也是在西方概念的新译名基础上被创造出来的。这种“文学”的概念与古典的“文学”概念大相径庭;然而,今天的“中国古典文学”也被迫按照现代文学的观点被全新地创造出来。“他们按照自己时代对欧洲现代文学形式和体裁的理解,实际上对中国文学进行了重写。……不论在这个基础上重新发现了什么东西,它们都不可能摆脱一种总是有欧洲文学参与的学术史和合法化过程。人们总是能够提出这样的异议:为什么一谈到体裁形式,就要用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形式来限制人们对汉语写作中可能存在的其他体裁类型而被排除在文学史之外呢?”(注: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263-307页。(另参见刘禾:《语际书写——现代思想史写作批判纲要》,上海三联书店,1999。)因此,对古典文学的研究,必须站在历史的角度,恢复中国人对文的看法。徐复观指出:“研究西汉文学,首先应在西汉人之所谓文学的范围内探索。西汉人的所谓‘文学’,姑且以《汉书•艺文志》的诗赋略为基点。”而“由诗赋略而可以了解西汉人所承认的文学范围,不仅后世之所谓古文(散文)未包括在内,且谏谥箴铭等有韵之文亦未包括在内,其范围较东汉及后之所谓‘文学’为狭。”③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54、398页)实际上,中国古代的文含义十分丰富。最早的“文”字,在甲骨文中是纹身的人像的缩写。其后,《易•系辞下》云:“物相杂,故曰文”。意思是指凡由线条与色彩构成的事物的美的外表形态,都称为“文”。可以说,从自然界的森罗万象到人类社会的礼仪道德、典章制度、言论著作、诗乐舞蹈、工艺美术等 都属“文”的范围。正如刘师培《广阮氏文言说》所云:“三代之时,凡可观可象,秩然有章者,威谓之文”。“文学”也不是指今天的文学作品,而是泛指学术文化。文学一词最早出现在《论语先进》:“文学:子游、子夏”。 杨伯峻《论语译注》说:“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最典型的莫过于《诗经》,今天我们自然视为文学作品,但在先秦,尤其春秋以前,人们是把它作为政治、道德和文化的百科全书来看待的。如《左传信公二十七年》载赵衰云:“《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论语•泰伯》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则说明它是进行政治、伦理和道德修养教育的重要手段。也就说,从先秦开始,文学所包含的内在的纯粹审美的要求并不是很突出,文学更多的与广阔的社会生活相联系。
因此,就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而言,我们应该摆脱近代以来西方文学的影响,“文学”观念应该以中国文学自身的文学发展来界定,如果按照西方文学的标准,则会将很多中国的传统文学排除在研究之外,这无疑就会造成对古代文学的偏见,造成中国古代文学不如西方文学的判断。只有立足于传统的文学观念,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学本身,了解中国文学有着自身的审美特点、追求与发展规律。“研究西汉文学,首先应在西汉人之所谓文学的范围内探索”。
③这表明徐复观有着鲜明的本土意识,认为在中西比较中,中学不应成为西学理论普遍性在中国的一个注脚。中西之间应该是一种平等对话的关系。但在五四以来很多的学者看来,现代的学术研究往往意味着斩断传统,中国的现代学术必须要建立在与传统的断裂基础上。这常常表现在在中西文学比较中存在这样一种问题的情境:中国为什么没有史诗,中国为什么没有悲剧,以及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的想象力比较的贫乏等等问题。徐复观指出这种中西比较里隐藏的西方中心意识,他说:“有的研究西方文学的人,曾倡言‘中西文学之不同,在于中国文学中的想像力的贫乏’。应分两方面来了解。一方面是,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实用性的文学——序传、论说、书奏等等,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这类文学中,当然不容许有丰富的想像活动。民初以来,因受西方文学的影响,许多人把这一类的文学评价得很低,而另标出或 ‘美文学’或‘纯文学’,以资与西方文学较一日的长短。但西方因报纸杂志等的发达,实用性的散文,在文学中已日居于重要地位,这已被西方的文学史家、文学理论、批评家所注意到了。文学保有实用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坏事。凡是拿西方文化中一时的现象、趋向,以定中国文化的是非得失,我愿借此机会指正出来,这是相当危险的方法”。(注:徐复观:
《中国文学中的想像与真实》,《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4页)在这里,徐复观明确地提出了中国文学的实用传统是中国文学区别与西方文学的最重要的特征。
三
中国文学的实用传统首先体现在中国文学的文体较西方复杂,徐复观认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同之点,在于西方文学只顺着纯文学的线索发展,而中国则伸展向人生实际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所以西方文学的种类少,而中国文学的种类繁,因此,在作品的整理与把握上,中国文学分类的重要性过于西方文学”。
③
徐复观:《文心雕龙》浅论之七,《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页)因此用纯文学的观念来研究中国文学必然会将中国文学的传统截断,从中抽离出能够符合纯文学观念的作品,将具有中国文学本身特点的文学或者排除在文学史研究之外,或者没有给予合理的评价。中国文学的类型比西方复杂,很多实用性的文章也是属于文学,不仅仅只有诗、小说之类近代以来所谓的纯文学的作品才有文学的价值。而中国文论家“自西汉之末迄东汉之初,已经有人注意到奏议、书论等的文学价值”。③就文体而言,如果按照西方文学的分类标准,他们只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几类,那么汉赋该归入哪一类呢?它是诗歌呢?还是小说?由此,按西方文学的标准,诏、策、令、教、表、启、书、檄等等,均不在文学研究的范围,收录这些文体的《昭明文选》就不能算做纯文学总集,讨论这些文体的《文心雕龙》也不能算做纯文艺理论的著作。而在徐复观看来,这些作品恰恰构成中国文学史的实用传统。
更深一层次,以西方关于小说“有一定长度的虚构的故事”的定义,中国史志著录的小说都不合标准。而用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将中国古代文学思潮分类的方法也从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文学思潮的自身发展。西方美学中关于审美的概念诸如悲剧、喜剧、崇高、优美等在我们的艺术当中并不能够找到相应恰切的作品,而我们固有的比、兴等艺术手法也在西方艺术理论的框架里面无所适从。“至于中国文学中人文化成的观念、原道宗经的思想、比兴寄托的方法、风神气韵的话语,都因为与西方文学思想、文学观念、文学方法、权力话语不谐而没有得到文学史家的足够关注和深入研究,以致中国的文学史实只能用来说明西方理论的正确,却不能用来作为建筑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学科体系的基石。”王齐州:“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史观的现代意义,武汉大学“中国近代化史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论文,2000年11月18-19日)
因此,徐复观批评萧统的《文选》,就是因为《文选》的所谓美文抹煞了中国文学的实用文学,“对西汉文学的误解,实始于《昭明文选》。萧统以统治者的地位,主持文章铨衡,他会不觉地以统治者对文章的要求,作铨衡的尺度,而偏向于汉赋两大系列的‘才智深美’的系列,即他所标举的‘义归乎翰藻’。”(注: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8页)也就说,文学的经典的确立无疑应该根据艺术标准,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文学史上经典是一个不断的确立的过程,这就意味着文学性本身就是在不断的变化之中。每一次文学经典的重新确立都是基于一定的文学观念的改变,文学的观念决定了人们对文学作品的衡量价值的标准。文学的文学性其实仍然是受着时代和政治的因素影响,文学性离不开政治思想的背景。以汉代文学为例,从东汉初年,已把文学的范围扩大到散文这一方面,而王充《论衡》中对刘向、匡衡、谷永这些人的奏议,从文学观点再三加以推重。曹丕《典论•论文》分文学作品为四科,四科中首推奏议。尔后陆机的《文赋》、刘彦和的《文心雕龙》,无不以奏议在文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究其因,徐复观认为,“萧统《文选》中收集了许多散文作品,但因统治者厌恶谏诲,可谓出于天性。他的父亲梁武帝晚年尤为显著。所以萧统竟然把奏议这一重要的文学作品完全隐没,而仅在上书这一类中稍作点缀。于是西汉在这一方面许多涵盖时代、剖析历史的大文章,又一起隐没掉了。这可以说是以一人统治欲望之私,推类极于千载之上。”(注:徐复观:《西汉文学论略》,《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73页)因此,徐复观非常重视中国文学的实用性特征,以及由此带来的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徐复观因此批评文选派以《昭明文选》所体现出的文章的骄俪之美作为中国传统文学的美的标准,他认为这不能完整地概括中国文学的整体特点,他们没有真正地契入中国文学的内在精神。徐复观认为这种实用性特征正是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文学传统,“所以《诗》大序说‘先王以是 ( 诗 ) 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这种要求,一直延伸到后来的小说、戏剧中去。”(注:徐复观:《中国文学讨论的迷失》,《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82-83页)也就是说,中国文学的发展流变,虽然体式多有变化,但其诗学主张一直则是沿着《诗》大序的方向,一路都是具有实用色彩。
而中国文学的这种实用性根源,在徐复观看来是根植于中国文化的性格,而“经学奠定中国文化的基型,因而也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线。中国文化的反省,应当追溯到中国经学的反省。”
④徐复观:自序,《徐复观论经学史二种》,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从而,经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中国文学实用性特性的形成关键。所谓的经学就是经世致用之学,经学对历史和政治阐述是以实用为目的,但其中仍然包含着文学的艺术性。通过经学,我们才能对中国文学实用与审美之间的关系进行深入的考察。例如,《诗经》的文学性就体现了文学的实用性与审美性的互动。而在《先汉经学之形成》一文中,徐复观详细考察了经学所给予《墨子》、《庄子》、《管子》、《韩非子》及《吕氏春秋》的影响。基于这种基本认识,徐复观高度评价了刘勰的文学观,认为刘勰把《原道》、《征圣》、《宗经》三篇作为文之枢纽,就是要把文学纳入到“经”这个文化大流之中。他说:“《五经》在中国文化史中的地位,正如一个大蓄水库,既为众流所归,亦为众流所出。中国文化的‘基型’、‘基线’,是由《五经》所莫定的。《五经》的性格,概略的说,是由宗教走向人文主义,由神秘走向合理主义,由天上的空想走向实用主义。中国文学,是以这种文化的基型、基线为背景而逐渐发展的。所以中国文学,弥纶于人伦日用的各个方面,以平正质实为其本色,用彦和的词汇,即是以‘典雅’为其本色。”在曹丕的《典论论文》和刘勰的《文心雕龙》中,“丽”只是诗和赋的审美要求,这仅仅是中国文学美感意识的一个方面。而其他诸如铭诔、奏章、书论等实用文体的美感意识则是不同于“丽”的“典雅”、“尚实”等。
在徐复观看来,中国文学的实用传统并不是浮浅的功利主义,而是基于人格修养的人文主义④,而这正是“经”的主要内容。正因为此,在讨论作为现代文学较为推崇的想像和虚构的概念时,徐复观认为,正是这种人文主义造成了中国文学崇尚对人世界的现实关怀。与西方文学以想像和虚构作为文学的本质特征不同,中国文学的根本特点不在于想像和虚构,而在于其人间情怀。中国文学并非没有想像和虚构,但是中国文学的想像是一种关怀现实世界的想像,而非超绝理念世界的想像,也就是他说的“中国文学家生活在人文世界里”,这也正是为什么中国文学没有西方悲剧之所在,他说:“中国从西周初年起,已开始摆脱原始宗教而走向‘人文’之路。印度佛教进入到中国后,也只发挥其无神论的一方面;并将印度的各种‘大地震动’这类的奇特表现,逐渐转变而为‘平常心是道’的平常的表现。人文的世界,是现世的,是中庸的, 是与日常生活紧切关连在一起的世界。在此种文化背景、民族性格之下,文学家自然地不要作超现世的想像,不要作惨绝人寰,有如希腊悲剧的走向极端的想像。中国文学家生活于人文世界之中,只在人文世界中发现人生,安顿人生;所以也只在人文世界中发挥他们的想像力。中国不发展史诗(《诗经》中便有不少史诗),是因为中国的史学发展得太早。中国不出现悲剧,是因为中国民族的性格、文化的性格,不愿接受走向极端的悲剧。这其中没有能不能的问题”。徐复观:《中国文学中的想像与真实》,《徐复观文集》第二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95页)
因此,不理解中国文学的实用传统,用纯文学观来审视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就不能真正把握中国文学精神。“中国文学,从历史的发展上来说,有与西方文学不同的地方。在中国文学史上,叙事诗、戏剧、小说,虽然不是没有,但未能得到适当的发展,所以过去用故事情节来批评文学的很少。”(注:徐复观:《文心雕龙》浅论之七,《中国文学精神》,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在纯文学的观念下,文学的实用性与文学的道德教化作用被贬低了,甚至被认为是与文学的审美性相对立的。这种观念如果说不是错误的,至少也是偏离了文学史发展的事实。(注:在文学史中,即使是在西方文学里面,与纯文学的审美主义宣称相反,审美并不是文学的惟一目的。班纳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指出,小说阅读在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创造中产生了重要的作用。卡勒说:“在19世纪的英国,文学呈现为一种极其重要的理念,一种被赋予若干功能的、特殊的书面语言。在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中,文学被作为一种说教课程,负有教育殖民地人民敬仰英国之强大的使命,并且要使他们心怀感激地成为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启迪文明的事业的参与者。在国内,文学反对由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滋生出来的自私和物欲主义,为中产阶级和贵族提供替代的价值观,并且使工人在他们实际已经降到从属地位的文化中也得到一点利益。文学对教育那些麻木不仁的人懂得感激,培养一种民族自豪感,在不同阶级之间制造一种伙伴兄弟的感觉能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最重要的是,它还起到了一种替代宗教的作用。”(〔美〕乔森纳•卡勒:《文学理论》,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页。)至今,英国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利维斯点评了两百多年来的英国小说,疏理出以道德要义和兴味关怀为基准的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参看利维斯(F. R. Leavis)著:《伟大的传统》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事实上,在重新对这种文学观念的反省之后,现代的研究者们已经认识到这种文学观的局限性。近来,国内的文学史研究者们提出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不是纯文学的‘文学史’”(注:马中红:《多学科视角研究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史百年研究国际研讨会综述》,文艺报2004,12月14日,2004年第140期),这种认为只有纯文学才构成文学史的思维方式,是承接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受西方唯美主义影响的结果,这种文学史的叙述可以说是一种审美霸权,其结果是对中国文学本身产生隔膜,使中国文学史上丧失了很多有意义和价值的东西。这种文学史观念是以西方文学标准衡定中国文学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潜在表现。
结语
徐复观强调文学的中西差异,这是中西空间性的历史文化差异。就文学来说,从来不存在一种普遍的文学和一成不变的文学观念。徐复观因而重视中国文学本土性特征,他关于文学研究“历史的动态”的观点,实际上构成其中国文学研究自觉的本体意识。他对进步论的反思,体现了文化上的本体意识,文学研究的本土意识。他指出进步观是一种静态的历史观,它否定文化的多元性与民族文化的个性,“由西方哲学的一元论而形成一元底历史观,拿一个东西作历史文化惟一的测量尺度;在其惟一底尺度下,世界的文化,都是同质的;只有时间上的前进或落后,而无异质底个性文化之并存”。
(注:徐复观:《文化的中与西》,《中国学术精神》,华东师大出版社,2004年版,第249页)
中国文学的处境也是整个中国文艺的处境,中国文艺必须放在中西的艺术比较系统中才能有价值,这里包含这样的一个深刻意识:中西文艺通过比较得以互相发明,这个过程里面,必须伴随着中国文学的自觉意识。实际上,中国文学研究中自我意识的获得乃是自我文化价值的认同,对中国文学价值的肯定实际就是对自我文化价值的肯定。而关注中国文学的自身经验并不是希望通过中国文学的地方性经验给西方人的视野提供一个奇观,而是正视我们的文学传统,发现我们文学中的有益经验,从这种文学经验中探讨文学发展的规律,从而使得中国文学的经验成为整个世界文学经验中宝贵的财富,丰富我们对文学理解,拓展文学的内涵。因此,徐复观并不因为中国文学的自我意识而忽视文学的普遍规律,否定文学性的存在。他认为文学的价值以及文学区别其它文章的就是文学性,但是这种文学性在中西之间有着区别。
徐复观并没将传统与现代对立——也没有将中西之间对立起来,在《中国艺术精神》以及中国文学的研究中,他大量运用西方美学文学的理论进行中西的比较互释。但是,对他来说,西学只是作为参照系而存在,通过与西学的比较,使中西二者之间可以互相发明,从而使中学获得新的意蕴。他对五四以来文艺研究的反思体现了他强烈的中国自我意识,他认为中国文学史的建立必须回到中国文学本身。把文学放回到历史语境当中,恢复文学的中国意义,才能发现中国文学的自身特性对中国文学作出恰当的理解,那种以西方文论的模式来格式化中国文学的做法,往往让我们丧失了自身的文学传统,切断中国文学的源头。只有当我们恰当地理解了中国文学传统,才能从这一传统当中获得有生命力的东西,一种活的精神。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中文系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