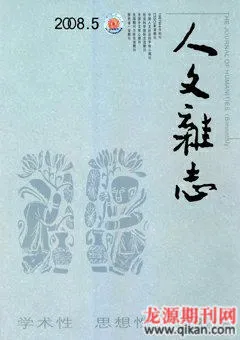与其是反传统,毋宁是反正统
内容提要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往往着眼于其“新”的一面,强调其对西方思想的接受,然而如果我们具体看一下当时代表人物的言论,会发现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然而与传统文化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谓的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正统,五四自有其传统的根源,并非西学可以完全解释。
关键词 传统 正统 儒家国家学说 中西文化的两难选择
〔中图分类号〕K26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48-05
“五四”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义,但它在社会文化思想方面带来的广泛解放与深刻震撼是中国走向世界的新起点。这里论述的“五四”并非仅仅是这场学生爱国运动,而是指五四前后若干年内所进行的一种文化运动或思想运动,其上限至少可以追溯到一九一七年的文学革命,下限则大抵可以一九二七年的北伐为界(注:时间跨度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是广义的五四运动。
对于五四运动的研究和评论,我们往往着眼于其“新”的一面,尤其是接受西方思想的部分,而强调对中国的传统思想持坚决否定的态度,然而从当时人们的言论来看,我们会发现五四运动虽然以提倡新文化为主旨,然而与传统文化却有着割不断的联系。所谓的反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是反正统,五四自有其传统的根源,并非西学可以完全解释的。本文从以下方面论述。
“五四”所谓的反传统
一提“五四”我们往往和彻底反传统与全盘西化联系起来。在这里我们首先应该明确两个概念:传统和正统。传统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等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而所谓的正统则指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潮(定义参考《辞海》1989年版)。明确了这两个概念,我们看一下当时领导人物的言论便会发现这种结论的偏颇之处:
五四前夕,胡适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当时人认为新的地方,主要在于他不同于封建时代哲学史书代圣贤立言,为经传作注解……他把孔丘和其他哲学家摆在同一地位上,供人们评论,这是一个大的变革。(注: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97页)
先生又怪我把“孝”字驱逐出境。我要问先生,现在“孝子”两个字究竟是什么意义?现在的人死了父母都称“孝子”。孝子就是居父母丧的儿子(古书称为“主人”),无论怎样忤逆不孝的人,一穿上麻衣,戴上高梁冠,拿着哭丧棒,人家就称他做“孝子”。(注:胡适:《我答汪先生的信》,见《胡适文存》,第一集卷四,第691-692页)
上述言论说明,胡适先生所谓的反传统,不过是把孔子从独尊的地位上拉下来,与先秦百家平起平坐。难道先秦百家之学不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吗?只不过自从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整个封建王朝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思潮。因此,胡适先生所谓的反传统不过是反正统,是恢复我们原来的传统文化的原貌而已。至于其关于“孝”的言论,不由使我们想起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的语调何其相似!他们之所以要毁坏礼教,是因为礼教已经成为某些人的工具而貌合神离了。而从《胡适家书》和《四十自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懂得“大孝”的胡适,他以自己的一生诠释了孔子的“色难”(注:《论语•为政》)之说。
陈独秀于1916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一系列全面批孔的文章:
“若夫别尊卑,重阶级,主张人治,反对民权之思想之学说,是为制造专制帝王之根本原因,吾国思想界不将此根本恶因产出净尽,则有因必有果,武术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当然接踵应运而生,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的三纲主义。……”(同上)
并进一步坚决指出,“本志诋孔,以为宗法社会之道德,不适于现代生活。”认为“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存之余地”。陈独秀先生之所以批孔如此决绝,从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反对的是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孔子,是已经被工具化了的孔子。因此,他批孔意在打破当前的正统文化。
在文化阵营中,鲁迅先生是新生文化阵痛时的呐喊者,他发表了一系列抨击旧道德旧文化的文章,然而我们谁都不能否认他同时也是传统中国文化逝去时的守夜人,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喜爱,否则不会用八年的时间来沉静地抄写古碑。虽然此举当时也是为了排遣郁闷的心情,但如果没有喜爱怎么可能以此来排遣心情呢?看看他的《中国小说史略》以及杂文,我们可以发现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深刻的体认,也正因为此才有其晚年的《故事新编》,正如张文江先生所说,鲁迅所以为鲁迅,在于十年抄古碑。刘半农曾赠给鲁迅一副联语“托尼学说,魏晋文章”,据说鲁迅自己也以为很恰当,但这是“五四”初期的鲁迅。事实上鲁迅不但爱好魏晋文章,而且深受魏晋思想的感染。据许寿裳讲:
鲁迅对于汉魏文章素所爱诵,尤其称许孔融和嵇康的文章。我们读“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便可得其梗概。为什么这样称许呢?就因为鲁迅的性格,言气正性,宁愿覆折,憎恶权势,视若蔑如,皓皓焉坚贞如白玉,懔懔焉动烈如秋霜,很有一部分和孔、嵇二人相类似的缘故。(注:转引自曹聚仁《鲁迅评传》(上),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版,第47~48页,
并且在许氏提到的这篇文章中,鲁迅还特别援引了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非汤武而薄周孔”那句话,对他们“毁坏礼教”的罪名力加洗刷,他说:
例如嵇、阮的罪名,一向说他们毁坏礼教,但据我个人的意见,这判断是错的。魏晋的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见《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5月版,第94页)
这些话在当时显然颇有几分“夫子自道”的意味。鲁迅尽管自1918年起在《新青年》发表了《狂人日记》等一系列的小说、随感,猛烈的抨击旧道德,他的犀利的批判也反映了他对儒家文化的深刻认识,尤其是对传统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与中国人性格症结的深入了解。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忽略,鲁迅先生在其晚年的作品《故事新编》中,尤其是《非攻》、《理水》充分肯定了墨子的思想。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便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藉于旧传统者是多么的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去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的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的旧格局。”(注:时间跨度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7页)
由以上三位在当时具有主导作用的人物的著作及言论我们会发现,他们往往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抨击的传统对象主要是儒家。其抨击的主要原因在于儒家的独尊地位导致的言论思想等的不自由;儒家学说有碍新政体的发展;儒学的虚伪即礼教等等,然并非全面否定儒家,它所否定的主要在于被统治阶级利用的那部分内容,丧失生命力的一部分。在文化上则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出现了其他支流学说地位上升的局面,如墨学成为显学,墨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源流之一,秦汉以后,墨学逐渐衰落,成为绝学。晚清以后,墨学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五四时期,梁启超、章士钊、胡适等人都有不少关于墨学的著述。梁启超《欧游心影录》中,将孔、老、墨“三圣”并称,墨子与孔子平起平坐。鲁迅也对墨家实干的精神大加赞扬,墨学的地位显著提高。通过这些现象我们应该洞悉其深层的原因,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谈:一体化的政治结构和西方文化的撞击。
儒家作为国家学说
金观涛曾提出:中国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一体化,即儒家国家学说(注:参考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其具体表现则为:国家利用具有同一信仰的知识分子建立官僚机构,来执行管理国家的功能;在儒家国家学说的指导下,各级官员都要受到“忠君保民”信条的约束。因此我们可以说儒家学说的兴衰与政治命运息息相关。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即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反常时期。东汉中后期,各地军阀混战,大一统的结构遭到破坏。儒学成为知识分子沽名钓誉的手段,儒家的名教与儒生的行为脱离,同时门阀贵族结合,使得知识分子入仕无门。儒学受到沉重打击。当时不少知识分子从事先秦诸子的研究,也有人企图推翻汉代经学,重新在原始的儒家经典中作新的发掘,也有人想综合各家,别创新说。这种以复古为手段试图摆脱僵局的努力,使得许多消沉泯灭的学派开始活跃起来,作为儒家补结构的道家兴起,加上佛教的流入,使得玄学发展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五四运动的反传统与此有着一定的相同之处。
然儒家学说作为一种国家学说,本身与时代发生了不适宜。陈寅恪指出,“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活之方面。”(注: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见《陈寅恪史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11页)当法律制度和公私生活在20世纪后的中国发生巨大变化时,附丽在其上面的儒家学说便显得百无是处,反儒似乎也就成了历史的必然。辛亥革命,推翻了君主专政的政治体制,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在中国建立了一个实行议会制和责任内阁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宗法一体化的国家结构已经不复存在,而普遍王权则是维持政治秩序和文化秩序密切联系的重要关键。正因为普遍王权对此二者的高度整合作用,当政治秩序因王权的崩溃而毁坏,文化秩序的命运也无可避免瓦解的。
另一方面,辛亥革命的失败,袁世凯篡权复辟之后所推行的一整套尊孔读经、复古倒退政策,又从反面教育了新的一代知识分子,使他们在传统与革新、政治革命与文化思想革命、反封建与反传统等一系列问题上开始了进一步的反思。经过认真反思,深化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投入了反传统、反封建的伟大斗争。这就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是在总结辛亥革命以后的经验教训中开始的。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旗帜鲜明地提出:
中国虽然经过辛亥以来的革命而黑暗未尝稍减,其大部分原因“则为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这就使得“单独政治革命所以于吾之社会、不生若何之变化,不收若何效果也”。
这腐旧思想布满国中,所以我们要诚心巩固共和国体,非将这班反对共和的伦理、文学等等旧思想,完全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可。否则不但共和政治不能进行,就是这块共和招牌也是挂不住的。(注: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第3页)
这可以说是五四先进知识分子对于辛亥革命所作反思的共同结论,是当时五四先驱的逻辑。单独的政治革命只能对社会结构进行某种外在的形式方面的改革,却不能带来社会深层次的、即文化心理结构的真正变化。而社会表层结构的某些改革,很快就会为根深蒂固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旧的社会心理与习惯势力所淹没。也就是鲁迅所说的,若没有以传统文化为根基的国民性的改革,“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注:《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2页)。不少人认为这是儒家国家学说的思想的禁锢,所谓“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行为之改善”、“一国之民精神上物质上如此堕落,即人不伐我,亦有何颜面有何权利生存于世界”。(注:陈独秀:《我之爱国主义》,见《陈独秀文章选编》(上),第132页)所以当时的先驱集全力来批孔批儒,认为建设必先以破坏,以打破禁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政治上的革命家如章太炎等,却不重视文化思想上的反封建斗争,甚至固守着传统旧文化的堡垒,幻想什么“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注:章太炎:《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辞》,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69页)最后终于如鲁迅所批评那样,“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注:《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见鲁迅《且介亭杂文末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
因此,五四批儒一方面是儒家学说自身的地位所致,另一方面则是辛亥革命给知识分子留下的伤疤的反馈,认为现代中国社会、政治与经济改革的先决条件是思想革命,而这种思想革命首先需要全盘摒弃中国的过去,儒家文化作为封建的国家学说自是首冲。
理智选择西方,情感上丢不开传统
任何运动都有一定的酝酿期。五四运动是中国对西方入侵的反应的一连串发展显露出来的一个高峰。这个高峰是挫折中产生出来的一个昂扬,它是中华民族文化潜力的新涌现。西方政治经济上的强大,使得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把目光投向西方,他们希翼西方先进的文化能使祖国强大起来,这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心声。早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以传播西方民主思想为主的思想启蒙运动拉开了序幕,黄遵宪、严复、谭嗣同、梁启超等一批先进人物都积极介绍和传播西方文化思想,其中严复翻译介绍西方著作最多,如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原富》、穆勒的《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等。影响最大的是《天演论》和卢梭的《民约论》,特别是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思想在当时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
然而“任何一个文化,对于外来文化刺激所作反应,总是站在自己文化的基线(cultural base line)上做反应”。(注:殷海光:《中国文化的未来展望》,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6页)华勒士根据他研究美国西北部艾科斯银印第安人的文化濡化的结果提出:如果要将一个文化改变成为一个外来文化,那么必须改变这一文化里的文化分子之基本模式性格结构。例如佛教与中国人的性格无甚冲突,因此佛教在中国容易普及;而基督教与中国人的文化性格核心即儒家文化冲突,因此基督教在中国难得普及。我们看一下当时人们所介绍的西方思想。
“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此纯粹个人精神也。……”(注: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青年》第1卷第4号,转引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1页)
“法律上之平等人权;伦理上之独立人格,学术上之破除迷信,思想自由,此二者为欧美文明进化之根本原因。”(注:陈独秀:《袁世凯复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转引于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1页)
胡适的理论归结起来大致为:要培养道德首先要发展经济,满足其基本需要;发展科学,热爱真理;推崇西方的宗教与道德理智化、人文化和社会化。陈序经则主张全盘西化,理由有二:欧洲近代文化的确比我们进步得多;西洋的现代文化是现世的趋势,并且通过老庄的自由观点等来非孔。
由他们的观点我们会发现他们所倡导的无非是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等,这些在晚清时已经大力提倡。然而中国几千年来沉淀下来的家族制度,长幼尊卑等的观念均已根深蒂固,个人精神谈何容易!在当时那个“救亡压倒启蒙”(李泽厚语)的时代,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究竟对西方文化的精髓理解了多少,不过是搬过来几个名词而已。这也让我们明白了为什么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中支流的文化浮出水面,就像余英时先生所说“至于外来的新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某些已有的观念上,才能发生真实的意义。所以言平等则附会于墨子兼爱,言自由则附会于庄生逍遥,言民约则附会于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注:时间跨度参见余英时《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见《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化诠释》,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52页)胡适在当时对西方文化最有亲切的体会,但他的“非孝”说也还是根据王充、孔融以来所谓“父之与子,当有何亲”那一派的言论,所以“五四时代”,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反正统的作品,从哲学思想到小说戏曲歌谣,都成为最时髦最受欢迎的东西。而胡适把“整理国故”当作“新思潮的意义”的一部分,正可见“五四”与传统间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鲁迅为新文化呐喊,但他自己仍然作了不少“整理国故”的工作,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故事新编》以及他的《小说旧闻钞》的再版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五四新文化运动借用了西方的启蒙话语,这是事实。但中国的启蒙运动决非欧洲启蒙话语的横向移植。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情不同、思想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固然是当时中国眼界最开阔、最善于吸收外来思想文化养分的人,但他们毕竟不可能与自己的文化传统一刀两断。已故的列文森对近代中国思想史曾提出一个有名的论断,认为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大体是在理智方面选择了西方的价值,而在情感方面却丢不开中国的旧传统。正如鲁迅先生所说:试到中央公园去,大概总可以遇见祖母带着她孙女在玩的。这位祖母的模样,预示着那娃儿的将来,所以倘有谁要预知夫人日后的丰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当然要有些不同的,但总归相去不远,我们查帐的用处就在此。……LeBon先生说,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诚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类究竟进化着。……总之,读史,就愈可以觉悟中国改革之不可缓了。……一改革,就无须怕孙女儿总要像点祖母那些事。(注:鲁迅:《这个和那个》,见《华盖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37-138页)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
责任编辑:刘之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