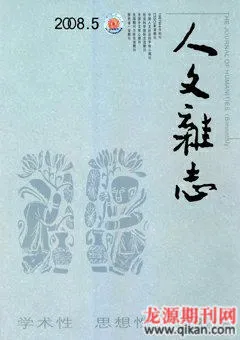透明的媒介:论麦克卢汉对媒介本质的现象学直观
内容提要 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深入研究,最终奠定了技术主义范式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对媒介的研究也常常被人指责为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本文从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整体的人”、“媒介即信息”三个方面来考察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研究,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思想具有现象学的视野,他悬置了社会政治、经济等背景,而纯粹地考察了媒介的作用,并以“整体的人”为立足点,对西方文明的异化展开了批判。
关键词 麦克卢汉 现象学 媒介技术决定论 地球村
〔中图分类号〕G206、B08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08)05-0033-06
麦克卢汉对媒介技术的深入研究,最终奠定了技术主义范式在传播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但他对媒介的研究也常常被人指责为有“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本文从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整体的人”、“媒介即信息”三个方面来考察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研究,认为麦克卢汉的媒介技术思想具有现象学的视野,对麦克卢汉的“媒介决定论”的指责是有失偏颇的,麦克卢汉并不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我们只有在现象学的层次上才能更清楚地理解麦氏的传播思想。
一、现象学作为一种哲学方法
近年来,胡塞尔所创立的现象学在我国已经越来越多的引起学者的关注。作为现代以来最重要的哲学思潮之一,现象学以其独特的方法论著称于世。胡塞尔指出:“现象学:它标志着一门科学,一种诸科学学科之间的联系;但现象学同时并且首先标志着一种方法和态度:特殊的哲学思维态度和特殊的哲学方法。”(注:〔德〕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倪梁康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页)作为一种哲学方法,现象学对现代西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现象学的本质其实是对西方理性的拯救,即“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康复。”(注: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导引》,《中洲学刊》1996年第6期)在胡塞尔那个时代,整个欧洲危机四伏,灾难不断,反思欧洲危机的根源几乎成了当时思想家的时髦话题。和同时代的哲人一样,胡塞尔也对欧洲危机进行了反思,他深入到欧洲理性精神的源头来揭示欧洲危机的根源。在胡塞尔看来,欧洲危机其实就是欧洲理性的危机。胡塞尔指出:“伽利略在从几何的观点和从感性可见的和可数学化的东西的观点出发考虑世界的时候,抽象掉了作为过着人的生活的人的主体,抽象掉了一切精神的东西,一切在人们的实践中所附有的文化特征。这种抽象的结果使事物成为纯粹的物体,这些物体被当作具体的实在的对象,它们的总体被认为就是世界,它们成为研究的题材。”(注:胡塞尔:《欧洲科学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第71页)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客观世界被理解为脱离人的物质世界,人能够对这个世界达到精确的把握。这导致了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泛滥,而人的精神和意义世界则被遗忘。因此,胡塞尔主张“要求对科学主义和非理性方法的真理概念进行一种彻底的反思和追溯,返回到古代思想的源头,即认为真理就是显现出来而被看到的东西,是直接被给予的自明的东西,其他一切(逻辑、概念、事物的存在等等)都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并由此得到彻底理解的。”(注:邓晓芒:《胡塞尔现象学导引》,《中洲学刊》1996年第6期)现象学的方法也就是“本质直观”,即“非常执拗地努力查看现象,并且在思考之前始终忠实于现象。”(注:倪梁康主编:《面向事实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5页)胡塞尔要求尽可能地排除本质并且排除所有本质科学,而“只运用我们能在意识本身中和在纯内在性中洞见到的东西”,因此,胡塞尔指出:“现象学事实上是一门纯描述科学,通过纯粹直观对先验纯粹意识领域进行研究的学科。”(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55页)经过彻底的现象学还原后,就剩下了先验纯粹意识,在胡塞尔看来,只有它才具有彻底的自明性。
作为一种重要的方法,现象学的目的是恢复人的生存意义,拯救欧洲危机,它对西方存在主义、语言哲学等重要哲学学派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已经不仅仅局限在哲学领域,而且向许多人文社科领域渗透,时至今日,现象学依然是一种重要的哲学方法,并且是我们理解现代以来的西方哲学不能缺少的通道。
二、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
麦克卢汉曾在西方掀起了一股“麦克卢汉热”,他的思想一出世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欣赏者誉他为“继牛顿、达尔文、佛洛伊德、爱因斯坦和巴甫洛夫之后的最重要的思想家”,反对者则因为他晦涩的语言而批评他“刻意反逻辑,迂回论证,同义反复、绝对,滥用格言”。经验实证学派嘲笑他对“被媒介影响的感官环境的关注胜过逻辑的关注。”评论家克里斯托弗.里克斯更不留情,说他的风格“凝滞的迷雾、朦朦胧胧的暗喻在迷雾中跌跌撞撞”。各种各样的批评固然与麦克卢汉有时的故意夸大其辞虚张声势有关,但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在于对麦克卢汉研究方法的不了解,主要便是批评者自身缺乏现象学的视角,而对麦克卢汉传播研究中的现象学方法没有注意到。
麦克卢汉在1974年致约翰.W.摩尔神父的信中提到:“一直很留意康德、黑格尔和近年的现象学”⑥〔加〕梅蒂•莫利纳罗等编:《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仲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62、550页)。尽管我们不能肯定麦克卢汉是否有意地运用现象学的方法,但可以肯定麦克卢汉受到现象学的影响。麦克卢汉在1973年给华盛顿联邦通讯局局长尼古拉斯.约翰逊的一封信中说:“我的工作是难懂,但媒介本身更加难懂。我研究媒介的方法是多年研究象征派艺术和诗歌之后演绎出来的;……象征派使我懂得:在一切情况下,结果都走在原因的前面……理解媒介的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西方人头脑接受的训练是从A到Z,而不是从Z到A。这个头脑正在逐渐退化,越来越迷糊,它完全靠视觉原理(即逻辑)工作;视觉原理主张事物是连接的、同质的。这个道理只适合视觉;到了电气时代,一切感官都发挥作用,视觉和理性统治的时代从此终结”⑥。“从A到Z”的思维模式正是近代自然主义的科学思维,这种思维模式是直向思维、外向性思维,却不善于回过头来反思到出发点。而麦克卢汉的研究方法则是“从Z到A”,从结果返回到原因,这正是现象学的返回事物本身,考察直接呈现的东西。麦克卢汉还曾经直接说过:“我们求证的第一准则是:如果要想求得理解,就必须按照事物本身的属性去着手研究。爱伦.坡率先强调指出,有必要从结果出发开始逆向回溯。”③〔加〕梅蒂•莫利纳罗等编:《麦克卢汉书简》,何道宽、仲冬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09、564页)这也是对麦克卢汉现象学方法的证明。胡塞尔曾这样描述现象学的基本态度:我们的“出发点先于所有的立场,即:以直观的,并且先于所有理论思维的自身被给予之物为出发点,以所有人都可以直接看到的并且可以直接把握到的东西为出发点。”④倪梁康:《现象学及其效应》,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189、30页)
1969年《花花公子》杂志记者在采访麦克卢汉时开场第一句话问道:“麦克卢汉你在干吗?”麦克卢汉则机智地回答说:“我在探索。我不知道这些探索会把我引向何方”。“我的书只构成探索发现的过程,而不是终极的产品。我的目的是把事实作为探针、作为洞察的手段、作为模式识别”,“我从来没有把探索的结构当做揭示的真理。我没有固定不变的观点,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紧接着记者又问到:“这方法论难道不是有一点飘忽不定、前后不一吗?”麦克卢汉则回答到:“任何研究环境问题的方法,都必须保持充分的弹性和灵活性,以便涵盖整个的环境源头,因为环境是处于常衡不断的变动之中。……只有站在现象的旁边对它进行全局的观察,你才能发现它的运作原理和力线。”麦克卢汉自己也曾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而这种新的方法,在麦克卢汉那里就是探针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注重洞察,不死守任何一种理论,而是根据环境的变化,“站在现象的旁边对它进行全局的观察”,这与现象学方法的基本精神有暗合之处。
麦克卢汉自己曾宣布他的方法的反传统:“我以崭新的眼光重新考察人的延伸,几乎没有接受传统智慧中看待它们的任何观点”、“我实在不明白,如果你从一开始就对某个东西抱着支持或反对的立场,你怎么可能去研究它呢”③,通常认为麦克卢汉是反传统实证主义的,但通过上述的论述,我们可以发现,麦克卢汉的文风也是对传统思辨逻辑的拒斥。倪梁康教授指出,“现象学意识开拓了一种新的哲学传统,这种传统拒绝借助于旧的传统,拒绝借助于以往的理论、前人的学说,而是要求直接、明证、原本地把握绝对真理自身。”④
魏敦友也指出现象学要求“回到事物本身,去直观在人的认识活动中直接亲身体验到的东西,并对事物按照其直接向我们呈现的样子进行描述。”魏敦友:《回返理性之源》,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17页)现象学的方法最重要的便是直观和描述,直接地面对现象本身,拒斥任何先入为主的独断。麦克卢汉对传统研究方法的拒斥以及重探索重描述重现象的研究方法都表现了麦克卢汉传播学研究具有现象学方法,尽管我们不能判断麦克卢汉是否自觉地运用了这一方法。
三、“整体的人”——麦克卢汉的人学现象学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麦克卢汉的关注点是“人”,他对媒介技术的考察最终也是立足于人的感官本身,是考察媒介技术如何影响人的感官进而推动社会发展。“媒介是人的延伸”是麦克卢汉一个著名的思想论断。根据这一论断,麦克卢汉把电子媒介看作是人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延伸,而把其他一切媒介,特别是机械媒介看作是人体个别器官的延伸,“在机械化时代,我们实现了自身的空间延伸。如今,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电子技术的发展之后,我们已在全球范围内使中枢神经系统得到延伸,在全球范围内消除了时空差别。”麦克卢汉根据他的这一思想,把人类社会分为四个传播时期,即口耳传播、拼音文字传播、印刷传播和电子传播。在这四个传播时期中,麦克卢汉更倾向于口耳传播和电子媒介传播这两种传播方式,认为口耳传播的人是部落里的人,而电子媒介则是使人类重新部落化。麦克卢汉认为,在前文字时代,或者说是部落时代,口头语言和耳朵占据统治地位。人们是依靠面对面的交流,因此,部落的人是感官平衡发展的人,没有被分割,“整合的部落网络里人们相互依赖,所有的成员都生活在和谐之中。”(注:纪莉:《“论麦克卢汉传播观念的‘技术乌托邦主义’”》,《新闻与传播研究》2003年1期)而拼音文字的产生打破了人的感官平衡,人由整体的人变为分割的人,视觉统治的文化造成了一个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专门化的社会。拼音文字产生后,部落时代的感官平衡和谐发展的美好时光一去不复返,文字人或视觉人创造的一个环境是强烈分割的、个人主义的、显赫的、逻辑的、专门化的、疏离的文明。麦克卢汉对电子媒介抱以乐观的态度,认为在电子媒介时代,“我们身披全人类,人类就是我们的肌肤。”
作为一位人文学者,麦克卢汉曾在文学中、在艺术中体验着人类部落时代的美好时光,但在现实中却感受到拼音文字和印刷文明的异化。麦克卢汉的文明史观反映了他的“人”的观念,即人应当是什么样子?人的交往应当以什么方式?……只有理解了他的人的观念,才能清楚地理解他的传播思想,这一点容易为学者们所忽视,至少在笔者所掌握的资料中还没有看到。这不能不说是研究麦克卢汉的一个遗憾。我们从上面对麦克卢汉思想的论述中,从他对部落人的赞美中,可以看到,麦克卢汉认为,“人”应该是“整体的人”,是各种感官平衡发展的人,而不应该是理性分裂的人(这是一种异化状态),在交往中,人的诸感官和谐发展,共同参与交流,因此麦克卢汉才激烈地批评拼音文字和印刷文明,同时麦克卢汉却推崇艺术家,其理由也就是在印刷文明面前,只有艺术家“在新技术的打击使意识过程麻木之前,就能矫正各种感知的比例”,只有艺术家“是具有整体意识的人”。麦克卢汉对媒介与人的思考已经具有了历史的视野,他是在人类传播从部落到重新部落化的历史序列中,直观到人的本质——“整体的人”的。人的这一本质不是依靠逻辑所推理出的,也不是靠实证所得出的,而是依据现象学意义上的“直观”,具有超越传统媒介与人二分的视角。
四、“媒介即信息”的现象学视野
“媒介即信息”是麦克卢汉最著名的一个观点。也是一个遭到广泛批评的观点。最主要的批评就是认为麦克卢汉对传播媒介的分析与更广阔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孤立,没有看到其他社会因素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对媒介的分析忽视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比如英国文化研究学者威廉斯。这就是被麦克卢汉的批评者广泛引用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的确,如果以传统的眼光打量麦克卢汉的思想,那么他的各种观点都有浓厚的媒介技术决定论的倾向。但这样的结论却是有失偏颇的,因为忽视了麦克卢汉传播研究的现象学,当然也就没有看到“媒介即信息”这一论断所具有的现象学视野。
其实麦克卢汉在解释这个观点之前,提醒人们:“我们这样的文化,长期习惯于将一切事物分裂和切割,以此作为控制事物的手段。如果有人提醒我们说,在事物运转的实际过程中,媒介即是信息,我们难免会感到有点吃惊。”以往对媒介的研究主要是对媒介传播内容的分析,这其实是分裂的研究问题,而缺乏对媒介整体的把握。当我们以整体的方式来“看”媒介时,我们会发现“任何媒介(即人的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任何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我们任何一种延伸(或曰任何一种新的技术),都要在我们的事务中引进一种新的尺度。”这就是麦克卢汉“媒介即信息”的含义。这一结论可谓是“石破天惊”,其最大的理论贡献是提醒了人们对媒介自身的研究,使人们意识到媒介技术就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动力。此后学者们纷纷从这一论断中寻找灵感,但对麦克卢汉如何得到这一观点却研究不多。
尽管麦克卢汉没有明确提及他得出这一结论的研究方法,但我们也可以从他的论述中看到现象学的影子。麦克卢汉在解释他的“媒介即信息”这一观点时,说到:“铁路的作用,并不是把运动、运输、轮子或道路引入人类社会,而是加速并扩大人们过去的功能,创造新型的城市、新型的工作、新型的闲暇。无论铁路是在热带还是在北方寒冷的环境中运转,都发生了这样的变化,这样的变化与铁路媒介所运输的货物或内容是毫无关系的。另一方面,由于飞机加快了运输的速度,它又使铁路塑造的城市、政治和社团的形态趋于瓦解,这个功能与飞机所运载的东西是毫无关系的”。麦克卢汉还在另一处提及媒介技术对人的感官的影响,“由于媒介对人无所不在的影响,媒介本身成了讯息,而不是其内容成了讯息……实际上,媒介作用于每一种感知的比率、渗透进去,塑造它、改变它。任何一种媒介的内容和讯息的重要性,实际上和原子弹弹壳上镌刻的文字一样。”……从上述的只言片语中,我们可以看出,麦克卢汉实际上是“悬置”了各种社会因素和媒介内容而纯粹地考察媒介技术的作用,同时,他的媒介技术的研究不是用思辨推论,而是直接进入媒介本身的存在结构,对媒介对人的影响作了心理学意义上的描述,这显然正是现象学的基本方法和核心精神。从这点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麦克卢汉为何关注媒介对人的感知的影响了。因此,给麦克卢汉扣上“技术决定论”的帽子是没有道理的。麦克卢汉并没有认为媒介的内容没有任何作用,正如胡塞尔所说:“被置入括号者并未从现象学的黑板上被抹消,而只是被加上了括号,因此被提供了一个标记”(注: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李幼蒸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3-184页)。麦克卢汉说:“我强调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