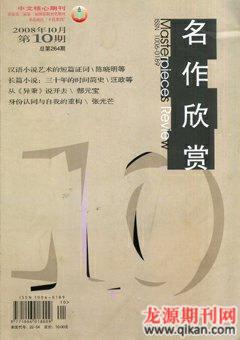新世纪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书写
【推荐理由】
阎连科是一位具有标本意义的作家。他的创作历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变化与转换。他在新军旅小说和新乡村小说上都卓有建树。人们往往注意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取得的成就。其实,他的短篇小说在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中同样有非常重要的代表性,富有独特的艺术品质。如《黑猪毛白猪毛》就是新世纪乡村小说当代性书写的典范之作。这种当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从当下、现时出发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它体现了当代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心理情绪以及审美趣味。面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却无奈、批判又理解以及情感状态和创作方法上的复杂而混沌是它三个主要的特点。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渗透。
在以往的乡村小说创作中,基于现实主义传统的要求,作家往往将自己的思考重心投注在发现现实中的问题,并指明事物发展的方向。鲁迅、沈从文、赵树理、柳青以及高晓声等都概莫能外。但是,在这种现实主义的写作中,我们读者到底得到了什么呢?我们对这个世界发展的认识又是什么呢?我们是否为这个世界的改变做了什么呢?很显然,任何一位优秀的作家都没有给我们提供满意的答案。特别是在这个经济与文化日益呈现出窘态的新世纪,在这个社会整体繁荣的表象下乡村呈现出破败景象的转型时期,这是一个问题成堆的世界。面对冗杂无序的世界,作家想要给大家提供一个满意的答案几乎是不可能。
乡村小说是新时期文学30年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意义上说,乡土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为乡村小说的创作提供了大量的素材。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全球化的进程激荡着神州大地,乡村小说借助乡土中国的文化资源优势做出了可贵的探索,并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成绩。这种探索既体现在主题意旨、创作立场上,同时也体现在创作方法的选择上。新世纪以来像贾平凹、张炜、莫言、阎连科、范小青、迟子建、孙惠芬等一批乡村作家往往突破了仅仅书写他们所看到的乡村世界和乡村历史,集中火力直面乡村、介入当下,提出问题。阎连科在谈到乡村小说的创作时曾经有过这样的论述:“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无论是你的人生经历也好,你的阅读经历也好,写作经历也好,你都到了应该明白一个道理的时候,即‘乡土文学应该有第三条路可走。沈从文的写作道路肯定不适合我,鲁迅的道路也不适合于我。现在,文学是21世纪的文学,不是上个世纪的30年代,也不是解放后的五十年代。文学是经过90年代的各种借鉴、融合之后到了21世纪,‘乡土写作应该走出鲁迅、沈从文之外的‘第三条道路。”①这其实是阎连科对自己乡土小说审美追求的一种诗性的阐述。而这种言说与其说是一种艺术上的宣言,倒不如说是作家对新世纪乡村小说创作现状的一种概括。我曾经把这种新世纪乡村小说所体现出的独特品质概括为当代性:“当代性主要表现为一种从当下、现时出发对世界所持的一种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它体现了当代人特有的生存状态、心理情绪以及审美趣味。面对现实问题的介入却无奈、批判又理解以及情感状态和创作方法上的复杂而混沌是它三个主要的特点。三者之间彼此关联、相互渗透。”②
阎连科是当下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新时期文学30年最不能忽视的作家之一。他的创作历程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时期文学30年的变化与转换,是一位具有标本意义的作家。而阎连科的《黑猪毛白猪毛》(《人民文学》,2002年第10期)就是新世纪乡村小说当代性书写的典范之作,具有非同一般的文学史意义。这是一篇有着极大冲击力的短篇小说,说的还是耙耧山区底层农民的生存故事:刘根宝因为家里穷,人又怯弱老实,29岁了也没能娶上媳妇。“早先时候,有过几门亲事,女方都是到家里看看,二话不说,也就一一荒芜掉了,无花无果。”这是嫌他穷。后来又介绍过一个寡妇来相亲。她问了根宝家有没有亲戚在村里乡里当干部。她试着叫根宝打她,根宝不敢动手。她见根宝懦弱憨实,没有腰骨的样子,怕嫁了他受人欺负,也就抬腿走人。这是嫌他无权无势。“实在说,没人欺负根宝一家,可就是因为他家单门独院,没有家族,没有亲戚,竟就让根宝娶不上一门媳妇来。”根宝为了攀上村里乡里的权势人物,也为了满足自己做一回男人自然本能的最低欲求,他所梦寐以求的就是顶替酒后驾车轧死人的镇长去坐牢。根宝丢尽一切尊严说服吴柱子让出机会,村人送他去坐牢像多年不遇的喜事。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村民们认为他们是送根宝进“天堂”——为镇长坐牢而换取基本的生存权利,同时也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希望,如大伙说的:“根宝兄弟奔前程了,千万别忘了你哥啊。”“有人帮着拿行李,根宝爹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一根接一根朝人们递,人家不接了他硬朝人家的嘴里塞。村里是许多年月没有这样送行的喜庆繁闹了,就是谁家孩娃参军也没有这么张扬过、排场过。”对此根宝心满意足。可正当他满心欢喜地去“当镇长的恩人”之际,事情有了变故,“镇长轧死人的那家父母通情达理呢,压根儿没有怪镇长,也不去告镇长,人家还不要镇长赔啥儿钱,说只要镇长答应把死人的弟弟认作镇长的干儿子就完啦”。刘根宝的希望就这样破灭了,虚无的结局再次出现。
这篇小说之所以让人产生震撼的阅读效果,是因为读者阅读时会自然而然地想起五四时期的乡土小说,就像在阅读贾平凹的《阿吉》时想起鲁迅的《阿Q正传》一样。1990年代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中国乡村显然与前工业社会的乡土中国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阿Q以及看客的人性在新时代得以延续。刘根宝可以说就是新世纪的阿Q。时代进步了,可人性没有进化,甚至有退化的可能。刘根宝不仅仅性格懦弱,更主要的是甘愿被精神奴役,被权力奴化。由此可见,权力侵入到人们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已经到了怎样的田地!李屠户不就是因为乡长在他的小店上住过一宿而生意兴隆吗?然而,与“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五四乡土小说的思想命题相比,与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视角相比,“在阎连科这部同是有着强烈批判锋芒的作品中,更深植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悲悯”。这种感同身受的悲悯甚至冲淡了小说的批判主题。“鲁迅尖锐、愤懑和哀婉的叙述风格,在阎连科的笔下逐渐化为以同情与怜悯为主调、以尖刻批判为辅调,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作者的写作倾向,即在当今社会环境下,对于人性的关注光靠尖锐的批判与鞭挞还不够;唤醒人性,使之成为民族性格的自觉,更要靠悲剧的力量来拯救灵魂的堕落,激烈的批判则是辅助性手段。这反映了阎连科小说的审美选择。”③而这种审美选择使得他不仅仅与五四一代的乡土作家区别开来,同时也与1980年代的乡土作家有了很大的不同。即便是在权力书写的作家中也表现出他小说创作的独立品质和独特追求。
那么,阎连科为什么在批判的同时却被浓郁的悲悯情怀所笼罩呢?为什么会表现出这种浓厚的当代性呢?首先是农民生活的艰难和贫困。里夫说:“小说是真实生活和风俗世态的一幅图画,是产生的那个时代的一幅图画。”④1980年代,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涌现出了无限生机。可到了1990年代农村日益承受中国改革的各种压力,“农村成了泄洪池”。“三农问题”日益突出,部分乡村弥漫着悲观的情绪。农村不但没有成为现代文明合法的分享者,反而日益贫困。而这种贫困状况在处于内陆腹地的豫西山区更为明显。“河南人,特别是河南农村人的生存状况非常糟糕。河南农民所受的外部压榨,以及外部压榨造成的内在的、精神的伤害”⑤,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使人感觉痛之又痛。阎连科和农村人一起感同身受,把自己当作农村中的一员。“我之所以直到今天还说自己是农民,大约有两层含义:一是我的全部的亲人,今天几乎还在土地上耕作,几乎全部都靠着土地生存;二是我虽然以写作为生,是一个专业作家,但我的作品几乎都是写农村、农民,而且我的日常生活、一言一行都非常的农民化。”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民间身份定位和情感体验,阎连科对当下“疼痛的乡村”感到极大的无奈。因而他也一定程度上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呈现出令人百感交集的杂色调,使人理解乡土中国,介入当下中国乡村,把握当下农村的脉搏和情绪。
其次,阎连科对乡村政治情有独钟,是“因为我自己从小生活在乡村的最底层,对村干部有一种敬畏感,这可能使我对乡村的政治结构有一定了解而形成一种崇拜心理,它可能会成为我作品的‘村落文化非常大的一部分。……有人类以来,与之相伴的就是权力的存在,这是文学一个永恒的话题,你从小对权力有一种崇拜,你就不可能不表现这一主题。”⑥童年记忆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一个人成年后的思想内涵。阎连科的乡村小说最能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作者不动声色的冷峻叙述下所抒发的对底层的人性关怀,写出了贫困艰辛的生活重压下耙耧山民对权力的卑微渴望。刘根宝的经历之所以让人在辛酸的背后感觉到彻骨的悲凉,让人内心浸润着同情和悲悯,这是因为人们面对强大的官本位权力钳制的社会束手无策,徒添无奈。
乡土中国是一个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国家,“中华文化始终受到强大的中央集权政治力量的控摄、支配,从而形成以‘求治为目的的鲜明的政治型范式”。“由于长期专制统治的压抑和专制文化的熏陶,社会对于凌驾于自身之上的绝对君权,形成一种莫名的敬畏心理。”“对于专制君主的无限恐惧和绝对服从,是中国专制政治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社会心理因素。”⑦这种文化心理表现在日常生活上就是对权力的微薄渴望。村长借助公共权力随意支配他人,决定他人的命运,而广大村民对权力的争夺也只是想改变自己被奴役的地位。然而获得权力自然也是以他人的不自由,以他人的被奴役地位作为代价。乡村社会到处活动着政治人或类政治人的身影。由此,我们不难发现阎连科揭露了封闭落后的耙耧山区最缺乏的东西——现代性精神。新世纪的刘根宝们比五四时代的阿Q还要“虫豸”。时代进步了,而人的主体性却变得更为孱弱。
从《黑猪毛 白猪毛》中,我们不难看出阎连科的乡村小说在理性审视的同时,常常不由自主地流溢出对农民命运的真诚关注,深得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精髓,但是却又有些不忍。同时,他与同时代的河南作家李佩甫对农村政治的冷峻剖析(如《羊的门》)也不一样,他显得更伤悲、更欲哭无泪。阎连科的当代性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创作态度常常是矛盾的:有批判,有不忍;有痛恨,也有同情。显然,阎连科对乡村文明的现代化命运持有明确的批判态度,只是作者的理性有时难免会受到怜悯情绪的冲击,从而削弱了理性之光。而这些又使他的小说更多地具有了一言难尽的意味。
作者系复旦大学中文系在站博士后,咸宁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①张学昕,阎连科.现实、存在与现实主义[J].当代作家评论,2008,2.
②陈国和.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以贾平凹、阎连科和陈应松为个案[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③丁帆.论近期小说中乡土与都市的精神蜕变——以《黑猪毛 白猪毛》和《瓦田上空的麦田》为考察对象[J].文学评论,2003,(3).
④转引自[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修订本)[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⑤阎连科,姚晓雷.写作是因为对生活的厌倦与恐惧[J].当代作家评论,2004,(2).
⑥阎连科,梁鸿.巫婆的红筷子——作家与文学博士对话录[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2.
⑥ 冯天瑜,何晓明,周积明.中华文化史(第2版)[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