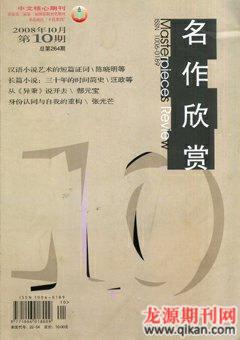文明落差间的心灵风景
毕光明
【推荐理由】
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哦,香雪》,是“新时期文学”中留给人们印象最深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铁凝没有附和“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文学潮流,去讲叙一个文明与愚昧相冲突的故事,而是基于自我感兴,将审美的关照,聚焦于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白璧无瑕的处子们——一群单纯淳朴的山村姑娘,满怀善意地观察这些敏感的姑娘对新鲜事物所做出的心理反应(以对人的心灵关照取代了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以散文化和抒情的手法表现了生命情态的美,体现了纯文学独特的功能与价值,给20世纪80年代耽于历史反思而过于紧张的文学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型。小说的创作和获奖,表明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创作主体那里自发地开始了由社会性向文学性的重心转移,作家与读者的审美意识一起觉醒,这无疑是对“文学回到自身”的最初的询唤。置于20世纪文学背景上,这篇小说在“人的觉醒”与“文的自觉”同时展开方面具有结构性意义。
198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哦,香雪》无论对于作者铁凝还是对于当代文学史,都有重要意义:铁凝因为这篇作品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及首届“青年文学奖”而成为知名作家,她的文学抱负得到初步的实现,创作生涯展现出诱人的前景;小说在评奖过程中得到犹豫的肯定①,获奖后迅速产生广泛而强烈的反响,表明当代文学在20世纪80年代初从创作主体那里自发地开始了由社会性向文学性的重心转移,作家与读者的审美意识一起觉醒。虽然铁凝后来的创作日益丰富,审美品格也随着作家创作思想的成熟和文学环境的变化而有较大的改变,但这篇风格纯净的抒情小说从未减损它独有的魅力和独特的价值,这是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纯文学的固有的魅力和价值。《哦,香雪》与它同时代的汪曾祺的《受戒》、王蒙的《海的梦》等作品一起,复活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诗化、散文化的抒情小说传统。纵然作品同它的主人公一样,身上保留着稚嫩的痕迹,小说的故事叙述中也存在着人性表现对时代话语的迎就②,但正是这些或显或隐的问题,使得《哦,香雪》以“清水出芙蓉”般的自然,映现着变动的时代在人的心灵中搅起的波澜。抒情小说的特质是主观化,人物的情感世界代替故事情节而成为主要的表现对象,作品在表现这一情感世界时也灌注了作者的主观感情,这样的表现赋予小说以诗性气质,具有直接的感染力。《哦,香雪》的文学价值能够与它的文学史价值并存,就在于它从作者的审美经验世界里复制出了淳朴天然的女儿心灵图景,这是比任何生活形态都有美感的精神风景。
《哦,香雪》所描绘的心灵风景,镶嵌在古老中国的传统农业文明遭遇到现代工业文明冲击这一历史背景上。大山深处的台儿沟,一个只有十几户人家的与世隔绝的小山村,仅仅因为地理的原因,被人类文明进程抛在了后边,在20世纪的后半叶,仍然固守在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简单的生存方式里。当“现代化”突然膨胀起来,台儿沟的宁静被打破了。两根顽强延伸的纤细、闪亮的铁轨从山外延伸过来,引来“绿色的长龙”——火车,用它威猛的气势和窗口内的风景震撼了、吸引了台儿沟的生存主体,开始改变他们的生活。不过,作者铁凝,并没有附和“八十年代”初的反思文学潮流,去讲叙一个文明与愚昧相冲突的故事,而是基于自我感兴,将审美的关照,聚焦于农业文明孕育出来的白璧无瑕的处子们——一群单纯淳朴的山村姑娘,满怀善意地观察这些敏感的姑娘对新鲜事物所做出的心理反应。就如同她的文学宗师沈从文、孙犁等人一样,铁凝更关心的不是生活形态,而是生命形态。也许受孙犁影响更深的缘故,也许自身审美个性所致,初涉文坛的铁凝,歆爱的是具有纯净美的生命形态,这种生命形态的极品,自然是尚未被现代文明惊扰和污染的偏僻山野里的年轻姑娘。以主人公香雪和凤娇为代表的台儿沟的姑娘们,就是这样的生命形态。她们的美,不只在于外表,更在于心灵——还没有学会势利和算计,保留着善良天性的心灵。这种在现代文明世界里所见无多的生命形态,对于现代人来说,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铁凝塑造香雪这样的艺术形象,其动机超越了对社会改革的思考,以满足审美需要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目的,这体现出她创作的个人性,《哦,香雪》产生反响和具有持久的艺术魅力,正来自作家和作品的这种纯文学品质。
铁路修到了偏僻闭塞的台儿沟,从首都开往山西的火车,每晚在这里停留一分钟,这意味着呼啸而来的现代文明,以它的速度与力量打破了山乡的宁静与停滞,以它的丰富与神奇向贫穷落后显示了它的无可抗拒的优越性和吸引力。火车经过这里时,已经在享用现代文明的人们,从车上“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驶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这样的情景,反映的不是文明的冲突,恰恰是文明的落差带来的有意味的生活现象。车上与车下的人,虽同处于一个时代,但他们实际上却生存于不同的文明史阶段,他们生活的是两个世界。现在行驶的火车,把他们的空间界限打破了:通过火车这个工业文明的象征物本身,以及列车窗口里的山外城市人的饰物与用品(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人造革学生书包,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等),台儿沟的姑娘看到了一个对于她们来说陌生而新奇的世界。她们本能地对这个世界感到好奇,并产生了解的愿望,还满怀羡慕和憧憬。文明的落差在低处溅起了兴奋的水花。这水花就是没见过世面的山村姑娘窥见新世界后引起的内心的情感激荡。从前她们跟大人们一样,吃过晚饭就钻被窝,有火车开来后,“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把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得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的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胭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与其说火车进山改变了山村人的生活节律,不如说现代文明的冲击,在静止的农业文明主体身上引发了一场心理事件。也许对于处在不同进化阶段的两种文明作价值判断过于冒险,也有困难,但可以肯定,因文明的冲击而引起的积极向上的心理——何况是花季女子纯净澄明的心灵世界,体现的是生命的价值,故而对它进行艺术表现乃是纯文学作家本能的选择。
台儿沟的姑娘们是一个群体,她们有着山村姑娘共有的纯真、朴实和善良,以及对美的热爱和隐秘的梦想。她们的性格与心灵,在对火车与火车带来的山外的事物与人表现出强烈兴趣,以及在用土产从车上的旅客那里换回日常生活用品和用于打扮自己的饰物等行为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哪怕是类似“(火车)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你们城市里一天吃几顿饭”这样的真诚而幼稚的发问,都让人感应到她们美不胜收的心灵世界,不由得到一种精神的澡雪和享受。然而小说对台儿庄姑娘集体性格的描写,似乎是对主要刻画对象的必要的铺垫与烘托,或者说,台儿沟姑娘美丽的心灵世界,在主要角色香雪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在对现代文明表现出热爱和追慕上,香雪是台儿沟姑娘的领头人和杰出的代表,因为看火车“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尽管在陌生的事物面前,香雪表现得更胆小,比如当火车停住时“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边,双手紧紧捂着耳朵”,但是对火车所载来的新的世界,香雪比以好友凤娇为代表的其他同村姑娘有更执著的追求。更重要的是,她们所追求的对象很不相同。凭着青春期的敏锐,同样是从五彩缤纷的车上世界里捕捉到自己的喜爱之物,凤娇们一眼看见的是“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香雪发现的却是“人造革学生书包”,都是山里人不曾享用的先进的工业产品,但前者是用于美化自己的外表,满足人对物的需求,后者则用于对知识的学习,帮助人在文化上提升自我。不同的发现,透露了她们精神世界原有的差异,这是自然和文化、感性与理性的差异。这差异来自于香雪受过更高的学校教育,是台儿沟唯一的女初中生。受教育的程度不同,意味着她们的生命品质存在看不见的差异。所以对于每天晚上七点那宝贵的一分钟,她们有不同的期待,对于火车带来的山外之物,她们有不同的愿望对象。凤娇很快暗恋上的,是第三节车厢上的那个“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的“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从第一次接触到后来的无功利目的的交往,凤娇从中得到了难以言传的情感和心理的满足。这种连巨大的城乡差别都阻挡不了的坚决而美好的一厢情愿式的爱恋,本质上是一种不需要学习的与生俱来的爱欲。而香雪呢,强烈渴望于火车的,是帮助她得到一个朝思暮想的铅笔盒——能够自动开关的铅笔盒。香雪心里一直装着这种铅笔盒和它的价值:“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叫人瞧不起。可见,铅笔盒能够满足的是比爱的需求更高一个层次的自我实现需求。是这样的深层需求,驱使着香雪为向车上的旅客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和问它的价钱而追赶火车,当终于从火车上发现了这种铅笔盒,便想都没想来不来得及,毫不犹豫地冲上车去,用一篮子鸡蛋与铅笔盒的主人大学生交换,以至于被火车带走……香雪为了打听铅笔盒而去追火车,被凤娇们认为“是一件值不当的事”,香雪不同意她们的看法,说明她的精神世界比她们要广阔。“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 她们更喜爱的是发卡、纱巾、花色繁多的尼龙袜,而香雪总是利用做买卖的机会向旅客“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这表明,火车停站的短暂的一分钟带给姑娘们的喜怒哀乐,是有着不同的内容的。小说通过这样的对照,把香雪心灵世界的内涵渲染了出来。
铅笔盒这个象征性的实物,是这篇小说的纽结所在,自始至终也是主人公的情结。小说所描绘的,主要就是这个铅笔盒所引起的内心波澜。铅笔盒作为一个文具,自然可以看成知识的象征。对知识的追求,正是上世纪80年代初现代化运动兴起的时代背景上最响亮的话语,乡村中学生香雪的铅笔盒故事,不能说没有呼应关于现代化的历史诉求,故事的讲述多多少少也就带有叙事性。但是铅笔盒故事里的道具意义,它所不断暗示的,还是人性的魅力。在山村姑娘香雪来说,铅笔盒留给她的,是创伤的记忆。在公社中学里,她使用的父亲亲手做给她的木头铅笔盒,遭到了同学们的取笑,心地单纯的她,自尊受到了严重的伤害。造成这种伤害的力量,主要不是同学,而是现代文明:城市里才有的机器制造的可以自己关上的塑料铅笔盒,把她的手工制作的木铅笔盒比得那样寒伧。让她受到伤害的,不只是铅笔盒,也包括闭塞的台儿沟所保留的一天只吃两顿饭的落后的生存方式。当老实善良的香雪终于明白她和她的台儿沟是被人耻笑的对象,她的内心也就埋下了对现代文明的向往。香雪那个时代的现代文明,也就是由铅笔盒所代表的工业文明。只要能拥有这种铅笔盒,她就能理直气壮地生活在同一种文明里,失去的自尊就能找回,再也不会被人看不起。所以得到新型铅笔盒,首先是香雪的个人需要,是获得尊严、实现自我的需要,即使叙事主体受制于开放改革时期的国家话语,但对人物的刻画只能遵循人性的逻辑。香雪的情结就是要洗雪文明的落差带给她的屈辱。从首都开来的火车给她带来了机会。她不惜代价地从女大学生手中换来了自动铅笔盒。这个铅笔盒将改变她的身份,使她进入先进文明的行列,与山外的同学平起平坐。这是未曾遭到文明撞击带来的屈辱的凤娇们所难以理解的。铅笔盒不仅给了香雪巨大的力量,帮助一向胆子小的她战胜了走夜路的恐惧,还改变了香雪对这个世界的感受: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和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来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
借着自然风景的描写,香雪获得了自我的心理感觉得到了生动的抒发。自然风景皆“著我之色彩”,也就变成美丽的心灵风景。小说出现大量的拟人化描写,无不是成长中的主人公内在世界外化的需要。当然,它也是铁凝艺术才华的显现。铁凝用诗的笔墨,给上世纪80年代耽于历史反思而过于紧张的文学③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
对香雪精神世界的表现,来自于作者的生活经验与文学追求的契合所引起的创作冲动,在深层上也是作者的心性、品格和审美理想的艺术外化。铁凝的文学写作是一种很本真的写作。香雪这个北方山村女孩儿美好的形象与美丽的心灵,难道不是铁凝这个钟情文学、有才华的北方女子的内在世界的投射?台儿沟和香雪的故事,固然是作家对生活的发现,对历史足音的感应,但也自然地透露了涉足文学世界的铁凝对人的一种由衷期待。正是这种期待,使得她发现了香雪这样的美好的生命,从而充满深情地唱出了一曲理想的生命之歌。铁凝笔下的香雪让我们想起沈从文《边城》中的翠翠。火车的呼啸,居然“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这个香雪,多像“边城”的那个“小兽物”,秉有自然赋予的单纯、质朴和灵敏。所不同的是,对于生活和生活的世界,读书的香雪远比没读过书的翠翠主动。香雪的美与可爱,既在外表,更在心灵,是一个只有在远离城市文明才能找到的晶莹剔透的女孩儿。她不仅像她的同伴夸羡的那样“天生一副好皮子”,心地也十分单纯美好,待人格外真诚。这从她跟车上的旅客做买卖就看得出来: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静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香雪不知道什么叫受骗,也从来不做骗人的事。一个例子是,“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旧汗褂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灵魂也如此一尘不染,称得上从里到外洁净温润如玉。由台儿沟的姑娘们烘托出的香雪是一个“这个”。这一几近圣洁的形象,在上世纪80年代萦绕着历史沧桑的文学人物画廊里,显得格外清新宜人,因而在美学形态上为“新时期”文学拓出了新生面,这篇小说因此成为近30年来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作品之一。香雪这一形象的真实性和美质,来自于特殊年龄阶段和没有污染的农业文明环境里的年轻姑娘身上才有的不会长存的“女儿性”。我们从后来铁凝塑造的超过了这一年龄段而进入物欲对象化的人生期的女性(如《玫瑰门》里的司猗纹),显露出女性生命中卑琐丑陋的一面,就可以感受到香雪的生命情态其实是一种难以挽留的本真美。《哦,香雪》的不可替代,就在于它的作者以审美的态度观照了两种文明撞击时闪现出来的生命与人性之美,以及工业文明的到来带给人的现代化焦虑。
由于相对自由的创作环境促进了作家主体性的发挥,小说的叙事焦点始终在主人公找回自我的努力,和这一寻找过程中的心理活动上。小说通过主观化的叙写,特别是通过香雪发现了渴望已久的自动铅笔盒而跳上火车以致被火车带走,和如愿得到铅笔盒之后一个人走夜路回家的动静和情景的刻画,生动地展现了新世界的出现在一个富有自然美的山村女儿身上引发的精神事件,表达了青年女作家铁凝对人性美的审美取向,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型。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出现的诗性叙事,它以人格成长的人文内涵和主观化的表现方式,加入了“文学回到自身”的努力,呼应了再度奏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主旋律。——这就是重读《哦,香雪》可以感受到的这篇小说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结构性意义。
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①据担任评委的著名短篇小说专家崔道怡先生介绍,1982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在第一批提供评委参考的备选篇目中,没有《哦,香雪》,第一次评委会(1983年1月29日)也没有提到这篇小说。第二批的备选篇目中有《哦,香雪》,第二次评委会(1983年2月26日)的最后才被提名,沙汀、唐弢、王蒙等几位评委各自表示了对这篇小说的偏爱,并建议在排名上靠前,小说终以第五名的名次获奖。评奖活动进行中,老作家孙犁写给铁凝,对《哦,香雪》表示激赏的信,为《小说选刊》转载,对这篇小说的获奖起了积极作用。崔道怡说他在一篇文章里对这一情况作过评说:“《香雪》之美能被感知,感知之后敢于表达,存在一个暂短过程。这个过程表明,在评价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含量与交融上,有些人还有些被动与波动。当社会强调对文学的政治需求时,社会性更受重视;当形势宽松了对文学的制约时,艺术的美感才得更好地焕发其魅力。”——参见崔道怡的《从头到尾都是诗的小说——铁凝的〈哦,香雪〉》。
②可参看蒋军《重读铁凝的〈哦,香雪〉》(《文学教育》,2007年第11期)一文的分析。
① 洪子诚先生在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里,根据黄子平对新时期文学特征的评价,指出:“作家的意识和题材的状况,影响了80年代文学的内部结构和美感基调。在相当多的作品中,可以感受到一种沉重、紧张的基调。”——见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2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