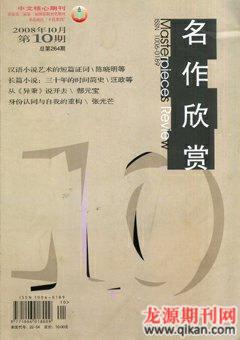身份认同与自我的重构
张光芒
【推荐理由】
《归去来》是韩少功的第一篇寻根小说,同时也是当代最早表现出自觉的寻根意识的创作之一,其“归乡/寻根”叙事模式成为当代创作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型意象。小说在某种程度上引领了寻根潮流,但其语言气质、叙事结构及思想内涵又远非“寻根”所能概括。它首次向世人预示,对于民族之根的追寻,对于民族自我的重铸,与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于个体自我的重构是同步进行的。在这一过程中,主人公既对那个“巨大的我”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同时更重新确立着自我的本质,自我重构的价值与可能性被充分地打开。小说由此也获得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人类学内涵。认同之路尽管充满艰难和焦虑,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自我”正在生成。小说叙事成为一次文化重建的尝试,一场身份认同的冒险,一种自我重构的寓言。
迄今为止,研究界对韩少功《归去来》的解读和推崇主要是与“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或者魔幻现实主义等关键词联系在一起的。也正是由于将《归去来》置于这些涵盖面颇大的关键词和文学现象之下,反而限制了对该小说丰富内涵及其特色的进一步挖掘。尤其是作为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创作现象或创作潮流,“知青小说”“寻根”小说或者魔幻现实主义这些说法各自都有一些更有影响的代表作,因此若受制于这些概念,固然容易对《归去来》进行文学史定位,但其独具特质的重要性与文学价值也不可避免地被遮蔽掉一部分。在笔者看来,《归去来》不仅与当时的文化寻根思潮和有着复杂的关系,而且表现出为极为独特的身份认同的新型主题,正如作品题目所暗示的,小说人物始终处于“归去——归来”的梦幻与现实的交织之中,进行着“迷失——追寻”的民族认同与自我认同的不懈努力。
《归去来》是韩少功的第一篇“寻根”小说,同时也是当代文学史上最早表现出自觉的“寻根”意识的创作之一。不过,对于《归去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一般把韩少功的《文学的“根”》与中篇小说《爸爸爸》分别视为当代“寻根”小说思潮在理论和创作上的代表作,但最能体现以《文学的“根”》为代表的理论主张的作品恰恰不是《爸爸爸》,而是《归去来》。只要联系1980年代中期那批作家和批评家对于“寻根”运动的理论倡导和观点阐释,我们会发现,《爸爸爸》其实主要是揭示了我们民族文化长期因袭的一种麻木迷信、保守愚昧的“劣根”。通过阿Q式的永远长不大的丙崽形象的塑造,作家对民族文化形态进行了集中的理性批判。而“寻根”小说家的初衷却是要追求“一种对民族的重新认识,一种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苏醒,一种追求和把握人世无限感和永恒感的对象化表现”。他们坚信“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而作家的责任就是“释放现代观念的热能,来重铸和镀亮”“民族的自我”①。1986年,韩少功在《寻找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一文中进一步对“寻根”这一概念做了明确界定,指出所谓“寻根”就是力图寻找一种东方文化的思维和审美优势,以促进中国文化的重造和再生。也就是说,寻“根”的同时也就是寻找文化发展与文学发展的动力,而能够构成“动力”的显然绝非那个愚顽不化、丑陋不堪的丙崽形象,亦非《女女女》的主人公所能承担,而《归去来》恰恰就是探究这种“优根”而非“劣根”。正如另一位寻根思潮的积极倡导者李杭育所说的,一个好的作家,仅仅能够把握时代潮流而“同步前进”是很不够的。仅仅一个时代在他是很不满足的。大作家不只属于一个时代,他跟前过往着现世景象,耳边常有“时代的召唤”,“而冥冥之中,他又必定感受到另一个更深沉、更深厚因而也更迷人的呼唤——他的民族文化的呼唤”②。小说的主人公黄治先便在这种“冥冥之中”接受了乡民们—— 一种文化传统的呼唤,将自己当成了人们记忆中的“马眼镜”,即使在他回到城市后仍然没能改变这一角度的转移。
此后,《归去来》的这种“归乡/寻根”成为韩少功创作、知青文学乃至许多当代创作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型意象或者叙事模式。这反映了1980年代在现代性与传统的思想碰撞中一代作家内心回归的渴望与强烈的情感焦虑。一方面,就个体而言,传统总是以无意识的形态决定着人们的心理结构,正所谓“文化制约着人类”。在《访法散记》之《我心归去》中,韩少功就说过:“使你热泪突然涌流的想象,常常是故乡的小径,故乡的月夜。月夜下的草坡泛着银色的光泽,一只小羊还未归家,或者一只犁头还插在地边等待明天。”这不仅仅一种对乡土难以割舍的留恋,更是一种强大的和潜在的情感倾向性。这一倾向在《归去来》便表现为,主人公黄治先在离乡返城多年之后,再到一个没有从来去过的乡村时,竟然有一连串神秘的预感被证实,那些茅草屋、未老先衰的水牛、雷电击毁的大树,哪怕是一些小小的细节,“似乎都在我的想象之中”。当一位位乡民把一件件关于马眼镜的故事安置在我身上时,“我”接受起来也是那么自然,甚至是心安理得,尽管“我”也常有犹疑之处,但并不会引起人们的怀疑。
另一方面,从乡村文化这一方面来说,那里的民心向背和正义感,遵从世训的道德意识和无私高尚的品格,纯洁的情感和质朴的表达方式等等,这些本身就对“我”充满着强大的吸引力,使“我”欲拒不能。这些凝固的传统因素与“我”的潜在的心理结构几乎是一拍即合,甚至甘愿承受四妹子的抱怨,帮她实现姐姐未竟的心愿。“我”的这番神秘体验隐喻了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对人的无所不在的巨大影响力和形塑作用,同时也深刻地意味着,自我的失落与重构离不开对于历史之“根”与文化之“根”的开掘。
1980年代是城乡文明及中西文明冲突极为剧烈的时期,对于知青作家来说对于这种冲突的感受尤其强烈。正如有评论者注意到的,知青作家与上一代或上几代作家相比而言,他们缺乏一种强大的政治信念作为精神支柱,因而当现实的政治理想失落之后,他们必须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来证明他们存在于文坛的意义,即使在现实中找不到,也应该到想象中去寻找。在排除了对城市文明的完全认同和对于西方文化的全盘接受之后,他们“利用起自己曾经下乡接近农民的日常生活的经验,并透过这种生活经验进一步寻找散失在民间的传统文化的价值”③。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民族之根的追寻,对于民族自我的重铸,与一代人的身份认同及其对于个体自我的重构是同步进行的。因此,《归去来》与“寻根”文学有着远为复杂的关系,而且在寻根理论与寻根创作本身也充满着悖论与复杂性,在某种程度上,《归去来》从创作上引领了寻根潮流,但它又远非“寻根”小说所能概括的。
身份认同问题是现代性的产物,尤其在1980年代后,我是谁?我从何而来,到何处去?这些问题在日益复杂的社会文化矛盾中成为知识分子不得不面对和苦苦追寻的问题。实际上,《归去来》中的主人公便是最早表现出这样一种身份认同焦虑的形象。在他整个精神游历与神秘体验过程中,始终存在着一系列历史与现实、自我与他者、真实与虚幻、记忆与遗忘、怀疑与确证、认同与拒绝的矛盾冲突之中。即使当他“潜逃”出那个山寨,试图告别那个“莫名其妙的我”,回到从前的“我”的时候,却又对那个原来的“我”——黄治先发生了怀疑,感觉“永远也走不出那个巨大的我了”。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这一身份认同问题,我们不妨暂时把这一位主人公切割成三个不同的人物形象:黄治先、马眼镜和介入二者之间的“我”。先看黄治先,从小说的叙述中可知,黄治先是一个曾经下过乡的知青,现在在城市中生活,他的具体的工作、职业等情况我们不得而知,但这并不重要,我们只需要从小说的一些信息可以看出他的基本的生活状态:从他说自己“一生都会奔波辛苦,我……有我的事业”来看,他的工作很辛苦。他向朋友挂长途电话时,本想问问对方在牌桌上把那个曹癞子打“跪”没有,这说明他在城里的生活比较无聊。甚至当四妹子谴责“你们城里人,是没情义的”的时候,他几乎没有辩解,说明他对“城里人”并不认同。从故事叙事中,我们可以发现他似乎本是为香米和鸦片来山寨的,但小说最后又说“其实我要香米或鸦片干什么呢?似乎本不是为这个来的”。综合这些情况可以表明,黄治先对在城里的整个生活状态不满意,甚至常常有迷去“自我”的感觉。“黄治先”这个名字似乎也有暗示,“黄”是传统文化,“治”可以理解成文治武功的“治”,而“先”指先在的、先验的,存在于人物潜在心理结构之中的。综合起来也就是说,一种文化传统已经先在地或先验地存在于人物的心理结构之中。
正是由于黄治先对现实生活的失望,对“自我”的怀疑,使他在返乡之旅中发生了严重的身份转移。当他踏上去山寨的路时,另一个潜在的“自我”被逐步激活。“一个人只有在其他自我之中才是自我。在不参照他周围的那些人的情况下,自我是无法得到描述的。”“我通过我从何处说话,根据家谱、社会空间、社会地位和功能的地势、我所爱的与我关系密切的人,关键地还有在其中我最重要的规定关系得以出现的道德和精神方向感,来定义我是谁。”④因此,尤其当山寨的人们以“马眼镜”视之时,那个先在的本处于潜伏状态的“自我”借马眼镜这一形象得以复活。
“黄治先”于是不仅成为山寨人眼中的“马眼镜”,而且他自己也对“马眼镜”产生了强烈的自我认同。关于马眼镜这一形象,我们从小说叙事中可以看出,他过去与黄治先有着相似的经历,只是他过早地离世了。在这土地上,他与人们建立了和谐美好的人际关系,亲密无间的融合于这一文化场域之中。而且他用自己的知识和能力帮助人们,甚至还杀过一个恶人,深受这里人们的爱戴。这一形象虽然不是黄治先,但它唤起了黄治先自我重构的冲动。《归去来》最有贡献的地方就是对这一自我重构过程的描述。小说叙事主要是通过对话和心理活动展开的,正是在充满乡土色彩的语言交流和越来越近的心理交流中,黄治先成了马眼镜。正如泰勒强调的:“我对我的同一性的发现,并不意味着是我独自做出的,而是我通过与他人的、部分公开、部分隐藏在心的对话实现的。这就是为什么内在生成同一性之理想的发展,赋予了认同一种新的和关键性的重要性。我自己的同一性根本上依赖于我与他人的对话关系。”⑤在语言/对话与自我重构的同步进行中,黄治先一方面找到了归属感,对那种“强大的我”产生了强烈的身份认同,而另一方面又重新确立着自我的本质。这一本质从小的方面说,是对于一种充满传统文化底蕴的正义感与和谐美好的人性,从大的方面说,则可以视为对于人类本质的向往,那就是爱与美与创造性的人生形式。自我重构的价值与可能性被通过艺术形象被充分地打开。想象中的“马眼镜”也许才是更加真实的“自我”,这时,那个庸庸碌碌的“黄治先”则更像是假的“自我”,因此“我”有了如此“异样的感觉”:穿鞋之前,我望着这个蓝色的我,“好像这身体很陌生,很怪”。《归去来》由此也获得了深厚的文化意蕴与人类学内涵。
然而,重构自我的道路却不是那么平坦的,“重新确认自己的认同,这不只是把握自己的一种方式,而且是把握世界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们获得生存理由和生存意义的一种方式。”“新的信仰和自我认同需要新的社会制度作为实践条件,因此,寻找认同的过程就不只是一个心理的过程,而是一个直接参与政治、法律、道德、审美和其他社会实践的过程。”⑥也就是说,身份认同需要“自我”与整个社会环境之间产生一种良性的互动,才能顺利完成,而当时的社会文化现实并没有提供这样的充分条件。小说的叙述者“我”作为最为现实性的人物形象,最终深切地感受到了在两个“自我”之间转换的艰难甚至分裂感和尴尬,小说结尾处的“我累了”“妈妈”等感叹道出了其身份认同的困难和自我重构的焦虑。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欣喜地发现,当“我”打电话想问问牌桌上的事情的时候,“出口却成了打听自学成才考试的事”,这就意味着,认同之路尽管充满艰难和痛苦,但一个新的充满希望的“自我”正在生成。所谓三个人物形象,黄治先,马眼镜,“我”,其实就是三个“自我”,他们分别与“归”“去”“来”三个动作意象相对应——回归乡土的黄治先,已经逝去的马眼镜,失而复得并正在走向未来的“我”。由此,小说《归去来》成为一次文化重建的尝试,一场身份认同的冒险,一种自我重构的寓言。
作者系南京大学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②李杭育:《理一理我们的“根”》,《作家》,1985年第9期。
③何言宏、杨霞:《坚持与抵抗:韩少功》,上海人民出版社,第72页-第73页。
④泰勒:《自我的根源:现代认同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49页。
⑤泰勒:《现代性之隐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第55页。
⑥ 汪晖:《现代思想的悖论——〈汪晖自选集〉自序》,《死火重温》,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