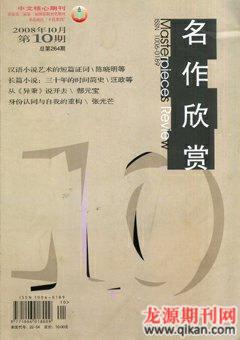理想精神的诗化表达
王春林 陆 琳
【推荐理由】
要从新时期最起码数以几十万篇计的短篇小说中,选择出十多篇带有经典意味的短篇小说来,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即使是仅仅要从王蒙的短篇小说中,选出一篇最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来,难度也是很大的。王蒙当然是新时期以来最为重要的小说作家之一,他在长中短篇小说,甚至于在微型小说的创作方面均有显著成绩取得。该选择哪一篇短篇小说呢?《春之声》《海的梦》《夜的眼》《木箱深处的紫绸花服》《坚硬的稀粥》《十字架上》,还是《哦,穆罕默德•阿麦德》,似乎选择哪一篇都有充分的理由。思虑再三,最终还是选定了《海的梦》。因为这是一篇文体特色特别鲜明的短篇小说,是一篇通篇都流淌着诗意的纯粹的短篇小说。夸张一点说,这一篇《海的梦》简直就是一首关于知识分子理想精神的优美抒情诗。
《名作欣赏》编辑部意欲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演变历程,从数以几十万篇计的短篇小说中选取了十二篇佳作,是谓新时期经典短篇小说。内有王蒙的短篇小说《海的梦》,因我向来关注王蒙的文学创作,所以就将鉴赏评论《海的梦》的任务交待于我。这样,我也就自然有了一次重读《海的梦》的机会。
关于《海的梦》,我自然阅读过不止一次,最早是在上大学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自己根本谈不上什么审美能力的具备,更多地只是人云亦云地生吞活剥而已。当时读过《海的梦》之后,感觉自然很好。但究竟好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说这是一篇相当精彩的短篇小说呢?自己其实根本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能是顺乎时代潮流地将其看作一篇带有现代主义色彩的意识流小说而已。
后来当然也有机会再次阅读《海的梦》,这个时候已经明显地感觉到了所谓意识流小说的理解与定位的荒唐可笑,只是没有机会将这种感觉整理成文。这次《名作欣赏》约稿,我正好又刚刚读完王蒙洋洋一百二十多万言的自传,其中有许多谈及自己小说创作的文字。我认为,作者的这些文字,对于我们重新理解他的作品当然大有裨益。这样,我也就能够结合王蒙的自传,将我阅读《海的梦》 的体会全部写出了。
我注意到,不仅在小说发表的当时,有许多评论家,甚至包括那个时候的王蒙自己,都把《海的梦》看作是意识流式的小说作品。而且,一直到现在,一些当代文学史著作也仍然还是有着这样的一种看法。其实,这样的一种看法是很难站住脚的。
为什么呢?且让我们先来看王蒙自传第二部《大块文章》中的这样一段文字:“是我的一系列实验小说:《布礼》《蝴蝶》《夜的眼》《海的梦》《风筝飘带》与《春之声》,实际影响不小。但包括我自己的关于‘意识流的谈论是绝对皮相的与廉价的。我至今没有认真读过例如乔伊斯,例如福克纳,例如伍尔芙,例如任何意识流的理论与果实。对于意识流的理解不过是我对于这一汉字的望文生义。意识,很好,写到了心理活动的细部。流,更好,它像溪水的流动,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风风雨雨,飘飘荡荡。啊,这将是怎样摇曳多姿的文字!”①
虽然王蒙自己当年也曾经一度将《海的梦》一类的作品指认为所谓的意识流的作品,但通过王蒙自传中的这一段话语,我们却不难看出,这样一种将其与西方意义上的意识流联系起来的理解,其实是比较荒唐的。因为,这样一种理解明显地忽略了对于小说文本的充分尊重。从小说的文本实际来看,应该说,王蒙上述文字中自己从汉字意义上对于意识流的解说,才是更加切合于小说艺术品格的一种理解。《海的梦》的确既触及到了“人物心理活动的细部”,同时却也具备了如王蒙所说的这样一种“闪闪烁烁,明明暗暗,淅淅沥沥,隐隐现现,风风雨雨,飘飘荡荡”的摇曳多姿的文字风格。
实际上,篇幅不到一万字的《海的梦》的故事情节是极为简单的。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时年已经52岁了的缪可言,这样一位曾经在非常的政治岁月里被打成了“特嫌”,“从来没有到过外国,甚至没有见过海”的知识分子,终于有机会来到海边疗养,终于有机会见到了自己早就在各种文学作品中见识过,却一直没有机会亲眼目睹的梦寐以求的大海。小说所主要展示的便是缪可言在海边的短短五天时间里的所见所闻,不,更准确地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见闻,只能说是所思所想。而这所思所想,也正切合了王蒙在自传中所说的“心理活动的细部”。
虽然是一篇近万字的小说,但活动于其中的人物其实只有缪可言一人,除了偶然提到过的那对青年男女以及休养所所长和汽车驾驶员之外,别无他人。这样,我们也就可以说,小说的主体部分其实只是描写展示着缪可言与茫无边际的大海之间(也即人与大自然)的一种无言的情感交流过程。
难道一篇小说竟然可以只是写一个人与大海的情感交流过程吗?这样的小说又会有什么意义呢?对于已经习惯于接受具有明确主题意向的中国读者,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中国读者而言,这的确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关于这一点,王蒙在自传中也有着真切的记述与谈论。王蒙写道,自己的这一系列小说新作(当然包括《海的梦》)之所以遭到普遍的误解,“原因是,我们中的许多人,其中不少是文艺工作的领导太相信小说目的论了。对于他们,小说的故事、细节、语言、人物与描写都是手段,主题思想才是目的,政治思想的正确、及时、尖锐或者深刻、稳妥或者勇敢才是目的。而他们需要获得的主题思想是那样浅白,那样需要与报纸上的、教科书上的,至少是他或她本人的一篇论说文的某个标题挂钩。”②
而王蒙自己的小说创作呢,“我追求的是一种突然的感触,是内心的一个颤抖,是一个不知来自何方的启示,一个小说与世界,小说与灵魂终获相通的狂喜,一种远久的回味,一种不是你在写而是‘天假尔手的感觉——更正确说是一种状态,有点像运动员‘打疯了的那种状态。……言者不辩,辩者不言,真正的主题当然是有的,然而是言说不清楚的。因而,在目的论者那里,那样的言说不清的小说永远不在正册。”③
在我看来,《海的梦》正是鲜明体现着王蒙小说艺术追求的优秀小说。这篇根据王蒙1978年6月上旬的一次北戴河之旅演绎而成的短篇小说④,当然是有主题的,“然而是言说不清楚的”。这里,实际上就出现了一种悖论。王蒙说,自己的小说(包括《海的梦》)是有主题的,但这主题却言说不清楚。小说家当然可以这样表达,但对于批评家来说,却又是必须言说清楚的。一位对于自己的批评对象言说不清楚的批评家,肯定不会是一位合格的批评家。所以,我们也就只能勉为其难地尝试着解说一下《海的梦》这一“言说不清楚”的小说内在的主题含蕴了。
那么,王蒙的《海的梦》究竟要表达怎么样的主题意向呢?联系王蒙自己坎坷曲折的人生经历,我觉得,《海的梦》其实可以被理解为是对于一种知识分子的理想精神的诗化表达。缪可言刚刚抵达海边时,出现在他眼前的大海景观是这样的:“不,它什么都不是。它出现了,平衡,安谧,叫人觉得懒洋洋的。那是一匹与灰蒙蒙的天空浑成一体,然而比天的灰更深、更亮也更纯的灰色的绸缎,是高高地悬在地平线上的一层乳胶。隐隐约约,开始看到了绸缎的摆拂与乳胶的颤抖,看到了在笔直的水平线上下时隐时现、时聚时分的曲线,看到了昙花一现地生生灭灭的雪白的浪花。”这当然是一种高度主观感觉化了的大海景观,其中所映现出的其实是缪可言痛感青春与生命白白消耗的无望与无奈。“他只是联想到自己误了点,过了站,无法重做少年。他联想到不论什么样的好酒,如果发酵过度也会变成酸醋。俱往也,青春,爱情,和海的梦!”“呵,我的充满了焦渴的心灵,激荡的热情,离奇的幻想和童稚的思恋的梦中的海啊,你在哪里?”“然而,他游不过去了,那该死的左腿的小腿肚子!那无法变成二十五的五十二个逝去了的年头!”从以上的叙事话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缪可言一种痛感韶光已逝青春不再的精神痛苦。本来,缪可言是寻梦而来的,然而,他从大海那儿却没有能够找寻到自己的梦想,于是,失望之极的他便准备提前离开休养所了。
然而,就在他准备离开休养所的前夜,他在与满月下的大海告别的时候,却发现了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大海:“所有的差别——例如高楼和平地,陆上和海上——都在消失,所有的距离都在缩短,所有的纷争都在止歇,所有的激动都在平静下来,连潮水涌到沙岸上也是轻轻地、试探地、文明地……而超过这一切,主宰这一切,统治着这一切的是一片浑然的银光。亮得耀眼,活泼跳跃却又朦胧悠远的海波支持着布满青辉的天空,高举着一轮小小的、乳白色的月亮。在银波两边,月光连接不到的地方,则是玫瑰色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黑暗,随着缪可言的漫步,‘银光区也在向前移动。这天海相连,缓缓前移的银光区是这样地撩人心绪,缪可言快要流出泪来了。这一切都是安排好了的,海在他即将离去的前一个夜晚,装扮好了自己,向他温存,向他流盼,向他微笑,向他喁喁地私语。”“海——呀——我——爱——你!他终于喊出了声,声音并不大,他已经没有了当年的好嗓子。然而他惊起了一对青年男女。”与之前的大海景观相比,这绝对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充满了希望与憧憬的大海景观,在其中,很明显地蕴含着曾经饱经坎坷曲折的缪可言曾经一度的迷惘失落之后的精神复活与精神自我超越。
“不,那不会错,那就是人,就是刚刚被惊动了的那两位热恋中的青年人。缪可言又有什么怀疑的呢?如果是他自己,如果倒退三十年,如果他和他的心爱的姑娘在一起,他难道会怕黑吗?会嫌冷吗?会躲避这泛着银光的波浪吗?不,他和她会一口气游出去八千米。就是八公里,就是那个极目所至的地方。爱情、青春、自由的波涛,一代又一代地流动着、翻腾着,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淡漠,更永远不会中断。它们永远和海,和月,和风,和天空在一起。”
真可谓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蒙这里是在描写大海吗?是的。王蒙这里仅仅只是在描写大海吗?不是的。作家在这里所描写的其实是主人公缪可言从失落与迷惘中走出来之后,重建自己的理想精神世界的心路历程。如果我们可以将缪可言看作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化身的话,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说,实际上,王蒙是在借助于缪可言这一人物形象,传达着自屈原起就一直潜藏于知识分子精神深处的,一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理想主义情结。
必须注意到,王蒙《海的梦》的写作时间是在1980年。那是一个“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但“文革”的观念思维方式却依然影响很大的时代。王蒙在那样的一种时代文化语境中,能够写出如同《海的梦》这样带有明显的“言说不清楚”的主题意向,深刻地寄寓着知识分子理想精神的诗化短篇小说来,的确是相当难能可贵的。虽然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三十年,但至今读来,《海的梦》却依然能够深深地感动我们这个时代的读者。这就充分说明,《海的梦》的确已经成为了一篇实际上已经跨越了不同文化时空的经典短篇小说。
作者王春林系山西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作者陆琳系合肥工业大学人文经济学院副教授
① ②③④分别见《王蒙自传•大块文章》,花城出版社,2007年4月版,第91页,第56页,第56页,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