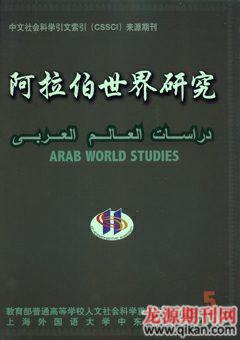反恐战争与美国—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演进
摘要:“9•11”事件后,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推进,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反恐战争的认识和反应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导致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超出国家范畴,向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延伸,形成了一个国家对抗一种宗教群体的局面。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重大演变导致双方的敌意和对立进一步加剧,成为影响当前国际局势的主要因素之一。
关 键 词:美国中东政策;反恐战争;伊斯兰世界;意识形态化
作者简介:张屹峰,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东欧中西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上海200020)。
文章编号:1673-5101(2008)05-0048-07中图分类号:D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上海合作组织进一步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研究”(07BGJ004)的阶段性成果。
“9·11”事件后,反恐成为美国对外战略的重中之重。在反恐的大背景下,美国与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本文以“9·11”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演变为切入点,考察反恐战争导致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深刻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对美国、伊斯兰世界和国际局势的深远影响。
一、“9·11”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及其特点
19世纪以来,以中东地区为核心的伊斯兰世界一直是英、法、德、意、俄等近代殖民主义列强的传统势力范围,美国难以插手其事务。因此,“美国没有卷入与穆斯林国家的血腥冲突,没有直接统治阿拉伯和穆斯林的土地或实行欧洲的帝国主义政策。”[1]38而且,一战后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十四点计划”所包含的民族自决原则和非殖民化主张,符合伊斯兰世界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关系相对超脱,不像欧洲列强与之存在尖锐矛盾。二战后,美国积极寻求霸权地位并开始大规模介入伊斯兰世界事务,两者之间的关系才有了实质性转变。
冷战时期,美国将共产主义视为最大“威胁”,遏制共产主义扩张是美对外政策的主要战略目标。在中东,对美国构成挑战的是伊斯兰世界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它不仅威胁美国在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还为社会主义阵营在伊斯兰世界扩展影响创造了条件和机会。美国出于冷战的需要对伊斯兰世界推行实用主义政策,即“只要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保持稳定,并支持反共和保持能源供应,美国就支持维护现状,不推动在伊斯兰国家内部进行政治和经济改革。”[2]美国不仅容忍或低调处理伊朗、利比亚等伊斯兰激进国家的反美行动,还积极与主要伊斯兰国家合作甚至结盟以对付苏联,支持包括本·拉登在内的伊斯兰激进势力进行抗苏斗争。“美国在20世纪八十年代,因力求遏制苏联在阿富汗的扩张、遏制伊朗输出其革命,对伊斯兰主义一些集团持支持的态度。这说明伊斯兰主义者和西方二者采取非意识形态立场所达到的程度。”[3]35与此同时,伊斯兰世界虽对美国在巴以和阿以冲突中一味偏袒以色列的立场极为不满,但土耳其、巴基斯坦、埃及、伊朗、约旦、沙特等伊斯兰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在不同时期都与美国进行密切合作甚至结成军事同盟。
冷战后国际政治格局的一个深刻变化就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迅速复兴。伊斯兰不再是纯粹意义上的宗教,已成为包含政治思想、意识形态、民族、文化观念等在内的复合体。伊斯兰政治力量先后在苏丹、阿尔及利亚上台执政,并利用与中亚各国的民族、语言、宗教、文化等方面的传统联系向其积极渗透以使之走上伊斯兰发展道路,另外还积极干预巴以冲突、波黑战争等地区热点问题。1991年4月,来自世界55个国家和地区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在喀土穆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西方将其视为国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大聚会。“伊斯兰教已经在伊斯兰世界的许多国家战胜了自由民主制度。在伊斯兰主义尚未获得政权的国家,伊斯兰也对自由构成了严重威胁。”[4]277因此,“伊斯兰复兴成为美国外交政策面临的最重要问题。”[1]74
美国将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视为冷战后所面临的主要威胁之一。应该指出的是,美在冷战后虽然开始将伊斯兰世界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相联系,但又避免公开将伊斯兰世界及伊斯兰教简单等同于恐怖主义以免激怒整个伊斯兰世界。因此,强调伊斯兰极端势力只是极少数,并将伊斯兰教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明确区分开来。[5]39-40
从整体上看,“9·11”之前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矛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经济领域。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而插手或利用伊斯兰世界内部的矛盾,支持某些国家或政治势力,对抗与压制另一些国家或政治势力。同时,美国还根据形势的变化调整压制对象,敌人与盟友的转换主要以利益为依据,意识形态领域的对立与冲突并不妨碍美国的政策;其二,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主体是国家或政府。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主要集中在国家和政府层面上,矛盾的解决也是在国家和政府之间进行,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双方矛盾的产生和消退与政府更迭变化之间具有高度的相关性。美国避免将伊斯兰世界视为一个整体性的政策主体,而是针对具体的伊斯兰国家制定不同的政策措施;其三,美国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矛盾具有高度的可逆转性。美国在伊斯兰世界虽然树敌众多,但敌友转换频繁、彻底而且“随意”,“埃及从美国之敌转变为重要盟友,伊朗由美国在海湾的‘支柱转化为受遏制的对象,长期反美的叙利亚则在海湾战争中站到美国一边。”[6]
二、美国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世界的反应
“9·11”事件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其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并迅速举起反恐旗帜。美通过其国际恐怖主义受害者身份占据了道义制高点,再加上超强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具备了主导反恐战争的道义合法性和物质基础。同时,恐怖主义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一大“公害”,打击恐怖主义符合国际社会的要求和利益。2001年10月,美国发动的针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政权的阿富汗战争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的道义和军事支持。
由于“9·11”事件与其他绝大多数恐怖袭击是伊斯兰极端组织支持、策划和实施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自然就成为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的主要打击目标。在反恐战争之初,美国的反恐领导地位与反恐措施得到了世界主要国家的理解和支持。因此,伊斯兰世界的处境显得十分微妙:一方面,面对恐怖主义对全球造成的安全威胁,伊斯兰世界必须旗帜鲜明地支持国际反恐斗争;另一方面,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反恐战争主要针对伊斯兰教的特定指向心态复杂。
出于现实利益考虑,伊斯兰世界大多数国家的政府在反恐问题上顺势而为,大多公开或非正式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但伊斯兰世界的社会民众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态度与其政府立场不完全一致。2002年以来,皮尤研究中心每年的全球民意调查显示,伊斯兰世界对美国及其“反恐战争”充满敌意,甚至在世俗的土耳其也不例外,伊斯兰普通民众普遍认为美国的反恐战争就是对他们共同宗教和信仰的恶意进攻。同时应该承认,在反恐战争初期,尽管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不太认同其政府在反恐问题上的政策立场,但也基本默认了政府的行动。因此,伊斯兰世界总体上支持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对美国的反恐战争并没有作出过激反应。
由于美国的反恐政策深受其称霸世界战略的影响,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走入歧途并沦为美实现地缘政治目标和国家利益的政策工具。2002年1月,布什在“国情咨文”中宣称,恐怖组织遍及世界上60多个国家,还把伊拉克、伊朗、朝鲜、叙利亚和利比亚列为支持恐怖主义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邪恶轴心”、“失败国家”和“流氓国家”。2003年3月,美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发动了伊拉克战争,并将“民主化”作为反恐的主要战略。2004年美不仅出台了全面改造伊拉克的重建方案,还提出“大中东民主计划”,对以中东和北非为中心的伊斯兰世界进行民主改造。2005年,美还大肆利用中亚伊斯兰国家的选举期,幕后支持政治反对派,策动所谓的“颜色革命”以改变这些国家的政治态势。
在美国反恐战争重心发生严重偏离的情况下,伊斯兰世界对美反恐战争的认识和态度发生了深刻变化,伊斯兰世界在反恐战争问题上出现了明显的“政府—社会”二元对立特征。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越来越认为,美发动的反恐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实质上就是针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伊斯兰世界各国政府支持美反恐战争的政策行动越来越得不到社会民众的认同,政府和民众在反恐战争上的立场分歧升级为行动上的对立。恐怖主义势力也极力利用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的宗教信仰和民族认同,纷纷以“圣战”的名义号召民众在世界各地打击美国。2006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美反恐战争所面临的挑战为,“恐怖组织越来越分散化。他们不再依赖集中的指挥系统,更多地依托一些由共同意识形态鼓动的小团体。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成为恐怖分子重振旗鼓的宣传旗帜。”[7]9200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关于全球恐怖主义发展趋势的报告也认为,“伊拉克境内恐怖活动的成功,将鼓舞更多的恐怖分子在其他地方继续进行恐怖活动。在伊拉克的武装斗争已经成为伊斯兰圣战组织的神圣事业,正在形成一种对美国干涉穆斯林世界的深刻怨恨,并培养全球伊斯兰圣战运动的支持者。伊斯兰圣战组织充分利用了穆斯林世界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8]2
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态度和反应的发展变化,对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发展方向产生了深远影响,导致伊斯兰世界反美思潮和行动日盛一日,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又为恐怖主义势力急剧膨胀提供了一定的社会基础。2005年全球范围爆发了新一轮恐怖袭击狂潮,形成了中东-中亚-南亚-东南亚这一“恐怖高危”弧形地带。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指出,“反美和反全球化的情绪高涨,并推动其他的激进主义意识形态。这可能促使一些左翼、民族主义和分离主义组织采取恐怖手段袭击美国利益。这一激进化过程更快更广泛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一些不知名组织发动突然袭击的可能性。”[8]1-4“由于没有明确的政治目标,许多恐怖组织的形成与活动都是以意识形态或宗教动机为基础,这也使恐怖组织的结构体系发生了变化,许多恐怖组织不再采用严密的等级结构,而是以松散网络组织的形式存在。来自不同国家的理念相同或相近的恐怖组织在行动、后勤、训练方面互相合作或提供支持;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与后勤支持趋于多样化,资金来源中有相当数量的自筹资金,其支持网络既包括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也包括一定数量的合法商业或社会团体。”[9]
简言之,伊斯兰世界对“9·11”事件以后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的反应存在明显的“政府—社会”二元对立特征。随着美国反恐战争重心的偏差,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对反恐战争认识的宗教信仰认同大大超越了国家和世俗政治认同,伊斯兰民众日益质疑美反恐战争的特定指向,认为美的反恐战争是针对伊斯兰世界的宗教战争。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的认识和立场虽然不能完全上升为国家的外交政策,但却可通过社会信仰和宗教理念等,在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形成浓厚的反美主义社会氛围。
三、美国对伊斯兰反美势力认识的意识形态化
伊斯兰世界在反恐战争问题上的“政府—社会”二元化反应,已成为伊斯兰世界风起云涌的反美主义思潮和行动的主要社会根源,深刻影响了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和判断。
“9·11”事件后,美国学者福山就提出,“目前的冲突不只是反恐战争,也不是针对作为一种宗教或文明的伊斯兰的斗争,而是同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斗争……伊斯兰-法西斯主义已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挑战,这种挑战在某些方面比共产主义的挑战还严重。”[10]58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认为,“伊斯兰极端主义就像历史上的布尔什维克主义一样,是一种武装了的思想。它是一种由狂热的、信仰坚定的宗教信徒来推动的进攻性意识形态。”[11]但美国政府在“9·11”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只是笼统地把反恐战争的对象定为恐怖主义,并没有将恐怖主义对象具体化。布什政府试图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伊斯兰世界区分开来,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反恐战争的敌人并不是单一的政权、个人、宗教或意识形态,而是恐怖主义。”[7]5
美国政也强调反恐战争包括与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展开意识形态的斗争。2002年9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就提出:“为了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美国将发动一场观念之战。”其中就包括“支持温和的现代政府,以使促进恐怖主义发展的条件和意识形态在所有国家都丧失赖以存在的基础,尤其是在穆斯林世界。”[7]62004年8月6日,赖斯也认为反恐战争是一场“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战争。“要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我们必须作好打一场意识形态战争的准备。”“要进行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观念战争,仅凭美国政府的努力是不够的,必须动员整个美国社会的参与。如果我们整个国家以冷战期间开展观念战争的方式来应对今天的挑战,那么我们必将赢得反恐战争的胜利。”[12]
随着美国反恐战争的深入推进及其出现的偏差,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对反恐战争的反应发生了深刻变化,导致伊斯兰世界中长期存在的反美主义不断上升。美国反恐战争的反伊斯兰特征越来越突出,美国的反恐战争与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之间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出现了“越反越恐”的局面。
美国政府开始改变以往在反恐战争对象问题上的笼统立场,逐渐把恐怖主义上升为一种意识形态,同时将美反恐战争的重点转到意识形态领域。2006年2月1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佩斯上将签署了《反恐战争国家军事战略计划》,其中最突出的特点在于注重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恐斗争。[13]2006年3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开始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并将其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等意识形态威胁相提并论,“20世纪见证了自由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威胁的胜利。然而,现在又面临着一种新的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威胁,它并不是源于世俗哲学,而是源于一种狂妄傲慢的宗教。这种意识形态类似于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 [7]1它还提出:“反恐战争在一开始是对恐怖分子及其意识形态的军事战争和观念战争。短期来看,反恐战争要动用军队和其他国家机器来对付恐怖分子;从长远来说,它是一场观念之战,要赢得反恐战争就意味着必须获得观念之战的胜利。”[7]9
美国逐渐明确地将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强调其意识形态威胁的严重性。2006年7月20日,美国参议院共和党联合会主席里克·桑多拉姆在一次演说中明确提出:“我们正在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对抗。他们发动‘9·11袭击就是因为我们是他们实现统治世界这一使命的最大障碍。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威胁就像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一样危险。”[14]8月10日,布什也认为:“美国正处在一场与伊斯兰法西斯主义者的战争之中”。[12]因此,美国与恐怖主义的斗争,“不只是一种军事冲突,它更是21世纪的一场决定性的意识形态斗争”,“是自由和专制、稳健与极端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斗争。”[12]
布什指出,恐怖分子不仅坚定地信奉其意识形态,还积极寻求将其意识形态付诸实践。“恐怖分子具有一种明确而牢固的意识形态和一整套邪恶而务实的信仰,他们受一种激进和不正当伊斯兰观念的驱动,希望建立一个横跨中东的被称为哈里发的政治乌托邦,并按照他们的意识形态实行统治,是一个包括欧洲、北非、中东和东南亚的所有穆斯林地区的伊斯兰集权的统治帝国。”[12]布什在纪念“9·11”事件五周年的全国演说中明确提出,“打击恐怖主义敌人的战争不仅仅是一场军事斗争,更是21世纪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意识形态斗争。”[12]
布什政府公开把恐怖主义定性为“伊斯兰法西斯主义”,把反恐战争称为“反伊斯兰法西斯战争”,美国的反恐战争就成了“西方的民主自由力量”对抗“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战争。尽管布什政府没有直接把恐怖主义等同于伊斯兰教,但显然已把恐怖主义与特定的伊斯兰教派组织联系在一起,使反恐战争的战略指向更为明确。布什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有失明智的行动,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深刻矛盾。
四、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意识形态化的影响
冷战结束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不仅在国际政治和经济领域对抗,而且在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层面上相互敌视和竞争。美方认为,伊斯兰世界狂热、愚昧、落后,大多数伊斯兰国家政治上专制、腐败,应该通过外部力量改造。伊斯兰世界则认为,美在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上全面进攻伊斯兰世界,伊斯兰世界面临着严重威胁,必须保卫伊斯兰的宗教、文化和领土。美与伊斯兰世界都认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宗教、文化和价值观是具有普适性的真理,力图将之推广到对方的世界,并把对方看作自己最大的威胁。
“9·11”事件之后,美国将恐怖主义视为最大的威胁,并将反恐作为首要任务,恐怖主义这一非国家主体就上升为美的主要对手,造成美反恐战争的对象无限泛化甚至虚体化,这在客观上加强了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非国家化趋势。更为关键的是,美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并将伊斯兰世界的反美思潮和行动视为对自由世界的意识形态攻势,这引起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对反恐战争的不满和质疑,导致伊斯兰世界对美的认识和反应在社会层面上出现了空前的敌意,从而为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的急剧高涨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氛围。在反恐战争的形势下,美面临的主要压力不是政府层面上的伊斯兰国家的政策行为,而是伊斯兰世界在社会层面上的反美思潮和行动,这在客观上把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之间的矛盾从幕后推到了前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反恐战争导致美与伊斯兰世界的矛盾从政治经济领域向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延伸,矛盾的主体由国家—国家演变为国家—社会。
由于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观念与国家层面的冲突和矛盾不同,它一旦形成就具有相当稳定的发展定势。除非形成这种观念的条件改变,否则将长期和持续地产生影响。2007年6月27日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全球47国民意研究报告显示,对美国肯定性评价最低的几个国家和地区分别是:土耳其9%、巴勒斯坦13%、巴基斯坦15%、摩洛哥15%、阿根廷16%、约旦20%、埃及21%、马来西亚27%、印度尼西亚29%。[15]132008年3月17日到4月21日,皮尤研究中心有关美国形象的调查结果显示,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国对美国持积极评价的受调查者分别占22%、19%、12%和19%,而持负面看法的人则高达75%、79%、77%和63%。[16]22伊斯兰世界社会民众对美国的认识和态度不断恶化,正是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意识形态化在社会层面的直接反映和必然结果。
五、结语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意识形态化,不仅赋予伊斯兰极端势力一种前所未有的“对手”地位,还强化了伊斯兰世界反美势力与美国进行斗争的意志。伊斯兰世界许多社会民众虽然反美,但并不主张采取极端的暴力行动。美国把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直接联系在一起,而且对伊斯兰世界的认识出现了严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将伊斯兰世界反美主义思潮和行动的发展视为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进攻。这不可避免地引起伊斯兰世界普通民众和温和力量的强烈不满,甚至使一部分反美的伊斯兰社会民众发展成为真正的恐怖分子。美国的反恐战争面临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的危险。
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主导地位实际上导致其处于一个国家对抗一种宗教的境地。美国主导的反恐战争不仅难以取得真正的胜利,而且极大地消耗了美的战略资源,甚至削弱了国家实力。美国政府也逐渐认识到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意识形态化所产生的不良后果,开始反思其主导的反恐战争。2006年2月1日发布的《反恐战争国家军事战略计划》指出,美军采取任何军事行动必须对时机、地点、方式作出慎重的考虑,必须清楚当地的文化和宗教敏感之处,防止因出现失误而被恐怖组织用作舆论宣传,这种区分和对战争时机的强调就是要争取伊斯兰世界中温和派的支持,避免美国反恐战争目标的“泛伊斯兰化” 。 [13]
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矛盾的意识形态化还加剧了两者传统的在国家层面上的政治经济矛盾,使得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政策在国内更具有社会民意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当前美与中东反美伊斯兰国家的斗争,既是美与伊斯兰世界深刻矛盾的表现,也是引发美与伊斯兰世界矛盾进一步发展演变的因素之一。2006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中明确指出,“叙利亚和伊朗这些国家继续在国内庇护恐怖分子,并鼓动国外的恐怖活动。”[7]92006年4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一份评估报告在分析全球恐怖主义的趋势时也认为,“伊朗和叙利亚仍然是支持恐怖主义的最积极的国家。”[17]3因此,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相互敌视和对抗,增加了国际局势中的不稳定因素,不利于世界的和平。
[参考文献]
[1] Fawaz A. Gerges. America and Political Islam[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2] P. W. Singer. Time for the Hard Choices: the Dilemmas Facing U. S. Policy towards the Islamic World[R]. The
Brooking Institution, Working Paper No. 1, September 2002.
[3] 安维华.论美国与伊斯兰世界的冲突[J].国际政治研究, 2003(2).
[4]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2.
[5] 高祖贵.美国对“伊斯兰威胁”的认知与政策演变[J].国际问题研究, 2005(3).
[6] 高祖贵.伊斯兰世界的反美主义分析[J].西亚非洲, 2005(4).
[7]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R]. Washington D.C.: GPO, March 2006.
[8] http://www.odni.gov/press_releases/Declassified_NIE_Key_Judgments.pdf[EB/OL]. [2008-04-09].
[9] Countering the Changing Threat of International Terrorism: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errorism[EB/OL]. [2008-05-12]. http://www.fac.org/irp/threat/commission.htm
[10] Francis Fukuyama. Their Target: The Modern World[N]. Newsweek Special Issue, 2002.
[11] Margaret Thatcher. Islamism Is the New Bolshevism[N]. The Guardian, 2002-02-12.
[12] [EB/OL].[2007-04-26].http://www.whitehouse.gov/news/release/2004/08/print/20040806-1.html.
[13] [EB/OL].[2006-11-07].http://www.defenselink.mil/qdr/docs/2005-01-25-Strategic-Plan.pdf.
[14] [EB/OL].[2008-03-13].
http://www.santorum.senate.gov/public/index.cfm?FuseAction=PressOffice.View&ContentRecord;_id=1942
[15] The Pew Global Attitude Project. Global Unease with Major World Powers: 47-Nation 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R]. June 27, 2007.
[16] [EB/OL].[2008-07-19].http://pewglobal.org/reports/pdf/260.pdf.
[17] [EB/OL].[2008-06-27]. http://www.odni.gov/press_releases/Declassified_NIE_Key_Judgments.pdf.
U.S. Anti-terror War and the Evolution of U.S.-Islamic Contradiction
ZHANG Yifeng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since 9·11, the perceptions and reactions of the Islamic World toward the war against terrorism have changed greatly. These changes that resulted in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World have exceeded the category of state and extended into the social and ideological fields, which leads to the situation of “one country confronts one religion”. This important evolution resulted in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onflict and hostility between Untied States and the Islamic World,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crucial factors shaping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Key Words U.S. Middle East Policy; Anti-terror war; Islamic World; Ideological Trend
(责任编辑:钮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