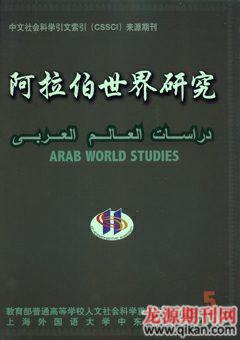中东地区清真寺功能的演变
摘要:清真寺是伊斯兰教最重要的建筑物,其功能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中古时期的清真寺以宗教功能为基础,兼具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在穆斯林生活中占据核心地位;近代以来,清真寺保持和加强民族认同以及提供情感依托和社会支持的功能得到强化,大众动员功能逐渐增强。这些功能在全球化时代得到进一步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全球化引起的伊斯兰国家民族认同危机、经济结构面临调整、人口跨国流动增加等压力。
关 键 词:清真寺;社会功能;民族认同;全球化;伊斯兰文化
作者简介:吴冰冰,博士,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阿拉伯语言文化系副教授(北京100871)。
文章编号:1673-5161(2008)05-0055-07中图分类号:G371 文献标识码:A
*本文属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东国家的清真寺社会功能研究”(06JJDGJW007)的阶段性成果。
伊斯兰世界处在从未止歇的演化过程之中,清真寺的功能也是如此。把伊斯兰世界理解成自古以来就是一成不变的,这本身即为东方主义(Orientalism)的一种表现。[1] 125从历史的角度,用发展变化的观点来认识伊斯兰世界,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作为伊斯兰教最重要建筑物的清真寺,除了建筑样式的变化之外,作为宗教信仰、权力结构、社会关系和经济体系的外在表现,其功能也随着历史发展而不断演变。
一、中古时期清真寺的功能
追溯清真寺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的故居。最初的清真寺,“也就是穆斯林聚集在一起礼拜的地方,实际上就是先知的房屋前的院子。”[2]49宣礼员所站的屋顶,沿正向搭起的简易的遮阳棚,以及棚厅中央用枣椰树做成的讲坛,这是最早的清真寺的三个基本要素。[3]162在所有这些要素中,政治功能最集中的体现是讲坛(minbar)。讲坛并非从一开始时就有,由于到先知房屋前的院子里参加礼拜的人越来越多,公元628年开始设置讲坛。就是在这个讲坛上,“穆罕默德率领信徒做礼拜、执行审判、颁布新法律,他的所有继承者也是如此。站在会众清真寺里那升高的讲坛上做聚礼日礼拜,遂成为哈里发和地方统治者的特权,并由此而演化成政治和宗教的行为。”[4]8在那个时代,麦地那的清真寺兼具宗教、社会、政治和司法功能。它是穆斯林的宗教活动场所,是增强穆斯林情感和社会联系的场所,也是进行社会动员和司法裁决的场所。
在哈里发欧麦尔和奥斯曼时代,阿拉伯人在伊斯兰的旗帜下进行了大规模的征服。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清真寺也在各地建立起来。新的清真寺的建立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巴士拉、库法、弗斯塔特、凯鲁万等新建的军镇城市。在这些军镇城市里,清真寺都是模仿麦地那的清真寺建造的。这些军镇城市,往往是区域性统治中心,建有地方长官公署(dār al-imārah)。值得注意的是,早期的地方长官公署大多建在清真寺附近。在巴士拉,建于635年的地方长官公署在清真寺的东北面;在库法,萨阿德·本·艾比·瓦嘎斯于638年建造了库法的清真大寺,同时在清真寺的一侧也建立了地方长官公署,与清真寺之间只有一条狭窄的街道隔开,后来于644年重建的地方长官公署也在离清真寺不远的地方。[4]8欧格白·伊本·纳菲阿在凯鲁万建设军镇城市的过程,就是“先修建清真寺,接着就修建政府公署,使民房以此为中心。”[5]303正是因为伊斯兰教在大征服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清真寺所具有的综合功能,使得清真寺往往是新建的军镇城市中最早出现的建筑。另一种情况是在先前已经有居民居住的被征服城市,阿拉伯人往往利用城市里旧有的建筑作为清真寺或履行清真寺的功能。在这种情况下,地方长官公署也是在清真寺附近。比如在大马士革,穆阿威叶建造的地方长官公署绿圆顶宫(al-Qubbah al-Khadrā)就在清真寺附近。由于清真寺是选用旧有的神圣宗教建筑,因此更能说明地方长官公署的选址是依据清真寺的位置而定的,即在时间顺序上是先有清真寺,后有地方长官公署。
事实上,这种建筑格局体现了政治和社会治理与宗教之间的密切联系,是与伊斯兰大征服时代的治理结构相一致的。“在伊斯兰教的初期,政府某个地区的将军,就在那个地区里兼任礼拜时的领拜者(伊玛目)和那个地区的法官。”[5]201正是这样的治理结构,决定了地方长官需要并且能够利用清真寺来完成宣示统治、宣布法令和社会动员等活动。在新征服的地区,新皈依的穆斯林数目较少,在此情况下,清真寺及其附近的地方长官公署,构成了地区性的政治、司法和伊斯兰宗教的中心。
在倭玛亚时期,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685~705年在位)于691年在耶路撒冷修建岩石清真寺。尽管该清真寺享有盛名,且成为后代众多清真寺建筑结构的典范,却是由哈里发瓦立德(705~715年在位)进行的。他于705年制订了重建麦地那清真寺的方案,710年建成。这个清真寺引进了四个高耸的宣礼塔,可能源自拜占廷城堡的方形瞭望楼;麦地那清真寺还首创了壁龛,可能是借用了基督教堂中常见的神龛形式。[3]168-170这些后世清真寺建筑的经典样式,都是通过重修的麦地那清真寺而确立的。与此同时,瓦立德还于705年接收了大马士革奉献给圣约翰的长方形教堂,并在教堂的原址上修建了倭玛亚清真大寺。事实上,大规模修建和重建清真寺的工作本身就是极具政治性的行为,其核心目的是增强倭玛亚王朝的合法性。“对大马士革和耶路撒冷宗教建筑的资助提升了叙利亚作为倭玛亚王朝中心的地位,对哈里发的虔诚以及他们企图效仿同一地区基督教堂的辉煌努力都作了很好的宣传。”[2]62在656~661年和680~692年,阿拉伯帝国先后经历了两次大的内战,伊斯兰世界发生了分裂,形成了倭玛亚党人、阿里党人、佐拜尔党人和哈瓦立吉派等最初的政治集团。正是由于佐拜尔党人当时控制麦加,倭玛亚哈里发阿卜杜·马立克为了与之相抗衡,以吸引朝觐天房的群众,于691年在耶路撒冷修建岩石清真寺。在与阿里党人的斗争中,叙利亚与伊拉克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在叙利亚的中心大马士革修建倭玛亚清真大寺,将之提升到伊斯兰教的第四大圣地的地位,是为了维护叙利亚的中心地位。从另一个方面讲,修建规模宏大的清真寺,也是为了与基督教的宏伟建筑相抗衡,宣示伊斯兰教的力量。[5]257,307
伊斯兰教初期,清真寺的功能是综合性的。“对于阿拉伯社会来说,清真寺是一个集会的地点,委员会举行会议的地方,法庭、国库、军事行动的中心。行政命令在这里宣读,政治家在这里宣布自己的政治誓言,商人和学者在这里聚首,书籍在这里宣读,也就等于出版。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在这里休息,甚至还可能享受一顿晚餐。它代替了传统的集会或者论坛,成了城市中主要的集聚会地。只是在一百年之后它才变成了一个神圣的地点,其含义接近西方的‘神圣的地区。”[2]50-51伊斯兰教初期清真寺功能的综合性,可能正是对应了这一时期政府机构的简单状态和职能的分工的模糊状态。随着政府机构日益完备,清真寺的政治功能有逐渐减弱的趋势,宗教功能日益突出,与宗教活动相联系的社会功能得到保留,文化功能开始逐渐发展起来。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普通清真寺与清真大寺在功能演化上是有区别的。清真大寺的很多功能是普通清真寺原本就不具备的,因此,前者的宗教功能在诸种功能中更为突出。
虽然清真寺的政治功能开始出现弱化,但是由于伊斯兰教中政治和宗教的紧密联系,在清真寺中进行的宗教活动体现着明确而重要的政治含义。在清真寺星期五聚礼的祈祷词中是否提到某位统治者的名字,就代表着是否承认他的政治权威,或者至少在名义上承认其权威。阿拔斯王朝时期,在帝国东部最先拥兵自立的塔希尔(?~822年)为了表示自己的权威,从每周五聚礼日的祈祷词中删掉了哈里发的名字。在西班牙建立后倭玛亚王朝的阿卜杜·拉赫曼(756~788年在位)于757年在每周五的祈祷中停止了对阿拔斯哈里发的祝福。由于不同的政治势力之间往往分属不同的教派或者教法学派,因此清真寺也具有了在政治和宗教上区别教派和教法学派的功能。
历史上,清真寺具有了传承伊斯兰文化的功能;第一,随着历史的发展,出现了专门的宗教学者、教法学家,他们专职领导和管理清真寺的事务,领导社区乃至更大范围的宗教事务。这些宗教学者本身就是伊斯兰文化继承和发展的载体;第二,宗教学者作为传统社会知识分子的主体,承担了社会的教育工作,因此很多学校都附设于清真寺,通过以伊斯兰经典为核心的教育,清真寺也具有伊斯兰文化的传承功能;第三,清真寺被用作图书收藏所,特别是有关宗教文献方面的收藏;第四,清真寺本身的建筑因素,都起源于先知穆罕默德在麦地那创建的清真寺,伊玛目等人包括领拜、讲道在内的活动,也是效仿先知。因此,清真寺的各种建筑因素本身,以及伊玛目等人在清真寺的活动,都将穆斯林大众的生活与先知穆罕默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伊斯兰文化;第五,很多清真寺是与圣徒的墓地联系在一起的,穆斯林大众在清真寺礼拜的同时,也被激发起对圣徒的纪念和追思,强化了伊斯兰文化对穆斯林现实生活的影响。
在诸种文化功能中,清真寺的教育功能居于突出的地位。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显然与清真寺有着密切的联系。初级教育一般是在清真寺完成的,“小学校(kuttāb),即使不是清真寺本身,也是清真寺的附属物。” [5]483伊斯兰教的“头一所真正的高等学校”,是1065~1067年由尼扎姆·穆勒克创立的尼扎米亚大学,是一所为政府所承认的宗教学校(madrasah)。这种高等宗教学校起源于在清真寺进行的学术辩论。在伊斯兰教的早期,穆斯林往往在清真寺进行学术辩论,讨论宗教问题。在辩论的过程中,他们会聚集在博学的穆斯林学者身边,征询意见,聆听教诲。一些博学的穆斯林学者也逐渐开始在清真寺组织定期的宗教讲座,称作“集会”(majlis),聆听者则形成“小组”(halqah)。高等宗教学校和宗教大学正是从这样的宗教学术“集会”和“小组”演化而来。在今天最负盛名的爱资哈尔大学,与清真寺的关系更为密切。什叶派的法特梅王朝于972年建成爱资哈尔清真寺,988年哈里发阿齐兹(975~996年在位)在该清真寺设立一个学院。
清真寺除以宗教功能为基础兼具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外,还具有司法、经济等功能,这就确立了清真寺在穆斯林生活中的核心地位。
二、近代以来清真寺功能的转变
随着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西方力量开始进入并控制中东。中东地区的历史发展中主要存在着两种矛盾,一种是以本土力量为一方,西方列强为另一方,双方之间属于总体性矛盾,从本土力量的角度,这种矛盾引发了民族解放运动;另一种是本土力量内部在发展方向问题上产生的分歧所引发的矛盾。
与清真寺相联系的伊斯兰宗教学者,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教学者中的上层在社会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和巨大的影响,而宗教学者中的中下层又深深植根于社会和群众之中,除了组织和领导日常宗教活动外,他们还通过联姻、亲友、邻里等各种途径与群众的各个阶层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联系。宗教学者既在纵向结构上有着比较严密的组织系统,又在横向结构上与社会的其他部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样的社会组织状况,加上因为从事与宗教有关的事务而获得的合法性,使他们能够在领导群众反对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方面发挥巨大而有效的作用。
1798年,拿破仑入侵埃及,开罗人民发动的第一次武装起义,就是在伊玛目的带领下,从清真寺出发的。土耳其苏丹号召反对法国人的敕令传到埃及,由伊玛目在清真寺里公开宣读。开罗人民酝酿起义,“清真寺的教长们在讲经时激励人们揭竿而起;宣礼员在清真寺的尖塔上公开号召向专横暴戾的邪教徒发起圣战……下层长老、学生和伊斯兰法学家们在爱资哈尔清真寺内组成若干负责组织起义的委员会。”[6]33-341798年10月21日清晨,起义爆发。“整个爱资哈尔区成了革命的中心和明亮的火炬,愤怒的群众从四面八方涌向那里,通向爱资哈尔区的街道上挤满了起义者。”[6]34
穆罕默德·阿里在埃及掌权之后,开始对付伊斯兰的长老阶层。从1809年开始,埃及伊斯兰长老阶层的地位急剧衰落。打破了伊斯兰长老阶层的地位,但是又无法建立起新的自上而下有效的动员机制,使得“穆罕默德·阿里虽然建立起了一个在政治上具有帝国倾向,在经济上具有垄断性质的国家,但是,当他和外国殖民主义发生冲突时,却发现没有一种像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法国入侵时那样,能肩负抵御欧洲殖民主义侵略重任的人民力量来支持他。”[6]64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清真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宗教学者在领导民族解放运动中所起的作用。
尽管清真寺和宗教学者在近现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具有强大的大众动员功能,但是在总体上清真寺和宗教学者的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这与中东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的选择有关。
从西方殖民势力入侵开始,包括阿拉伯、波斯和土耳其在内的中东国家,开始进入被称为“现代化”的过程。在中东,现代化这个概念是与西化和世俗化等概念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是结合在一起被引进中东的。在这个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一批西化的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他们可能是自由主义者,或者民族主义者和左翼力量,也可能是政治上的保守势力。自由主义者的代表是1905~1911年伊朗立宪运动的支持者,民族主义者的代表是纳赛尔,左翼力量的代表是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复兴党政权,保守势力的代表是伊朗的巴列维王朝。上述力量分别构成西化派中的右翼、左翼和保守派。但是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推崇世俗主义,主张通过限制伊斯兰教来推进现代化进程。这种政治和文化精英所代表的西化文化,与本土的民众中间存在的大众文化相脱离。因此中东伊斯兰地区形成了文化上具有深刻影响的二元结构。
从20世纪直到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前,中东大部分地区都是西化力量掌权,因此清真寺的功能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其教育功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新兴的国民教育体系所取代,宗教学者的社会地位和作用受到削弱。西化力量试图剥离清真寺的社会和政治功能,削弱其文化、司法和经济功能。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巴列维王朝时期的伊朗。
在二元结构的基础上,清真寺的功能发生了变化,其首要功能成为保持和强化民族认同。安东尼·D.史密斯(Anthony D. Smith)在民族主义的研究中,倡导“族裔—象征主义”分析模式,关注民族认同中的“象征、记忆、神话、价值和传统文化因素”[7]62。在有关伊斯兰的象征中,没有什么比清真寺更具有代表性了。而且,清真寺本身就包含着记忆、神话、价值和传统因素,这一点在某些清真寺身上有更为明确而深刻的体现,比如麦加禁寺、麦地那先知寺、耶路撒冷岩石寺,马什哈德、纳贾夫、卡尔巴拉等地埋葬着什叶派伊玛目的清真寺等。
因此,在受到外来文化强烈冲击的背景下,清真寺对于保持和强化民族认同就具有更为特殊的意义。这种保持和强化民族认同的功能是二元结构背景下清真寺的最重要功能。值得注意的是,西化力量与世俗化力量,往往尝试用新的象征来取代清真寺的这个功能。如在巴列维时代,就试图用波斯波利斯遗迹、古代伊朗国王的称号等一系列前伊斯兰时代的伊朗象征取代清真寺等伊斯兰时代的象征,重构伊朗的民族认同。而法国在1798年入侵埃及后,也曾试图唤醒古老的埃及民族主义和阿拉伯精神,以此来取代伊斯兰教的纽带作用,从而煽动埃及人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敌。因此,尽管以清真寺为代表的一整套象征体系对于中东地区的民族认同非常重要,但是往往受到西方力量和西化精英所倡导的另一套象征体系的挑战。事实上,存在着对重新诠释传统权力的争夺,但是因为清真寺文化属于大众,因此真正对民众有影响的诠释,最终还在清真寺文化中。
经济和社会的二元结构,加大了城乡差别的鸿沟,从而导致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他们构成了城市的边缘群体。以开罗为例,贫困的新移民所居住的城市边缘区,其人口估计在200万到500万之间。“边缘区人口主要是不能进入主流都市生活的赤贫移民,他们在所从事的职业、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上迥然不同于现代都市人,打上了乡村生活的烙印,成为城市中的孤岛”。[8]215对于这个群体而言,失去了原先乡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也无法顺利进入城市新的社会体系,因此处于“悬浮”状态。在他们眼里,清真寺就是重要的情感依托的基础和社会支持的来源。这种情感依托(心理调适)和社会支持功能,是清真寺对于二元结构中的弱势群体的重要功能。
西化和现代化的发展,削弱了清真寺的功能。但是,也正是由于西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所导致的二元结构,强化了清真寺保持和加强民族认同以及提供情感依托和社会支持的两个重要功能。而上述两个功能的聚合则逐渐增强了清真寺的“大众动员”功能。传统文化的捍卫者与大量的弱势与边缘群体,通过清真寺获得了日常性的、体制性的宣传和组织管道。在西化精英领导的政府面临政治和经济困难的时候,清真寺组成的“大众动员”系统就构成了挑战既存政权的重要力量。
除上述功能外,清真寺的教育功能仍然得到了保存。像古代一样,今天的很多清真寺仍然设立《古兰经》学校。这种学校招收4~16岁的孩子,教他们诵读乃至背诵《古兰经》。读完整本《古兰经》一般需要3~4年的时间。与古代不同的是,现代的《古兰经》学校一般是在学生学校教育之外的课余时间进行,即在上学前或放学后,是作为普通学校教育的补充,而不是学生学业的全部。[9]
有些国家在国民教育体系之外,还保留了宗教教育体系。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附设了一整套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宗教学校。初级宗教学校为6年,预科学校为3年。学生在接受完为期9年的教育后,可以继续在高级宗教学校完成4年的学业并升入爱资哈尔大学,也可转入教育部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进入普通高中或职业学校。据统计,1981/82学年爱资哈尔系统的初级、预科和高级宗教学校的学生数分别是128,048人、66,344人和99,757人,到了1994/95学年分别增加到701,979人、187,326人和168,830人。在2001/02学年,分别有26%和29%的埃及新生希望接受爱资哈尔系统的普通教育和大学教育。[9]宗教教育体系的保留本身就体现了对清真寺教育功能的认可,而宗教教育体系的存在又强化了清真寺的功能和影响力。
三、全球化对清真寺功能的影响
进入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世界全球化进程迅速加快,全球化的研究也日益深入。全球化最表象化的体现,是在交通、通信技术持续高速发展以及金融、贸易制度与规则不断完善和扩展的基础上,人员、信息、商品和资本大规模的快速流动。由于西方在技术、资本、体制方面占据优势,全球化被理解成美国化或者西方化,被认为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利益、民族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以及民族国家政治权力的一种冲击,受此冲击的文化—社会和政治层面尤其值得关注。
在文化方面,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对民族和传统文化构成巨大冲击。在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或译詹明信)看来,对于很多人而言,“这是界定全球化的真正核心:世界文化的标准化;美国的电视,美国的音乐,好莱坞电影,正在取代世界上其他的一切东西。现在,这种恐惧确实弥漫在我们后面两个范畴之中:一方面,这明显是经济支配和本地文化工业被美国文化工业取代的后果;同时,这种恐惧更深层次的方面在于社会,而文化现在被视为惟一的症候:换言之,这种恐惧是,特定种族—民族的生活方式在这种文化标准化的过程中将遭到破坏。” [10]108詹姆逊指出了在全球化过程的文化层面对社会的影响,即美国的大众文化模式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生活方式的破坏。他又进一步指出,除了文化层面之外,全球化过程本身还有一个社会层面,即“消费文化”的广泛传播。“所谓的消费文化事实上是一种特殊的日常生活方式,是社会结构组织的一部分,几乎不可能与它分开。这显然是在世界其他部分有时被称为西方物质主义甚或美国物质主义的东西”。这种“消费文化”破坏旧的家庭、世系和村庄,即破坏日常生活的结构组织,破坏传统意义上的社会。[10]114
在政治层面,可以概括为全球化对民族国家构成的挑战。尽管安东尼·D.史密斯驳斥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民族(Nation)和民族主义是另一个时代的残留物,一旦它们在地球的各个角落走完应走的历程后注定会消失,会让位于一种世界性的文化;但是史密斯也承认,的确存在着对于国家权力与合法性的批判,国家自身目前存在着危机。他强调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批判和危机。“第一种是外部的危机和批判,在一个被大众电子通讯连接起来的,由规模庞大的跨国公司,军事集团以及洲内联合体组成的世界里,国家的军事和经济权力发生了危机。第二种危机和批判是内部的,是对民族国家有效性的挑战,是对民族国家能够满足其公民需要及利益的合法性与代表性的挑战。”[11]114-115
对于处于转型阶段的伊斯兰国家而言,无论是全球化的文化、社会层面还是政治层面,都对本土的传统文化以及在其基础上形成的民族国家认同形成尖锐而激烈的挑战。正是在这种激烈的挑战面前,清真寺所具有的保持和强化民族认同的功能得到凸现。作为传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最重要代表,清真寺往往成为抵御西方大众文化的坚固堡垒。
全球化见证了市场经济体制的扩展,全球化促进的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资源重新配置,在很多国家造成了两极化和大量的贫困人口(与传统部门和体力劳动相联系)。这些在全球化过程中形成的大量弱势群体,更需要清真寺的情感依托和社会支持功能。此外,全球化过程还带来大量跨国移民。移民在经济、文化和社会等诸多方面面临更多的困难,如果移民本身是穆斯林而他们所移入的国家是非伊斯兰国家,那就会增加产生跨文化冲突的可能性。对于这样的穆斯林移民而言,清真寺的多种功能都会得到强化。而清真寺功能在西方国家穆斯林新移民社会中的强化,会随着新移民在移出国和移入国之间的流动,以及信息和社交网络的传播,影响伊斯兰国家的清真寺功能。
[ 参考文献 ]
[1]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9.
[2] 罗伯特·欧文.伊斯兰世界的艺术[M].刘云同,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 罗世平,齐东方.波斯和伊斯兰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4] 约翰·D·霍格.伊斯兰建筑[M].杨昌鸣,陈欣欣,凌珀,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
[5] 希提.阿拉伯通史(上册)[M].马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 穆罕默德·艾尼斯,赛义德·拉加卜·哈拉兹.埃及近现代简史[M].埃及近现代简史翻译小组,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7] 安东尼·史密斯.民族主义:理论、意识形态、历史[M]. 叶江,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
[8] 毕健康.埃及现代化与政治稳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9] Uzma Anzar. Islamic Education: A Brief History ofMadrassas with Comments on Curricula and Current Pedagogical Practices[EB/OL].[2008-03-01]. http://www.uvm.edu/~envprog/madrassah/madrassah-history.pdf.
[10] 王宁.全球化与文化:西方与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11] 安东尼·D.史密斯.全球化时代的民族与民族主义[M]. 龚维斌,良警宇,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The Evolution of the Functions of the Mosque in the Middle East
WU Bingbing
Abstract The most important pattern of Islamic architecture is considered to be the mosque, whose functions have witnessed a continuous evolution in the history. In the medieval times, the mosque was the core of the life of Muslims, for it developed social, political,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n the basis of its religious function. In modern times, the mosque has been executing stronger functions of main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identity, providing emotional and social support, and mass mobilization. All these functions have been further developed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to deal with various problems, such as the threatened national identity of Islamic countries,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adjustment, and the large-scale transnational migration.
Key Words Mosque; Social Function; National Identity; Globalization; Islamic Culture
(责任编辑:余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