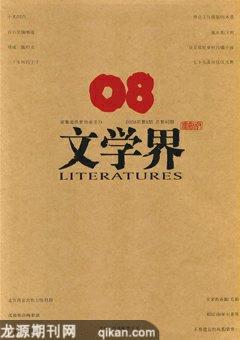七十七盏河灯
吴光辉
一
由来已久的死亡预感,牢牢地袭占着父亲的心头,如魔咒附体、小鬼缠身,让他使尽全身解数也无法解脱。当父亲忽然住进了医院用CT查出可能是肺癌的时候,我就想起了父亲去年春节时,表情严肃地对我们兄妹说的这个隐藏在他的心头多年的这个死亡预感来,想起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说祖父去世后,在废黄河里放河灯时出现的怪事。直到这时我才认认真真地回想祖父去世那天发生的情景。
我记得祖父出殡的那几天,一直是冬雨绵绵、寒风凄凄。为祖父守灵的那两个夜晚,伯父、父亲和我、堂弟家迷、迷成等一干孝子贤孙们,腰系麻片臂戴黑纱,依次跪在堂屋东侧上首的盖着子孙被的祖父遗体的搁饭头边。我们苏北里下河地区人死之后安放遗体时要供奉送老饭,将一双筷子竖插在米饭中央,叫作搁饭头。引魂灯在搁饭头边一跳一跳地闪着黄光,油灯棉芯不时地爆出一声又一声灯油清脆的炸响。孝子贤孙们轮流给丧盆里送着纸锭为他烧纸钱。到了头更天,我便随长辈们去废黄河里放河灯送无常。里下河地区是个水网密布的水乡,老人们认为人死后无常鬼来带魂魄西去时要走水路,也就用放河灯的形式恭送无常了。
姑父提着引魂马灯在前开道,捧着哭丧棒的伯父、端着装有酒饭筛子的父亲紧跟其后,我们几个叔伯兄弟居中而行,有的扛着柳魂枝,有的洒着纸钱,有的举着招魂幡,后面有十多个女眷嚎哭着跟在后面,最后是几个吹手。我们送无常的队伍一路哭声震天、一路唢呐镗锣地直奔废黄河而去。在河边供上酒饭、焚烧纸钱、下跪叩拜之后,我们几个孙子辈的孩子就开始朝河里一只一只地放着河灯。这些河灯一共七十七只,全都是用牛皮纸糊成的小船,在船上又点着小蜡烛。漆黑的夜如同黑色的海,那一阵阵喊魂的锣声,一阵阵哭泣的唢呐,一阵阵女眷们悠长沙哑的嚎哭,在夜空中传播开去,如同在海面向四处蔓延的波澜。片刻过后,河面上就飘荡着一片星星点点闪烁不已的烛光了。在这一阵阵锣声、哭声里,我的伯父就发出低沉而悲伤的长鸣:“三尺红绫书姓字……一捧黄土埋尸骨……呜呼……恭送无常大仙西去呀……”这拉长了声调的喊声,像一只凄楚长鸣的乌鸦,穿透层层雨雾,在一片河灯闪烁的水面上盘旋着。放河灯的仪式一直持续到二更天才告结束。也就在我们准备回转,伯父要求我们不能再回头看的时候,父亲惊叫了一声:“你们看!那河灯怎么排成了两排?”那七十七盏河灯仿佛变成了一个舰队,同时整齐划一地排成了两排,朝西慢慢漂去,最后居然在河弯处又自动形成了两个直角。
从此,迷茫的河面,凄楚的冬雨,莫名其妙地排成两排、形成两个直角的七十七盏河灯,便深深地印刻在了父亲的脑海里了。河灯之谜就像盘桓在记忆天空的迷雾,几十年来一直徘徊在父亲的脑海里缭绕不散。此后的二十多年间,每当他说到这个河灯之谜的时候,听者总是付之一笑。去年三十晚上,他坐在他从淮阴买回去的那把人造革椅子上,忽然又说起了这事:“直到你伯父去世时,我才弄懂河灯之谜。”他告诉我们说那两排形成直角的河灯,是在向他和伯父暗示一个数字:77。接着他又直截了当地说,祖父是七十七岁去世的,后来伯父果然也是七十七岁死的,恰好暗合了河灯显示的“77”。父亲还由此推论,七十七岁也是他的一“关”。2007年父亲过七十七岁了,明显地表现出从未有过的紧张和惶恐,总是窝在家里叹息,如同一头等待死亡的非洲老象。他多次表示什么地方都不去,生怕会出什么意外。当时在父亲说这话时,我们兄妹只把他的话当作是笑谈,因为那时父亲的身体看上去很结实,谁也不会相信他会像祖父、伯父那样死于七十七岁。而今天看到医院的CT后,我突然想起了父亲的这句七十七岁是他一“关”的话,心也就像压上了一块大石头,情不自禁地往下一沉。
二
我们所有人都不相信父亲会死,连父亲本人也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自己会得不治之症。他平时十分注重保养,退休后从报刊上剪辑下来的保健知识,装订起来足足有三大本。前年来淮阴时,我专门为他买了本地特产钱集老鹅招待他,可他一口也不吃。他慎重其事地说鹅是发物,吃下去会致癌的,好像我给他吃的,不是老鹅而是毒药。他常常告诫我,生活一定要有规律,平时几时几分吃饭,几时几分睡觉,几时几分大便,都要有严格的时间规定,不得相差一分。对于这一点,姑父姑母一直称赞父亲养生有方。父亲看上去也确实红光满面、精气神十足,一直到今年八月也还是安然无恙。因此,我们兄妹对县医院的检查结果的第一反应是怀疑。前年和父亲住紧隔壁的老陈主任,就被县医院查出了肺癌,最后到市里大医院再一查,只是肺气肿而已,到现在老陈头还是活蹦乱跳的,什么事也没有。
我们决定到大医院去复查确诊。可医生说要想确诊只有通过穿刺活检,从肺上切片,而父亲肺上的肿瘤偏偏长在肺门上,切片十分危险,很可能造成肺部血管破裂而导致死亡。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按肺癌去治疗,死马当作活马医吧。当然更不能动手术,只有化疗、服药、挂水。而如果化疗父亲就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说不定吓就被吓死了,同时又怕父亲的身体吃不消。因此,我们决定先服药挂水,保守治疗。
父亲住进医院后,一下子失去了往日的丰采,脸色紫暗虚肿,胡须多日未刮,稀疏花白的头发也有些零乱,手面到处都是针孔留下的暗黑色瘀斑。父亲开始因为心脏病发作被送进县医院的心内科,谁知道心脏病治好之后又发现了肺病。为了不让他知道自己得了癌症也就没有转到肿瘤科。再加上心内科的主任是我的同学,也便于照顾。
在这一个多月的住院期间里,父亲稍一好转就坚持按他的作息时间表生活,并且坚持每天在挂水之后,在病房的走廊里慢慢地走上两个来回。只是两腿有点发软,两脚有点打飘,要人搀扶、拄着拐杖,才能站稳,走几步就累得呼呼直喘,就要停下来,靠在墙边的扶手上休息。
等到三个疗程的叫作恩度的药水挂完之后,父亲不但没有死,而且还精气神十足地出了院。医生也说简直就是个奇迹。挂的恩度、吃的斑蝥胶襄,一般人都有药物反应,要么就是过敏,要么就是呕吐,根本不能用。同学的爱人得了癌症后就用过这两种药,结果都有反应,被迫停用。可父亲使用这两种药后什么事也没有,感觉良好。出院前再做CT一查,肿瘤大为缩小。而胸腔的积液血水,通过B超定位抽出三百亳升后,父亲的感觉明显好转,再拿去一化验,更让我们喜出望外,化验单上用蓝章盖着几个大字:未见癌细胞。
出院那天,我心里又想起了父亲常说的七十七岁是他一“关”的话来,觉得父亲肯定不会死的,那河灯之谜完全就是迷信或者是心理作用。特别是父亲出院回到家后,有时还能和他的麻友搓上两圈麻将,我们全家人都为他长长地舒了口气。
三
我们就是在这种不愿承认父亲病入膏肓的心理驱驶下,带着一种侥幸的期待,在悲伤不安中过一天了一日的。一直到父亲那天在麻将场上一连六次自摸,成就了父亲一生麻将史上的最后辉煌之后,才再一次住进了医院。上次出院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一直感觉良好,可到了十二月的中下旬,马上就要过年了,就要闯过他的七十七岁的“关”,他的哮喘病却越来越严重了,要不是托人从北京买回一台制氧机,他几乎会被憋死。我回去看他时见他气喘不上来,吞嗓管子里有很多粘痰堵着,呼呼啦啦像拉风箱似的直响,可又咯不出来,把脸咳得彤红,全身咳得出汗,喘得全身上下起伏。
起先他是不肯再次住院的,他说是住院不方便,其实是怕花钱。我推想他恐怕一直生活在对生命的自欺之中,到最后恐怕连他自己也几乎完全相信了这种自欺。他也曾问我母亲和妹妹好像有什么事情总是瞒着他,他总觉得她们鬼鬼祟祟的。我对他说没有什么事情对他隐瞒的。他又问我检查的化验单为什么不给他看看,我就把那次化验未发现癌细胞的单子拿给他,他戴上老花镜,认认真真地看,正面看,又翻过来看,然后又找来放大镜看,足足有十几分钟,最后确认无疑后才递还给我。这时我看到他的两只眼睛里放射出多日未见的光芒。
或许是我们对他隐瞒得太巧妙,或许是他更想向好的方向想,他再也没有问及他的病,只当作自己肺气肿发作。只是他一直怕花钱,生怕把自己一生的积蓄全都花光了。一旦见到花钱的事,他的情绪就明显的不好。他和母亲一辈子都将钱分开,各人用各人的,就像是银行里两个单独开设的帐户,独立核算,互不扯皮,这恐怕是我国AA制实行最早的家庭。上一次住院就花了五万五,其中恩度和斑蝥胶襄都是自费药,后来我妹夫找人捣膊弯子,报销了一部分,自己还要贴进去两万多元,一下子用去了父亲一辈子积蓄的四分之一。从北京买回来的制氧机,他一直在心里想让我们兄妹出钱,可又不好意思开口。所以,那些天他的脸色很是不好,动不动就不吃不喝,也不肯下地走动,总是睡在床上不肯起来,能一直睡到中午。母亲也因为钱的问题心里一直不痛快,说她起早待晚地服侍他,结果父亲还为钱和她吵架。我听到这些话之后,倒是觉得父亲至今仍没有觉察到自己的病情,否则也就不会因为钱而斤斤计较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呢?
一直到父亲再一次住进了医院,我回去看望他时,他依旧没有觉察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只有不到一周的时间了。那天我被医生叫去告知父亲的病情已经到了很严重的程度,要我们家属做好办理后事的准备。我心情沉重地回到病房,强装笑容地走到父亲的病床前面,见父亲正在挂水,脸上浮肿充血,张大了嘴巴直喘粗气,原本肥胖的身体一下子瘦了几十斤,全身皮肤也变成了枯树皮。他大概是见儿子孙子都回去看他了,心里十分高兴,提出要从床上爬起来,想下地走几步。我们就扶着他下了地,可他站在地上直打晃,两腿一软就倒在身边的床上。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让我们扶着重新躺上了床,将氧气管插进他的鼻孔,等了好长一阵子,他才算平静了一些。
这时,他突然对我说已经好长时间没有刮胡子了,想刮刮胡子。我当时并没想到这是他的一生最后一次刮胡子。我用热毛巾为他焐了脸,让他自己用我上次回来给他买的电动剃须刀去刮,可是不知是他这一辈子从未用过这个洋玩艺而不会用,还是因为他的胡子好长时间没有刮了太长太多太硬,横竖就是刮不下来,最后只得找出他多年来一直使用的刮胡刀片。
为他刮胡子的时候,大家都围在他的床边看着,嘴上都称赞着父亲把胡子刮了,看上去很有精气神。也就在他刮了他这一生的最后一次胡须之后,他居然笑着对我们说:“等我病好了,出院回去,我一定,一定要买一个大套房子,省得你们回来,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总是住在宾馆里。”他说这话的时候,还用干瘪了许多、青筋突显、留下无数针孔的双手做了一个手势,比划着很大的样子。我看他这表情,好像压根就没有想到他自己再也站不起来了,再也不能好了,再也不能回家了,当然也更不可能想到他自己离死只有五天了。我们听了他的这句话,眼泪都忍不住地从眼眶里奔涌而出。
四
不管母亲怎样一趟又一趟地朝射阳河边的兴国寺去求神拜佛,也不管我们兄妹是怎样一再请求医生采取一切可行的医疗方案,上苍还是按它原来的意愿行事,让父亲无可选择地撒手人寰,乘鹤西去,无可置疑地让父亲的那句死亡预言,在农历春节到来之前得以应验。当然,这个预言只是父亲的潜意识,只是他对生命的一种感悟、一种直觉,而他的主观思想却是绝对不愿离开这个世界的。
父亲的最后日子,并没有出现我们一直担心的痛苦。当癌细胞扩散到淋巴以后,因为肿瘤压迫了他的脑神经,使他已经感觉不到这种痛苦了。所以,那几天他总是昏睡不醒,大小便几乎都不知道了,两只已经变得瘦骨嶙峋、枯树皮一般的手,下意识地重复着一个动作,握拳然后又松开,松开后再握拳,再松开,再握拳,仿佛是想抓住一根救命的稻草。五十多岁的护工徐奶对我们说,她护理了不少病人,看到病人做这个动作时,恐怕就快了。父亲有时候也清醒一些,好像是一觉醒来的样子。一次清醒的时候,他死死地拉紧母亲的手说,他刚才看到屋里多出了一个人影,可看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是谁,那个人影总是背朝他,半明半暗,模模糊糊,只能看到一个背影。母亲就叫他别说胡话,屋里明明只有我们这几个人,怎么会多出一个他认不识、叫不出名字的人呢?徐奶就悄悄地对母亲说肯定是小鬼来带他了。
我推想父亲一直到他临死前两天,恐怕才猛然省悟到自己即将离开这个世界,可是到这个时候他已经说不出一句话来了。当我们全家赶回阜宁,父亲已经被送进了抢救室,嘴里插着输氧管,两眼紧闭,像是又睡着了,全身一动也不动,只有心电图还能显示父亲还活着。我便哭泣着对准父亲的耳朵哽咽着说:“爸,儿子今天跟您说实话,您得了肺癌,是晚期……我们没有告诉您,是怕您接受不了,影响您的治疗……我们让医生使用国内最先进的药,才让您拖到今天……现在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您,您就安心地去吧……爸……”当我说完这些的时候,我们全都痛哭起来,只见他的右脚动了一下,他的嘴也跟着翕动了一下,眼眶里渗出了两滴泪珠,两只布满针眼的手也动了一下,最后将食指、中指一起搭在大拇指上,做了个“七”的手势,就再也没有动弹。父亲的生命犹如一盏油灯,被大风吹得左右摇摆、闪烁不停的灯火,终于熬干了油,熄灭了。
我想起了去年春节前夕的三十晚上,父亲对我们兄妹说的那句七十七岁是他的一“关”的话,他做的这个一生中最后的一个手势,不正是告诉我们那个“77”数字吗?父亲生于一九三一年农历正月十八,死于二00七年农历十一月二十五,恰好是七十七岁。这样,父亲的死也就应验了他的死亡预感,祖父、伯父和父亲全都是死在七十七岁。如果再过一个月就过了年,他就是七十八岁了,可上苍偏偏不让他闯过这一关。
在父亲的葬礼上,我捧着哭丧棒跪在父亲的墓地前,看着丧盆里燃烧纸钱时飘摇而上的青烟,我又想起二十年多前的那一幕。迷茫的河面,凄楚的冬雨,莫名其妙地排成两排、形成两个直角的七十七盏河灯……
责任编辑:赵燕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