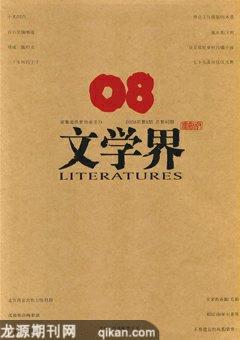绕城三圈
但 及
1
救护车叫着。咕噜,咕噜。声音穿透街道、树木和房子。
我驾着车,朝着向阳小区奔跑。中午的街上一派繁忙。路上,有好些人都瞪着眼睛看车子,目光里带着好奇和茫然。我心情不好,可以说有些沉重。每次有这样的事,我的心情就糟糕。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印象中,这算是第三回。都是院长亲自点的名。你把这无赖送回去,院长今天这样命令道。我有些犹豫,我不想做这样的事,这样的事让我难受。你叫另外的司机吧,我说。院长瞪了我一眼。这还要讨价还价吗?院长的口气变了。院长这样一说,我的信念就动摇了。工作就是这般的无奈,我们常常违背心愿。
大街上、小店里都挂上了福字,到处是新年来临的气氛。到处都是一片红橙橙。新年就在眼前,新年触手可及了。
我熟悉这座城市,熟悉城中的每一条路。每一条路都像是回家一样。
当救护车在向阳小区门口稳稳地停住后,我把头探出窗外,与传达室的老人打了个招呼,老人一看是救护车,就急忙开门。铁门的轮子拖着地,嘎嘎,嘎嘎地叫,叫了几声,门就敞开了。我就朝着北边的楼开去。三幢103室,我记着院长写在纸条上的这个地点。
车子在三幢前停下。几个老人们坐在树荫下,交头接耳,然后他们站起,并一点点朝救护车靠拢。我把车门打开,跳下车,然后去拉后面的门。门哗地开了。护工老张先跳下车,护工小陈还站在车上。病人躺在车里面,一动不动。事实上,把他抬上车的时候,他连眼睛也没有睁一下。当时,护士没有说话,医生没有说话,我们大家都没有说话。像这样的情况已经不止一次出现了,大家都习以为常。
现在,我们靠近他,指望他能睁开眼睛,看一眼四周,然后说上一句:唔,到家了。但,什么也没有。他安静极了。
我的心头突然涌上一种不祥之感。
老张来到三幢前面,前后张望了一番。就是这个楼梯,他指着前面的楼道说。
陆陆续续地,边上围拢了人。他们很好奇,来看一看救护车里到底装了什么。到底怎么啦,有位老婆婆悄悄地问我。我没有答理她,我只管从口袋里掏烟,点上,喷雾。老张侦察完,回到车上,与小陈商量一阵以后,就开始抬人。病人躺在担架上,上面罩了一块白布,病人的头露在外面,但眼睛始终紧闭着。
老张与小陈,一前一后把病人抬起。老张在车下,他用手托起担架,小陈则站在车上。这时,老张的一只手受不了力了,一松,担架的一头就塌了。担架撞到了车沿,发出咣地一声。直到这个时候,那个躺着的病人才稍稍动了动。大概这一下,把他弄难受了。
小心呀,你要摔死他不成?小陈这样说。
你他妈的是怎么在抬,用力一点也不均匀。老张也在埋怨。
闲话少说,快点快点。我喷着烟,不耐烦地说。于是,他们两人互相看了看,又一声不响地再次抬起了病人。这时,边上的人议论开了,有人甚至走到担架前,好好地看了一眼躺在上面的人。
我走在前,后头跟着小陈和老张。我从口袋里掏出纸条,上面写着地址,那是院长亲自交给我的。院长说,终于把地址弄到了。我完全理解院长的心思,的确,像这样的病人太可恨了,住院二个多月,连一分钱也没有交。怎么能永远白吃白住呢?医院也是一个企业,都照这个样子,这医院不出几个月就该关门大吉了。院长把那张纸条交给我时,似乎带着重托,辛苦了,这事情就交给你啦。我理解他的想法。我们长期在一起,我怎么会不懂院长的心思呢?
据我所知,为了弄到这个地址,医院也花了功夫。他是车祸以后进来的,当时被撞得血肉模糊。也是我这辆救护车去拉的,在一个叫三塔的地方。他骑摩托车,和一辆卡车正面相撞。当时的情景我清楚地记得,他被抬起后,有一只脚还在地上拖,就像一把断了的扫把。血肉模糊。血腥味充满现场……我把警报一拉就直接往医院开了,可没有想到,他竟会成为医院的累赘。
103。两个转弯以后,我就看到门了,看到印着的门牌了。
楼道不大,几个人一站就显拥挤。我伸出手,去敲103的铁门。铁门发出当当声,那声音回荡在了楼道里。
敲重一点。老张说。
老张这样一说,我的手掌就加大了力量。门被擂得震天响。这时,看热闹的人更多了,楼梯里围满了人。有人对我喊:你不用敲的,那是租出去的房。那人这样一说,我怔住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今天这趟可能要扑空了。不祥的预感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对面,对面那户人家是房东。这时,楼梯外面有人这样喊。
这句话拯救了我们。我们一下子好像又看到了希望。
就这样,我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转到了对门,对面是104。我朝那个门看了一眼,是一个防盗门,像是新安的,很新,上面闪着亮光。我伸出手,有点犹豫,但终究还是敲了。敲了一阵后,门缓缓地打开一条缝,从里面探出一个头来。光头,闪着亮。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目光里还带着疑问。
对面是你房客吧,我问。
他不解,看着我,看着我们的担架。然后,他点了点头。
他出事了,一直住在医院,现在我代表医院……我这样说着。这时,那人好像一下子懂得了我的意思。
这不关我事,这不关我事。他一边说一边摇头。我的面前闪过一道道亮光。
就在他准备缩头时,我迅速地把一只脚伸了过去。我用脚顶住门,我不让他把门关上。不行,这事情与你有关。我边说边去推他的门。他的脸涨得通红通红,红得像鸡冠。他使劲想关门,我则使劲要开门。
事情就这样,我们形成拉锯。毕竟,我是当过兵的,有些力气。我一点点往里推,门就开了一个口子。我看到了希望。希望就在眼前。
那口子也让老张和小陈鼓起了勇气,他们像咀虫一样使劲地往里挤。尤其是老张,半个屁股贴着门,直往里面顶。他满脸通红,额上都是汗。那副担架啊,被挤进挤出。外面看的人更多了,议论也更多了。口子越来越大,担架的一个角已经顶入了。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头。我信心满满起来。
然而,就在我以为万无一失时,情况却出现了。不知什么原因,当我们乘胜追击时,担架突然倾斜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局面出现了,病人从担架上滚落下来。
我听到病人跌落的声音。那是他的头颅,他的头颅撞到了水泥地。
病人翻倒在地。人群里一阵惊呼。那道门也乘机怦地一声,响亮地关上了。
这真是糟糕无比啊。
2
病人被重新放上担架。我们面面相觑。
我失望至极。我想,今天真的不应该接这个活,随便找个理由,把院长给忽悠一下。现在好了,我不想干的事,偏偏干成了这样。我内心也为这位病人难过,但我没有办法呀,这是我的工作呀。
此时,病人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我有些好奇,顺手在病人的鼻孔处探了探,这一探,我吃了一惊。我发现他没气了。这让我紧张,也让我惊讶。于是我又伸手探了探,没有,一点气也没有。这是我没有意料到的。我开始慌张起来。
难道摔死了?我不敢往这里想。
老张和小陈看着我,眼睛里满是迷茫。
我告诉自己要镇定,这时千万要镇定。遇事不乱,才能成大事。
很快,我就让自己心跳平稳下来。悄悄地,我还紧握起了拳头。我内心在责怪眼前这两个人,老张和小陈。他们愚蠢无比,就像堂吉诃德和桑丘。他们不像样,动作缓慢、拖沓、死气沉沉。他们每天在抬这副担架,可偏偏没抬好。我狠不得上去揍他们几拳。
抬回救护车。我气呼呼地说。
这两个家伙,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还不明白发生了什么。迟疑了一会,才慢吞吞地把担架抬起。边上都是眼睛,好在这些眼睛都没有发现这个秘密。我的心提在高处,我怕有人会说,这人死了。他们抬着一个死人。好在这众目睽睽形同瞎子,谁也没有发现秘密。当病人重新回到救护车上,我那颗提心吊胆的心才稍稍放下。
但我的心依然还是很乱。我不知道怎么办。
围观的人在议论。我头也不抬,匆忙走出人群。我想,怎么办?人摔死了,调查的话,我们都是责任人。好在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事。上车后,我脑子还是一片空白。发动汽车后,我也不知道车该往哪里开。
救护车顶上的灯转动着,闪烁出幽蓝的光。
小区里聚集了好多人。当车子开动时,我看到一双双陌生而又焦虑的目光。救护车缓缓地驶出小区。
当车子重回大街时,我决定给院长打电话,汇报这事。我边开车,边掏手机,然后拨号。院长办公室的电话通了,但没有人接。一直是嘟嘟地叫。等了一会,我放弃了,我又打院长的手机,不巧的是,他竟然关机。合上手机时,我变得十分茫然。怎么办呢?总不能再把死人拉回医院吧,我想。
就在这时,我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这思想来得快,一下子统率了我的大脑,我决定把死者送到殡仪馆。先送去,送后再告院长。我回了一下头,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老张和小陈,但这两个鬼,竟然靠着座椅睡着了。尤其是老张,居然张着嘴,呼噜也起来了。那小陈也紧靠椅背,闭着双眼。他们根本不知道边上已经多了一个人死了。两个麻木、无趣的人,堂吉诃德和桑丘。
路上车不多,我把笛声拉得更响了。
当车子在殡仪馆宽阔的广场停下时,老张和小陈才从睡意中醒来。睁开眼,发现是殡仪馆,两人都怔了一下。
人,死了。我平静地对他们说。
两人面面相觑,互相你看我,我看你。惊醒后,又慌乱地跑到担架前。他们就趴在那里,看这个人。或许是知道了死,有些忌讳,他们不敢贴近他。真的死了啊,真的死了啊,他们在叹息。
到了殡仪馆,我的心反而平静了。心跳平稳,呼息正常,刚才的紧张消散了。我想,只要咬紧牙关不说是摔死,就不会有事。像这样的人随时随地会死去的,他现在死了,反而省事。这对医院,对他自己,甚至对房东都有好处。我这样想,就一通百通了,我甚至感到了一丝轻松。
老张和小陈盯着那人看一阵后,就下车了。他们打开后车门,摇摇晃晃地,把担架从救护车上抬下来。
这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在向我走来。是吴丽娜,我的同学。这地方,我常来,经常把死人拉进这里的大烟囱。因此,我与这里的好多人都熟得不能再熟。但吴丽娜不同,她是我初中同学。同学就比较亲切。她是殡仪馆办公室秘书,长相一般,每天把头发扎成一束马尾。她告诉我,她喜欢这里,一是工作清闲,二是收入高。是的,这烧死人的地方,独家经营,富得流油。
我喜欢和吴丽娜聊天,她是信息发布站。每次遇上,总会告诉我许多事。比如某某同学发财了,某某同学离婚了,某某同学出国了……事实上,我内心一直有一个心思,我想泡吴丽娜。我觉得这些年吴丽娜变得好看了,成熟了,连胸部也丰满了,不像以前读书的时候,既不活跃,也不性感。因此,最近一段时间,我到殡仪馆总想会一会吴丽娜。有时,甚至还有些想入非非。比如,想像在吴丽娜的办公室里抱住她,然后亲她,然后解她的扣子……
吴丽娜一到,刚才那些烦心事就抛开了。老张和小陈抬起了担架,我指了指方向,他们就朝冷冻室走去。他们对殡仪馆很熟悉,和我一样,常来。等他们一走,我就从驾驶室出来,朝吴丽娜走去。现在吴丽娜漏出来的春光抓住了我,我发现她穿了很一件领口很低的衣服,我眼睛轻轻一抬,就看到了她明晃晃的半个胸部。这个胸部让我想入非非,我甚至想像自己的手已经摸到了那白嫩的皮肤。我就是这样俗,没有办法。于是,眼睛就一阵阵往她胸前飘。
正好,葛飞来了,我们晚上一起吃饭吧。她说。
葛飞是我们的同学,现在在深圳开公司。这些年,一直没有她的消息,没有想到会一下子出现。
我订了包厢,在新大州酒店。吴丽娜道。
这真是一次好机会,我一直在寻找泡她的机会,没有想到机会就这样出现了。我来请客吧,我大方地说。吴丽娜笑笑,说晚上再说吧。
吴丽娜的出现,一扫刚才的霉劲,我顿时觉得精神气爽了。
于是,吴丽娜就告诉我葛飞的事,说葛飞现在发了,估计有好几千万了,生意做到了国外。说着,她就从身边的小包里,掏出几张照片。我接过照片看,发现都是葛飞,葛飞在埃菲尔铁塔前,葛飞在金字塔前,葛飞在巴拿马运河旁……看得我眼花缭乱。
好,真好。我附和着。
他们都发财了。吴丽娜突然叹息起来。
这让我一下子尴尬起来。我想,论收入,我可能比吴丽娜还低。她这样一说,我好像一下子说不上话了,连头也不敢像刚才那样昂扬起来。我想,他妈的狗屁葛飞,不就是多了几个钱吗?我内心这样暗骂着葛飞。
就在这时,小陈突然气喘吁吁地跑到了跟前。
不好了,不好了。他满头是汗。
我怔了怔。不知发生了什么。
他活了,他又活过来了。小陈用手指着冷冻室方向。小陈这样一说,我大吃一惊。这怎么可能呢?他刚才明明是没有气了呀,我记得清清楚楚呀。
怔了一下,我就抛下吴丽娜,跟着小陈朝着殡仪馆大厅跑去。在冷冻室门口,我看到了这人。他竟然已经从担架上坐起,脸色苍白,毫无血色,此时正在拉自己的头发。
是不是遇到鬼了呢?我想。
我是个无神论者,我不怕鬼。如果怕鬼,我还敢开救护车吗?但这会儿看到他,我还是有些异样,我感到后背发酸。好像有什么东西拖住了我。
这时,这人停止拉头发,他用一双凄迷的、茫然的目光注视着我们。他的眼向外翻着,那双眼睛好像随时会跌落下来。
还好,还好,没有及早把他送进冷库,否则还了得。这样想时,我的心开始狂跳。我嘴里一遍遍念着阿弥陀佛。我跑救护车已经十多年了,常常有死人拉进拉出。但遇到今天这样的事,还是第一回。我真的吓出一身冷汗。从前,听说乡下有死人敲棺材板的笑话,现在看来可能还真有其事。
今天真是一个倒霉的日子,刚想一想女人,就差点出大事,晦气啊。我心里在叹息。
这时,我看到吴丽娜,她也从远处急匆匆地赶来了。
3
救护车又开动了。
我拉响了笛声,车在咕噜咕噜叫,我们重新上路。病人还是躺在后面的担架上,老张不停地朝他张望,好像在看一个怪物。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种不畅感,好像与一个幽灵在一起。
车里一片静默。压抑的气氛弥漫在救护车里。心好像悬了起来,挂在了半空里。
我重新给院长打电话。他的办公室还是没人,手机依然关机。我想怎么办呢?他现在又活过来了。不管怎么,院长给我的任务我肯定是要完成的,我不可能再把这个人拉回医院。尽管这样的做法心狠了点,但这实在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医院毕竟不是福利院啊,这样想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念头,我想还是把他放回家里去。让他回家,或许,应该还是最好的选择。
有了这样的主意后,我就开始加大油门。车子呼啸而过,旁边都是张望的人头和迷茫的脸。病人在车厢后翻来翻去。现在我又像刚从医院出来时那样,开始往他住的小区跑。
当救护车重新开进小区的时候,传达室的老人好奇地睁大了眼睛,他想了想,还是像前面那样咕噜咕噜地把门打开了。车子再次朝着前面的三幢跑去。
车子停稳,我从驾驶室向后张望。老张和小陈都用迷惑的眼光看着我,他们不知所措了。
送进去。我坚决地命令道。
老张和小陈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站起了身。
这时,躺在车里的病人好像有了预感,他伸出一只手来,紧紧地抓住了车上的一个不锈钢把手。或许是太过用力了,连青筋都暴露出来了。我突然有一种奇怪的感觉,我觉得这不是一双活人的手,而是一双死人的手。死人的手紧紧地抓住了救命稻草。我看到这幕骇人听闻的景象时,就是这样想的。
当老张和小陈试图抬起担架时,他握得更紧了。他抓住了,抓紧了,抓死了。
此时,车边上有人围了过来,他们来看热闹。老张和小陈试图努力,但依然没有办法抬走。
我跑下驾驶室,来到车子后面。当我把眼光投过去的时候,我的目光与他的目光撞到了一起。这是一双陌生无比的眼,眼光里带着绝望,还带着愤怒。我甚至还发现他的眼球里几缕红红的血丝……我的目光移开了,我不忍,和他的目光对恃。
围的人多起来了,人们七嘴八舌。
老张在车上,小陈在车下,他们放下了担架。小陈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那意思是怎么办?奶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以前,我也送过几个欠费者,每次都是顺利送到目的地,没有波折。是啊,医院没有理亏啊,理亏的是病人,病人欠医院大额费用,难道还抬得起头来吗?但眼前这个病人不同,他让我感到棘手。
病人的手紧缠着,没有丝毫的松动。围观的人都看着他,看着这只手。那是一只苍白的手,上面汗毛干枯,看上去就像一根皱树干。
围观的人多了,看着这些人,我一下子又没了方向。边上的人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们都盯着我。我的心很虚,我不敢看他们。怎么啦,这个人怎么啦,有人一直在问。我受不了,我的心在煎熬。
在议论声中,我回到驾驶室,重新发动了汽车。
就这样,救护车像前面那样,再次驶离小区。我透过汽车的反光镜,看到后面齐刷刷的目光。人们一脸茫然,盯着救护车的屁股。
我沿着老城墙开,作绕城运动。一圈,二圈地绕。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开着这个车,到处转。我想不出办法,又没有脸回医院。我希望能在转悠过程中,寻找到处理这件事的办法。
有一会儿,我甚至想把他放在城墙下一个冷僻的地方。但我这个方案被老张否决了,老张说这样会让别人发现的,说出去对医院不好。我觉得老张的话有道理,我问哪放哪里呢?老张想了想说,郊外,郊外最好。
当我们绕着城墙跑到第三圈的时候,就一致决定跑郊外了。我想,这肯定是一个解决问题好办法。别无良策。于是,救护车掉头,朝着郊外跑去。
当原野的风从远处的吹来时,我感到一丝轻松。田野一片空旷,没有庄稼,没有农民,只剩下稻茬子和黑乎乎的土地。透过反光镜,我看车后。我看不到担架,但我能想像到他的情形。我琢磨着,病人到底是醒还是睡呢?
没跑多久,天阴沉了,不一会儿竟然有雨点跌落下来。一滴滴,一滴滴,在车窗前化成一个个小圆圈。这天落雨了,那还能把他放哪里呢?我的头又大起来了。这些倒霉事都凑到了一起呢。
难道把他放在雨里吗?听到这哗哗的雨声,我作不了决定。我想,我肯定不忍心这样做的。这个时候,我希望病人开口,告诉我们家人或亲戚的地址。我想,再远,我也会送去的,但这个家伙闷声不响,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他漠不关心。
原本我是计划选择一块空地,离开公路一小段路,荒僻,无人。但我又想,不能离路太远,太远了别人不会发现。内心里,我希望他能遇上好人,被好人发现,被好人拯救。我真心希望他能遇上这样的人。但现在的雨,又让我犯睏。看来我想好的计划要泡汤了。
怎么办啊?我听到老张也这样问道。
我相信,老张和小陈都清楚我的心事。这事,我难受,相信他们也难受。谁愿意做这样的难人啊,但我们都身不由己,这是工作的需要啊,是命运的安排啊。我们十万个不愿意,但没有办法,又不得不做。隐约中,我感到这是让我最难受的一天。
桥洞,桥洞下面吧。这时,小陈指着前方的一座立交桥叫了起来。
我的眼前顿时一亮。这真是一个好的主意啊。我们看到了一个很宽的桥洞,外面下着雨,但桥洞下面干燥无比。这是不是一种天意呢?遇见了这样一座桥洞,让我们豁然开朗。
雨在哗哗地下,越下越大。道路上湿漉的,还升腾起雾气。当在桥洞下稳稳地停车后,我长长地抒了一口气。此刻,路上没有车,除了雨声,四周很安静。
老张和小陈也会心一笑。就在这里吧,我指了指眼前说。
老张和小陈精神抖擞,重新抬起了担架。这时,我们又听到一个古怪的声音,那是病人发出的,像是猪在嗷。我有点想笑出来,小时候到农村,看到农民家里杀猪就是这般模样。猪在叫,在挣扎。这二幕就有点类似,它把我带进回忆。这时,他又抓住了不锈钢把手。现在周围没人,老陈轻轻一掰,他的手就松了。
当老张和小陈把担架放到地上时,叫声更厉害了,他在薄薄的棉被下面挣扎着。我走了过去,看了一眼,发现他的脸很可怕。这是一张垂死的人,没有血色,没有肉,连眼睛也几乎陷得快看不出来了。这时,我的内心涌起了一丝同情,我想,我们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我的胸口有点闷,我开始觉得浑身不舒服起来。
强……强盗,强强……他开始骂人。
他这样一骂,反而让我平静了。他没骂,我觉得我们理亏;他一骂,就变成了他理亏。老张和小陈蹲下身体,用手拉住了担架下的床单,他们拉住床单,把那人重新抬了起来。连同床单一起,他们把病人放到了地上。病人身上盖着被子。
被子怎么办?小陈问。
送给他吧,免得他冻着。我平静地说。
病人就在被子里蹬腿,好像要把被子踢翻。我不忍心看,就把头转到了外面,我看到立交桥上面一缕缕飘下来的雨。雨丝飘扬,飘到了我的身上,我的头发被打湿了。现在病人就躺在桥洞下一块干燥的地方,那里有柔软的草皮。或许是缺少阳光和雨露,这些草大多已经枯黄。病人就躺在枯黄的草上。这真是一个好地方,我心里这样想。
一切进行得很顺利。这中间,只有一辆大卡车从桥下经过。那卡车上装满了货,经过时,驾驶员看也没有朝我们看一眼。这让我很放心。
看了一会后,决定返回。我们上车,车再掉头,然后朝着城里跑。
开了一小段,我有些迟疑,我感到心里七上八下的。于是我又把车倒了回来。
老张和小陈不懂我的意思,睁着大眼看我。车回到桥下,我拉开门,朝着那人走去。我看到被子已经被他踢开,他的两只脚在外面乱舞。我沉重地走到他的跟前,蹲下身,开始掏皮夹。我掏出五百元钱来,然后轻轻地把钱放在他的头边。此时,病人一动也不动,他冷冷地看着我。
他的嘴在动,好像要说。我不忍再看,决定快走。
重新回到救护车上,我长长地抒了一口气。我觉得我做了一件我应该做的事。我感到心安了许多。
你给他钱了?小陈好奇地问。
我没有吱声,只当没听见,我觉得这样的事是不能告诉别人的。
忘了这不愉快的事吧,我对自己这样说。
4
酒店里灯火通明,音乐从墙缝里渗出来。
傍晚时分,我早早来到酒店。我想早一些的话,单独与吴丽娜相处的时间会长一些。我有些惦念吴丽娜,想泡她的欲望似乎更强了。但没有想到的是,当我刚跨进包厢,就看到吴丽娜和葛飞,她们早来了。看到我,她们站了起来,与我打招呼。葛飞胖了,胖得我几乎认不出来。她完全像一个富贵女人了,香水一阵阵地跟着来。
吴丽娜让我坐最里面,这让我不舒服。就这样,我只能远远地对望吴丽娜。这让我心情受影响。
葛飞在谈她的生意经,她在全国各地推广她的连锁分店。人与人就是这般不同,十多年不见,好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
不久,更多的同学出现了,他们有阿福、王兵、沈丽红和朱海。我没有想到吴丽娜会叫上这么多同学,这简直变成了同学会。全靠葛飞,让我们大家欢聚在一起,吴丽娜这样说。
同学一多,我那不快的情绪就一点点放睛了。我们开始吹牛,开始打听各自的家庭、子女和收入。等酒一上来,气氛就更活跃了。叮叮当当,酒杯碰个不停。我们坐着又站起,站起又坐下,不亦乐乎。据说同学相聚一定要喝酒,没有轰轰烈烈的干杯,就不是聚会的氛围了。
今天,我发现自己酒量好得惊人,常常站起,与人碰杯,然后一杯酒倒进口里。我喝的是白葡萄酒。我这样的好酒量让所有的人都刮目相看。以前,在学校,你是个闷葫芦,没有想到今天会有这样神勇的表现,葛飞这样一通话,让我飘飘然。于是大家都说我本事大,说我变得外向和豪爽了。
我沾沾自喜。
其实,我知道,我这样的超常酒量源自于吴丽娜。没有她在,我就不会有这样冲动。我是在向她展示,在向她献殷勤。可惜,她没有明白,她的眼睛一直没有往我这边来。不过,我想,她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我站起来,向吴丽娜举酒杯。吴丽娜笑了笑,笑得很甜。她轻轻地抿了一口,我好像受到了鼓舞,头一抬,又把一杯白葡萄灌了下去。
爽。我听到阿福在叫。
酒喝得差不多时,葛飞突然拿起了遥控器。她手一摁,挂在墙上的电视就打开了。让我看看家乡的事吧,她这样说的时候就快速地搜索着。
很快,她按到了当地的主频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把眼睛盯到了电视上。平时,我不爱看电视,我喜欢搓点小麻将。现在,葛飞手一指,我也就把目光转了过去。就在这一转的时候,我看到了一只手。这只手晃了一晃。
我记忆一下子激活了。我觉得是这是一只熟悉的手,但一时又想不起来。
但,当下一个镜头出现一座立交桥时,我的心被抛到了空中。电视里播的东西居然与我有关,确切地说,与我今天做的事有关。我开始发冷。
画面上,那个病人,正被拖进一辆救护车。边上有许多的围观者。警察也在一边。
呀,这不是你下午送到殡仪馆的那人吗?吴丽娜条件反射般地说。
我睁大眼睛,一动也不动。我的呼吸几乎快停止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感到胸口被堵住了,气都喘不过来。我的那些同学,都齐刷刷地把目光向我投来。他们的目光就像一支支箭,锋利、闪亮,带着责问与疑惑。
此时,电视主持人站在立交桥下。主持人在说什么,但我听不清楚。我觉得脑里一片空白。我的眼前还是这只手,这只手紧紧地握着不锈钢扶手。他握得死紧死紧,连青盘筋都凸出来了。现在我又看到了他的手,他躺在担架里,手下垂着。一双无力的手。
老人是怎么被扔到这里,现在并不清楚,警方还要作进一步的调查。目前,他将被送往人民医院,将作进一步的检查。主持人拿着话筒这样说。
人民医院,天啊,这不就是我所在的医院吗?
我眼前乌黑一团。
冥冥中,我感到包厢里所有的眼光都投在我身上。他们在拷问,为什么?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目光真的很刺痛。我能感受到这种尖锐的痛感。我不敢正视这样的眼光,我把目光放下,看着自己的手。我的手还握着酒杯,酒杯里的有一些已经洒到了外面。
我朝吴丽娜瞄了一眼,我发现她盯着我。这目光很烫,烫得冒火星。但明显不是情人的那种发烫的目光,而是不信任的、怪罪的目光。我怕这样的目光。很怕。
这时,我站了起来。我没有作任何的解释,我也不知道怎样来解释。
我朝卫生间走去。酒店里优雅的灯光就落在头顶,路旁还有好些植物簇拥着。我在想怎么撒谎,怎样去编一个说得圆的故事呢。
我们绕啊绕,绕城三圈,送他出城,最后竟然又莫名其妙地回到了医院。你说,这不是上帝在作弄我吗?
我走进卫生间,我选择其中的一间,把自己关了起来。我一屁股坐在马桶盖上。现在我还有些隐痛,我觉得不应该给他钱。五百元哪,这也不是一个小数字了。我不知道这钱现在到了哪里,是给人拿走了?还是被警察没收了?我不敢想像。我拍自己的脑瓜,想,自己真糊涂啊。
就这样,我直愣愣地坐在马桶盖上。我不时听到外面进进出出的声音,但我一声不吭。我看着自己的皮鞋。皮鞋上还有灰尘。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知道我是个傻瓜,如果今天这个事告诉老婆的话,我肯定会被她奚落。她会骂我笨蛋,骂我狗屁不懂。看来,我真的是狗屁不懂啊。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的手机响了。手机在口袋里,我不想接,但手机响了一遍又遍。我想,肯定是吴丽娜,他们找不到我了。我从口袋里掏出手机,一看,更慌了。
蓝色的屏幕上显示的是院长的手机号。
责任编辑:易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