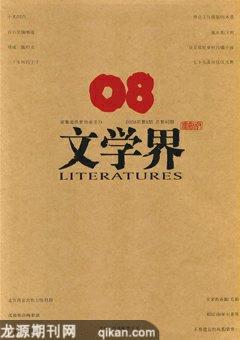三十年河西
王 子
一
半夜12点多,老黑打来电话,老黑说惊了你的好梦了。我说现在的男人本来就脆弱,让你这么一吓,非残废不可。
你知道明天是啥日子吗?
我说不知道。我想起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我说明天一定是好日子。
老黑说你猜猜,你要把这个日子忘了,你就啥也不是。
我说我根本就啥也不是。钱没挣着,官儿没当上,除了自己的媳妇,连第二个女人的味都没闻着——明天是中秋节吧?
刚吃完鸡蛋就他妈的过中秋节啦?我看你的脑袋让驴踢了。
我说那肯定是你的结婚纪念日。
老黑在那头阴阳怪气的地笑了:我结婚纪念日半夜三更的打电话告诉你干啥?我怀疑你家是不是在飞机场附近住,你的脑袋肯定让飞机膀子刮了。我告诉你:明天是咱们下乡30周年纪念日!
我彻底醒了:真的?!
骗你干啥,现在的手机比儿童玩具都便宜,你干嘛不买一个?害得我一整天找不到你。明天咱们这些老知青组团回饮马河村,我还邀请了电视台和报社的记者一起去。你好赖也算个作家,虽然不值几个钱,小名还是有的,灵感一来,没准你还能写点啥呢。
空着手去?我问。
到老丈眼子家还得拿两包糕点呢。听说村子现在还很穷,咱们毕竟在那生活了8年,应该帮帮他们。我准备拿两万,你们随便拿一点,每人再多带些旧衣服,也算是尽了咱们一份心意。别忘了,明早6点在我公司集合。
不等我再说啥,老黑已经把电话摞了。
什么事那么急,觉都不让睡好。妻子睡眼惺松地嘟哝着。
我说明天我们要回饮马河村,一晃我们下乡都30年了。听说那里还很穷,大家准备捐点钱,再多找几件旧衣服。
妻子一下把眼睛瞪得很大:捐钱?咱家哪有钱?我还想让别人给咱家捐点钱呢。一定是老黑挑的头,有俩×钱不知道咋烧包了。
我说多有多捐,少有少捐,毕竟在那待了8年,总要表达一下心意嘛。人家老黑捐两万呢。妻子说他捐20万也应该。妻子忽然坐起身,很兴奋地说:我有办法了,你带二百本你出的书,反正也卖不出去,堆在床底下都快长毛了。
我觉得妻子说的有道理。这几年我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散文,去年自费出版了一本散文集,除送给亲戚朋友外,只卖了十几本。于是我开始清理床底下的散文集子,妻子忙着找旧衣服。这时我突然想起黄老三。黄老三返城后,在建筑公司当瓦工,有一年不小心从7楼的脚手架上摔下来,脑浆都摔出来了。黄老三在知青点时是伙夫,在那样的年月能把我们这20多口子喂得人模狗样的,还多亏了黄老三。
第二天,我早早来到天宇公司的办公大楼。这是老黑自己的公司。老黑和黄老三原来都在建筑公司当瓦工,老黑的脑子灵,心眼转得快,几年时间从瓦工班长升到工长段长,并很快成立了自己的建筑公司。当老黑承建的第一栋楼拔地而起时,老黑的腰也像大楼一样挺拔起来。老黑说他一生除父母外最感谢两个人:一个是黄老三,在他当知青和瓦工时给了他很多帮助,另一个就是邓小平,给了他一个敢闯敢干的胆子。
老知青们陆续到齐了,大家相互打着招呼,显得很亲切。虽然生活在一个城市里,但平时各忙个的,见面的机会不是很多。岁月无情,当年风华正茂的青年全都变成了半百老头子和老太婆,大家便都有些百感交集。有几个人还把自己的孩子也带来了,他们穿着奇装异服,一副玩世不恭的样子。我们当年下乡时,也是这个年龄,一晃30年过去了。领孩子的老知青聚在一起,背着孩子们发着牢骚。说现在的孩子自私懒惰,不求上进,不顾父母的死活,就知道伸手要钱,而且永远也不满足。这次带他们回饮马河村,就是让他们亲身体验一下农村生活的艰苦,和父母当年在农村时的艰难,对他们进行一次传统的革命教育。我们这20多个老知青中,除老黑发了财,还有我和几个人仍然在机关和事业单位混着,其他的人全都下了岗。外号叫大萝卜的刘军,下岗后在胡同口摆了个修鞋摊儿,由于常年风吹日晒,刚刚48岁的他,就像84岁一样。当年知青点最漂亮的郑玉梅,现在一点也看不到当年美人的影子,满脸的皱纹,牙齿脱落,像个老巫婆。郑玉梅是接父亲班进机械厂的,机械厂当时很兴旺,每月的工资不但比其它单位多4元钱,而且还有8元钱的奖金。那时的人民币可值银子了,6毛钱能买一斤好猪肉。没想到好景不长,机械厂就像一个整天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人突然患重病一样,说不行就不行了。郑玉梅下岗后,弄了个蛇皮袋子和铁钩子,到各个住宅小区的垃圾箱里捡破烂,供养正念高中的儿子。大家虽然生活得很困难,但一听说重访当年下乡的地方,要为那里仍然生活在贫困中的村民做点什么,大家的热情都非常高。我们在饮马河村生活了8年,我们把青春和汗水全奉献给了那里,那里是我们的第二故乡。大家每人都带了十几件旧衣服,有的把皮夹克重新打了油。大家还捐了数额不等的钱,装在一个用红纸糊成的大信封里,大萝卜和郑玉梅每人也捐了100元,这让大家都很感动。
大客车缓缓地启动了,那几个孩子早已一见如故,凑在一起玩起了扑克。30年前的今天,我们也是从这条路奔向饮马河村的,当然那时坐的是敞蓬汽车。不知谁说了句:要是黄老三能和咱一起去就好了。大家一下就都静了下来。
二
经过近7个小时的跋涉,我们乘坐的大客车终于驶进饮马河村的地界。山还是那些山,饮马河还是从村前缓缓地流过,但村子已经完全变了样,当年的茅草房不见了,准确地说只剩下了一栋,青一色是红砖铁皮盖房,铁皮房盖在阳光的照耀下,像饮马河水一样粼粼闪光。大客车驶进村子,村道竟然是水泥路面,路两旁竟然也有路灯,路灯下竟然有供人休息的长条椅,家家户户的院子里,瓜果累累,鸡鸣狗叫,村子的变化可以说是翻天覆地。我们不相信这就是那个我们曾经生活了8年的穷山村。还没等我们缓过神儿来,一阵鞭炮声蓦然炸响,随后是让人感到亲切的唢呐声和锣鼓声。在村委会门前的空场地上,数百名村民手持三角小彩旗夹道欢迎我们。村委会的大门上悬挂着横幅:热烈欢迎老知青们回家!熟悉的唢呐声和村民们亲切的笑脸,尤其是横幅上那句暖心窝的话,使我们这些年近半百的老知青不由潸然泪下。一进饮马河村我就有一种预感,这次回访肯定要有不同寻常的事情发生。
我们一边和村民们握手问候,一边寻找当年那些熟悉的面孔。让我们更加感到吃惊的是,现任村党支部书记竟然是冯三球。30年前我们到饮马河村时,冯三球才9岁,是个两眼滴溜溜乱转一肚子坏水,谁见了都想踹他两脚的淘小子。那时知青点房后有个茅房,按着村里的习惯,谁上茅房谁就把裤带挂在茅房的门上,以证明里面有人。有一回冯三球弄个破腰带挂在茅房的门上,然后躲在一旁看热闹。有几个知青急着上茅房,见茅房的门上挂着腰带,便强忍着在外面来回走动,脸都憋青了。躲在一旁的冯三球忍不住笑出声来。还有一回几个女知青上茅房,冯三球将一块石头很准确地扔进粪坑,屎尿溅了女知青一屁股,冯三球却心满意足地逃之夭夭。可以说冯三球在十几岁之前就把该做的坏事做完了。就是这么个淘得没边没沿的坏小子,十几年前被老支书看中,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我提起当年冯三球的累累“罪行”,现任冯支书哈哈大笑,他说哪有的事?我怎么都不记得了,一定是你这个作家编的,吃柳条子屙柳筐——胡编。我说人证物证都在,你想抵赖也不行,坦白从严,抗拒更严。正说笑着,70多岁的老支书也来了,老支书满口只剩下4颗牙,说话透气漏风,见了我们这些知青,眼里便有了泪水。老支书当年对我们就像父母一样,如果没有他,我们不知怎么样度过那8年。我还在人群中发现了大娟子,那时大娟子经常到知青点去玩,常偷偷从家里拿些吃的东西给我,后来我们就好上了,我们经常在苞米地里约会,把苞米杆儿压得“哔叭”直响,我们有好几次眼看就要到达胜利的彼岸,但又都激流勇退偃旗息鼓。那时要是未婚做爱可是天大的罪孽,不像现在做爱和握手一样随便。我走过去,我说你好吗?大娟子笑了笑,眼角的皱纹很多,但那双眼睛依然明亮。大娟子说我挺好,听冯支书说你能写书了,能送给我一本吗?我说一会儿就送给你一本,那本散文集有一半的文章是写知青生活的,你看看能不能找到你的影子。大娟子好像很幸福地说:你可别写得太明显了,让孩子们看了还不笑话我。这时老黑走过来,老黑一脸坏笑地说怎么样?想不想重温旧梦?青纱帐、草甸子,当初可是没少留下你们的身影。大娟子倒很坦然,她半真半假地说:想重温旧梦也来不及了,我孙子都两岁了,等来世再说吧。冯支书扯着嗓子喊道:大家马上到餐厅,有什么话咱们边喝酒边唠。然后对我和老黑说:吃完饭我领你们参观一个地方,保证让你们大吃一惊。
村食堂的餐厅居然很大,装修得很有特色,一条横幅挂在墙上,上面的字非常醒目:老知青们:回家了!吃好喝好!十几张桌子上已经摆满了酒菜,全村每家出个代表参加宴会,大家兴致很高,说多少年也没有这样的大聚餐了,说冯支书平时抠得要命,上面来人,不管是什么级别的,一律是四菜一汤的,有一次一个副省长来检查工作,县里提前打电话给冯支书,让他把饭菜准备好,可到饭时,仍然是四菜一汤。副省长那天吃得很多,连连说好吃。村民们对我说:兔子跟着月亮走,我们今天是借你们的光了。
冯支书拿起话筒要讲话了,下面马上鸦雀无声。冯支书说:30年前的今天,26个高中毕业的青年从城里来到我们饮马河村,这些知青在我们村生活了8年,为我们村做出了很大贡献。知青们来了以后,我们才陆续学会刷牙,我们上厕所时才不再用树棍而用报纸,我们的孩子才知道读书的重要,我们说话时嘴上才不带鸡巴而变得文明起来。我可以肯定地说,没有这些知青的到来,就没有我们饮马河村的今天。我提议:为感谢知青们所做的一切,也为他们回家来,大家共同干杯!
那天,我们所有的知青都喝醉了,有几个知青还鼻涕眼泪地哭得一塌糊涂。那几个知青的孩子早和村里的孩子混熟了,漫山遍野地疯跑着。半夜时,我把老黑叫醒,我说咱们带来的那20多包旧衣服就别往外拿了,他们好像不需要。老黑说:是呀,没想到村子变化这么大,我看村民的生活比咱有些知青家的生活还好。老黑又说:那大家捐的钱怎么办?我想了想,说:钱太少,暂时也别往外拿,拿出来反而尴尬。老黑说:操,谁能想到是这样!
三
早晨被叫醒的时候,我仍然感到头晕目眩,天旋地转的。昨天的酒喝得太多了。那样的场合,那样的气氛,谁能不为之所动?那几个孩子早早就起来了,不知去谁家摘了几方便袋香瓜海棠果,还有西红柿和黄瓜等,像耗子一样“嘎吧嘎吧”地吃着。孩子们第一次看见每家院子里的手压井,没事儿的时候就“嘎吧嘎吧”往外压水,把头淋的像水鸭子。大萝卜的儿子对我说:我爸说农村生活特别艰苦,说让我来受受教育,说你们当年如何如何不容易,我看纯粹是骗人。我倒觉得这儿比我们家强多了,水果蔬菜都是新鲜的,要吃鱼上池塘里捞,想吃鸡现宰现杀,有啥不容易的?其他的孩子也说,父母动不动就说他们下乡时怎么艰苦,好像受了多大罪似的,一管他们要钱就老大不愿意,其实是推卸责任。现在要是号召上山下乡的话,我第一个报名到这儿当知青。我和老黑听着这些话,互相看了看,只能是干笑,不知做何回答。
吃罢早饭,冯支书带领我们去参观“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地方——那栋村中唯一的草房。还没走到茅草房近前,就有人惊叫道:咱们的知青点!我先是愣了下,然后便和知青们孩子似的向那栋茅草房跑去。草房的草盖肯定是新苫的,黄灿灿的,墙皮也是用麦秸沫掺黄泥新抹的,窗框刷的仍然是当年熟悉的蓝油漆。房子三大间,中间开门,左边是男宿舍,右边是女宿舍,门上有块牌子,上写知青点三个大字和某年某月等字样。这就是我们生活了8年的地方!看到这熟悉的房子,我们这些老知青不由感慨万千,心潮起伏,几个女知青早已是泪眼迷朦。老黑在冯支书的肩上拍了拍,动情地说:感谢你把知青点保存得这么完好,你们没有忘记我们呀!冯支书说:这也有老支书的一半功劳。当年全国得有几万个知青点,能把它保存到今天的恐怕仅此一家。我要让村民们永远记住你们,因为你们的到来,村里才开始接受一些新的东西,才能有今天这样的变化。
走进屋内,我们除了感到吃惊外,还特别感到亲切。因为室内的陈设和我们在这儿居住时完全一样,包括农具的摆放,连厨房的锅碗瓢盆都放在原地,好像我们昨天还在这儿居住过。当年我们返城时,把所有的东西全扔下了,就像一支溃败的军队。老支书没让村民拿走一样东西,而是按知青们平时摆放习惯恢复原样,并派五保户秦瘸子看守知青点。村子统一规划时,所有的草房全都拆了,冯支书却坚持把知青点保留下来,而且每年都要维修一下。冯支书和老支书想得一样,不能忘记那些城里的娃娃们,况且知青点也算是村级重点保护单位呢。
大家在黄老三的铺前驻足良久。当年黄老三常穿的劳动服就挂在墙上,墙上贴着一张发黄的宣传画,但画面仍清晰可辨:一个头戴安全帽手拿瓦刀的建筑工人微笑着站在脚手架林立的工地上。我突然发现那画上的建筑工人很像黄老三。老黑在黄老三的枕头上抚摸着,声音有些哽咽地说:老三,我们来看你了……
从知青点出来,大家都有些闷闷不乐,为了调整一下大家的情绪,我把话题引开了。我问冯支书,有人背后叫你冯小抠和冯老狠,你知道吗?冯支书笑着说,我怎么不知道?上面来人了——我说的上面来人,是指所有来饮马河村的人,你想啊,从国家主席到省长市长县长和乡长,都能管着我这个村官儿,他们来了,我从没给他们准备过大鱼大肉,好酒好菜,一律是四菜一汤,你吃就吃,不吃就饿着,所以,他们背地里叫我冯小抠,对于村民我是比较严厉的,有时我甚至骂他们的祖宗,对违反村规民约的,我往死了罚他们,罚得他们心疼肝疼,所以村民们背地里叫我冯老狠。话说回来,我要不抠点,村里能有这么大的家业吗?村民每家盖新房时,村里都补助一万元。小学中学全部免费,上大学的还补助一万元。别小看了人这张嘴,多大的家业都能被它吃光。对村民不严厉些,他们就不听你的,有些事就落实不下去,我说的话也就当放屁,那村子里就什么事也办不成。
我说那村民们不记恨你吗?冯支书摇了摇头,不会吧,我都是为了他们好。最主要的是我不贪不占村里的一分钱,我屁股擦得干净,就敢问他卖糖稀的多少钱,他不服行吗?
正说着,大娟子领着个姑娘从后面追上来。大娟子看了看冯支书,笑着问:我能和作家说几句话吗?冯支书调侃地说:可以,恋爱自由,婚外恋也自由。大娟子说昏你个头吧,我找他有事。那个姑娘是大娟子的侄女,在村小学教书,平时也喜欢写点东西,看了我的散文集后,想求教于我。我看了一下她写的散文和小说,生活气息很浓,语言也有些特色,我便答应她把稿子带回去,争取在报纸上发表。大娟子说那太谢谢你了,晚上到我家喝酒去。我说我可不敢到你家去,别让你家那口子给打出来。大娟子很开心地笑着说:他可不像你想得那样,平时他还给孩子讲我们当年的事儿呢,说你妈当年也是村里的一枝花,连城里的知青都追过她。我说可惜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他说农村一枝花,全靠粪当家。
四
晚饭是在村民家吃的。村民们都想请到我们,但我们只有20多个人,一百多户没法分,争执了半天,最后达成协议,几家合在一起请一个知青。大娟子和她的侄女等几家非要请我,冯支书把脸拉得很长,不容置疑地说:作家和老黑到我家去,谁也不用争。大娟子有些不高兴的嘟哝着:别人好几家请一个,你一家就抢走俩,还是你牛×,冯支书听到这话反而乐了,我就牛×咋的?这个家我说了算!
喝酒的时候,冯支书说:看见没有?大家心里有你们。老黑说:这次来让我很受感动,说心里话,这两天我就像做梦。冯支书和我们碰了一下酒杯,然后把半杯酒一口喝干。冯支书说:临来的时候你们打电话,说要为村民捐些衣服和钱,我代表大家谢谢你们。那些衣服怎么还放在大客车上,是不是舍不得,又想拉回去?
我和老黑尴尬地笑了笑,我说没想到村子变化这么大,村民的生活也很好,他们不会需要那些旧衣服的。那两万块钱就捐给学校吧,买些篮球什么的,也算是我们的一点心意。冯支书连连摆手:你说得不对,什么叫不需要?衣服不管新旧,说明你们没有忘记我们,吃完饭就卸车,每家分几件。至于钱,我们一分不能要,你们也不容易呀。老黑说我们都还过得下去,冯支书说过得下去个屁,听说你们很多人都下岗了,在城里下岗就意味着没有饭吃,不像在这儿,有地就饿不着。今年春节,我在电视上看到郑玉梅和大萝卜了,说心里话,如果不提他们的名字我都认不出来了。当她从市领导手里接过面粉和猪肉时,我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我就有个想法,我想让你们那些下岗的老知青回饮马河村来,这里有几十家采石场,养殖场,还有上百栋蔬菜大棚,只要肯吃苦,还愁挣不到钱?可我又怕伤你们的自尊,城里人对农村扶贫好像很正常,我们农村人要反过来帮助你们,你们肯定觉得脸面上过不去。
老黑说要是那样可太好了,什么屁股脸的,这年月没钱要脸又有啥用。来,我俩代表知青们敬你一杯!
冯支书端起酒杯说:有多少人想到饮马河村来找活干,都被我们挡了回去。知青们谁能比得了?他们就是这儿的人,出去闯荡了几年又回家了,这儿是家呀!说完把酒一饮而尽。
吃完饭不一会,村委会房顶上的大喇叭就响了起来,冯支书让村民们马上到村委会来,说老知青们给乡亲们带来了一些衣服,让大家来领。随后大喇叭就传出歌曲《父老乡亲》的音乐。听得出来,冯支书显然喝多了,说话时舌头有点硬。
第二天早早吃了早饭,我们收拾东西准备返城。我和老黑把冯支书邀请下岗知青回饮马河村的事说了,大萝卜和郑玉梅都很高兴,他们说回去处理一下家务,然后就来。只要有活干有钱挣,宁肯第二次下乡当知青。那几个孩子根本不想走,他们在这儿玩得很开心。来送行的村民陆续聚到村委会,我和知青们惊讶地发现,村民们都穿着我们带来的旧衣服!虽然袖子短了些,有的裤腿卷了起来,有的裤裆兜得很紧,但他们确确实实地穿在身上。我觉得鼻子有些涩涩的,多么善良的村民啊!
冯支书来了,他居然也穿着一件我们带来的旧衣服,而且就是我三年前穿过的旧西服。他和我们一一握手,把我们送上大客车,他大声地对我们说:饮马河村随时欢迎你们回家来。大客车慢慢离开了饮马河村,从车窗望过去,仍能看见村民们站在那挥舞着手臂。这时老黑的手机响了,老黑说了几句后把手机递给我,冯支书在电话里说:听说你写的书是自己花钱出的,我按书的定价给你拿去三千块钱,就放在你的背包里,算是村里的赞助吧,我会让大家好好看看的。我刚要说什么,那边已经把手机关了。我打开自己的背包,看见里面有个厚厚的信封,我拿起信封,手里竟然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
责任编辑:赵燕飞